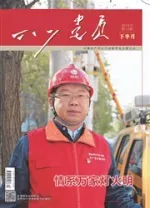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假記者之困”
一些假記者打著“輿論監(jiān)督”的旗號,對鄉(xiāng)鎮(zhèn)機關(guān)進(jìn)行敲詐勒索,嚴(yán)重干擾了部分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工作的正常開展。
在河北省邯鄲市某鎮(zhèn)黨委書記李俊山(化名)的辦公桌上,有一本厚厚的名片夾,里面存放的都是和他打過交道的“記者”名片。從名稱上看,既有傳統(tǒng)報紙,也有新興網(wǎng)絡(luò),既有公開媒體,也有內(nèi)部刊物;從地域上看,有河北省內(nèi)的,也有北京的。李俊山說:“這么多名片,只有一張是真的。”
“繞來繞去最后都離不開錢”
在多年的鄉(xiāng)鎮(zhèn)工作經(jīng)歷中,李俊山見慣了形形色色的假記者,可謂飽受困擾:“熟識點的,來了直接攤牌搞發(fā)行;關(guān)系不熟的,一般都打著批評報道的旗號,繞來繞去最后都離不開錢。”
“通常幾千塊錢就能‘搞定’,從這些年的情況看,沒有低于1000元的,也很少有高于1萬元的。”李俊山說。只有一次例外:當(dāng)時因為修路引發(fā)群眾上訪,某報社“記者”采訪完后,直接把附有現(xiàn)場照片的稿子寄給了縣長,聲稱“3日內(nèi)沒有回信,直接登報”。縣長批示下來后,李俊山找到該“記者”溝通,最終花了2.5萬元訂閱該報社的刊物。“花了錢以后,稿子是沒登,但是刊物一直也沒見到。他們說那刊物都是給省里領(lǐng)導(dǎo)看的,你說可笑不可笑?”
一張放羊照片“吃”遍三個鄉(xiāng)鎮(zhèn)
在陜西省安塞縣,一位有過鄉(xiāng)鎮(zhèn)工作經(jīng)歷的干部告訴記者,實行退耕還林以來,陜西省制訂了封山禁牧條例,但在有放羊傳統(tǒng)的陜北,仍時有農(nóng)民偷牧。“一些‘記者’開車進(jìn)山找羊、拍照后,拿著照片到鄉(xiāng)鎮(zhèn)談價錢。由于陜北地形地貌比較相似,有時在安塞找不到素材的,就跑到鄰近的靖邊縣找羊群拍照,再跑到安塞的鄉(xiāng)鎮(zhèn)要錢。更有甚者,一張照片從鐮刀灣、化子坪、譚家營一路敲詐,走哪‘吃’哪。”
多地鄉(xiāng)鎮(zhèn)干部反映,這種以采訪為名行敲詐之實的活動,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成了基層鄉(xiāng)鎮(zhèn)的負(fù)擔(dān)。每年僅此一項開支,少則數(shù)萬元,多則10多萬元。“每月都有兩三撥,一撥一到兩人。”
近年來,在山西忻州,“當(dāng)記者”已漸漸成為城鄉(xiāng)無業(yè)青年的一種“職業(yè)”。這里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忻府區(qū)合索、曹張鄉(xiāng)令狐莊和原平市神山村等當(dāng)?shù)芈劽摹坝浾叽濉薄_@些“記者”,有的曾以賣花圈為生,有的做過牛販子,他們“當(dāng)記者”的目的只有一個——利用當(dāng)?shù)睾诿旱V詐錢。基層政府為不被曝光,常常會嚴(yán)令被“逮住”的礦不惜一切代價擺平事件,否則整個地區(qū)都有被集體停產(chǎn)的“連坐”之憂。這時,一種“合作互保”的方式就出現(xiàn)了:被逮住的礦出大部分,周圍所有黑礦都給它贊助“擺平費”。
“假記者也不得不包容”
談到面對假記者時的心態(tài),鄉(xiāng)鎮(zhèn)干部們普遍五味雜陳,一方面既不堪忍受乃至反感他們的騷擾,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敢得罪。之所以會如此,河南省蘭考縣某鄉(xiāng)黨委書記表示,一是鄉(xiāng)鎮(zhèn)工作的確存在問題,擔(dān)心曝光;二是工作中打“擦邊球”,怕經(jīng)不起深究;三是本來問題不大,擔(dān)心媒體炒作,輿論壓力大,增加解決問題的難度。
河南省濟源市承留鎮(zhèn)前任黨委書記翟偉棟認(rèn)為,在一些地方,鄉(xiāng)鎮(zhèn)干部明知是敲詐,但又不敢得罪假記者,一定程度上還跟“害怕給領(lǐng)導(dǎo)添麻煩”的心理有關(guān)。“有些地方領(lǐng)導(dǎo)對媒體報道過于敏感,一旦出現(xiàn)負(fù)面消息,往往是先處理人再說事。這樣一來,鄉(xiāng)鎮(zhèn)即使沒事也擔(dān)心假記者找事。”
一個基層宣傳部長的“記者經(jīng)”在將近20年的宣傳工作生涯中,某縣宣傳部副部長老丁(化名) 接觸過上千名記者。老丁琢磨出了一套鑒別真假記者的經(jīng)驗:和對方寒暄時,他會跟這些人聊國家最近的方針政策。假記者這時候一般只會打哈哈,而真記者則會和老丁有一個對等的交流。
對于假記者,老丁從不揭穿他們,但對他們的“輿論監(jiān)督”也不買賬。而僅僅在幾年前,老丁的底氣還沒這么足:“那時媒體剛放開,小報不斷地辦,你得重視它,畢竟我們是基層。我并不是怕小報曝光,而是擔(dān)心,這種只印十份八份的小報,可能直接寄給市里的領(lǐng)導(dǎo),或者省里的領(lǐng)導(dǎo)。領(lǐng)導(dǎo)可能對報紙不大了解,一看我們這里有這么大的污染事件,會過問,領(lǐng)導(dǎo)就會有壓力。”
隨著對假記者的鑒別力與日俱增,老丁也更加應(yīng)對自如:“幾年前,一些小報要給哪個單位曝光,我們會給個兩三千元。我可以負(fù)責(zé)任地說,最近3年內(nèi),一分錢都沒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