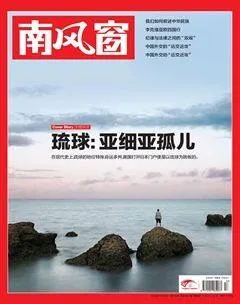危險的信號
石勇
剛剛過去的廈門公交縱火案,引發了全國各地對公共交通的“安檢”升級。傳遞的信息是:為應對公共安全日益嚴峻的局面,整個社會將付出更大的防御成本。
防御或許是有點用的。但它當然并沒有切入真正的問題。包括縱火者在內的47條人命帶來的慘痛教訓,以及應該引發的行動,在當前的政治、社會語境中,遠不止于此。
縱火者不是瘋子。把一個身處底層的失敗者在公交車上縱火,并和其它人同歸于盡視之為沒有政治、社會因素的刑事案件顯然并不妥當。它更不能簡單化地歸入“泄憤”、“報復社會”的標簽之下。
性質其實很清楚:一個在殘酷的社會競爭中遭到了“迫害”,或想象自己遭到了“迫害”的底層失意者、失敗者,在今天的政治、社會、經濟格局中,心理上已經活不下去,于是拖著別人一起玩完。這是多年來積累的社會風險轉化為實際的危險,轉化為每個人生命安全受威脅的信號。
似乎是要注解這一性質,公眾輿論呈現出和縱火者一樣紊亂的社會認知和心態。
在網絡上,充斥著“同情”縱火者的聲音,因為這代表了沒有 “活路”后的“反抗”。而擺出“反思”pose的人,也堅稱縱火者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迫害”。抽象的“政府”和“社會”,成了為縱火者承擔罪責的主體。它們就像是一個公共污水溝。
這種社會認知和心態,似乎沒有看見相關事實:46條無辜生命被殘忍剝奪、縱火者有性格缺陷、他并不是無法依賴自己或國家而活下去。事實上,沒人對此感興趣。一次縱火案,成全的,不過是一種以正義姿態釋放的“被迫害妄想”的狂歡而已。
社會各階層彌漫著“被迫害妄想”,正是今天社會風險向危險的轉化已經具備了心理基礎、現實基礎的一個重要特征。
對于既得利益集團來說,他們的“被迫害妄想”有特定的內容,擔心被“清算”,被“打土豪分田地”。背景是他們對中下層的剝奪,在積累起來的社會情緒中,引發了自身的恐懼。“被迫害妄想”作為可能被“清算”的神經過敏的預先防御,就是治療恐懼的藥方。它還具有這種功能:固化既得利益集團對中下層的恨和所主宰的剝奪秩序。
被剝奪的中下層所產生的“被迫害妄想”,內容和功能恰恰相反。
這種“被迫害妄想”的背景就是實際的“迫害”,諸如強拆、限制上訪者的人身自由、貪腐、權力資本的掠奪、機會不平等,等等,作為“公共經驗”,中國人已經非常熟悉。在這個背景下,中下層會產生一種被剝奪,被傷害,看不到希望,同時又反抗不了的感覺。為了在心理上防止可能受到傷害或再受到傷害,把對自己生活處境所承擔的責任給推出去,以及獲得正義感所支撐的道德優勢,人們就會強迫自己產生“被迫害妄想”。它相當于一種另類的“弱者的武器”。
當既得利益集團和中下層的“被迫害妄想”相遇時,結果是注定的:只能相互強化。要既得利益集團“讓步”非常艱難,因為要解除他們的心理防御。而既得利益集團不讓步,又會刺激中下層的“被迫害妄想”。社會進入了一個死結。
這不是唯一讓人深為不安的地方。關鍵的問題還在于,既得利益集團的“被迫害妄想”,看不到政府責任的在場,它對剝奪秩序的固化,深度地瓦解社會團結。而中下層的“被迫害妄想”,同樣也把社會撕為碎片,制造出一個個充滿仇恨,好像誰都欠他的失意者、失敗者。
于是,兩種“被迫害妄想”聯手干了這件事:在社會殘酷競爭中失意、失敗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責任給推出去,說成是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迫害”,而他們不想活了拉著別人一起死,也就具有了充足的理由。這種社會心態,在公交縱火案之類公共安全的事件上重復一次,就會強化一次這類事件的“發生邏輯”。
這已經相當于一個社會的“自殺”了。只不過,當社會雖然處于潰敗,但整體秩序仍然可控時,離“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或“一群人對一群人的戰爭”尚有距離,處于社會食物鏈末端的失意者、失敗者,其拖著一起玩完的對象,更多地是和自己有差不多命運處境或生活交集的人。就是說,處于風險、危險之中的,不是權力控制下的治理秩序,不是既得利益集團剝奪中下層的利益秩序,而是公共安全——而且隨著“被迫害妄想”的加劇,心理失衡的人越來越多,情況會越來越糟糕。
政府該對此承擔什么責任是清楚的:它沒有盡到或很好地盡到諸如抑制既得利益集團對中下層的剝奪,以及提供機會平等、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的責任。社會要承擔的責任也是自明的:平等尊重,不對在殘酷競爭中失意、失敗的人進行羞辱。但個體呢?很顯然,他的基本保障、處于一個公平的制度下去參與競爭,由政府解決,認同由社會解決,但諸如生活處境的改善,只能靠自己,并交給市場去解決。
一個把對自身的責任推出去、認為誰都欠他的個人,和一個連公民的私域都要控制卻不負責任的政府部門,有著相同的精神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