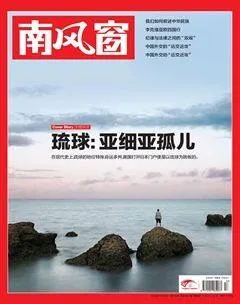靠不住的“偉人”
謝奕秋
美國發明家、外交家富蘭克林諷刺“羅馬教會是一貫正確的,而英國教會是永遠不會錯”。以此反觀美國的開國之父們,亦非無可指摘。
“以身許國”的華盛頓,在針對英國的“預防性媾和”政策激起民意反彈時,選擇了急流勇退,成就了總統兩屆到頭的不成文慣例。但他早年錯誤伏擊了一支法國外交使團,有生之年對奴隸制的默認,乃至在總統府蓄奴,都不難讓人抓到把柄。
亞當斯的短短一屆總統任期避免了對法開戰,但他礙于國會中聯邦黨人的情面,批準了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提案中的兩項,其中的《處置叛亂法》允許起訴任何對政府領導人發表“錯誤的和誹謗性”言論的人。這在當時就被副總統杰斐遜以匿名的方式公開批評。
杰斐遜是親法派,在法國大革命轉為血腥殺戮階段后他致函友人說,“與其讓(法國革命)這一事業夭折,我寧愿看到半個世界被毀滅。”他的首個總統任期陷入與最高法院無果的纏斗中,而他在第二任期內以中斷貿易向羞辱美艦的英國施壓(暗合了拿破侖對英“大陸封鎖”政策),也被證明枉費心機。
杰斐遜的密友和繼任者麥迪遜在首個任期將結束時,趁拿破侖進軍俄羅斯,草率開啟了對英國和加拿大的戰爭,導致白宮被英軍燒毀。最后還是門羅總統以與英國在美洲“排他性共處”的方式,讓英美關系步入良性循環。
從華盛頓到麥迪遜4任總統,無疑都是偉大的“建國者”—華盛頓打贏了獨立戰爭,亞當斯是大陸會議的靈魂人物,杰斐遜撰寫了《獨立宣言》,麥迪遜起草了聯邦憲法和《權利法案》—但令擁躉們失望的是,后3人的總統任期都不那么光彩照人,尤其對麥迪遜而言,在白宮的8年遺憾甚多。
華盛頓的總統生涯波瀾不驚,但如果他繼續第三個任期,有可能像亞當斯所說的那樣,被血氣方剛的前侍從官漢密爾頓“支配”著投入一場與法國的戰爭,從而使美國無法以和平手段從拿破侖手里廉價購得對美國西擴意義深遠的路易斯安娜地區。當然,歷史無法簡單假設,畢竟華盛頓在卸任的第三年就去世了。
杰斐遜及其后繼者們,創造了一黨連贏10屆總統選舉的輝煌,但也正如華盛頓生前所擔心的,杰斐遜所憧憬的一個由小土地所有者的選票維持的農業共和國,不可避免地要依賴于奴隸制—奴隸制已經內嵌在這種農業經濟模式中。
廢除奴隸制,最終要待一個新興政黨的代表來完成。林肯,華盛頓之后又一克制力與進取心完美結合的標桿、4年內戰的最后贏家,罕有人知他在《解放奴隸宣言》發布前后,曾將“遷移自由黑人到中美洲”奉為上策,只是計劃實施不順,才保全了這位“奴隸解放者”的英名。
“從偉大崇高到荒謬可笑,其間只相差一步。”這些被時代局限性驅策的“偉人”,有時能突破分權制度的屏障,借助昔日威望集合群力鑄成大錯,這就需要定期自由競選制和任期限制來防止囿于偏私者一條道走到黑;或干脆說,必須防范克倫威爾、拿破侖那樣的善惡參半者完成走向獨裁的驚險一躍。
今天薩達姆、卡扎菲、波爾布特等獨夫早已惡名遠播,但埃爾多安等克里斯瑪型領導人仍享受著好時光,只是土耳其近期的民變說明,這好時光也是稍縱即逝的。
“偉人”不世出,一貫正確、永遠正確更只是傳說。網絡時代,誰還會迷信 “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