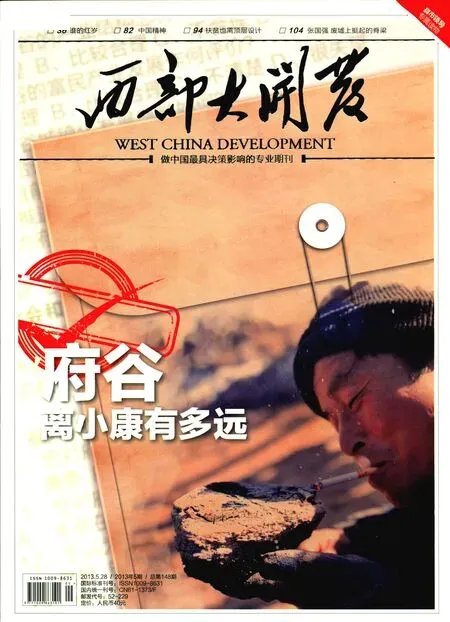檐水叮當
□ 文 / 王云奎

小時候,我長時間盯看過我們家的房檐水。那叮叮當當?shù)牡嗡曄褚皇赘瑁犞犞吞兆砹似饋怼?/p>
我的老屋,是一個不太規(guī)則的四合院。院子的東邊是圍墻和頭門,西邊是土崖和土崖上一溜排開的三孔窯洞。南邊和北邊,除了幾堵與鄰家的隔墻外,便各是三間廈房,是大西北最標準的一邊蓋房子。房子的四周用土坯壘起,上面是屋架。屋架上分別覆蓋了一層薄薄的雨薄和厚厚的泥皮。雨薄是用蘆葦編織的,泥皮則是土、水和鍘短了的麥草稈攪拌而成。有了這兩樣東西作鋪墊,瓦才能擺上去,才能起到遮風擋雨和御寒的作用。瓦是小青瓦,灰灰的,擺在屋子上面,老遠看去,像是灰色的鴿子落滿了屋頂。小青瓦發(fā)揮最大作用的時節(jié)是在雨季。那時候雨多,特別在秋季,一上云就下雨,常常還是“淋子雨”,一下就是幾天,多的時候十天八天,連一月四十的“淋子雨”我都經(jīng)歷過好些回。
雨下得不停,孩子們沒地方玩。拿個小凳,坐在房門口看房檐水,聽檐水叮叮當當?shù)温涞穆曇簦蟾攀羌拍凶钣腥さ氖虑榱恕S浀糜幸换兀赣H走親戚去了,雨大路滑,好幾天了不能回家,就我和弟妹幾個人在家,實在沒有啥可玩的了,我就拉個小凳子,兩肘支在膝蓋上,兩手撐在下巴上,看房檐滴水,聽房檐水的歌唱。天下得正大,雨珠碰上小青瓦便開了花,屋頂白霧一片,眨眼間,雨水匯聚在一起,順著瓦溝向下奔流,一到瓦口,形成了一股水柱,奮不顧身地向檐下躍去。這時候的房檐水,可以說是最為壯觀、它的歌聲是最為雄渾的了,每年夏季突如其來的雷陣雨也不過如此。
一般說來,房院臺下都有磚鋪的滴水窩,是為了防止天長日久房檐水淘空了房基。可這會兒的房檐水,已經(jīng)完全不顧人們?yōu)樗脑O計和安排,超出滴水窩許多,在前面的土地上落腳——哪里是落腳,簡直就是沖擊!只聽見嘩嘩的水聲,水聲響處,便是一窩黃泥湯翻涌著,只一會兒工夫,便是一個不小的坑了。
雨漸漸小了,奔涌而下的房檐水舒緩了許多,這時候是從瓦口垂直而下,端端地滴在了滴水窩的正中,它的歌聲也成了歡快的那一種。雨再小一些,房檐水落下的角度又發(fā)生了變化:它流到瓦口的時候,好似一個將要出遠門的人,不由得回頭望望身后,看還有什么事情沒有安排妥帖一樣,緊貼著瓦口的下巴滴下來。它的歌聲也成了叮-當,叮-當輕慢的那種。這時,它滴落的地方不是滴水窩的中心,而是房院臺的邊緣。不知道你注意過沒有,一陣急雨過后,隨著時緊時慢時大時小的叮叮當當?shù)牡嗡曂A讼聛恚嗡C周圍常常有三處地方被洗刷一新,一是滴水窩的正中,一是它前面不遠處的小土坑,再就是房院臺的邊上了。
在以后的多次“觀察”中,我發(fā)現(xiàn)這三處地方幾乎是固定的。由于日積月累,所以,盡管當初建房的時候,工匠用最結(jié)實的磚塊鋪滴水窩,它的中心仍然被啄掉了一塊,成了凹下去的形狀。有的老房子的滴水窩里,甚至能放個雞蛋。房院臺的邊緣,剛砌成的時候鋒利得能割破小孩子的手,也經(jīng)不住日積月累的沖刷,變得又圓又鈍的了。
這些都是大自然留在兒時自己記憶中的印象。忽然有一天,我的腦海里倏地跳出了“水滴石穿”這個成語。是啊,石頭是堅硬的,可是,在看似毫不起眼的水滴面前,它的堅硬又能怎樣呢?生活有時比水柔軟,許多時候卻比石頭還堅硬了很多。可是,在叮當作響的檐水聲中,它又能有多大的能耐呢?
叮叮當當?shù)拈芩暎瑹o形中竟成了自己心底深處力量和信心的源泉。生活中每當遇到比石頭還堅硬的屏障時,心里不由自主地就響起了這種叮叮當當?shù)穆曇簦瑵u漸地,漸漸地屏障從中心開始消融,瓦解,直至煙消云散,天開日出,重見燦爛的陽光。隨著年歲的增長,我時不時就想起了我們老家的房檐水,真想像兒時一樣盯著看房檐水和聽那叮當聲,哪怕是一整天,我也不會覺得寂寞。可是,不光現(xiàn)在的雨少了,在現(xiàn)代化不斷加速的城市和鄉(xiāng)村,過去那種房檐口也是越來越難找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