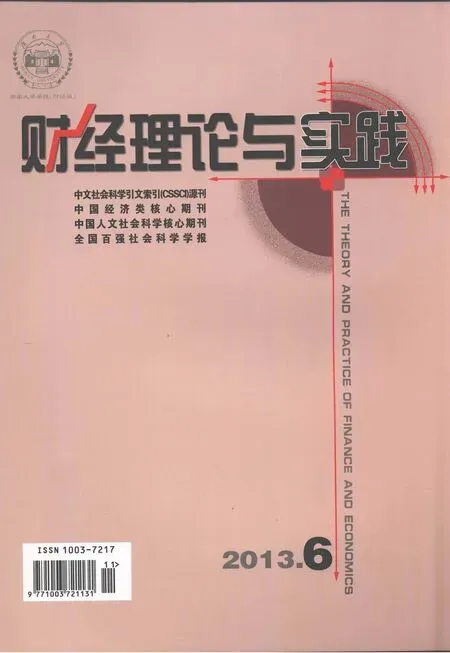基于系統整體性的商業銀行系統重要性評估方法
彭建剛,馬亞芳
(1.湖南大學 金融與統計學院,湖南 長沙 410079; 2.湖南大學 金融管理研究中心,湖南 長沙 410079)*
一、引 言
在美國次貸危機中,由單家金融機構的風險暴露造成整個金融系統的劇烈波動,引發了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高度關注。對花旗銀行的大規模救助、華盛頓互助銀行的破產等事件使得各國監管者開始重視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監管。系統重要性銀行一般呈現業務規模大、組織和業務結構復雜程度高、負外部效應顯著的特征,其個體發生的風險事件會通過金融網絡給該銀行所在地區甚至全球的金融體系帶來大的沖擊,使得金融體系無法正常運轉。
針對這一問題,2011年以來,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和巴塞爾委員會(BCBS)先后共同起草發布了《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評估方法和附加損失吸收能力要求》、《強化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強度和有效性》、《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治理框架》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從風險防范和風險處置等方面研究制定了針對系統性風險的政策措施。中國銀監會2011年頒布了《中國銀行業實施新監管標準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除對系統重要性銀行提出了1%的附加資本要求外,還對系統重要性銀行提出了更為嚴格的審慎監管要求。這些新的監管構架能夠實施的前提是能夠對系統重要性銀行進行界定。
雖然BCBS已于2011年11月和2012年11月兩次公布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BCBS還將于2017年11月前根據積累的數據對評估方法進行必要修改[1],說明系統重要銀行的評估方法尚未最后確定下來。
為了防范系統性風險,有必要建立整體性監管制度。整體性即指銀行業的整體效應不等于各銀行業機構效應之和,相對于各銀行業機構的效應及其簡單總和而言,銀行業整體的效應會發生質變;在研究銀行業系統性風險防范時,應充分考慮整個金融體系內部的相互作用和金融體系與社會的相互作用[2]。由于系統與外部環境的相干性,系統外部風險因子的沖擊可能引發系統中各銀行發生違約(default)。由于系統內各銀行的內在相關性,可能幾家銀行同時發生違約,這些違約的銀行成為系統性風險的傳染源;系統內其他銀行可能受到傳染發生違約,進而在系統中將風險放大。在這一風險形成和放大的過程中,不僅對存款客戶造成損失,也會對系統內的其他銀行造成損失。基于這一思路,下面將從系統整體性出發,提出一種商業銀行系統重要性評估方法。
二、相關研究綜述
在已有的銀行系統重要性的定量評估方法中,從不同的視角可以有多種分類方法,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可根據需要選取適當的評估方法。經過對已有的相關文獻進行分析比較,可按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不同分析途徑對現有的銀行系統重要性評估方法進行分類。自上而下方法是銀行系統發生極端損失時,分析其中各單家銀行對系統性風險所做的貢獻。這一方法是按照單家銀行對系統性風險的貢獻確定其系統重要性。自下而上方法則是一家銀行發生極端損失時,分析其整個銀行系統受此影響所發生的損失。這一方法是根據單家銀行對系統性風險的影響程度確定其系統重要性。由于銀行業機構之間的相關性,一家銀行出現問題的同時,很可能有另外幾家銀行也出現了問題,此時系統所受到的影響是這些問題銀行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其中一家銀行單獨作用的結果,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很可能會將一家銀行對系統的影響不適當地放大。因此,本文擬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開展商業銀行系統重要性評估方法研究。
Huang等以及Lahmann和Kaserer計算了當銀行系統發生極端損失時各銀行對系統風險保險額度的邊際貢獻來度量各銀行的系統重要程度[3-5]。Acharya等以及Bownlees和Engle研究了當整個銀行業作為整體資本不足或平均收益下降到某個既定水平時,單家銀行的預期資本短缺額,用其度量各銀行的風險貢獻[6,7]。他們的研究都考察了環境變化對銀行業系統內要素的影響,但對銀行業系統內的相關性未予考慮。
2012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Lloyd Shapley因為在“穩定配置的理論和市場設計中的實踐”研究領域的杰出貢獻,于2012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近年來,他提出的夏普利值在商業銀行管理領域逐漸得到了應用。Drehmann等利用夏普利值提出了一種商業銀行系統重要性評估方法[8]。在分析銀行間的相互作用時,僅僅考察了某一銀行是否會通過傳染造成其他銀行發生違約,而對其他銀行遭受的損失未作考慮。其分析過程不能較好地體現銀行系統內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且其計算方法容易造成銀行系統重要程度與銀行規模的線性關系,不能充分反映銀行間的關聯性和復雜性對系統重要程度的影響。賈彥東采用銀行間支付結算數據,利用夏普利值對中國主要銀行的系統重要性水平進行了評估,其研究工作對風險在銀行間的傳播進行了有價值的分析,但對銀行業系統外部的沖擊未作考慮[9]。
我們曾采用夏普利值確定各商業銀行的風險貢獻,進而將風險貢獻運用到經濟資本的配置中[10],該研究的目標是從微觀審慎管理整體最優的角度確定單家商業銀行各分支機構的風險貢獻和經濟資本限額,沒有在宏觀審慎管理層面上考慮銀行間以及銀行業系統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本文擬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從系統整體性出發,研究在外部沖擊和商業銀行系統內部傳染共同作用下,其存款客戶和相關銀行遭受的損失,并根據這兩方面的損失運用夏普利值計算各商業銀行對系統性風險的貢獻,從而對商業銀行的系統重要性進行評估。
三、評估方法的設計
(一)理論基礎及相關假設
依據系統整體性的理念,系統外部的沖擊和系統內部的相互作用是系統性風險的誘因。在分析銀行業系統性風險時,考慮商業銀行兩種情形的“違約”(本文指銀行資不抵債的情況),第一種情形是由于系統外部風險因子沖擊使得銀行資產價值發生變化,導致商業銀行資不抵債,發生“基礎性違約”;第二種情形是由于系統內一些商業銀行發生違約,使得其他商業銀行無法足額回收同業資產,導致其資不抵債,此類違約為“傳染性違約”。在一個開放的商業銀行系統中,一旦系統中有銀行發生基礎性違約,風險便在系統內傳染,發生傳染性違約,直到沒有新的銀行違約為止;此時可通過計算整個基礎性違約過程和傳染性違約過程中存款客戶及相關銀行遭受損失之和,來表示系統性風險的大小。
為方便分析,將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簡化為表1所示的幾個部分。

表1 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構成
其中,IBAi表示銀行i的同業資產,OAi表示商業銀行i的總資產扣除同業資產之外的其他資產,IBLi表示銀行i的同業負債,OLi表示商業銀行i總負債扣除同業負債之外的其他負債(為便于說明,用存款代稱該部分負債,OLi的債權人用存款客戶代稱),Ki表示銀行i的所有者權益。并且假設銀行i的負債結構不變。
(二)模型
一家銀行的資產會受到諸如宏觀經濟條件、行業風險等因素影響。假定銀行i的資產收益服從均值為μi,方差為σVi的正態分布,dzi是維納過程,則銀行i的資產價值Vi滿足下式:

在考察期內任意時刻t銀行i的資產價值Vi服從對數分布。若初始時刻銀行i的資產價值為,根據引理,則在時刻t銀行i的資產價值可表示為:

其中,Zi~N(0,1)進一步將Zi分解為Zi=為共同風險因子,可視為宏觀沖擊因子,ρi為共同因子載荷且ρi∈[0,1],表示各銀行與共同風險因子M的相關程度。Xi為銀行i的特質風險因子,且M,Xi為獨立同分布的服從標準正態分布的隨機變量。
根據前文假設,在考察期內0~t時刻,銀行的負債總額及負債結構不變,模擬各個銀行資產價值變化,若模擬結果得到:
Vi=OAi+IBAi≥OLi+IBLi,則銀行i是正常經營的。相反,若Vi=OAi+IBAi<OLi+IBLi,則銀行i發生基礎性違約。
設銀行i持有的銀行j的資產為xji,那么,銀行i持有同業的資產,即其同業負債共為。令表示銀行j借給銀行i的資產占銀行i的同業負債的比例,則銀行i的基礎違約還可表示為:

其中,π為n×n矩陣,e=(e1,…,en)表示在時點t各銀行償還了存款客戶(OLi的債權人)之后,可用于銀行間支付的剩余價值,其中:ei=Vi-IBAi-OLi=OAi-OLi。
系統中一旦有銀行發生基礎性違約,則系統內部開始清算,系統內的清算規則及清算過程參考Eisenberg與Noe(2001)[11]。清算最重要的一條原則是優先償還存款客戶的債務,銀行發生違約時,銀行的資產(包括從同業回收的資產)應優先償還給存款客戶。
利用Eisenberg &Noe(2001)的研究成果,系統穩定時(沒有更多的銀行再陷入違約),各銀行清算支付向量的求解可轉化為下面的線性規劃問題的求解:


其中,p=(p1,…,pn)表示系統內清算的支付向量,f(p)為關于pi(i=1,…,n)單調遞增的線性函數,IBL=(IBL1,…,IBLn)。若 給 定f(p)=,上述線性規劃問題就是求解極值問題,即在滿足支付條件約束下,要求系統內銀行最大程度地償還同業間債務。容易知道,系統穩定時銀行的清算支付向量應滿足:
其中表示銀行i在系統清算時實際支付給其他銀行的額度。式(5)表示銀行i能全額償還其同業債務;式(6)表示銀行i只能償還部分同業債務;式(7)表示銀行i不能償還其同業債務。
(三)系統內部脆弱程度指數
求解清算支付向量之后,可立即判斷出i是否因傳染發生違約。
容易知道,當銀行i的情況是式(3)情形時,銀行i發生了基礎性違約。若:

同時成立,則銀行i發生傳染性違約。傳染性違約意味著銀行自身是穩健的,但由于系統內部的相互作用變得資不抵債。
對各家銀行發生基礎性違約和傳染性違約的次數進行統計,分別用和表示各家銀行發生基礎性違約和傳染性違約的次數。據此構造出一個表示各銀行在系統內脆弱程度的指數,該指數表示銀行i受到其他發生基礎性違約的銀行影響進而發生傳染性違約的可能性。βi越大,說明銀行i越容易受到其他銀行影響發生傳染性違約,銀行在系統內部越脆弱,越應該注意防范傳染風險。
(四)系統性風險的測算
下面對整個過程中形成的損失進行分析。顯然,只有當銀行發生違約時才會形成損失。結合式(3)、式(8)、式(9)可判斷銀行是否發生違約。
若銀行i發生違約,依據清算中優先償還存款客戶的規則,OAi與從同業回收的資產都應優先用來償還存款客戶。所以,若銀行i的OAi與之和大于OLi,則能還清對存款客戶的債務;否則,會對存款客戶造成損失,綜合起來,對存款客戶造成的損失可表示為:


那么,整個過程形成的總損失為:

用這個損失值來表示系統性風險的大小。L越大,系統性風險越大,當L大于某個閾值LVaR時,認為發生了極端的系統性風險事件。
本文對兩種違約的判斷與Drehmann相同,但在計算損失時,Drehmann假設一旦銀行i違約,其造成的損失為OLi×Ii×LGD,這種處理方法對損失的計算比較粗糙,且忽略了違約銀行對其相關銀行造成的損失,這樣的簡化計算不是很合理,因此,以下將結合系統性風險貢獻的計算給出詳細分析。
(五)用夏普利值計算風險貢獻
在定義了系統性風險事件之后,用夏普利值計算各家銀行的系統性風險貢獻。設系統N包括n家銀行,系統內銀行i的夏普利值的一般形式為:

其中,ns表示系統N內銀行子組合Nsub中銀行的個數,C(ns)表示包含ns家銀行的所有銀行子組合形成的集合,θ表示特征函數。
結合具體問題,定義特征函數θ為系統對整個經濟體系造成的損失L。因此,本文的夏普利值表示為:

這表示,銀行i的風險貢獻是第i家銀行對所有包含它的組合Nsub的邊際風險貢獻的期望值。結合前文對系統性風險事件的定義,進一步得到:


其中,j,Lj>LVaR表示只計入滿足約束Lj>LVaR的事件,表示滿足約束的事件次數。若定義LVaR為L的某個分位數Lq時,根據,式(15)就等價為:

最終,用式(16)計算各銀行的系統性風險貢獻。
結合式(16)分析計算總損失時加入對相關銀行造成損失的必要性。若只考慮對系統外非銀行存款人造成的損失,式(16)可表示為:

當所考查的事件是極度極端事件時,按照Drehmann的方法計算,則:

Ii是銀行i違約與否的示性函數。此時,第i家銀行的夏普利值等于OLi×Ii×LGD。也就意味著,在極端情形下,Drehmann的方法得到的銀行系統性風險貢獻是銀行的存款規模的線性函數,這種結果不能體現銀行間的關聯性和復雜性等其他方面對其系統重要程度的影響。若加入對相關銀行的損失則可以避免這一問題。
四、實證研究及結果分析
(一)數據說明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及計算條件的限制,選取我國上市銀行中的10家(其中,由于農業銀行2009年和2010年尚未上市缺相關數據,故只在2011年的分析中將其加入)作為研究對象,采用樣本銀行的年報數據和股票價格數據,對其2009~2011年的系統重要性進行分析。各銀行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在實證過程中,利用各年度相關數據,利用默頓模型重復模擬銀行資產價值,得到各年度10000次系統發生損失的事件。
(二)系統內部脆弱程度指數估計
根據計算過程中數據整理得到表2。以招商銀行為例,對表2各項進行簡單說明:kdf表示在2009~2011年的模擬計算過程中,招商銀行平均發生了1359次基礎性違約,而其因受到其他8家銀行的基礎性違約的影響,平均發生了2887次傳染性違約。從表2所列的結果來看,工商銀行β值最低,所以該銀行在系統內部也最為穩定,其系統內部脆弱程度較低,系統內的相互作用對工商銀行的影響最小。此外,興業銀行、南京銀行、北京銀行、中信銀行的β最高,說明這些銀行更容易受到系統內其他銀行的影響發生違約,這些銀行要格外注意控制傳染性風險。

表2 樣本銀行系統內脆弱程度指數
(三)系統性風險貢獻占比及系統重要性排名
根據各年度數據重復模擬計算得出的10000個系統損失的99.5%分位數來界定系統性風險事件。再利用夏普利值計算各家銀行的系統性風險貢獻。經過測算,主要結果列出見表3。

表3 2009~2011年樣本銀行風險貢獻占比及系統重要性排序
對表2中的計算結果分析如下:從2009年、2010年的結果來看,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比其他幾家銀行(因農業銀行2010年上市,故2009年和2010年沒有對農業銀行進行排名)更凸顯其系統重要性。2011年,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四家銀行的系統性風險貢獻占比之和達到了70%之上,說明我國銀行業的系統性風險比較集中,“大而不能倒”的現象在我國是存在的,監管部門應當密切關注這一問題,采取措施控制大型商業銀行的風險溢出效應。
從表3的數據可以發現,銀行的系統重要性不僅僅與其規模有關,如中國銀行的資產規模不及建設銀行,但其2009年和2011年的系統重要程度均高于建設銀行。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國銀行的同業業務占比較高,而建設銀行的同業業務占比相對較低②,中國銀行在系統內與其他銀行的關聯更為緊密,故中國銀行的系統重要性更強。
應注意的是,2009~2011年商業銀行的系統重要性排名在不斷發生變化。因此,監管機構要適時調整更新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
五、結 論
1.以上提出了基于系統整體性的銀行系統重要性評估方法,并運用該方法測算銀行系統重要性受銀行規模大小和該行與其他銀行之間關聯程度的雙重影響。這一方法解決了Drehmann方法造成系統重要性與銀行規模呈線性關系的問題。
2.對監管機構而言,不僅要確定科學的系統重要性,銀行評估方法還要正確把握影響系統重要性的關鍵因素,在識別系統重要性銀行的基礎上,根據影響系統重要性的關鍵因素制定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將銀行的風險集中度把握在可控范圍內。
商業銀行可根據那些影響系統重要性的關鍵因素適當調整業務結構來降低其系統重要性程度,以避免受到更多監管要求的約束。
3.內部脆弱程度指標能反映銀行間風險傳染效應對單家銀行的影響程度。商業銀行對系統性風險的貢獻體現了單家銀行對銀行體系的影響,而系統內部脆弱程度指標能反映銀行體系對單家銀行的影響,兩者結合能較全面地體現單家銀行和銀行體系之間風險的相互作用。相對于大型國有商業銀行而言,股份制銀行和部分城市商業銀行的內部脆弱程度指標較高,這反映了這些銀行在應對風險傳染時的抵御能力較弱。鑒于此,監管機構應當關注那些容易受到系統重要性銀行風險溢出效應影響的銀行,引導這些銀行增強其在系統內部的抗風險能力。
注釋:
①kcf是銀行i在所有銀行子組合(Nsub)中發生傳染性違約的總次數的平均值,因此,出現了某些銀行的kcf>10000的情況。
②2009年和2011年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的同業資產占樣本銀行同業總資產的比分別為38.29%、26.53%,8.85%、10.4%。2009年和2011年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的同業負債占樣本銀行同業總負債的比分別為20.82%、22.02%,16.77%、14.36%。
[1]陶玲.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風險防范標準[J].中國金融,2012,(2):79-80.
[2]彭建剛.基于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的銀行業監管制度改革的戰略思考[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1,32(1):2-6.
[3]Huang X,Zhou H,Zhu H B.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systemic risk or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J].Journal of Banking &Finance,2009,(33):2036-2049.
[4]Huang X,Zhou H,Zhu H B.Systemic risk contribut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2012,(42):55-83.
[5]Lahmann W,Kaserer C.Measuring systemic risk and assessing systemic importance in global and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s using the ESS-indicator[J/OL].http://papers.ssrn.com/s ol3/papers.cfm?abstract_id=1906682,2011.
[6]Acharya V,Pedersen L H,Philippon T,Richardson M P.Measuring systemic risk[J/OL].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595075##,2010.
[7]Brownlees C T,Engle R F.Volatility,correlation and tails for systemic risk measurement[J/OL].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611229,2012.
[8]Drehmann M,Tarashev N.Measuring the systemic importance of interconnected banks[J/OL].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859244,2011.
[9]賈彥東.金融機構的系統重要性分析——金融網絡中的系統風險衡量與成本分擔[J].金融研究,2011,(10):17-33.
[10]彭建剛,吳云,馬亞芳.基于一致性原理的商業銀行經濟資本配置方法[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3,33(2):338-344.
[11]Eisenberg L,Noe T H.Systemic risk in financial systems[J].Management Science,2001,47(2):236-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