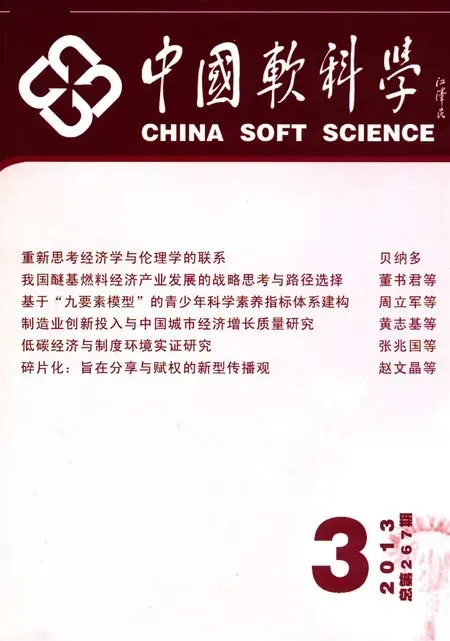低碳經濟與制度環境實證研究——來自我國高能耗行業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張兆國,靳小翠,李庚秦
(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湖北武漢430074)
一、問題提出
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氣候不斷惡化已給自然環境、人類生活和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這已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而已上升為一個全球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為了積極應對全球氣候的不斷惡化,英國政府在2003年發布的《能源白皮書》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經濟”之概念,并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與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相比,低碳經濟是一種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張坤民,2008)[1]。這種經濟發展模式被普遍認為是各國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要發展低碳經濟,就必須在技術和制度等方面進行創新。但相比之下,制度創新更重要,因為低碳經濟的核心是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通過各種制度的制定和創新來推動各種技術的開發與應用(Vrijnoed et al.,2009)[2]。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講,低碳經濟是一種典型的制度經濟(肖國興,2010;陳柳欽,2010)[3-4]。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在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的背后卻是過度的能源消耗和嚴重的環境污染。據國際能源機構測算,我國的能源消耗量2009年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國。過度的能源消耗必然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從而給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失。為此,我國政府把節能減排納入了社會經濟發展的中長期規劃。2006年提出了201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2005年下降20%左右的約束性指標;2009年確定了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溫室氣體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的行動目標。為了完成這些目標任務,我國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法律制度、稅收政策、信貸政策、財政補貼以及環境污染產權交易試點等內容。那么,這些制度安排的實施效果如何或者說企業對這些制度安排的態度和反應如何呢?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對于有的放矢地制定和完善節能減排的制度安排,發展低碳經濟,應對氣候惡化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然而,目前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實證研究還不多見。
本文首先以我國2006-2010年深滬兩市化工、鋼鐵、石油冶煉、熱力和火電、有色金屬和水泥等高能耗高排放行業的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從制度層面上,實證分析稅收政策、財政補貼、信貸政策、法律制度、市場化程度和社會輿論等制度性因素對低碳經濟發展的影響。然后,通過問卷調查進一步分析企業管理人員對這些制度性影響因素的看法,以便對回歸分析的結果加以印證、解釋和補充。通過研究發現,稅收政策、財政補貼、信貸政策和社會輿論對低碳經濟發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法律制度和市場化程度對低碳經濟發展雖有正向影響但不顯著;制定能耗標準和排放標準對企業有一定的約束與激勵作用。這些研究結論的政策意義在于:要發展低碳經濟,就必須在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個方面制定和創新相應的制度安排,以充分發揮這三只手的協同作用;雖然政府采取的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對低碳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從長效機制看,更應該發揮法律制度和市場機制的作用。
本文余下的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論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設;第三部分是回歸分析,包括樣本選擇、數據來源、變量解釋、模型構建和回歸結果;第四部分是問卷調查分析,包括調查對象、調查方式和調查結果;第五部分是研究結論及政策意義。
二、理論分析
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要發展低碳經濟,就必須解決其外部性問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外部性是指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對其他經濟主體的福利會產生影響,而施加這種影響的主體卻沒有因此付出代價或獲得補償(Meade,1952)[5]。根據外部性所產生的經濟后果對承受者是有利還是有害,可把外部性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兩種。其中,正外部性是指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給其他經濟主體帶來了額外收益,而受益者卻無須付出代價;負外部性是指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給其他經濟主體帶來了額外損失,而制造損失者卻沒有為此付出代價(Viner,1931)[6]。這兩種外部性在低碳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都可能存在。如果企業投資環境保護,減少污染和排放,而自己卻又不能獲得額外補償,即社會收益大于企業收益,這就是正外部性。相反,如果企業為了自身利益,不顧環境保護,給社會造成了損失,而自己卻又不承擔成本,即社會成本大于企業成本,這就是負外部性。無論負外部性還是正外部性都是與低效率相伴隨的,都會對低碳經濟的發展造成不良影響。正外部性會挫傷企業保護環境的積極性,減少對環境保護的投入,而負外部性不僅在經濟上無效,而且會加劇企業對環境的污染。所以,要發展低碳經濟,就必須解決好這兩種外部性的問題,尤其是負外部性問題。
那么,又如何解決低碳經濟發展中所存在的外部性問題呢?其基本思路是將外部性內部化(Lohmann,2009)[7]。也就是說,要使正外部性的制造者能因此而獲得補償,使負外部性的制造者能為此付出代價。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一套相應的制度安排(North,1990)[8]。有實證研究表明,經濟增長并不會自發地導致污染排放的減少,也并不一定會導致污染排放的增加,而促使企業節能減排的關鍵在于完善環境治理機制和政策。目前,世界各國治理企業過度能源消耗與污染排放問題的制度安排大致可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政府力量(看得見的手),如法律手段、經濟手段、行政手段等;二是市場力量(看不見的手),如碳排放交易市場等;三是政府和市場以外的力量(社會之手),如社會輿論、社會道德教育等。本文將結合我國企業的制度背景,并考慮到數據的可取性,著重探討如下制度性因素對低碳經濟發展的影響:
1.稅收政策對低碳經濟的影響
“污染者付費原則”是目前有關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以及學術界普遍認同和倡導的一項基本原則或國際慣例。征收環境污染稅就是這一項原則的具體體現,目前已成為各國政府普遍采用的控制環境污染的措施之一。最早從價格的角度研究征收環境污染稅的學者是20世紀初著名的經濟學家庇古。Pigou(1932)[9]認為,要對產生負外部性的部門(或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的部門)征稅,而對產生正外部性的部門(或私人成本大于社會成本的部門)補貼,從而使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促使企業減少污染,保護環境,這就是著名的庇古稅。此后,大量實證研究支持了Pigou的觀點,發現征收環境污染稅對促使企業節能減排,保護自然環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Mountord and Keppler,1999;Langpap,2006;Tsai et al.,2007)[10-12]。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關于企業節能減排的稅收政策主要是從正外部性的角度考慮,以稅收優惠和減免為主。例如,對使用節能材料生產的產品可減半征收增值稅;對節能服務公司實施的能源管理項目可免征營業稅;2007年修訂的《企業所得稅法》進一步加強了稅收優惠的力度,規定節能減排的技術轉讓以及企業用于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的投資都可以從企業應稅所得額中扣除。
2.財政補貼對低碳經濟的影響
財政補貼是政府為了實現某種社會目標而對微觀經濟體進行直接干預的一種經濟手段(Harris,1991;姜寧和黃萬,2010)[13-14]。近年來,我國政府為了鼓勵企業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的財政補貼政策,如淘汰落后產能的財政補貼、合同能源管理的財政補貼、可再生能源的價格補貼和節能技術改造的財政補貼等。此外,各地方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的財政補貼政策。有資料表明,2005-2009年我國政府用于環境保護的財政補貼分別為132.97、161.24、995.82、1451.36和1934.04億元人民幣,呈明顯的上升趨勢。所有這些財政補貼政策與上述稅收優惠及減免政策并無實質性的差異。只不過是前者更加直接,而后者比較間接。
3.信貸政策對低碳經濟的影響
銀行信貸是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之一,它也是各國政府用來解決企業過度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問題的一種常用手段。大量研究表明,實行綠色信貸政策不僅有助于企業節能減排,保護環境,而且有助于銀行防范信貸中的環境與社會風險,實現“可持續金融”戰略(Gradeland Allenby,2003;Emtairah et al.,2005)[15-16]。正因如此,2002年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和荷蘭銀行提出了著名的“赤道原則”,要求銀行必須評估和防范貸款項目中的環境與社會風險。例如薩哈林2號油氣開發項目,相關的投資銀行雖已投資完成項目80%以上的工作量,但因對海洋生態環境和西部灰鯨生存有巨大威脅而被迫停止繼續投資建設。
我國從1995年開始實行綠色信貸,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如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關于貫徹信貸政策和加強環境保護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2007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發布的《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2007年工商銀行頒布的《關于推進“綠色信貸”建設的意見》;2008年興業銀行與國際金融公司簽署的《能源效率融資項目合作協議》等。有資料表明,截止2010年6月,我國四大國有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共投放的綠色貸款余額達到10970億元人民幣。因此,可以預期我國的綠色信貸政策對促使企業節能減排,推動低碳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4.法律制度對低碳經濟的影響
上述稅收政策、財政補貼和信貸政策等政府經濟手段雖然便于實施,刺激性強,見效也快,但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問題,使政府難以準確地計算環境污染的社會成本和均衡價格,因此依靠政府經濟手段便難以達到帕累托最優;由于稅收政策會通過產品價格轉嫁給消費者,因此不能很好解決應該由誰來付稅的問題;依靠政府經濟手段只能對企業形成短期、有限的激勵,而無法形成長效激勵機制;在我國處于經濟轉軌時期,由于政府壟斷著社會資源和缺乏監督,因此依靠政府經濟手段便容易產生尋租和腐敗問題。有鑒于此,從政府層面看,要促使企業節能減排,除了要采取經濟手段之外,更要采取法律手段。從各國發展低碳經濟的經驗看,法律制度是促使企業節能減排從“軟約束”走向“硬約束”的根本保證和有效途徑。公共壓力理論認為,法律制度是企業來自政府的最直接、最具威懾的一種壓力(Walden and Schwartz,1997)[17]。David et al.(2011)、Zizzo and Fleming(2011)[18-19]等研究表明,企業節能減排和披露環境信息的行為與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如果法律條款完善,執法也嚴格,能夠使違法的預期成本遠大于預期收益,就會促使企業自覺地遵守法律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相反,如果缺乏法律制度,或者法律條款不完善,執法也不嚴格,使企業無法可依或違法成本過低甚至為零,則企業在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下就缺乏節能減排的法律意識。
我國政府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在能源與環境保護方面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電力法》、《煤炭法》、《節約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等。據中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的報告表明,我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的能耗由2005年的1.276噸標準煤下降到2009年的1.077噸標準煤(均為2005年可比價),主要用能產品單位能耗逐年降低,能源利用率有所提高。隨著我國立法制度和司法制度的不斷完善,企業來自法律制度的壓力會不斷加大,從而在節能減排方面會更加努力。總之,以國家暴力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在產權保護方面有著不可爭議的比較優勢,它是保證低碳經濟發展的最根本性的制度基礎。
5.市場化程度對低碳經濟的影響
上述稅收政策、財政補貼、信貸政策和法律制度對低碳經濟的影響都是依靠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力量。但是,依靠政府力量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前面分析了依靠經濟手段存在的局限性,同樣依靠法律手段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如效率損失、訴訟結果不確定性、“理性的無知”和“搭便車”等問題。此外,目前我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條款還比較粗,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執法力度也不夠強。所以,在低碳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還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是組織化、制度化的交換。也就是說,市場也是一種制度安排或契約安排(康芒斯,1983)[20]。它對市場主體起著“看不見的手”的約束作用。產權理論認為,外部性產生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沒有一個市場來交換制造外部性的權力,如果能夠使外部性的產權清晰,并能夠通過市場討價還價以及轉移支付,則外部性就可以完全內部化(Coase,1960)[21]。按照這種理論,建立環境污染產權交易市場便有助于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解決企業環境污染問題。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環境污染產權交易市場是基于《京都議定書》建立的碳排放交易市場。Kossoy and Ambrosi(2010)[22]通過對歐盟排放交易市場的實證研究發現,2005-2007年該交易市場使整個歐盟的碳排放減少了2-5%。
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起全國性的環境污染產權交易市場,只是在山東、山西、浙江和天津等少數省市開展了試點。但是,我國的整體化市場程度卻可能對企業節能減排產生一定的影響。有實證研究表明,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政府官員的腐敗越少,資源配置的效率越高,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兼容性越大(張小蒂,2003;方軍雄,2006)[23-24]。
6.社會輿論對低碳經濟的影響
通過上述理論分析可見,政府和市場都可能對企業節能減排產生積極的影響作用。但是,從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看,政府和市場并非總是有效,有時也會存在失靈或失效問題(North,1981)[25]。因此,這就需要有社會輿論等第三方力量(社會之手)來對政府和市場的失靈問題加以糾正。報刊、廣播、電視和網絡等新聞媒體是以社會輿論為代表的“公共領域”,它們具有傳播信息快、影響范圍廣等比較優勢。因此,Besley and Prat(2001)認為[26],媒體監督是社會民主監督的一種重要方式,是社會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通過聲譽機制的作用,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機制(Dyck et al.,2010)[27]。在環境保護方面,Neu et al.(1998)、Aertsa and Cormier(2007)、Aertsa et al.(2008)等研究表明,媒體監督對企業促使減少環境污染和披露環境信息起到了積極的影響作用[27-29]。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輿論媒體對企業節能減排的監督作用。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中華環保世紀行活動的啟動儀式上強調,要充分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大力推動企業節能減排,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近年來,經過媒體曝光后解決了很多重大的環境問題。如2005年的“松花江事件”被媒體曝光后,迫使吉林化工企業建立了三級防排體系,2007年“藍藻事件”被媒體曝光后,迫使當地政府大幅度地降低了企業的污染排放量。這些案例表明,在我國這樣一個新興市場經濟的國家,由于法律制度和政府監管還不夠完善,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人治”問題,因此媒體監督對促使企業保護環境有著特別重要的作用。
通過上述理論分析可見,稅收政策、財政補貼、信貸政策、法律制度、市場化程度和社會輿論等制度性因素均對低碳經濟發展有著積極的影響作用。當然,這一理論分析的結果還有待于下文做進一步地實證檢驗。
三、回歸分析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根據《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報告》的披露,我國高能耗行業主要有六大行業,包括化工行業、水泥生產行業、鋼鐵行業、有色金屬行業、石油冶煉行業和熱力與火電行業。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十一五”期間這六大行業的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占到整個工業能耗和碳排放的70%以上。因此,本文以我國2006-2010年這六大行業的深滬兩市A股類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剔除數據不全的公司之后,共121家樣本公司,其中鋼鐵行業25家、化工行業7家、石油冶煉7家、熱力和火電45家、水泥行業17家和有色金屬行業20家。
公司能耗和排放方面的數據來自中國環保部網站、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在證監會官方網站上公布的年度財務報告和社會責任報告。社會輿論的數據來自知網中國重要報紙數據庫以及百度和谷歌網絡搜索。其他變量的數據來自色諾芬金融數據庫和國泰安數據庫。
(二)變量解釋
1.低碳經濟
由于低碳經濟是一種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本文以能耗指標和排放指標來衡量低碳經濟的發展程度。能耗指標是指把企業所有能耗按標準煤折算,并以2005年行業平均價格指數為基準計算的每萬元產值綜合能耗。排放指標是指二氧化硫排放(因為我國是用二氧化硫排放來描述高排放行業的減排目標),用每萬元產值二氧化硫排放量來表示(仍以2005年行業平均價格指數為基準)。
2.稅收政策
由于我國關于企業節能減排的稅收政策是以稅收優惠及減免為主,因此用稅收優惠及減免金額除以企業平均總資產來衡量稅收政策的力度。企業平均總資產等于年初總資產與年末總資產之和除以2。
3.財政補貼
用企業節能減排方面的財政補貼除以企業平均總資產來表示。
4.信貸政策
用企業節能減排方面的銀行借款(包括短期借款和長期借款)除以企業平均總資產來表示。
5.法律制度
根據Walden and Schwartz(1997)、王建明(2008)等文獻[17][31],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頒布的有關企業節能減排的法律、條例和規定的多少來衡量法律制度壓力的大小。
6.市場化程度
用樊綱等近年來編制的我國各地區市場化指數來衡量市場化程度。
7.社會輿論
借鑒Hamilton(1995)、于忠泊等(2011)等做法[32-33],以報刊、電視、廣播和網絡等主要媒體所曝光的企業過度能耗和環境污染的次數來衡量社會輿論監督的力度,如果沒有這方面的報道則取值為0。
此外,為了控制公司特征和所處行業等因素對企業節能減排的影響,還增設了公司規模、盈利水平、產權性質以及年度和行業等控制變量。上述各變量的解釋見表1。
(三)模型構建
為了檢驗各制度性因素對能耗指標的影響,本文建立如下檢驗模型(1):

為了檢驗各制度性因素對排放指標的影響,本文建立如下檢驗模型(2):


表1 變量的定義和計算
模型中各制度性變量取前一年的值,是因為各制度性因素對企業能耗和排放的影響不可能立竿見影,在時間上具有滯后性,需要先通過影響企業節能減排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然后才會影響企業能耗和排放。另外,由于任何因素的變化都具有一定的慣性,后一期結果往往會受到前一期結果的影響,因此為了避免遺漏重要變量或系統誤差所造成的估計結果不一致,在模型中增加了前一期的因變量作為自變量。為了控制企業自身特征對節能減排指標的影響,在模型中增加了公司規模、盈利水平、產權性質、所處行業等控制變量。
(四)描述性統計
表2是全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能耗指標和排放指標的最小值與最大值之間的差距比較大,說明各公司的能耗水平和排放水平存在較大差距。稅收政策、財政補貼和信貸政策的標準差都比較大,可能是因為在樣本期內政府逐年加大了對這些政策的執行力度。表3是分行業的描述性統計。其結果表明,各行業之間的能耗和排放差別迥異,能耗最高的行業是水泥業,排放量最高的行業是熱力和火電行業。表4是分年度的描述性統計。其結果表明,能耗指標和排放指標在各年度呈下降趨勢,不論最小值、最大值還是平均值都在逐年變小。

表2 樣本描述性統計

表3 描述性統計

表4 分年度描述性統計
(五)回歸分析
在回歸之前,首先對時間序列變量做了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各時間序列變量都不存在單位根,因此可以直接對各變量進行回歸。
表5是模型(1)和(2)的靜態固定效應回歸結果。采用Hausman對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兩種估計方法進行了檢驗,其結果是接受隨機效應模型的概率為0.025,說明固定效應模型更優一些。
表6是使用GMM方法對模型(1)和模型(2)進行回歸的結果。之所以在表5的基礎上又選擇GMM方法對這兩個模型回歸,是因為在這兩個模型中自變量里包含滯后一期的因變量,故回歸數據是動態面板數據,而不是靜態面板數據。在對動態面板數據進行回歸時,使用OLS/ML估計方法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倚和非一致問題,而使用GMM估計方法則可以得到模型的一致估計量(Nickell,1981;Blundell and Bond,1998)[34-35]。回歸時使用自變量的二階及更高階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Sargan檢驗的結果表明,工具變量是有效。同時也檢驗了殘差項的自相關問題,結果表明殘差項不存在這一問題。

表5 固定效應回歸結果

表6 動態面板數據回歸結果
表5的靜態回歸結果和表6的動態回歸結果基本一致。由回歸結果可見:①能耗指標和排放指標均與稅收政策、財政補貼和信貸政策呈顯著負相關。這表明這些經濟手段對促使企業節能減排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目前這些經濟手段基本上都是以“津貼”的方式來推動企業節能減排,而沒有充分體現“污染者付費”原則,因此從長遠來看,其作用可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②能耗指標和排放指標均與媒體監督呈顯著負相關。這表明媒體監督對促使企業節能減排起到了積極作用,企業也比較關注自己的聲譽。③能耗指標和排放指標均與法律制度呈不顯著負相關。這表明法律制度對促使企業節能減排的作用不夠明顯。其原因可能是:我國的法律常常是框架式的規定,再加上目前還沒有相應的實施細則,因此缺乏可操作性;執法部門的責任不夠明確,也未真正實行“問責”制;違法成本低,不足以引起違法者的重視(王明遠,2010)[36]。④能耗指標和排放指標均與市場化程度呈不顯著負相關。這可能是因為:我國處在經濟轉軌時期,市場化程度總體不高,特別是還沒有建立起環境污染產權交易市場,使企業缺乏節能減排的壓力和動力(羊志洪等,2011)[37]。
最后,有必要說明一點的是,上述各制度性因素對能耗指標和排放指標的影響之所以都一致,是因為能耗與排放的關系十分密切(Ugur et al.,2009;袁富華,2010)[38-39]。本文在統計分析的過程中也發現了這一點,即能耗指標與排放指標的變化趨勢高度一致。
四、問卷調查分析
為了了解企業管理人員對有關節能減排制度性影響因素的看法,以驗證、解釋和補充回歸分析的結果,本文進一步地進行了問卷調查分析。
(一)調查對象與調查方式
本文調查的對象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在貴陽、鄂爾多斯、鄭州和武漢開辦的EMBA班的學員;另一部分是回歸分析中的樣本公司。對前者采用的是課堂發放問卷的方式;對后者是通過發送電子郵件的方式。自2011年6月至2011年11月,共發放問卷450份,收回問卷344份,回收率76.4%。但考慮到本文所研究的樣本屬于高能耗行業,因此在收回問卷中只選擇與此有關的作為有效問卷,共計132份。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見表6。由此表可見,本文調查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是男性,占到了90%以上;所學專業集中在經濟與管理類,占60%以上;大部分是企業高管人員,占70%以上;所處行業比較分散。

表6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二)調查結果
問卷所涉及的內容包括四個方面,即對低碳經濟的關注、企業節能減排的措施、對現有節能減排制度的看法和對現有制度改進的建議。以下從這四個方面總結分析企業管理人員所提供的信息。
1.對低碳經濟的關注
在收回的132份有效問卷中,對“你對低碳經濟的概念是否熟悉”,有102人(77.3%)回答是熟悉或非常熟悉。對“體現低碳經濟要求的重要方面是什么”,有84人(63.6%)回答是“少開車、節約紙張”等低碳生活方式,只有45人(34.1%)回答是“企業節能減排”,其余人員回答的是其他內容。對“企業內專司節能減排管理的機構是什么”,有36人(27.3%)回答是董事會,96人(72.7%)回答是較低的執行部門,如社會責任管理部門或計劃部門。可見,企業管理人員對低碳經濟的認識還不夠全面,重視程度還不夠高,需要進一步加強對低碳經濟的宣傳。
2.企業節能減排的措施
在收回的132份有效問卷中,對“你所在企業的主要能源是什么”,112人回答煤炭,17人回答是電力,其余人員回答是天然氣或其他能源。對“企業目前節能減排的主要措施是什么”,有105人(79.5%)選擇淘汰落后產能和技術改造,還有21人(15.9%)選擇廢物利用和循環經濟,只有6人(4.6%)選擇利用清潔能源。對企業來說,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產業結構,也不可能改變主要能源,因而降低能耗和排放的主要途徑便是技術改造或淘汰落后設備。
3.對現有節能減排制度的看法
在收回的132份有效問卷中,對“企業比較關注的有關節能減排的制度安排或政策是什么”,選擇稅收政策、財政補貼、信貸政策、行政手段(能耗標準和排放標準)、法律制度、市場機制和社會輿論的人數分別是129、131、128、107、31、14和86。對“現有節能減排的制度或政策存在哪些主要問題”,有117人(88.6%)認為,政府在節能減排的稅收優惠、財政補貼和金融支持等方面的力度還不夠大;有88人(66.7%)認為,政府給企業下達的節能減排目標缺乏科學的論證和嚴格的考評,因而難以起到約束與激勵作用;有62人(47.0%)認為,相關監管部門不夠作為,監管力度不夠大;有25人(18.9%)認為,法律制度亟待完善。
4.對現有制度改進的建議
絕大多數人認為,政府要進一步加大稅收優惠、財政補貼和金融支持等經濟手段的力度;也有部分人認為,政府要進一步加大監管力度、硬化節能減排目標的約束和完善法律制度。
由上述可見,目前企業管理人員對稅收政策、財政補貼和信貸政策等政府經濟手段以及節能減排標準等政府行政手段都十分關注,對社會輿論比較關注,而對法律制度和市場機制的關注則不夠高。企業管理人員對這些制度性影響因素的不同關注程度便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解釋了前文回歸分析的結論。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意義
低碳經濟是一種典型的制度經濟,是各國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要發展低碳經濟,就必須建立一套相應的制度安排。我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在這方面出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但其效果如何卻有待于檢驗。本文首先以我國2006-2010年深滬兩市高能耗高排放行業的A股類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了稅收政策、財政補貼、信貸政策、法律制度、市場化程度和社會輿論等制度性因素對低碳經濟發展的影響。然后,通過問卷調查分析了企業管理人員對這些制度性影響因素的看法。通過研究表明,這些制度性因素均對低碳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具體而言,稅收政策、財政補貼、信貸政策等政府經濟手段和社會輿論對低碳經濟發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法律制度和市場化程度對低碳經濟發展有正向影響,但不顯著;制定能耗標準和排放標準對低碳經濟發展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上述研究結論的政策意義在于:要發展低碳經濟,促使企業節能減排,就必須在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個方面制定和創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充分發揮這三只手的協同作用。具體而言:
1.在“政府之手”方面,為了充分發揮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迫切需要解決如下幾個問題:①完善稅收政策。目前我國在能耗與排放方面所采取的稅收政策主要是稅收優惠與減免政策。這種稅收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激勵企業節能減排,但不符合“污染者付費”原則,致使一些過度能耗與排放的企業不承擔相應的成本。針對這一問題,借鑒國際經驗,一方面要按照“污染者付費”原則,對污染企業征收環境污染稅;另一方面要按照“使用者付費”原則,對使用污染產品的企業征收污染產品稅。而且要把這些稅收收入用于環境保護的投資。②改進政府行政監管。目前有關部門對企業能耗與排放的監管主要是制定能耗標準和排放標準。這種監管方式雖然對企業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有:一是要在事前確定一個科學合理的能耗標準和排放標準,以便給企業留下一個適當的“污染者特權”;二是要在事中對能耗標準和排放標準的執行過程進行統計和監控;三是要在事后對能耗標準和排放標準的執行結果進行考評,實行合理的獎懲。③加強法制建立。一方面,在立法方面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包括細化法律條款、制定實施細則、加大違法成本等內容;另一方面,在司法方面要建立“問責制”,使執法部門切實履行職責,加強執法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2.在“市場之手”方面,為了發揮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需要借鑒國際碳排放交易市場建設的經驗,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積極做好環境污染產權交易的試點工作,探索環境污染產權交易價格的形成機制。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全國性的環境污染產權交易體系,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治理環境污染方面的基礎性作用。
3.在“社會之手”方面,要在政府積極引導下,賦予新聞媒體、社會公眾和民間組織有關能源與環境保護的知情權和決策參與權,以充分發揮“社會之手”的作用,彌補和遏制政府和市場的失靈問題。
[1]張坤民.低碳世界中的中國:地位、挑戰與戰略[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3):1-7.
[2]Vrijmoed S,Hoogwijk M,Hendriks C,Erbong G,Lambert F.The Potential of Carbon and Storage:under Different Policy Options[J].Energy Procedia,2009,1(1):4127-4143.
[3]肖國興.中國節能減排的法律途徑[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6):55-60.
[4]陳柳欽.低碳經濟演進:國際動向與中國行動[J].科學決策,2010,(4):1-18.
[5]Meade J.External 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in a Competitive Situation[J].The Economic Journal,1952,62(245):54-67
[6]Viner J.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J].Journal of Economics,1931,3(1):23-46.
[7]Lohmann L.Climate as investment[J].Development and Change,2009,40(6),1063-1083
[8]North D 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9]Pigou A.The Economics of Welfare[M].London:Macmillan Press,1932.
[10]Mountford H,Kepple JH.Financing Incentiv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J].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1999,(240):133-144.
[11]Langpap C.Conservation of Endangered Species:Can Incentives Work for Private Landowners?[J].Ecological Economics,2006,(57):558-572.
[12]Tsaia W T,et al..Perspectives on Resource Recycling From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Taiwan[J].Resources Policy,2007,(32):69-79.
[13]Harris R.The Employment Creation Effects of Factors Subsidies:Some Estimation for Northern Irel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91,(31):49-64.
[14]姜寧,黃萬.政府補貼對企業R&D投入的影響[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0,(7):28-33.
[15]Gradel T E,Allenby B R.Industrial Ecology[M].New York:Prentice Hall,2003.
[16]Emtairah T,Hansson L,Hao G.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Banks in China:the Case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J].International Greener Management,2005,(50):85-96.
[17]Walden W D,Schwartz B N.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and Public Policy Pressur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1997,(16):125-154.
[18]David P,Tamara H,Nick J.Environmental Policy vs.Public Pressure: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of Alternative Bleaching Technologies in the Pulp Industry[J].Research Policy,2011,40(9):1253-1268.
[19]Zizzo D J,Fleming P.Can Experimental Measures of Sensitivity to Social Pressure Predict Public Good Contribution?[J].Economics Letters,2011,(111):239-242.
[20][美]康芒斯.制度經濟學(上冊)[M].于樹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21]Coase R H.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3):1-44.
[22]Kossoy A,Ambrosi P.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2010 Report[R].Carbon Finance at the World Bank,Washington D.C.,2010.
[23]張小蒂.市場化與環境保護的兼容性[J].管理世界,2003,(3):138-143.
[24]方軍雄.市場化進程與資本配置效率的改善[J].經濟研究,2006,(5):50-61.
[25]North D C.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R].New York:W.W.Norton Press,1981.
[26]Besley T,Prat A.Handcuffs for the Grabbing Hand?Media Capture and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R].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Working Paper,2001,20-68.
[27]Dyck A,Morse A,Zingales L.Who Blows the Whistle on Corporate Fraud?[J].Journal of Finance,2010,(6):2213-2252.
[28]Neu D,Warsameb H,Pedwellc K.Managing Public Impressions: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in Annual Reports[J].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1998,23(3):265-282.
[29]Aertsa W,Cormier D.Media Legitimacy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J].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7,(34):1-27.
[30]Aertsa W,Cormierb D,Magnanc,M.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Media: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64):643-659.
[31]王建明.環境信息披露、行業差異和外部制度壓力相關性[J].會計研究,2008,(6):54-62.
[32]Hamilton JT.Pollution as News:Media and Stock Market Reactions to the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Data[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5,(28):98-113.
[33]于忠泊,田高良,齊保壘,張皓.媒體關注的公司治理機制[J].管理世界,2011,(9):127-140.
[34]Nickell S.Biases in dynamic models with fixed effects[J].Econometrica,1981,49(6):1417-1426.
[35]Blundell R,BondS.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1l5-143.
[36]王明遠.論排放權的準物權和發展權屬性[J].中國法學,2010,(6):92-99.
[37]羊志洪,鞠美庭,周怡圃,王琦.清潔發展機制與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構建[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8):118-123.
[38]Ugur S,Ramazan S.Energy Consumption,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s:Challenges Faced by an EU Candidate Member[J].Ecological Economics,2009,(68):1667-1675.
[39]袁富華.低碳經濟約束下的中國潛在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10,(8):7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