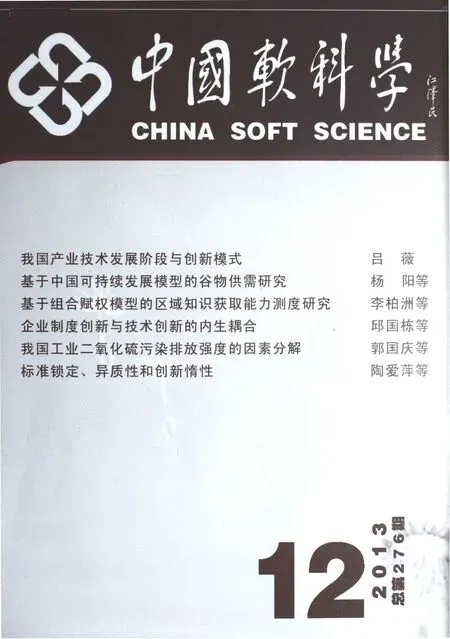我國工業二氧化硫污染排放強度的因素分解
郭國慶,錢明輝,張平淡
(1.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北京100872;2.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北京100872;3.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北京100875)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高度重視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工作。2005年3月,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提出要“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以下簡稱“兩型社會”)。同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兩型社會”建設,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再次強調要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并指出把建設“兩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之后,國務院于2007年12月批復武漢城市圈與長株潭城市群為“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更是將生態文明建設正式寫入黨章。由此可見,“兩型社會”建設是“十一五”以來中國政府所力推的重要政策。那么,與“十五”相比,中國在“十一五”期間是否正向政策預期的那樣向“兩型社會”邁進了呢?不同地區在“兩型社會”建設的路徑選擇是否存在差異呢?
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不是中國最早提出的,但是把兩者并列、將建設“兩型社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卻是比較新的[1]。相應,國外并沒有關于“兩型社會”的一般性研究,現有國外研究和部分國內研究主要是將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分別納入可持續發展的分析框架之下,討論可持續發展中的能源使用與環境保護問題,例如,Zhang(2000)分解了1980-2007年中國CO2排放量,認為能源消耗強度提高是CO2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2]。Hamilton and Turton(2002)分解了1982-1997年OECD 國家的CO2排放量,認為能源消耗強度降低有利于污染排放減少[3]。也說是說,如果將能源消耗強度降低視為資源節約,污染物排放減少視為環境友好,那么,資源節約有利于環境友好。類似的國內研究也不少。李荔等(2010)分解了1997-2007年中國各地區的SO2排放強度,同樣認為資源節約有利于環境友好[4]。還有一些研究認為,技術進步對治污減排至關重要。成艾華(2011)分解了1998-2008年中國工業SO2排放強度,發現技術效應對工業SO2減排的貢獻最大[5]。張平淡等(2012a)利用對數平均的迪式分解法(LMDI)分解了1998-2009年中國SO2排放強度,認為SO2排放強度的降低主要源于污染處理技術的提高,其次才是能源消耗強度的降低[6]。張平淡和何曉明(2014)利用LMDI 將工業粉塵排放強度分解為源頭防治、過程控制和末端治理3 個部分,以此判斷我國從“十五”到“十一五”期間全過程管理實現與否[7]。
本研究以工業SO2為對象,借鑒Sun(1998)[8]的完全分解模型將2001-2010年中國工業SO2排放強度分解為資源節約效應和環境友好效應,并借此衡量、判斷我國推行“兩型社會”政策之后是否發生了預期的變化,利用聯立方程模型檢驗我國各地區“兩型社會”建設的實現路徑,嘗試性探討“兩型社會”建設的內在機制。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利用完全分解模型,從結果衡量“兩型社會”的建設進展,避免了指標體系構建中的主觀因素和人為臆斷,為我國“兩型社會”建設評價提供新的視角;第二,利用實證檢驗從環保投資、環境規制、技術水平、環保意識和產業結構等角度梳理“兩型社會”建設的內在機制,對我國各地區“兩型社會”建設現狀的差異做出解釋。
論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兩型社會”的評價方法,總結并評價現有“兩型社會”評價方法,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強度進行理論分解,完成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的理論分離,以此評價“兩型社會”的建設情況;第三部分是“兩型社會”的評價結果,分解2001-2010年全國以及30 個地區的污染排放強度,比較各地區在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兩個路徑間的權衡;第四部分是“兩型社會”的影響因素檢驗,利用聯立方程模型檢驗環保投資、環境規制、環境技術、生產技術、環保意識、產業結構等因素對各地區“兩型社會”建設的影響,以解釋不同地區實現“兩型社會”的路徑選擇;第五部分是結論與建議。
二、因素分解模型
本研究選擇Sun(1998)[8]的完全分解模型,對污染排放強度進行分解。具體地,在時間段[0,t]內,污染排放強度可以寫成如下形式:
其中,Ⅰit代表i 地區t年的污染排放強度,Eit代表i地區t年的污染排放量,Yit代表i 地區t年的GDP,Git代表i 地區t年的能源消耗量。Git/Yit表示i 地區t年單位GDP 的能源消耗量,Eit/Git表示i 地區t年單位能耗的污染排放量。
在時間段[0,t]內,污染排放強度的變化可以寫成如下形式:

式(2)右邊第一項表示能源消耗強度的變化對i 地區污染排放強度變化的貢獻,第二項表示單位能耗的污染排放量變化對i 地區污染排放強度變化的貢獻,第三項是殘余項,將該項平均分配到第一項和第二項,分別定義為資源節約效應(recourse-saving effect)和環境友好效應(environmental-friendly effect)。資源節約效應和環境友好效應可以表達成如下形式:


用資源節約效應占排放強度變動的比例代表資源節約效應的貢獻率,環境友好效應占排放強度變動的比例代表環境友好效應的貢獻率。據此,可以評價某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兩型社會”建設情況。
三、因素分解結果
本文選取工業SO2排放量代表污染物作為研究對象,對2001-2010年中國工業SO2排放強度進行分解(表1)。研究數據來自《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需要說明的是,工業SO2只是眾多污染物(包括水、氣、聲、渣、重金屬等)的一種,可能無法反映污染物排放的全貌,但SO2是強制性減排的污染物之一,也是近些年我國治污減排的重點,在污染物選取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

表1 因素分解結果(全國范圍)
由表1 可知,工業SO2排放強度由2001年的0.0139 噸/萬元下降至2010年的0.0043 噸/萬元,下降幅度為69.17%。單位GDP 的能源消耗由2001年的1.4005 噸/萬元下降至2010年的0.8923 噸/萬元,下降幅度為36.29%。單位能耗的污染排放量由2001年的0.0099 噸/噸標準煤下降至2010年的0.0048 噸/噸標準煤,下降幅度為51.61%。從排放強度的分解結果看,資源節約效應與環境友好效應的貢獻率存在一定的變化規律。2001-2010年,資源節約效應的貢獻率逐漸提高,由2002年的-28.09% 上升至2010年的38.93%;環境友好效應的貢獻率逐漸降低,由2002年的128.09%下降至2010年的61.07%。從絕對值來看,資源節約效應和環境友好效應都在下降,本文致力于探索各地區“兩型社會”建設的內在機制,在某種程度上說,傾向于認為資源節約效應和環境友好效應的貢獻率大體相當。因此,盡管環境友好效應的貢獻率(61.07%)還遠高于資源節約效應的貢獻率(38.93%),但兩者的貢獻率正在逐漸趨同,兩者的差距也在縮小,表明我國正逐步向“兩型社會”邁進。
表2 列出了各地區的分解結果,由于數據缺失,樣本不包括西藏。

表2 因素分解結果(分省份)
由表2 可知,個別省份資源節約效應的貢獻率遠遠高出全國平均水平,甚至超過100%,例如海南、新疆和黑龍江;個別省份環境友好效應的貢獻率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甚至小于零,例如四川、甘肅、廣西和青海。根據全國資源節約效應(38.93%)和環境友好效應貢獻率(61.07%)的整體水平,將30 個地區劃分為兩個類別。第一類地區以資源節約為主,其資源節約效應的貢獻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環境友好效應的貢獻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包括海南、新疆、黑龍江、重慶、安徽、吉林、遼寧、山西、江西、內蒙古、天津、河南、貴州和北京等14 個地區;第二類地區以環境友好效應為主,其資源節約效應的貢獻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環境友好效應的貢獻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包括青海、廣西、甘肅、四川、山東、湖南、寧夏、河北、江蘇、福建、云南、廣東、浙江、上海、湖北和陜西等16 個地區。
四、“資源節約效應”與“環境友好效應”的影響因素檢驗
(一)研究假設
由表2 可知,不同地區在“兩型社會”的實現程度上有所不同,一些地區以資源節約效應為主,一些地區以環境友好效應為主。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各地區在“兩型社會”建設上選擇了不同的路徑呢?筆者認為,之所以不同地區在實現“兩型社會”途徑選擇上有很大差異,與其環保投資、環境規制、環境技術、環保意識、產業結構等因素都密不可分。
環保投資指的是各有關投資主體從社會的積累基金、補償基金和生產基金中,拿出一定數量用于污染防治、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其目的是促進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使環境得到保護與改善[9]。因此,環保投資的作用首先在于對已經產生的污染進行有效處理,消除污染排放的負面影響,這有助于環境友好效應的發揮。不過,環保投資在用于污染處理設施的生產過程中,也會產生污染。與此同時,環保投資還提高了生產技術水平,使得廠商在既定的環境規制下,減少能源消耗,進而降低污染排放[10-11]。不過,也有研究發現,技術水平越高,產量越多,反而污染排放總量越大[12]。因此,環保投資與資源節約效應的關系取決于技術水平對污染排放的關系。綜上,環保投資與“兩型社會”的關系較為復雜,既可能促進,也可能妨礙“兩型社會”實現。得到如下假設:
假設1a:環保投資越多,資源節約效應越顯著;
假設1b:環保投資越多,環境友好效應越顯著。
現有國內外研究發現,政府環境規制一方面有效降低了企業的污染排放[13-14],另一方面提高了企業生產效率,實現產業創新[15]。因此,環境規制既降低了污染排放,有利于環境友好效應的實現,又提高了能源效率,有利于資源節約效應的實現,對資源節約效應和環境友好效應都存在一定的促進作用。得到如下假設:
假設2a:環境規制越嚴格,資源節約效應越顯著;
假設2b:環境規制越嚴格,環境友好效應越顯著。
從全過程管理的角度看,環境技術對“兩型社會”建設的作用效果區別于全過程管理的各個環節。Zhang(2013)認為環境技術能有效促進末端治理和過程控制的效果,對源頭防治的作用仍未完全顯現[16]。張平淡和何曉明(2014)也發現,“十五”期間,工業粉塵排放強度的降低主要源自環境技術轉移,而“十一五”期間,工業粉塵排放強度的降低主要源自環境自主技術創新的實現[7]。可見,環境技術對“兩型社會”的作用效果是明確的,因而得到如下假設:
假設3a:環境技術水平越高,資源節約效應越顯著;
假設3b:環境技術水平越高,環境友好效應越顯著。
生產技術對“兩型社會”的作用通過三種途徑實現:首先,生產技術的改進有利于帶動經濟增長,從而間接消耗更多的資源,產生污染排放;其次,改進生產技術本身也直接消耗資源,產生污染排放;再次,生產技術的改進減少了單位產品的能源消耗,從而降低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可見,生產技術與“兩型社會”的關系并不確定,前兩種途徑不利于“兩型社會”的實現,后一種途徑有利于“兩型社會”的實現。因而得到如下假設:
假設4a:生產技術水平越高,資源節約效應越顯著;
假設4b:生產技術水平越高,環境友好效應越顯著。
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即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自覺性[17],近年來,我國公眾環保意識的總體水平呈上升趨勢[18],環保意識的增強也促進了各地環境規制的實施與執行,對“兩型社會”建設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得到如下假設:
假設5a:公眾環保意識越強,資源節約效應越顯著;
假設5b:公眾環保意識越強,環境友好效應越顯著。
由于各地區的產業稟賦不同,實現“兩型社會”的路徑也可能存在一定差異。隨著經濟結構的改善和優化,污染物排放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也就是說經濟結構調整有助于污染治理[19]。而在一些經濟結構較不合理的地區,地方政府過于依賴現有產業結構,只顧眼前利益,不管長遠發展,不利于“兩型社會”的實現。因此,經濟結構越優化,“兩型社會”的建設效果越明顯。得到如下假設:
假設6a:經濟結構越優化,資源節約效應越顯著;
假設6b:經濟結構越優化,環境友好效應越顯著。
(二)研究設計
為了檢驗如上假設,找出影響地區“兩型社會”實現途徑的因素,設定如下實證模型:

其中,方程(5)為恒等方程,表示工業SO2排放強度的變動(Total_eff)由資源節約效應(Ene_eff)和環境友好效應(Env_eff)構成。方程(6)和方程(7)是行為方程,表示資源節約效應(Ene_eff)和環境友好效應(Env_eff)由環保投資(Ⅰnvest)、環境規制(Law)、環境技術(Envi_tech)、生產技術(Pro_tech)、環保意識(Envi_awareness)、產業結構(Ⅰndustry)等因素決定。
因變量資源節約效應(Ene_eff)和環境友好效應(Env_eff)來自論文第三部分的分解結果,分別表示因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帶來的工業SO2排放強度的變動,這兩個變量為逆變量,即變量值越小越好。在變量選擇方面,環保投資(Ⅰnvest)用工業污染源治理當年投資來源總額表示,環境規制(Law)用當地政協關于環保建議提案數表示,環境自主技術(Tech_innovation)用當地環境科研課題經費表示,環境技術轉移(Tech_transfer)用當地技術市場成交額表示,環保意識(Envi_awareness)用當地有關環保的信訪來信總數表示,產業結構(Ⅰndustry)用當地第二產業占GDP 的比重表示。
研究樣本為2002-2010年中國30 個省份的270 個觀測點,數據為平衡面板數據。需要說明的是,變量資源節約效應(Ene_eff)和環境友好效應(Env_eff)是以2001年為基期的變化量,其他變量均采用當年的實際值,為了降低異方差問題,其他變量均采用自然對數的形式。
(三)描述性統計
表3 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由表3 可知,資源節約效應(Ene_eff)的均值為0.001,環境友好效應(Env_eff)的均值為-0.006,表明因資源節約效應帶來的工業SO2排放強度變化總體看來在上升,因環境友好效應帶來的工業SO2排放強度變化總體看來在下降,環境友好效應在降低污染排放強度、實現“兩型社會”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
(四)回歸結果
根據模型設定,本研究采用似無相關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Model,SUR)對模型(5)、模型(6)、模型(7)做回歸,結果見表4。

表3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4 “兩型社會”的影響因素檢驗結果
由表4 可知,當以全部觀測點作為樣本時,在以資源節約效應(Ene_eff)為因變量的回歸中,環保投資(Ⅰnves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環保投資越多,資源節約效應越不明顯,表明環保投資的增加并不利于資源節約效應的提高,假設1a 沒有得到驗證,其原因是本文研究以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來表征環保投資,這些投資主要用于治污設備和設施,帶動了能源消耗。環境規制(Law)的估計系數并不顯著,表明環境規制對資源節約效應的促進作用尚未發揮,假設2a 未得到驗證。環境技術(Envi_tech)的估計系數不顯著,表明環境技術對提高資源節約效應的貢獻不大,假設3a 未得到驗證。生產技術(Pro_tech)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環境技術越先進,資源節約效應越顯著,假設4a得到驗證。環保意識(Envi_awareness)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假設5a 未得到驗證,也就是說,環保意識還沒有對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消耗產生實質性影響。產業結構(Ⅰndustry)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第二產業比重越高,產業結構越不合理,因資源節約帶來的工業SO2排放強度下降幅度越大,資源節約效應越顯著,假設6a 未得到驗證。
在以環境友好效應(Env_eff)為因變量的回歸中,環保投資(Ⅰnves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環保投資越多,環境友好效應越明顯,表明環保投資的增加有利于環境友好效應的提高,假設1b 得到驗證。環境規制(Law)的估計系數并不顯著,表明環境規制對環境友好效應的促進作用尚未發揮,假設2b未得到驗證。環境技術(Envi_tech)的估計系數不顯著,表明環境技術對提高環境友好效應的貢獻也未顯現,假設3b 未得到驗證。生產技術(Pro_tech)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環境技術越先進,環境友好效應越不顯著,假設4b 沒有得到驗證。環保意識(Envi_awareness)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環保意識越強,環境友好效應越顯著,假設5b得到驗證,這表明環保意識提高有利于污染排放的減少。產業結構(Ⅰndustry)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第二產業比重越高,產業結構越不合理,因環境友好效應帶來的工業SO2排放強度下降幅度越小,環境友好效應越不顯著,假設6b 得到驗證。
值得注意的是,環保投資、生產技術、環保意識和產業結構在以資源節約效應為因變量的回歸中和以環境友好效應為因變量的回歸中符號恰好相反。這表明,上述4 種因素對資源節約效應和環境友好效應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換句話說,現階段沒有一種因素既能促進資源節約效應的實現,又能強化環境友好效應的改善,各地區根據自身稟賦與條件的差異,選擇最優的“兩型社會”實現路徑。在以資源節約效應為主的樣本進行回歸時,與全體樣本回歸結果不同的是,環保投資(Ⅰnvest)與資源節約效應(Ene_eff)的相關系數變得不再顯著,環保意識(Envi_awareness)與資源節約效應(Ene_eff)和環境友好效應(Env_eff)的相關系數也變得不再顯著。在以環境友好效應為主的樣本進行回歸時,與全體樣本回歸結果不同的是,環境技術(Envi_tech)與資源節約效應(Ene_eff)的相關系數變成顯著為負。由上述回歸結果可知,生產技術較先進、第二產業比重較高的地區,適合通過資源節約效應實現“兩型社會”;環保投資越多、環保意識較強的地區,適合通過環境友好效應實現“兩型社會”。
為了比較“十五”、“十一五”兩個時間段我國在“兩型社會”實現方面的差異,表5 檢驗了兩個時間段內“兩型社會”實現路徑的影響因素。由表5 可知,除變量環境技術(Envi_tech)和環保意識(Envi_awareness)外,其他變量的回歸結果在不同時間段內是一致的。“十五”期間,環境技術(Envi_tech)和環保意識(Envi_awareness)的估計系數均不顯著。“十一五”期間,環境技術(Envi_tech)與資源節約效應(Ene_eff)顯著負相關,與環境友好效應(Env_eff)顯著正相關,表明環境技術有利于資源節約效應的實現。環保意識(Envi_awareness)與資源節約效應(Ene_eff)顯著正相關,與環境友好效應(Env_eff)顯著負相關,表明環保意識有利于環境友好效應的實現,只不過,環保意識尚沒有深入到生產過程之中,未能對資源節約產生實質影響。因此,與“十五”期間相比,環境技術和環保意識的加強對“兩型社會”建設的實現與完善發揮了重要作用。

表5 “兩型社會”的影響因素檢驗結果(“十五”和“十一五”的比較)
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十分不平衡,當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時,還要面臨東部地區在發展之初忽視掉的資源環境約束問題。為了比較東中西部在權衡經濟與環境兩個問題時有何不同,表6 檢驗東中西部地區兩型社會實現路徑的影響因素。由表6 可知,不同變量在東中西部的回歸結果大不相同。環保投資(Ⅰnvest)與中部地區資源節約效應顯著負相關,表明中部地區環保投資的增加沒有消耗更多的資源,有利于“兩型社會”的實現。環境規制(Law)與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資源節約效應顯著正相關,與中部地區的環境友好效應顯著正相關,表明環境規制在東中部地區“兩型社會”建設中并沒有發揮積極作用。環境技術(Envi_tech)與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資源節約效應顯著負相關,與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環境友好效應顯著正相關,表明東西部地區環境技術的改進有利于其“兩型社會”的建設。生產技術(Pro_tech)在東中部地區對“兩型社會”建設的影響不大,在西部地區的作用較為顯著。產業結構(Ⅰndustry)與東部地區環境友好效應顯著負相關,表明結構調整在東部地區環境友好效應的實現中作用有限。另外,產業結構(Ⅰndustry)的估計系數在中部地區的回歸中不顯著,說明結構調整對中部地區“兩型社會”的作用尚未發揮。

表6 “兩型社會”的影響因素檢驗結果(分地區)
五、結論與啟示
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相對于“十五”,我國“十一五”期間是否已經或正在向“兩型社會”邁進?論文以工業SO2為對象,使用完全分解模型將污染排放強度分解為資源節約效應和環境友好效應,分解結果顯示,2001-2010年中國工業SO2排放強度降低38.93% 來自資源節約效應,61.07%來自環境友好效應,兩種效應的貢獻率在漸漸趨同,說明我國正在逐步邁進“兩型社會”。另外,實證研究表明,生產技術水平越高,二產比重越高,因資源節約帶來的工業SO2排放強度下降越明顯。環保投資越多,環保意識越強,因環境友好帶來的工業SO2排放強度下降越明顯。因此,現階段沒有一種因素既能促進資源節約效應的實現,又能強化環境友好效應的改善。生產技術較先進、第二產業比重較高的地區,適合通過資源節約效應實現“兩型社會”;環保投資越多、環保意識較強的地區,適合通過環境友好效應實現“兩型社會”。從時間跨度看,與“十五”相比,環境技術和環保意識的加強對“兩型社會”的建設與實現發揮了重要作用。另外,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在實現“兩型社會”的路徑上十分不平衡。東部地區主要依靠環境技術實現“兩型社會”,中部地區主要依靠環保投資實現“兩型社會”,而西部地區并沒有明顯的作用因素。
綜上,我國正在朝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邁進。各地區在實現“兩型社會”的路徑上存在一些差異,這些差異是由不同的環保投資、環境技術、生產技術、環保意識和產業結構決定的。因此,要想全面實現“兩型社會”,需要因地制宜,根據各地不同的產業稟賦和投資水平等因素,制定適用于當地的“兩型社會”實現路徑。
[1]簡新華,葉 林.論中國的“兩型社會”建設[J].學術月刊,2009,41(3):65-71.
[2]Zhang Z.Decoupling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 from Economic Growth:An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World Development,2000,28(4):739-752.
[3]Hamilton C,Turton H.Determinants of Emissions Growth in OECD Countries[J].Energy Policy,2002,30(1):63-71.
[4]李 荔,畢 軍,楊金田,等.我國二氧化硫排放強度地區差異分解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20(3):34-38.
[5]成艾華.技術進步,結構調整與中國工業減排——基于環境效應分解模型的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3):41-47.
[6]張平淡,朱 松,朱艷春.環保投資對中國SO2減排的影響——基于LMDI 的分解結果[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2(7):84-94.
[7]張平淡,何曉明.環境技術、環境規制與全過程管理——來自“十五”與“十一五”的比較[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即將發表.
[8]Sun J W.Changes i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Intensity:A Complete Decomposition Model[J].Energy economics,1998,20(1):85-100.
[9]張坤民.中國環境保護投資報告[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
[10]Lin Q H,Chen G Y,Du W C,etal.Spillover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t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J].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Engineering,2012,6(3):412-420.
[11]張平淡,朱 松,朱艷春.我國環保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126-133.
[12]申 萌,李凱杰,曲如曉.技術進步,經濟增長與二氧化碳排放:理論和經驗研究[J].世界經濟,2012(7):83-100.
[13]Laplante B,Rilstone P.Environmental Inspections and Emissions of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 Quebec[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6,31(1):19-36.
[14]Panayotou T.Demystify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Turning a Black Box Into a Policy Tool[J].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2(4):465-484.
[15]Lanjouw J O,Mody A.Innov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ve Technology[J].Research Policy,1996,25(4):549-571.
[16]Zhang P D.End-of-pipe or Process-integrated:Evidence from LMDI Decomposition of China's SO2Emission Density Reduction[J].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3,7:1-8.
[17]洪大用.我國公眾環境保護意識的調查與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1997(2):27-31.
[18]閆國東,康建成,謝小進,等.中國公眾環保意識的變化趨勢[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10):55-60.
[19]張平淡,朱 松,葛玉良.經濟結構調整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基于中國1985-2009年的實證分析[J].蘭州商學院學報,2012(5):5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