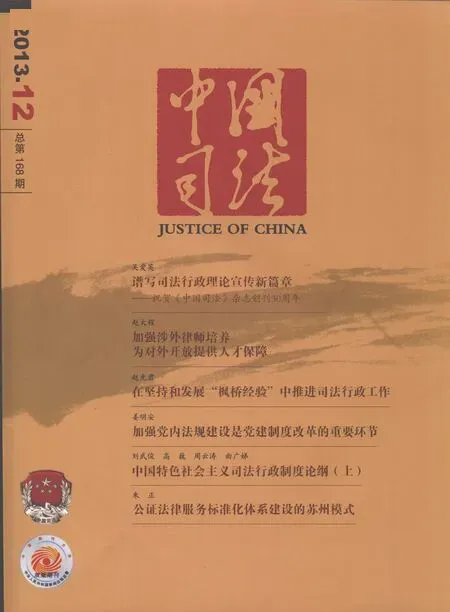試論對網絡誹謗的刑法治理
■陳 碧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
■孫穎菲 陳斐斐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
試論對網絡誹謗的刑法治理
■陳 碧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
■孫穎菲 陳斐斐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
隨著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的風生水起,互聯網大潮已席卷全球,我國也不例外。據統計,截至2012年6月底,我國已有5.38億網民。其中,手機網民為3.88億①數據引自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的《第3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網址:http://www.cnnic.net.cn/cnnicztxl/hlwtj15n/。。信息的傳播已不僅僅依靠傳統的報紙、雜志、電視臺等公共傳媒行業,動動手指,點擊“轉發”、“分享”,個人在互聯網上完全可以輕松成為信息的傳播者。人人都是媒體,人人都可以傳播,自媒體時代已經到來。誠然,言論自由、網絡空間開放,通過互聯網絡講講故事、曬曬心情、發發牢騷,無可厚非,不論原創或轉發,總能給自媒體的主體們激起點“小感覺”。然而,2013年以來,隨著網絡大謠“秦火火”、“立二拆四”、中石化“牛郎門”造謠者傅學勝被抓,讓眾多網民們認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網絡謠言無處不在、網絡誹謗就在身邊。如何在保障言論自由的前提下,有效地規范網民的網絡行為,成為政府、司法機關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刑法上關于網絡謠言入罪的條文,主要規定于第246條的誹謗罪和第221條的侵犯商譽罪。當然,個別內容特殊、后果嚴重的謠言還可適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等罪名。為遏制網絡謠言,凈化網絡空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9月出臺《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下稱“兩高《解釋》”),本文主要圍繞網絡謠言可能涉嫌的誹謗罪,著眼于從證據法角度解析誹謗罪名的成立。
一、網絡誹謗的入罪標準
我國《刑法》246條第1款規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眾所周知,誹謗罪通常情況下對社會的危害性較輕微,民法處理即可。只有在達到“情節嚴重”時,才應當按犯罪來處理。并且,此罪的最高量刑也僅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此罪如僅僅涉及個人,則屬于親告罪,如果沒有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通常情況下,如被害人不控告,司法機關也不主動追究。上述各方面都體現了刑法在此類行為追究上的謙抑態度。
通過網絡謠言構成的誹謗行為上,筆者認為,證明應主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主觀故意。通說觀點認為誹謗罪的主觀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并具有貶低、損壞他人人格、名譽的目的。這也應用于網絡誹謗。兩高《解釋》第一條規定中的“捏造”、“篡改”也印證了網絡誹謗的主觀方面應是直接故意。但是,在網絡誹謗案件中,構成誹謗罪的主觀是否只限于直接故意?有人認為,可以包括間接故意。因為造謠者對自己帖子的影響力是不能確定的,這種主觀故意在我國刑法理論上多認為是間接故意的典型形式之一②丁一覽:《網絡誹謗中名譽權的刑法保護——以網絡誹謗個案為考察對象》,《法制與社會》,2011年第2期。。對此觀點,筆者難以認同。對于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始作俑者、或者在網絡上散布誹謗信息的組織者、指使者,對于該信息將被點擊、瀏覽、轉發,將起到貶低、損壞他人人格、名譽的效果,在主觀上是持希望態度,而非僅僅為放任態度。對于不明事實真相,不加甄別、隨意轉發他人散布的虛假信息的自媒體“傳播者”,其主觀上才真正為“放任”,但卻不應是刑法打擊的對象。對犯罪主觀方面的把握必須嚴格,否則可能誤傷輿論。刑法是保護法益之法,但也應考慮網絡的特點。
(二)侵害對象。誹謗行為必須針對特定的自然人,既包括具體的指名道姓,也包括雖未具體指明被害人,但通過已知信息可以推知的特定人。如有的虛假信息中,為增加可信度,為實際不存在的被害人編造了真實的學校、工作單位,虛假信息通過網絡轉發后給真實的學校、工作單位造成極大影響。如,2010年的合肥“女教師誘奸門”網絡事件,發帖者編造安徽省合肥四十二中英語組女教師“孔菲艷”利用補課的機會,誘奸學校900名學生。而事實上,合肥四十二中根本沒有“孔菲艷”其人,但該網絡謠言卻給合肥四十二中造成極大負面影響③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063/11837204.html.。此類行為不宜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誹謗。這是因為,刑法并沒有規定單位可以成為誹謗罪的犯罪對象。盡管民法規定法人享有名譽權,捏造事實對單位的惡意攻擊確實可能導致單位名譽受損,但鑒于誹謗罪屬于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該罪保護的法益只能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不包括單位的相關權益。
(三)情節嚴重。有人指出,網絡謠言的傳播方式本身就是情節嚴重的表現,因為影響者眾,帖子如在天涯、新浪微博、百度貼吧等知名網站刊出,點擊、瀏覽、轉發極易以萬、十萬計,這和傳統的誹謗相比,情節絕對嚴重。兩高《解釋》也將情節嚴重明確到“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以上”,但這種觀點沒有考慮到,互聯網的信息更新速度相當快,人們對于信息的關注往往不具有持久性。雖然可以利用網絡鋪天蓋地散布對他人不利的言論。但當出現另外一個熱點問題,受眾眼球立即又轉向他處。并且自媒體天生的“自我糾錯”功能也能起到抵消效果。因此,筆者認為,不能僅僅從傳播方式和次數方面考量情節,而只有當侵犯行為造成他人名譽、人格的嚴重毀損,才可動用刑罰工具。美國法院曾經受理過某知名牧師狀告《好色客》雜志的案件,該雜志在一幅色情漫畫中直指原告牧師與母親亂倫,這是何等嚴重的一個誹謗!然而,法院認為,所有閱讀該雜志的讀者都只是一笑了之,誰也沒把這種事情當真。被告律師說,當年華盛頓總統何等神武,還被雜志丑化成一頭毛驢。而此案也無關格調,只關言論④Hustler Magazine V.Falwell,485 U.S.46,48,51-55(1988).。
(四)區別對待。謠言滋擾的個人,可以分成兩類,普通人和公眾人物。對于公共人物的刑法保護應該有所節制,在訴訟法上,應從證明程度上加大難度,體現對言論自由的保障。司法實踐中,已經體現出這一審慎態度。2010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文指出,不能把對個別領導干部的批評、指責乃至過激的言語當做誹謗犯罪來辦。這些規定都表明,我們的司法實踐中,對于被害人是公眾人物,尤其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誹謗案件,在證據規格和定罪標準上已經有了微妙的變化。如果不能證明網絡上的謠言行為、抹黑行為出于蓄意造假,那就應當推定該抹黑是正當的批評和善意的監督。
如此嚴格限制,主要原因是:名譽保護與言論自由的價值沖突,以及與刑法保護功能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后文將詳述之。
二、誹謗與言論自由之沖突:以美國誹謗罪發展為例
美國是一個深以言論自由為榮的社會。但令人意外的是,美國建國之后各州刑法中都存在刑事誹謗罪名。1962年,美國州法院還給誹謗罪下過一個很寬的定義:“任何刊出的文字只要有損被誹謗者的聲譽、職業、貿易或生意,或是指責其犯有可被起訴的罪行,或是使其受到公眾的蔑視,這些文字便構成了誹謗”⑤【美】安東尼·劉易斯著,何帆譯:《批評官員的尺度》,北京大學出版社。。按照這個解釋,很多批評行為都可能被判定為誹謗。
但從1964年的《紐約時報》訴警察局長沙利文案之后,美國司法系統在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的天平上明顯站在言論自由這一邊。目前在美國各州刑法中,僅在規范私人對私人名譽侵害的范疇內,刑事誹謗法依然有效。而對于公眾人物的名譽侵害,刑事誹謗法幾乎已經放棄作為了。他們的假設是,公共人物享有足夠資源在言論市場里為自己的名譽辯護,并不需要給予太多法律救濟的途徑。
以美國的誹謗去罪化進程為參照,筆者認為,我國司法界在處理網絡誹謗罪與非罪的界限時應當審慎。借助互聯網,網民通過自我組織成為主動向公眾發布信息的信息源,網絡得以成為公共事件的重要策源地。網民們的發言互動,構成了個體間特殊的“全民傳播”,這與Gregory Ulmer提出的“第五權”(The Fifth Estate)概念不謀而合⑥翁家若、徐玉紅:《自媒體時代的全民傳播現狀與輿論困境》,《天涯》,2011年4月。。在此種意義上,網民的自媒體言論權力應當得到保障。他們通過此種媒介表達對某一事件的訴求,對某一人物的評論,對某一事件的態度,無論言辭激烈粗鄙與否,只要并非以貶低、損壞他人人格、名譽為直接目的,只要不會帶來即時的明顯的危險,應當得到法律的保障。
如果在涉及到網絡謠言參與事件中,采取嚴格定罪的立場,很可能使得誹謗罪成為壓制言論的工具。在網絡誹謗案件中,刑法規則要兼顧秩序和自由這一刑法的兩大基本價值,同時也要兼顧網絡這一新生領域的特點和我國現階段政治民主的趨勢。刑法乃國之重器,應警惕成為公民言論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在以誹謗定罪之前,必須考慮民法是否足夠保護名譽權,而不用刑法越俎代庖。它包含了兩個假設:一是民事手段已經能夠提供有效的名譽保護;二是民事手段不像刑事手段那樣過度侵犯言論自由的邊界。如果民事法律能夠提供這樣的保護,刑法應慎用。
三、誹謗罪于證明責任的難題
(一)誰來承擔誹謗事實的舉證責任
誹謗的表現形式,主要體現為捏造或篡改事實,也就是虛構不符合真相或者并不存在的事實。只有假的事實才構成誹謗罪的事實,因此,此罪證明的重點之一就是證明虛假的事實是否成立。換言之,誹謗罪名之成立,關鍵不在于證明自己名譽是否被抹黑,而在于所言之事實是否存在。前者證明起來容易,而后者的證明是煞費苦心的。
在普通法傳統里,名譽侵權責任的成立,采取嚴格責任制。普通法的基本思維是,任何人的名譽,在被相反的事實證明之前,都享有法律保護⑦徐偉群:《論妨害名譽權的除罪化》,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在具體案件中,也就是說,被告只有自證陳述事實的真實性,才有可能脫罪。很明顯,普通法更傾向于保護誹謗案件的原告,至今英國仍在沿用這一傳統,因此被稱為“誹謗之都”,意思是在那里誹謗定罪太容易,一告一準。
普通法里把名譽侵害的舉證責任分配給被告,而有別于一般侵權法里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這實際上考慮了邏輯上的合理性,但未考慮對于言論的壓制后果。或者說,只考慮了技術,而未考慮價值取向。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把這個普通法原則顛倒過來,增加了證明的難度。其結果當然對于言論自由有利。原告負舉證責任問題到了刑事訴訟里面就更加明確,基于被告人權保護的要求,自訴人或公訴方負舉證責任的原則幾乎不可能動搖。而且不管被害人是公共或者非公共身份都同樣適用。并且刑事訴訟使用的證明標準明顯高于民事訴訟,因此對于原告的負擔加重。
于是,舉證責任問題會造成一種兩難處境:如果適用原告負擔舉證責任原則,可能造成過度壓縮名譽保護的不公平現象;如果適用被告負舉證責任原則,則我們不愿見到的有罪推定的惡果也可能真正發生。不僅如此,無論哪一種原則,都可能導致實質上的不公平待遇⑧徐偉群:《論妨害名譽權的除罪化》,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在這個角度上,我們有理由認為,名譽侵害行為應該盡量交給民事法來處理,而非刑法。
(二)故意內容如何證明
網絡謠言誹謗罪名的成立,要考察主觀故意是否為直接故意,并具有貶低、損壞他人人格、名譽的目的。故意內容的體現在于行為人明知自己是捏造、散布虛假事實誹謗他人,并且會造成他人人格、名譽受到嚴重損害的后果,卻希望這種結果發生。僅僅是“惡搞”,明顯地能使受眾感覺到“不可能”、 “不真實”,“娛樂而已”的虛假信息,沒有產生對他人人格、名譽的嚴重損害,即使被點擊、瀏覽五千次以上、或者轉發五百次以上,也不應認定為構成誹謗罪。針對普通人的網絡誹謗,如果行為人將虛假事實誤認為是真實事實加以擴散,也就是造勢,不構成誹謗。
在證明時應當注意:一定要區別事實和意見。故意散布的應當是不實事實,而非意見、評論。純粹的觀點評論,即使言語過激,一般認為是不受到誹謗罪的制裁的,即使有目的進行造勢傳播。
(三)公眾人物的名譽權如何保護
受網絡謠言滋擾的公共人物的名譽權,刑法的保護應該有所節制,在訴訟法上,應從證明程度上加大難度,體現對言論自由和網絡第五權的保障。
前文已述,無論是普通法系,還是大陸法系,都認為公眾人物的名譽權應該受到言論自由的限制。因此,對公眾人物的批評即使有不實言論,追究也應慎重。如果不能證明網絡上的造勢行為、抹黑行為出于對方的蓄意造假,那就應當推定批評和抹黑是正當和善意的。
涉及公眾人物的誹謗案件,必須由公眾人物自己提起告訴,同時由其證明對方明知所言不實,還罔顧真相地進行傳播,方有勝訴可能。由于自訴人身份的不同,證明的內容存在差異:作為公眾人物,證明誹謗者的故意內容包括:首先,事實不實;其次對方明知所言不實,仍然罔顧真相,懷有確實的惡意。
總之,刑事法律對于網絡謠言的打擊應當有所為,更應當有所不為。其行為雖惡,但言論自由的價值取向值得保護,而網絡謠言遠不值得妖魔化,其離“網絡黑社會”之實差距甚遠。即使對簿公堂,也可以用證據法加以區別對待,以平衡言論自由和名譽保護之間的緊張關系。
(責任編輯 張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