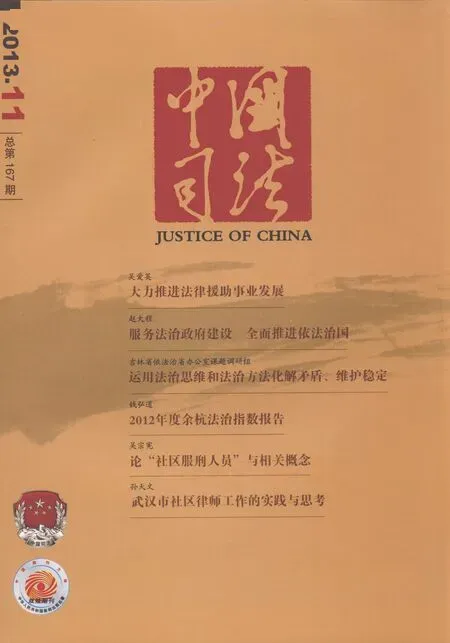鑒定意見爭議解決的基本思路
■郭 華(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
■劉榮志(遼寧省盤錦市興隆臺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科學技術盡管其本身是科學的,但在實際應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作為運用技術的鑒定人易受純科學領域專家思維的路徑依賴、傳統慣性和當下各種不相干因素的干擾,鑒定結果不再是或者不可能是完全科學可靠的。而訴訟活動尤其事實認定受“科學至上”以及科技應用司法實踐產生的效應的影響,致使作為證據的“鑒定錯了,裁判就會發生錯誤”①[法] 勒內·弗洛奧:《錯案》,趙淑美、張洪竹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 頁。,這種事實成為司法實踐難以避免、無法控制冤假錯案發生的絕對風險。這一肯定無疑的實踐性負面效應,在某種情況下還會因“鑒定對了”而司法鑒定制度或者程序機制不正當或者“失靈”導致選擇鑒定意見的判斷失誤。即使沒有上述問題的出現,其鑒定結果是可靠的,其選擇也是正確的,也有可能因采納鑒定意見作為證據的程序不公,誘發一些無實體價值的鑒定糾紛,致使當事人不斷尋求訴訟外非法律的途徑予以抗爭或者不惜付出沉重代價獲取有利于己鑒定意見,進而影響訴訟效率和司法權威。在存在不同鑒定意見時,這一作為“科學證據”的司法鑒定更會引發“案中案”,而這種案中案因染指科學技術的神秘與專家權威的盲從使原有案件處理起來更趨于復雜,司法鑒定的公信力因此而被折損以及鑒定人因不同鑒定結果的出現而權威漸漸式微。我國基于職權機關辦案工作需要在實踐中自然生成的司法鑒定制度因與現代訴訟制度、證據制度不斷發生碰撞與沖突,特別是屢屢遭遇訴權的質疑與正當性的追問,致使司法鑒定在現代訴訟活動中不斷穿梭于“重復鑒定”結果無價值的惡性循環之中,作為解決訴訟爭議的“證據之王”成為釀造新糾紛的“是非之王”,協助解決訴訟中專門性問題之利反而轉化為影響制約訴訟效率之障。在少數案件中,“打官司”成了“打鑒定”,有些案件因鑒定問題久拖不決,嚴重影響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影響了司法活動的公正與效率。如何解決鑒定意見的爭議以及何種解決思路更具有正當性、有效性是當前深化司法鑒定制度改革需要思考的問題,也是作為創新社會管理需要探索問題。
一、鑒定意見爭議亟待解決的基本訴求
司法判決具有權威不在于它們統帥著與科學家的共識相對應的律師們的共識,而在于它是從司法等級的上層傳達下來的。即使所有上下層法官意見都一致,他們的決定也比一致的科學判斷少一些內在的說服力,因為法官的方法比起科學家們的方法實在是太虛弱無力了②[美]波斯納:《法理學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 頁。。司法鑒定作為實現司法公正的技術性保障制度,其本身建構與安排的體系或者結構是否科學直接影響訴訟活動借此發現實體真實目標的實現,其運行機制的合理性也會影響科學技術或者專門知識保障訴訟發現真相功能的發揮,其結果蘊含的真理程度決定著案件事實認定的準確度并能夠增強裁判的說服力。然而,現代糾紛或者爭議的法律控制,基于有效性的考慮,無疑會選擇更多種類、更多形式以及多元化途徑的糾紛解決機制來對應不同類型、不同情況以及不同層次的紛爭,并促進法律在制度上更富有成效。200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作為未經試驗而直接從“紙面”轉化而來的法律盡管對司法鑒定體制的改革起到了積極推進作用,甚至被視為我國司法鑒定制度改革的里程碑,但從其實施以來的實際狀況看,其效果并不太顯著,不僅確立的統一司法鑒定管理體制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③參見2008年1月17日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進一步完善司法鑒定管理體制遴選國家級司法鑒定鑒定機構的意見》(政法[2008]2號)。該文件指出:“由于各有關方面對中央21 號文件和《決定》有關建立統一的司法鑒定管理體制精神理解差異,國家統一的司法鑒定管理體制尚未完全形成……”,而且改革前曾存在的需要統一司法鑒定體制解決的問題也未能得到有效解決,在訴訟實踐中相繼又出現了2007年廣西桂林“黎朝陽法官死因鑒定案”、2008年貴州甕安縣“李樹芬死因鑒定案”、2009年湖北界首“涂遠高死因鑒定案”等因鑒定引發的社會事件,以及2010年遼寧本溪南芬區公安局長謝志岡“死因鑒定案”、2011年湖北荊州紀檢干部謝亞新11 刀“自殺死”鑒定④在謝亞新事件新聞發布會上,政府通報:刀傷主要分布在頸部、胸部、腹部及左右手腕五個部位,其中致命傷胸部,鑒定為胸骨上窩處刺創致上腔靜脈破裂導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其損傷符合“自殺傷”的特征。家屬們對此提出了五點疑問,質疑“自殺說”。后因“家屬大鬧發布會”,原定2011年8月29日晚8 時的“謝業新死因新聞媒體發布會”被迫改到深夜11 點半召開。參見王婧:《11 刀“自殺”:一位紀檢官員的非正常死亡》,載《新世紀周刊》,2011年9月6日。等考驗司法鑒定制度的一系列有社會重大影響的案件或者社會事件。在這些案件或者事件中,人們對司法鑒定改革的渴望以及對《決定》解決鑒定“打架”的期待在實踐中漸漸演變為一種無奈,并因鑒定機構之間的利益爭斗而失去信心,因懷疑情緒的積累,導致期待的希望不斷向失望逃逸,鑒定視為科學的光環漸自暗淡,司法鑒定似乎步入了一個被不斷質疑與時時被挑戰的時代。
在現實中,不僅僅學者、職權機關以及社會公眾在鑒定制度改革前普遍指責的“重復鑒定”、“久鑒不決”等問題依然存在,同時在改革的過程中又衍生了對偵查機關在某些鑒定事項上的鑒定合法性的“質疑”,對司法行政部門管理的社會鑒定機構鑒定能力不足的“懷疑”以及對審判機關選擇性鑒定意見違反科學的“猜疑”。在實踐中還引發了當事人對鑒定意見不服而不斷要求或者啟動鑒定“難纏”的、更加復雜的問題,當事人因鑒定人對其提供的鑒定意見不利或者不符合職權機關的要求而恐嚇或者施壓鑒定機構或者鑒定人撤銷作出的鑒定意見的問題以及職權機關對不同鑒定意見難以選擇的遲疑不決的“難判”問題。偵查機關(主要是公安機關)因其受“不得面向社會接受鑒定業務”的限制,基于職權便利不斷對《決定》的限制鑒定的范圍予以開禁;司法行政部門沒有法律明確的“三類外”司法鑒定管理權卻實施對“三類”外鑒定事項的實質性管理;審判機關“抱怨”協助解決糾紛的鑒定意見卻成為需要處理的糾紛對象,“案外案”的衍生使得解決爭議鑒定意見的途徑不斷被行政化。如在死因鑒定中,不同的鑒定機構或者鑒定人對于同一尸體進行鑒定常得出不同或者相矛盾的鑒定意見。其中,在客觀上不乏存在一些因死因不明而鑒定人為了“臉面”人為安排結論的情況,或者死亡基于多種原因造成,在鑒定中僅僅說明一個原因又無法排除其他原因而得出的結論,死因鑒定成為鑒定意見爭議的主要問題。實踐中的這些困難與抱怨使得解決鑒定意見爭議成為司法鑒定制度改革不得不直面的課題。
二、社會對鑒定意見爭議解決的合理期待
由于我國鑒定體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刑事訴訟鑒定的主要事項上,其管理鑒定類別僅涉及職權機關的“法醫類、物證類及聲像資料” “三大類”鑒定事項,而實踐中存在的大量民事糾紛中需要鑒定的事項沒有納入管理范圍,致使在此領域內的鑒定存在較強的任意性或者出現管理的多元化,其規范性亟待解決,有些領域的鑒定也亟待規范。藝術品鑒定則是其中的例證。藝術品進行鑒定不僅有文物行政管理部門進行的,也有博物館實施的,還有拍賣公司自行評價的,甚至不乏個人以自己的知名度提供的。這種繁雜景象的背后不斷醞釀出藝術品鑒定的爭議與分歧,給糾紛的解決埋藏下一些隱患,并給訴訟增加了一些風險性因素。
然而,鑒定意見的爭議并非是孤立的個案,一些案件背后深藏著一些帶有普遍性問題,致使類似的問題不僅在我國長期存在,在國外亦是如此。如法國學者認為,“法官們常常為鑒定人之間的意見不一而不得不重新委托鑒定人,然而讓他們徹底放棄那些截然相反、互相矛盾的報告卻也是極少見的。⑤[法] 弗洛里奧:《錯案》,趙淑美、張洪竹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第205 頁。”德國學者認為,“雖然在法律上法庭不受鑒定結論的束縛,但是一些領域,尤其是自然科學,是如此的復雜和專業,法庭甚至不能完全地理解鑒定的理由,更不用說評價其可信度了。當幾個鑒定人提供了矛盾的鑒定意見時,這一困難就更加突出。目前還尚未找到有效解決這一難題的辦法。⑥[德] 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事訴訟程序》,岳禮玲、溫小潔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81 頁~182 頁。”也就是說,對于鑒定意見的爭議目前還沒有尋找到最佳的解決機制。因為一般人面對“截然相反、互相矛盾”的鑒定意見如何選擇,在專門知識欠缺的境況下如何保障其選擇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同并能獲得權威性且能夠有效地解決糾紛,的確是一件相對困難的事情。職權機關因負有查明事實真相的擔當而不能因判斷選擇上的困難而放棄應當履行的職責,也不能因為存在障礙而武斷地作出選擇。這就需要尋求能夠科學選擇鑒定意見爭議的思路與機制。如果鑒定意見選擇的不科學、不正當,不僅不能及時化解糾紛,還會影響裁判的權威,更會因解決鑒定意見爭議的武斷、專橫演變為惡性的“群體性事件”。如上述提到的“李樹芬死因鑒定案”,曾經造成甕安縣政府辦公大樓、縣公安局辦公大樓的100 余間辦公室被燒毀、砸壞,縣公安局戶政中心檔案資料全部被毀,還造成包括警車、摩托車在內的50 多輛車輛被燒毀,150 余人受傷。而2011年9月15日同仁醫院耳鼻咽喉科主任醫師徐文被王寶洺追砍21 刀,起因卻是訴至法院已有3年之久的醫療糾紛仍未結案,其根本原因則為醫院和患者提供了兩份不同的病歷導致醫療鑒定難以進行⑦參見劉珍妮、展明輝、陳博:《患者刀砍同仁醫生21 刀背后:訴訟3年無果》,載《新京報》2011年9月22日。。基于此,深化司法鑒定體制改革應當對上述實踐問題予以回應,尤其是職權機關借助于何種思路來解決這些鑒定意見爭議問題或者借助于何種長效機制來化解這些鑒定意見爭議,是鑒定制度深化改革理應積極探索的問題。
三、鑒定意見爭議解決的基本思路
在有些案件上,尤其在一些涉及前沿或者尖端科技的案件中,專家對案件事實認定具有高度的影響力甚至最終的決定力。“在證據法方面,否定從科學的新方法和新發展上獲得幫助是錯誤的。因而,允許專家就某一問題作證已經成為趨勢,除非該問題根本不涉及任何專業技術。⑧[英] 查理德·梅:《刑事證據》,王麗譯,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 頁。”從一定意義上說,案件的成敗勝負關鍵在于專家⑨參見楊良宜、楊大明:《國際商務游戲規則:英美證據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 頁。。這些問題如果能夠得到較好地解決,不僅可以減少實踐中的重復鑒定問題,提高訴訟效率,而且還有利于促進司法鑒定統一管理體制的完成,促進司法公正和樹立司法權威。在司法鑒定體制改革過程中,我國通過對鑒定機構國家資質評價和能力的評定,即遴選國家級司法鑒定機構來解決這些問題,2013年又通過了資質審核⑩2010年10月司法鑒定主管部門公布了10 家國家級鑒定機構,2013年國家級司法鑒定機構進行資質審核,認為10 家機構相關資質條件均符合《國家級司法鑒定機構評審標準》,同意繼續授予10 家機構“國家級司法鑒定機構”稱號。參見周斌:《十家國家級司法鑒定機構通過資質審核》,《法制日報》2013年9月4日。。這種機制盡管能夠解決一些不同鑒定意見的爭議,但因是以強鑒定能力的行政等級化的鑒定機構來解決的,不具長效機制的功能。“如果法院在制定新的正當程序方面得到了公眾的信賴,自己的決定也就獲得了極大的權威。?[日]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義與訴訟》,王亞新、劉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1 頁。”“為某一國人民而制定的法律,應該是非常適合于該國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竟能適合于另外一個國家的話,那只是非常湊巧的事”?[法]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6 頁。。
20世紀以來,科學失去了對其客觀性的確定感,甚至裂變為無以數計的次原則和次專家,以至于沒有人能夠輕易地說有關科學界是什么,更沒有人能夠說科學界是否已經“普遍認同”了某項技術或方法。這種發展使法官在面對眼前的證據并在相互對立的觀點之間作出判斷并說明其判斷的理由的任務變得復雜起來,鑒定人作為專家提供不同的鑒定意見更讓人困惑與揪心。因此,探索解決鑒定意見爭議的解決思路,旨在從中發現一些帶有共性和規律性的問題,借助于合理、科學的鑒定意見爭議解決機制來實現司法鑒定制度改革上的機制創新,為司法鑒定意見爭議尋求適合我國國情的解決途徑,并為深化司法鑒定制度改革提供建設性方案,并希冀“所設計的制度能夠通過持續地實現規制目標來不斷地增加自身的合法性”?Stephen Breyer,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Toward Effetive Risk Regulation,Harvand Press ,1993,p11.,不斷增加選擇的鑒定意見具有科學性與可操作性。我們認為,目前解決鑒定意見爭議的基本思路可設計為:
(一)鑒定意見爭議解決的重新鑒定
在通常情況下,當事人(控辯)雙方主要是對自己利益發生影響的鑒定意見提出異議而引發的爭議。職權機關或者辦案人員因自己缺乏專門知識,直面鑒定意見爭議時常因無法選擇而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境。“一方面要間接思考鑒定人的專業知識、中立性、獨立性等問題;另一方面又要直接對鑒定意見的內容進行證據評價,且最大限度地利用健全的常識進行全面評價,實施一般人能夠接受、專家可以認同的事實認定工作。?[日] 小島武司:《民事審理中的公鑒定與私鑒定——第三種證明模式之提倡》,載陳剛主編:《自律型社會與正義的綜合體系》,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 頁。”如果借助于職權作出強硬的處理,必然會激發當事人以及作為專家的鑒定人對職權機關的指責,從而使鑒定意見的爭議愈演愈烈。為了避免上述被動局面的出現,根據鑒定意見作為證據具有可替代性的特征,法律借助于回流程序將鑒定意見爭議“重返”鑒定人來解決,形成了立法上的重新鑒定解決鑒定意見爭議的制度?我國三大訴訟法對于重新鑒定的條件沒有規定,體現了寬容性,僅在程序上有些簡單的規定。相關司法解釋和規定中存在一些限制。如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207 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7 條,以及《公安機關辦理刑事程序規定》等。。
重新鑒定作為解決鑒定意見爭議的機制本身具有正當性。因為正確的鑒定意見只有一個,同一案件中的同一個專門性問題出現了不同的甚至截然對立的鑒定意見,只能說明鑒定發生了偏差,通過重新鑒定獲得正確的鑒定意見是對鑒定作為科學的尊重,以至于各國鑒定制度無一例外地規定了重新鑒定作為解決鑒定爭議的重要制度。然而,盡管專門性問題由具有專門知識的人來解決符合一般人的慣常性思維,但對這種做法的過分追求在實踐上極易造成“重新鑒定”不斷發生,在一定程度上還會誘發辦案人員或者當事人重新鑒定的欲望,借助于重新鑒定反復探求事實真相,解決鑒定意見爭議的機制成為激發爭議的因素,重新鑒定逐漸演變為“重復鑒定”,職權機關與當事人在重新鑒定的路徑上越陷越深而無法自拔。在鑒定制度和訴訟制度改革中需要限定重新鑒定的條件和程序,保持重新鑒定符合糾正鑒定存在瑕疵或者錯誤的制度本質。不宜簡單地限定鑒定的次數,否則,設置的條件就有可能成為誘發鑒定無休止的原因,從而促發鑒定意見爭議的加劇或者升級,致使形成重新鑒定逐漸從地方到中央所在地的行政化層級解決的機制。
(二)鑒定意見爭議的法庭質證
當事人(控辯)雙方或者一方對鑒定意見存有爭議,對于爭議的鑒定意見應當通過法庭質證程序來解決,借助于質證程序吸收或者消解鑒定意見爭議。這是訴訟法學理論界的基本觀點,也是訴訟活動中解決鑒定意見爭議較為理想的模式。
在這種機制中,法院通知鑒定人出庭作證,接受當事人(控辯)雙方對爭議鑒定意見的質疑、詰問。然后,通過當事人程序權利的充分行使,最終在法庭上解決當事人之間的鑒定意見爭議。在實踐中,由于涉及鑒定意見的案件不同于普通案件,當事人的普通常識與一般經驗難以完成對爭議鑒定意見的質證任務。為了保障當事人質證鑒定意見的有效性,法律增加了當事人聘請專家輔助人作為訴訟參與人來協助當事人質疑鑒定人的內容。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將此作為一項新制度規定在第192 條中,即“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申請法庭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2012年修改的《民事訴訟法》第79 條規定:“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或者專業問題提出意見。”特別是在一些知識產權、反壟斷案件中,職權機關增加了專家陪審員作為審判組織成員參與涉及專門性問題的審判活動。但對專家陪審制度需要一定的限制,以免在實踐中庭審活動成為專家的“科學技術研討會”,因作為專家在法庭的不斷爭議誘發審判偏離其應然的中心,法官、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專業知識阻隔不斷被放逐于法庭質證之外,成為一個無助的“執行人員”或者“執行機關”,造成事實認定結果出現偏差而使訴訟遠離公正。
“如果我們的法律遇到涉及其他學科和專業的問題,我們通常求助于有關學科或專業人員幫助,這是我們的法律應受尊重和值得贊賞的一面。因此,看來我們不僅尊敬我們自己的學科,也尊重其他學科。同時,我們認可、鼓勵其他的學科或專業成為值得贊賞的事物。”那么,如何保障“求助于有關學科或專業人員幫助”成為具有法治意義的有效機制,并能使其符合、滿足司法制度現代化、文明化的需要是解決鑒定意見爭議需要研究的問題。然而,“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有時夸大、甚至迷信科學解決我們社會問題和科學將我們從邪惡中拯救出來的能力。近年來的經驗警告我們,科學證據可能是誤判潛在的原因。?[英] 麥高偉、杰弗里·威爾遜主編:《英國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233 頁。”
(三)鑒定意見疑難判斷的選擇路徑
同一案件的專門性問題存在多個不同鑒定意見在鑒定實踐中是無法避免的,甚至同一專門性問題存在多個不同鑒定意見也是無法回避的,究竟哪一個鑒定意見更科學、準確,人們無法認識或者認為不同的鑒定意見均有道理,無法確定孰對孰錯的時候,認識論無法對爭議鑒定意見作出真假判斷,需要走出認識論進入價值論的考量,從價值上作出判斷。對經過鑒定后存在多個不同鑒定意見或者在爭議鑒定意見難以再次進行鑒定或再次進行鑒定無意義且專家也存在分歧的情況下,在鑒定意見選擇適用不影響定性的范圍內應當從更有利于保障權利人的合法利益出發作出選擇。
1、在刑事訴訟中,對鑒定意見爭議無法作出選擇時,應當遵循“當事實或證據存在疑問作出有利于被告一方的解釋和處理”的規則,對于不同鑒定意見難以判斷孰對孰錯時,應當采用有利于被告的鑒定意見,充分體現“保障人權”的價值訴求。如對于被告人存在輕傷和重傷兩種鑒定意見,且相互之間難以分清哪一個更可靠或者更可信時,應當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作出選擇,選擇屬于輕傷鑒定意見。
2、民事訴訟按照有利于權利人的原則選擇。民事訴訟的專門性問題雖然經過鑒定,因鑒定意見存在爭議法官仍不能對鑒定意見作出選擇,則選擇有利于權利人的鑒定意見作為定案根據。如在傷殘鑒定中,存在不同等級的鑒定結果,在無法確定不同傷殘等級的鑒定意見哪一個更為科學、準確時,因一方的鑒定意見難以絕對地駁倒另一方的鑒定意見,應當根據能夠使權利人受到充分的保障以及平衡當事人的利益出發,選擇有利于權利人傷殘等級鑒定意見。這種選擇屬于一種價值判斷,而非是對爭議鑒定意見可靠性的衡量,絕不能以后來驗證的錯誤來否定這種選擇原則的價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