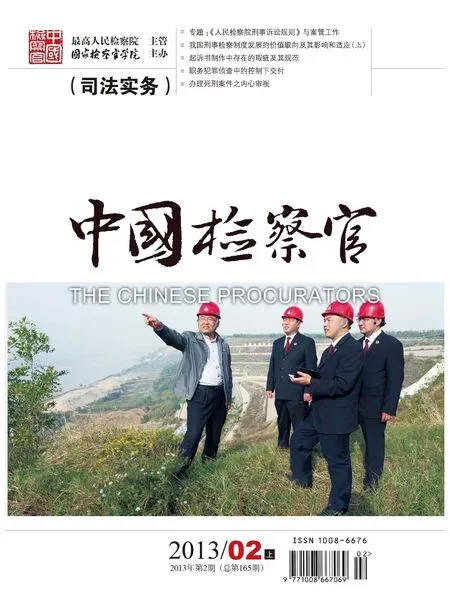論我國親屬容隱權(quán)的建構(gòu)——以修訂后《刑事訴訟法》為視角
文◎上官馨
我國著名社會學(xué)家瞿同祖先生曾指出:“古代法律可以說全為儒家的倫理觀念和禮教所支配。”[1]臺灣學(xué)者李鐘聲也說:“我國的法律制度本于人倫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體系,所以是倫理的法律制度。”[2]可見,我國的傳統(tǒng)法律一向特別注重對親情倫理的維護,然而在我國現(xiàn)行法律中卻難以找到一條旨在維護親情倫理的法律條文。我國《刑法》第310條規(guī)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48條也規(guī)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wù)。”由此可見,當我們的親人實施犯罪行為之后,我們只能選擇大義滅親。
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88條規(guī)定,“經(jīng)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該條規(guī)定免除了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強制到庭的義務(wù),這吸收了我國傳統(tǒng)的親親相隱制度,使得法律更為人性化,也維護了社會基本道德倫理關(guān)系,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shè)。
一、我國親屬容隱權(quán)的現(xiàn)狀
我國《刑法》第67條第1款規(guī)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由此確立了自首成立的兩個要件,一是自動投案;二是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guān)發(fā)覺,或者雖被發(fā)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guān)、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然而,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1款第三項規(guī)定:“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動,而是經(jīng)親友規(guī)勸、陪同投案的;公安機關(guān)通知犯罪嫌疑人的親友,或者親友主動報案后,將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應(yīng)當視為自動投案。”自首制度的目的在于感召犯罪嫌疑人主動投案和鼓勵更多的犯罪嫌疑人的家長、親友促使犯罪嫌疑人歸案。與自首制度立法目的相悖。該解釋看似與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相悖,卻仍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貫徹落實下來。
這其中的吊詭之處在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提供了這樣一種先損后補的模式:先違反“親親相隱”制度,以求快速有效地將犯罪嫌疑人抓捕歸案,然后再對其進行補償。也即是說:法律先強迫犯罪嫌疑人的親屬實施大義滅親行為,協(xié)助公安司法機關(guān)抓捕犯罪嫌疑人,然后再給予其量刑減讓的好處。從親情倫理的視角分析,我國法律割裂了植根于骨髓的親情倫理關(guān)系,因此法律需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將割裂了的親情倫理關(guān)系予以修復(fù)。先損后補的模式就這樣應(yīng)運而生,并在實施過程中產(chǎn)生了這樣一種親情倫理效應(yīng):被告人在實施犯罪行為之后,因害怕法律的制裁而東躲西藏,整日提心吊膽,憂心忡忡。被告人的親屬眼見其過著如此痛苦逃亡的生活,恨不能早日將其解救。正值此時,被告人的親屬看見了法律提供的“在大義滅親后的量刑減讓”,于是懷著拯救被告人早日脫離苦海之初衷,狠下心來實施了大義滅親行為。被告人的親屬為了使被告人早日結(jié)束逃亡生活、為了減輕被告人的刑罰、為了讓被告人早日回歸到溫馨的親情之中過上幸福的生活,不惜背負“大義滅親”的道德惡名,真可謂用心良苦。簡言之,被告人的親屬正是為了維護親情倫理,才實施了“大義滅親”這一不道德行為。
綜上所述,我國法律先強迫被告人的親屬實施大義滅親行為,然后再創(chuàng)造出“先損后補”的模式來對大義滅親行為進行變相買單。然而,先損后補模式所帶來的是對我國法制統(tǒng)一的破壞,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在法律適用上的混亂。由此看來,如此大費周折所創(chuàng)造的先損后補模式所帶來的負面作用,可謂“代價不菲”。怎樣才能既維護植根人們于骨髓的親情倫理又能有效的打擊犯罪活動成為法學(xué)界的一個=研究課題。筆者認為我國應(yīng)該借鑒“親親相隱”制度在立法上完善親屬容隱權(quán),賦予一定范圍內(nèi)的親屬相互隱匿犯罪的權(quán)利。
二、親屬容隱權(quán)的比較法考察
縱觀人類社會法律發(fā)展的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親親相隱并非中國古代法律獨有的現(xiàn)象,而是帶有相當程度的普遍性。正如著名的法史學(xué)家范忠信教授所說的那樣:“事實上,從古代到現(xiàn)代,從東方到西方,從奴隸制法、封建制法到資本主義法甚至社會主義法,都存在著‘親親相隱’之類的規(guī)定。”[3]
(一)大陸法系中的親屬容隱權(quán)
早在古羅馬的法律中就曾規(guī)定:親屬之間不得互相告發(fā),對于未經(jīng)特別許可而控告父親或保護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對他提起刑事訴訟;親屬間相互告發(fā)將喪失繼承權(quán),也不得令親屬作證。[4]《法國刑法典》第434條之一、之六規(guī)定: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直系親屬、兄弟姐妹及他們配偶、配偶或者眾所周知同其姘居的人,知其犯重罪不予告發(fā)或為窩藏、包庇的不處罰。[5]德國《刑事訴訟法》第55條規(guī)定:“每個證人均可以對如果回答后有可能給自己及其親屬造成因為犯罪行為、違反秩序行為而受到追訴危險的那些問題拒絕回答”;《德國刑法典》第258條(使刑罰無效)規(guī)定:“一、故意使他人因犯罪行為依法應(yīng)受的刑罰或保安處分 (第11條第1款第八項)全部或部分無效的,處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六、為使家屬免于刑罰處罰而為上述行為的,不處罰。”[6]
(二)英美法系中的親屬容隱權(quán)
英美法系同樣認可親屬享有藏匿、包庇、拒證特權(quán)。在英美刑法、刑訴法中,親屬的例外特權(quán)規(guī)定主要有:親屬間相盜不能控告,尤其不許夫妻間互相指控盜竊;夫妻間相互藏匿犯罪不罰;夫妻一般不得互相證明對方有罪。不過,與大陸法系相比,其立法宗旨似乎更專注于維護夫妻雙方構(gòu)成的核心家庭利益,更凸顯其個人權(quán)利觀念,因而享有這種特免權(quán)的親屬范圍小了許多,通常除了配偶,其他近親屬都被排除在外。[7]英國1898年《刑事證據(jù)法》規(guī)定:在一般刑事案件中,作為被告的丈夫或妻子僅可以充當辯護證人,并只能根據(jù)被告方的申請,即不得強迫作證,不得充當控訴證人。但在夫妻間互相傷害及傷害子女等案中例外。[8]英國刑法規(guī)定:出于親密關(guān)系而隱瞞他人犯罪者不罰,但若接受了報酬就應(yīng)罰。[9]《印度刑法典》第212條規(guī)定:“無論任何人,明知或有理由相信他人實施了犯罪,為掩護他逃避法律制裁而窩藏或隱匿:如果該人所犯罪是應(yīng)處以死刑的,處可達五年的監(jiān)禁,并處罰金……本條不適用于窩藏或隱匿丈夫或妻子的案件。”[10]
(三)日本、韓國、臺灣地區(qū)的親屬容隱權(quán)
《日本刑法典》第七章“藏匿犯人和隱滅證據(jù)罪”第105條規(guī)定:“犯人或者脫逃人的親屬,為了犯人或者脫逃人的利益而犯前兩條之罪(藏匿犯人罪和隱滅證據(jù)罪)的,可以免除刑罰。 ”[11]《韓國刑法典》第 151 條(窩藏犯人、親屬間的特例)規(guī)定:“(一)窩藏犯有應(yīng)處罰金以上刑罰之罪的犯人,或者協(xié)助其脫逃的,處三年以下勞役或者六十萬元以下罰金。(二)親屬、戶主或者同居家屬為人犯而犯前項之罪的,不予處罰。”第155條(湮滅證據(jù)、親屬間的特例):“(四)親屬、戶主或者同居家屬為人犯而犯本條之罪的,不予處罰。”[12]我國臺灣地區(qū)的現(xiàn)行刑法典第162條第五項規(guī)定:“配偶、五親等內(nèi)血親或三親等內(nèi)姻親犯第一項之便利脫逃罪者,得減輕其刑。”第167條(親屬間藏匿或頂替人犯罪)規(guī)定:“配偶、五親等內(nèi)之血親或三親等內(nèi)之姻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或第165條之罪(即犯藏匿或頂替人犯罪、湮滅刑事證據(jù)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三、我國親屬容隱權(quán)的建構(gòu)
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60條規(guī)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wù)。”第188條規(guī)定,“經(jīng)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從規(guī)定來看,其并沒有免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作證的義務(wù),只是規(guī)定在庭審階段可以免予強制到庭。盡管把在古代倫理法中占有極為重要地位的親親相隱制度有保留的加入,體現(xiàn)了我國刑事領(lǐng)域立法上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的進步,但是與臺灣地區(qū)和西方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涉及親屬容隱權(quán)的內(nèi)容還是很少的,是初步的和有限的。立法者應(yīng)該借鑒歷史傳統(tǒng)和境外經(jīng)驗的合理內(nèi)核,順應(yīng)新時期社會法律發(fā)展的趨勢,構(gòu)建符合國情的親屬容隱權(quán)制度。
親屬容隱權(quán)要求國家法律對親屬間的容隱行為作出一定范圍的豁免。此時所呈現(xiàn)出的是國家司法權(quán)與親屬容隱權(quán)之間的一種此消彼長之態(tài)勢。如果親屬容隱權(quán)過大,必然會影響國家司法權(quán)的行駛;如果親屬容隱權(quán)的范圍過小,又難以有效的維護親屬間的親情倫理關(guān)系。因此,在制度設(shè)計時,如何確定容隱權(quán)的范圍是本制度成敗之關(guān)鍵。根據(jù)容隱行為對國家司法權(quán)之侵害程度和容隱行為對親情倫理關(guān)系之維護力度,筆者認為應(yīng)當將容隱行為區(qū)分為積極的容隱行為和消極的容隱行為。并照此分類體系分別進行立法構(gòu)想。積極的容隱行為所具有的主觀惡性較大,對國家司法權(quán)之侵害也相對較大,故而應(yīng)當適當?shù)貒栏裣拗疲欢麡O的容隱行為所具有的主觀惡性較小,對國家司法權(quán)之侵害也相對較小,故而應(yīng)當適當?shù)胤艑捪拗啤?/p>
(一)積極的容隱行為
首先,積極容隱行為主要包括幫助犯罪分子逃脫法律懲罰的偽證、包庇、窩藏、窩贓、銷贓等行為;在國家公安司法機關(guān)采取強制措施后或者在刑罰執(zhí)行期間,幫助犯罪分子逃避監(jiān)管等各種行為。其次,明確享有容隱權(quán)的親屬范圍。如果像臺灣地區(qū)規(guī)定的“配偶、五親等內(nèi)血親或三親等內(nèi)姻親”那樣寬泛,則會過度影響國家司法權(quán)的行使,不利于刑事案件的偵查和打擊犯罪,可能導(dǎo)致社會治安惡化,更不利于社會穩(wěn)定。如果像英國和美國那樣把享有容隱權(quán)的主要范圍控制在配偶之間,又和我國固有的親情倫理觀念嚴重不符。在確定享有容隱權(quán)的親屬范圍時應(yīng)當考慮到我國的具體國情。具體說來,我國現(xiàn)階段的刑事司法資源相對有限,刑事偵查技術(shù)、刑事偵查設(shè)備以及刑事偵查手段還相對落后,一言以蔽之,我國現(xiàn)階段的刑事偵查能力仍然處于相對較弱的狀況。因此享有容隱權(quán)的親屬范圍應(yīng)限制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最后,確立對實施積極容隱行為者的刑罰。總的來說對實施積極容隱行為的親屬應(yīng)當減輕或免除處罰。應(yīng)當強調(diào)的是實施積極容隱行為的親屬在主觀上具有阻礙國家司法權(quán)之故意,并且隨著訴訟階段的不斷前進,其主觀故意之程度逐漸加深,因而應(yīng)當在各個訴訟階段實施逐漸加強之刑罰。比如在立案前實施了積極容隱行為的,應(yīng)當免除處罰;在刑罰執(zhí)行階段實施積極容隱行為的,只應(yīng)當減輕處罰。
(二)消極的容隱行為
首先,消極容隱行為主要指在犯罪行為發(fā)生時或發(fā)生后知情不舉和拒絕作證權(quán);其次,明確享有容隱權(quán)的親屬范圍。鑒于消極容隱行為的主觀惡性較小以及對國家行駛司法權(quán)之危害程度不大,因此其范圍應(yīng)當較為寬泛。具體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監(jiān)護人與被監(jiān)護人;最后,確立對實施消極容隱行為者的刑罰。筆者認為不應(yīng)當免除其作證義務(wù),但應(yīng)當對其免除處罰,如此便能保留其主動自愿作證之可能性。
(三)對容隱權(quán)的必要限制
即便在唐律中也并非所有的犯罪都可以相容隱,凡犯謀反、謀大逆、謀叛這些直接對抗于統(tǒng)治階級的大罪不得相隱。可見,我國古代先賢早就意識到一些嚴重危害國家利益的犯罪是不能相隱的。況且,據(jù)中國社科院發(fā)布的2010年《法治藍皮書》顯示,2009年中國犯罪數(shù)量打破了2000年以來一直保持的平穩(wěn)態(tài)勢,出現(xiàn)大幅增長,其中,暴力犯罪、財產(chǎn)犯罪等案件大量增加,并且據(jù)藍皮書預(yù)測,2010年中國的社會治安形勢仍然會比較嚴峻。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如果我們不對親屬容隱權(quán)作出限制,勢必會影響我國的社會治安,甚至會影響社會的穩(wěn)定。因此,借鑒古人之智慧,對于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重大利益的犯罪如恐怖犯罪、毒品犯罪以及黑社會性質(zhì)的犯罪,應(yīng)當排除親屬容隱權(quán)之適用。
注釋:
[1]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版,第326頁。
[2]耘耕:《儒家倫理法批判》,載法苑精萃編輯委員會編的《中國法史學(xué)精萃》(2002年卷),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頁。
[3]范忠信:《中西法律傳統(tǒng)中的親親相隱》,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1997年第3期。
[4]查士丁尼:《法學(xué)總論》,商務(wù)印書館 1997年版,第209頁。
[5]羅結(jié)珍譯:《法國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1995年版,第169頁。
[6]徐久生,莊敬華譯:《德國刑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頁。
[7]黃風譯:《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8][英]塞西爾·特納.肯尼:《刑法原理》,王國慶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71頁。
[9][英]魯伯特·克羅斯:《英國刑法導(dǎo)論》,樓杰科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頁。
[10]趙炳壽等譯:《印度刑法典》,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頁。
[11]張明楷譯:《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第42頁。
[12]金永哲譯:《韓國刑法典及單行刑法》,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