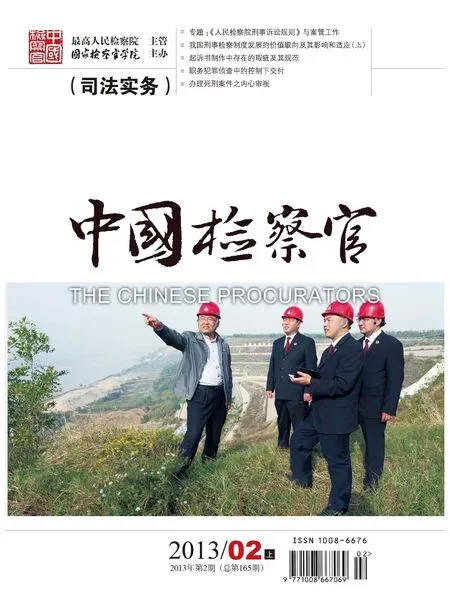基層檢察院開展民事審判活動違法檢察監督的困境和出路
文◎侯華生 陳彩琴 劉星寬
20 11年3月,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出臺了《關于對民事審判活動與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的若干意見(試行)》規定,對檢察機關糾正法院審判活動違法行為提供了依據,試圖嘗試從制度層面解決對審判活動監督難的問題。但是在實踐中,法院能否接受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意見,檢察機關開展審判活動檢察監督工作中自身存在的問題,基層檢察院與基層法院之間在某種關系上的協調與對立,縣級人大常委會、縣級政法委對審判活動檢察監督的認識和支持程度,上級檢察院對基層檢察院民事審判檢察監督之間的指導關系等等問題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直接影響到基層檢察院對同級法院審判活動的監督效果。
一、基層檢察院民事審判活動檢察監督存在的困境
基層檢察院目前在民事審判活動檢察監督中存在的困境主要表現在:
第一,由民事抗訴的對事監督轉變為兼對人監督,民事檢察部門與法院和法官的對立情緒潛在增長,原來的協調關系有所緊張。與民事抗訴案件的檢察監督不同,在以往的民事檢察工作中,民事檢察監督是對事不對人,檢察機關與法院之間就案論案,法院糾正錯誤裁判一般也是對案件進行糾錯,很少涉及到具體承辦法官。而民事審判違法監督直接的對象是具體法官的司法行為,直接牽涉到法官的個人利害關系,基于法院對外形象和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考評以及法官自身的聲譽,原來逐步達成融合的協調配合、相互監督關系發生了潛在微妙的變化。
第二,民事檢察監督缺乏監督的具體情形,直接影響到民事檢察部門對民事審判活動違法行為的檢察監督力度。
第三,民事檢察考評工作機制,導致基層檢察院民事檢察工作陷入困境。在不少檢察院對基層檢察院的考評指標都是追求數量最大化,考評數量上不封頂,甚至對排在后幾名的基層檢察院還要進行指名點評,并要求基層檢察院領導在一定級別范圍的會議上 “說明情況”,這些考評規則實際上忽視了案件質量。基層檢察院一方面受到考評壓力,另一方面受到案源壓力,難免會造成事無巨細地指責法院審判活動違法,引起法院的反感,使民事檢察監督難以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以往工作中法院指責檢察機關民事抗訴案件質量不高,對檢察機關民事抗訴工作多有微詞,也多是因考評機制上雖然要求案件質量數量并重,但實際考評的仍是案件數量所致。
第四,缺乏與民事審判活動違法相應的民事檢察監督措施,制約了民事審判活動違法行為檢察監督工作。這種情形主要表現在:
一是民事審判活動違法行為檢察監督與法院內部紀檢監察監督相沖突,為法院尋找了借口。一旦法院對檢察機關的民事檢察意見或者檢察建議不予回復,基層檢察院沒有制約措施。孫家瑞認為,在對事的查控程序中,現行法律只規定了檢察機關對生效裁判的抗訴;對于其他違法行為,例如審判過程中的個案違法行為,多個案件中反映出來的同類違法行為,工作制度和方法中違法或可能導致違法的問題,現行法律都沒有規定相應的監督措施。最高法院出臺了一系列規定對法官的違紀違法行為進行制裁,加強了法院內部對法官違法行為的監督與制裁,檢察機關的監督缺乏制裁的法律依據。二是法院對接部門不明確,糾正違法意見書或者檢察建議書送達存在障礙。由于檢察機關提出糾正審判活動違法的情形不同,文書送達的對象也不同,但檢察機關對法院民事審判活動違法行為監督的糾正違法意見書或者檢察建議書均以機關名義對法院制作,實際工作中,直接由院長在送達文書回證上簽收很不現實,辦公室、政治處、紀檢監察等部門往往相互推諉,審判監督庭、立案庭同樣對此類文書辦理無依據,直接送達相關業務庭也多有不當。三是調查程序欠缺,檢察建議或者糾正違法意見存在程序性問題。關于對違法事實的認定在沒有對被調查人員詢問,聽取被調查人員的辯解的情況下,即確認違法事實不符合相關程序,實際上存在確認程序不符合類似的違法案件調查程序規定,因而提出的糾正違法意見本身就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如果對發現的問題進行調查核實,又缺乏調查程序的規定,因而,實踐中對發現的問題往往是對法院提出建議,要求法院進一步核實并根據核實的情況進行處理。這種做法削弱了檢察建議或者糾正違法意見的力度。
二、產生困境的原因分析
第一,基層檢察機關對探索創新的概念理解混亂,實踐中存在隨意擴大法律監督權現象,引起一些不良反應。近些年來,檢察機關在相應具體監督措施不到位的情況下,一直強調民事檢察部門與法院的協調與探索,引起法院對諸如檢察機關以原告身份提起公益訴訟、對調解書抗訴、督促起訴、支持起訴等等一些問題上的排斥,再加上對審判活動違法行為的懲處缺乏明確的機構,往往最終是建議法院自我糾正,實踐中造成法院不同程度地對審判活動違法行為檢察監督的漠視等等。
第二,民事檢察追求考評名次的慣性壓力,助推了基層法院的對抗情緒。盡管早在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就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但是一直到現在民事訴訟檢察監督仍是在爭論之中。近些年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進展,法院雖然對民事訴訟檢察監督有所認識,但是思想上的抵觸情緒仍然在不同地區不同程度地存在。表現明顯的是法院借檢察機關內部對民事抗訴案件數量和抗訴案件改變率的考評,相互牽制,不配合民事審判違法行為的監督。
第三,基層檢察院民事抗訴案件少、社會影響不大,影響了人員配置和素質的提高。由于基層法院案件管轄受到案件標的額的限制,社會影響大的案件往往在法院得到了很好地處理,一些細小瑣碎的案件檢察監督社會影響度難以提高,在檢察機關內部,在人員編制緊張的情況下民事檢察部門比較弱化,人員不是“走馬燈”似的,就是如“死水”一般,“誰不行到民行”成為機關內部人才分配的潛流。
第四,檢察機關缺乏對民事檢察工作法理層面的深層次挖掘與研究,對民事檢察監督的定位存在爭議。比如,檢察機關自2001年出臺了《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以后,明確把檢察機關對民事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工作置之于“當事人意思自治”的民事活動規則大框架內,即使規定了檢察機關對“自行發現”的錯誤裁判案件進行抗訴,但實際工作中往往也受到自身的非議。有的地方還把此類案件限定在“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范疇之內,這些意見的根源就在于混淆了“法律監督活動”與民事活動的概念。民事審判程序的保護方法是權利救濟,民事檢察程序的保護方法是查控違法;保護權利方式的不同,正是民事審判權與民事檢察權的差別所在。有的地方檢察機關不考慮自身地位,片面迎合法院,在法院拖延審理抗訴案件時,法院總是以抗訴案件對方當事人的現住地址及聯系方式不清,不能送達法律文書為借口,檢察機關不是對法院此種行為進行法律監督,而是下文要求下級檢察機關必須為法院提供雙方當事人的現住址和通訊方式,檢察機關任由法院擺布,甘居當事人地位。這些問題反映了檢察機關對民事檢察監督的認識定位問題。這種認識導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諸如,對發現民事裁判確有錯誤,沒有當事人申訴的情況下檢察機關能否提出抗訴問題;法院對確有錯誤的裁判不采納抗訴理由拒不糾正的是否再提出抗訴問題,等等。曹建明檢察長在全國檢察機關第二次民事行政檢察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民行檢察通過對公權力的監督,間接具有權利救濟的作用。”人民檢察院通過受理申訴、控告、檢舉或者通過其他途徑,發現審判活動違法的,均應采取措施調查處理,追究違法人員的責任,糾正違法行為的錯誤,不得以任何借口 (例如無人申訴)逃避職責。如果提高到這一層面認識民事檢察監督,民事檢察監督工作將會有一個新天地。去年,河南省檢察院制定了《民事行政檢察調查辦法》很有見地,但是還要上升到發生法律效力層面,否則,檢察機關的民事檢察調查權還可能在某些案件上發生爭議,甚至是非議。
三、開展審判活動違法檢察監督的出路
第一,端正對民事檢察監督的定位認識。民事檢察監督是檢察機關對法院民事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這是民事訴訟法對民事檢察監督的定位。關鍵是如何理解這一定位,從法律規定上理解,是一種公權力對公權力的監督,不是公權力對私權利的監督或者救濟。有人認為民事檢察是檢察機關為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對民事活動的一種國家干預。這種說法明顯把權利救濟的間接功能誤為直接功能,就是把民事檢察程序混同于民事審判程序,把民事檢察權混同于民事審判權,我們過去也稱檢察機關的民事檢察監督為當事人維護合法權益提供了救濟途徑,其實這是對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的錯誤理解。監督的范圍包括民事審判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和錯誤裁判行為。因而,檢察機關的民事檢察監督案件來源不應當是當事人的申訴,而應當是當事人或者利害關系人的控告、知情人的檢舉、揭發。因為當事人或者利害關系人的控告含義直指對公權力的監督,法院的裁判是行使公權力的結果而不是遵從當事人權利自由處分的結果。原告雖然可以在審理過程中行使撤訴、認可證據、認可被告或者被告認可原告的證據等權利,但是,當事人不能自由處分法院依據法律對證據的判斷、事實的認定和裁判。因而,民事檢察監督是對民事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也是公權力對公權力的監督。
第二,制定必要的規范。要立足于公權力對公權力的監督制定法律規范,如檢察機關民事檢察的調查權、法院的被調查配合義務、對法院違反被調查配合義務的制裁措施、調查結果的處理措施、被調查法院對調查結果的申訴途徑和接受方法、檢察機關行使調查權過程中違紀違法行為的處理、被調查法院或者法官拒不接受處理的懲戒措施等等一系列規范,同時也可以借鑒刑事法律上檢察機關對公權力的監督措施,為檢察機關對民事審判活動違法行為的監督工作提供更為完善、更為有力的保障措施。
第三,科學化業務考核。檢察機關的業務考核應當科學化,目前的考核項目往往是名義上講質量數量并重,其實對比的還是數量。考核要摒棄近距離眼光,有人認為,實行對民事檢察履行職務盡責能力考核缺乏依據且有些問題可能造成考核結果責任承擔不明問題,而考核當年辦案數量有利于統計,不冤枉當任民事檢察人員和責任人,其實,恰恰相反,這樣反而帶來了不少問題,最主要的影響了民事檢察的社會評價,一時“得利',遺患無窮。因而,應改變考核思路,對不盡職、錯誤履職、怠于履職、玩忽職守行為、濫用職權行為加強考核,對提高案件質量和履職能力都意義深遠,它能夠真正起到以考核促工作、以考核促辦案質量、以考核促辦案成效、以考核贏得社會公認的效果。
第四,實行民行檢察縱向一體化。撤銷基層檢察院民行檢察部門或者在基層檢察院附設市檢察院民行檢察部門的下設接待組,接待當地群眾的反映,以便整合全市民事檢察的力量,實行縣(區)院檢察院回避制度,加大對民事審判活動違法行為查處力度。北京市檢察院二分院在積極探索以分院為辦案主體和基層院為基礎的縱向一體化聯合辦案機制方面收到了較好的實踐效果。
第五,充實辦案力量,培養調(偵)查型人才。對民事審判違法行為的調查,盡管是一種調查行為,但由于面對的是審判人員,其法律素質和法律修養遠遠高于一般公務人員,相應地其反調查、反偵查能力也遠遠勝于一般公務人員,因而,調查法官的違法行為單靠目前民行檢察人員的業務素質遠遠不夠。在檢察機關內部,民行檢察人員的素質業內人士都很清楚,“啥不行去民行”、“誰不行到民行”的隊伍業務素質狀況是制約民行檢察工作的根本性問題。因而,開展民事審判違法行為的檢察監督,首先應當充實民行檢察人員的業務素能。
第六,加強與法院的協商協調工作,爭取法院的支持與理解。共同促進司法公正既是法律監督的一項工作,又是法院的重要工作之一。積極與法院協調,共商審判活動違法檢察監督事宜,摒棄檢察監督糾正法院違法行為是給法院“抹黑”的思想意識,共同營造協調合作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