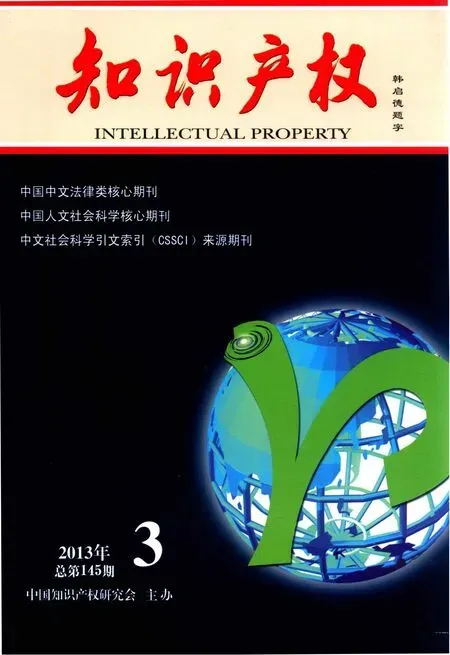著作權視野下反規避條款的法律協調機制
楊 濤
數字網絡環境下復制與傳播技術的發展對著作權保護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通過技術措施筑造“著作權長城”則成為著作權人自助的重要手段。基于著作權保護的現實需要,立法必須制定相應的反規避條款來認可著作權技術保護措施的法律地位。著作權法中反規避條款這一制度設計突破了傳統著作權法的結構范疇,對著作權法公益面向具有潛在的負面影響,故立法配套建構相應的法律協調機制尤為關鍵。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的反規避條款內容與美國、歐盟立場接近,但是相應的法律協調機制空間較小。本文欲以系統的觀念從著作權立法內與著作權立法外兩個角度來探討反規避條款的法律協調機制,并針對我國反規避條款提出相關的完善措施。
一、反規避條款的“超著作權”法律效應
盡管各國的反規避條款內容不盡相同,但其基本內容大都涉及到直接規避行為的禁止和規避準備行為的禁止。①較特殊的是澳大利亞法并不禁止直接規避行為,而加拿大則不禁止規避準備行為。反規避條款使著作權人可采取有效的科技措施保護其著作,禁止內容包含對著作的“接觸”,還獲得禁止他人未經授權而接觸作品及禁止規避技術措施的權利——“接觸控制權”。由于數字網絡科技的進步使得著作的利用方式逐漸改變,這種作品“接觸”與“利用”的分野有其合理性。在數字環境里,有必要給予著作權人足夠的法律保障及損害賠償的請求權,以對抗規避技術保護措施的行為。但是我們也必須辯證地思考其對著作權法的結構性影響,特別是要警惕“超著作權”效應。②Animesh Ballabh, Paracopyright, E.I.P.R. 2008, 30(4), 138-144.
(一)弱化與式微:合理使用空間的壓縮
數字環境中,合理使用的主張必須在作品利用人同時擁有合法“接觸”及“利用”作品的權利下才有主張的空間,所以反規避條款大大壓縮了著作權合理使用原則的存在空間。以美國DMCA規定為例,作品利用者非法取得“接觸”作品的權利,不可能獲得“合法利用”作品的權利,必定也是取得非法利用作品的權利,在合法的情形下,作品利用者不可能單純只擁有“利用權”而無“接觸權”,理論上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故在此情況下也無“合理使用”主張的可能。
即便作品利用者取得合法“接觸”作品許可卻未取得“利用”作品的情況下,而規避“控制利用”的技術保護措施時,作品利用人此時仍有機會主張“合理使用”作為抗辯事由,但可能會因為事實狀況而難有機會取得合理使用的特權。這是因為反規避條款所禁止的準備行為包含“控制接觸”及與“控制利用”技術保護措施有關的任何的技術、產品、服務、裝置、組件或其零件的制造、進口、向公眾提供、準備,或其他交易方式的提供行為,這也使得原本希望以合理使用原則來規避“控制利用”技術保護措施的作品利用者,也因該技術保護措施的準備行為之禁止,而無從獲得規避“控制利用”技術保護措施的技術、產品、服務、裝置、組件或零件的提供。因此,作品利用者欲以他人提供規避設施或服務來規避控制利用的技術保護措施,進而通過主張合理使用作為“未經授權利用”的想法也就難以達成。
(二)免費與付費:接觸行為狀況的變更
在數字化的信息科技時代中,技術保護措施賦予著作權人控制接觸及選擇利用其作品方式的能力,因此無論技術保護措施采用人是否擁有作品的著作權,將使得所有的數字內容只有在“按次付費”的情況下,才可被接觸或利用,且著作權人只要利用技術保護措施將作品鎖住就可以輕易排除他人在未經其同意下接觸作品的行為,因此反規避條款使得原先在某些情況下容許“免費”接觸行為的諸多狀況,改為“按次付費接觸”的機制,并幾乎沒有例外空間。③David Nimmer, A Riff on Fair Use in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148 U. PA. L. REV. 673(2000).反規避條款并不區分規避人是基于非法目的還是合法目的,④Mauricio Espana, The Fallacy That Fair Use and Inform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for Free: An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s to the DMCA's Section 1201, 31 Fordham Urb. L.J. 135(2003).這意味作品利用者在每次利用時都必須尋求權利人的同意與授權,甚至可能每一次接觸都必須付費。因此,可以想象未來將是一個著作權授權機制的時代,當按次付費的授權機制與反規避條款結合,將使得傳統上被認為是有限的獨占權的著作權轉為永久的獨占權,而這種改變也勢必破壞著作權法長久以來的權利衡平機制。
學者以“超著作權”來稱呼反規避條款,而非著作權侵權行為,這意味著反規避條款的特殊性不只顯現在法典編排上。如果說數字環境下必須給予著作權人獨特的對待并提供著作權人充分的救濟與保護,我們必須得以制定反規避條款來規范產業發展的話,那么我們也必須對著作權法基本內涵與架構的過度蛻變提高警惕。盡管反規避條款有極大的部分是在處理規避準備行為,其與著作權法之間的邏輯關聯性極小,但是反規避條款獨立立法已難成現實。⑤美國DMCA制訂過程中,美國商務委員會曾提出將反規避條款獨立立法比將其置于著作權法中更好。我們所能倚重的只能是在包含反規避條款的著作權法框架內,審慎地建構相應的法律協調機制,這樣方能柔化反規避條款對著作權法帶來的結構性侵蝕。
二、著作權立法框架內的協調機制解析
正如各國的反規避條款內涵不盡相同一樣,各國反規避條款的相應法律協調機制也有所區別。在某種程度上講,相對激進的反規避條款其協調機制的空間更為廣泛,故美國、歐盟反規避條款的法律協調機制在系統性和靈活性上都頗具特色。
(一)美國立法機制與行政規則制定的配合——“7+N”豁免機制
美國國會在決定有關DMCA中反規避條款的適用范圍時曾有過不小爭議,最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各個利益團體均積極運用其力量進行游說,以促使國會通過有利于己的條文。⑥Pamela Samuels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Why the Anti-Circumvention Regulations Need to be Revised, 14 Berkeley Tech. L. J. 519(1999).國會強調數字環境對著作權人產生了極大的威脅,因此有必要制定反規避條款,以對抗可能破壞著作權利益的技術措施及行為,但為確保社會大眾仍可對有著作權的著作為非侵權的利用,故特別在1201(d)項到1201(j)項中規定了七項免責規定。
美國靈活的行政規則制定(Rule Making)成為協調機制的重要內容。DMCA中雖然提供七種技術保護措施的免責規定,但是由于DMCA對于所規定的免責行為太過狹隘,顯然未考慮到尚有其它為合法目的所為的規避行為,也可能會對合理使用加以進一步的限制。在反規避條款所規范的三種禁止行為中,引發爭議最大的就是有關接觸控制的規范。而為確保社會大眾可繼續從事諸如合理使用等非侵權行為,并降低可能的沖擊,接觸控制是在DMCA開始實施兩年后才開始生效。在此兩年間,國會要求版權局必須決定哪些“特定作品利用”應該排除適用接觸控制條款,而該決定自該禁令生效時起試行3年,直至3年后再行評估以決定是否續行或是加入新的規范。⑦DMCA section 1201 (a) (1) (D).2000年國會圖書館和版權局首次發布了例外條款,包括兩種豁免規定。隨后于2003年與2006年分別認定四種和六種例外規定,最新一次認定是2010年的規則制定,其在前期認定的基礎上公布了六種豁免事項。⑧Us Copyright Office, Exemption to Prohibition on Circumvention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System s f or Access Control Technologies, (July 20.2010).
(二)歐盟版權指令的“兩步走”方針與成員國的變通措施
鑒于歐盟指令的特殊性,其并未引入傳統意義上的規避責任的例外,反規避條款協調機制則要從兩個角度來看,一是歐盟EUCD中的兩步走機制,二是歐盟成員國的變通機制。
歐盟版權指令要求成員國推動權利人為了實現“權利的例外或限制條款”所要達到的目的而采取“自愿措施”,包括實施權利人與其他利益集團之間為此而締結的協議。如果權利人沒有采取這樣的“自愿措施”,包括權利人與其他利益集團在合理的期間內沒有達成這樣的“自愿措施”,成員國就應當介入并采取適當的措施,以確保“權利的例外或限制”所帶來的好處得以實現。除此以外,EUCD立法者為了適應客觀條件的不斷發展變化,還在《歐盟版權指令》第12條設立了指令修改程序,尋求一種更為靈活的途徑來維護版權利益的長期平衡。⑨Article 12 of 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由于EUCD的轉化實施進程較為緩慢,尚未有報告審查技術措施保護是否對法律允許的行為產生了不利影響,亦未見EUCD的修改議案。
由于EUCD并未引入傳統意義上的規避責任的例外,指令混亂的用詞倒是給了歐盟成員國較多自由空間。對于例外,有的國家規定只有個人能夠適用例外,有的規定相關利益組織和第三人也有權主張,有的是規定行政組織促進適用各種例外。⑩Lucie Guibault, et,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in Member States' Law of Directive 2001/29/EC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final report 2007, pp105.法國2006年的《信息社會的作者權利及相關權利的法律》設置了關于技術措施的限制條款。?DADVSI law Article 13.德國法給技術措施使用人強加義務,即提供必要手段的義務和標示義務,要求權利人負有提供規避技術措施的必要手段的義務,以及授予例外規定受益人要求權利人提供規避技術措施的必要手段的權利以及要求著作權人明確標示其實行何種技術措施以及該措施的特征。
三、著作權立法框架外的協調機制解析
著作權立法上之外的其他反規避條款協調機制亦有頗大的作為空間。這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司法路徑,即禁止反規避濫用原則的適用;另外就是著作權立法外的立法途徑,即消費者,尤其是數字消費者權利的立法保障。
(一)司法路徑
法院是法律衡平機制的掌握者,反規避條款對著作權法產生的影響,取決于法院在判決上的解釋與適用。有學者從法院介入行政豁免條款的角度主張賦權法院增加行政豁免項目的條文,從而通過實務上的適用需求調整并放寬豁免項目,但是這種廣泛賦權無論是從立法角度還是司法角度來看都難具可操作性。如果法院通過擴大適用禁止著作權濫用原則,發展成禁止反規避條款濫用原則,在個案中調整反規避條款免責事項,這種有限賦權相對于Pamela Samuelson教授所主張的廣泛賦權來說更為現實。
禁止反規避條款濫用原則以禁止著作權濫用原則為基礎。美國法上禁止著作權濫用原則的適用需由被告證明兩個事實:即原告違反了反托拉斯法及原告不合法地擴張超越著作權范圍的獨占或違反著作權法下的公共政策。?Dan L. Burk, Anti-circumvention Misuse, 50 UCLA L. REV. 1095.著作權人濫用技術保護措施控制作品內容,都可能使著作權人取得超越著作權法原先賦予的權利范圍。有學者認為當著作權人利用反規避條款取得超越著作權法的權利,以及使用技術保護措施圍占公共領域的素材,均可采用“禁止著作權濫用原則”作為法院判斷余地的依據。?Jason Sheets, Copyright Misused: The Impact of The DMCA Anti -Circumvention Measures on Fair and Innovative Markets, 23 HASTINGS COMM. & ENT. L.J. 116.從該原則的適用來看,其處理反規避條款濫用稍嫌局限,故Julie E.Cohen教授針對技術措施問題提出“著作權鎖定濫用”的規制,?Julie E. Cohen, Reverse Engineering and the Rise of Electronic Vigilantism: Intellectual Property Implications of "Lock-Out" Programs, 68 S.Cal. L. Rev. 1091.后來Dan L. Burk教授提出禁止反規避條款濫用原則,認為DMCA所賦予的排除權是一項新權利,使著作權人不僅可以控制著作的接觸,還可以控制作品的利用,故反規避權是完全脫離著作權法的權利型態,其可能產生的濫用范圍可能遠遠超越預期,因此無法與專利濫用或著作權濫用相牽連,而是一種完全新型態的“反規避濫用原則”?Dan L. Burk, Anti-circumvention Misuse, 50 UCLA L. REV. 1095.。由此可見,學者大抵都同意關于技術保護措施的運用結果超越著作權法所賦予的權利范圍時,法院可以權利濫用原則作為調整特定案件利益衡平與否的基準,使反規避條款成為阻止數字盜版的根據,而非淪為著作權人限制競爭或控制市場的工具與手段。
(二)其他法律規范路徑
反規避條款僅單方面增加保護著作權人實行的技術措施的同時,削減合理使用的范圍,而未見增加著作權人何種負擔或義務,而技術保護措施作為著作權人“正當防衛”的手段,如果對其不加區別、不加限定、不加任何限制的保護,就必然會出現“假想防衛”、“防衛過當”、“防衛不適時”,乃至以“正當防衛”為借口的侵權行為合法化,從而對公眾利益造成損害。網絡時代的作品利用者具有數字消費者的身份,往往處于弱勢地位,“信息充分知悉”的消費者保障原則亦難以實現。基于多元的權利基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與著作權法相比,承載著不同的立法功能,也表征著不同的價值取向,因兩者處于同樣的法律位階,故無法律評價及法律適用上的優先選擇問題,也不因其差異而有顯性沖突,但是這種權利共存因其法律相關性而有客觀的協調作用和制約效果。
無論是在法制面還是經濟面,消費者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許多技術保護措施的運用對使用者影響重大,甚至不合理地損害了消費者的權益,那么通過立法確認數字消費者的權利,將部分本屬消極對抗的抗辯權,轉換成為積極的、具體的使用權,將有利于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各國消費者團體對數字產品的合理使用主張非常看重,希望藉由保障消費者的合理使用來避免消費者權利被不當剝奪。在美國有不少保障數字消費者的權利的提案,如《消費者技術權利法案》?Consumer Technology Bill of Rights, 107th Congress (2001-2002), S.J.RES.51.IS.、《數字消費者知情法》?Digital Consumer Right to Know Act, 108th Congress (2003-2004), S.692.IS.、《數字媒體消費者權利法》?H.R. 107, Digital Media Consumers’ Rights Act of 2003.、《增進作者利益且不限制進步或網絡消費需求法》?H.R.1066, Benefit Authors Without Limiting Advancement or Net Consumer Expectations Act.等。這些提案大都認為,當消費者合法取得數字內容后,不應僅限于消極的使用,還應有一定的積極權利。?六項積極權利:1. 消費者可進行時間的轉換;2. 消費者可進行空間的轉換;3. 消費者可對內容進行檔案備份;4. 消費者可自行選擇取得內容所需使用平臺;5. 消費者為兼容目的可將內容轉換為其他格式;6. 消費者可利用技術以達到前述的各項權利。在著作權法外的法律體系中正面強調相關數字消費者權益,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對反規避條款的負面影響有弱化的效果。
四、我國反規避條款法律協調機制完善建議
我國反規避條款在內容上與美國、歐盟較為接近。但與之對應的反規避條款法律協調機制,我國相關立法內容單薄、方式僵硬,僅《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在第12條豁免了部分直接規避行為。?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12條所豁免的范圍為:1. 為學校課堂教學或者科學研究,通過信息網絡向少數教學、科研人員提供已經發表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而該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只能通過信息網絡獲取;2. 不以營利為目的,通過信息網絡以盲人能夠感知的獨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經發表的文字作品,而該作品只能通過信息網絡獲取;3. 國家機關依照行政、司法程序執行公務;4. 在信息網絡上對計算機及其系統或者網絡的安全性能進行測試。這種粗線條的立法模式,雖然就法律文件來說有語義確定性上的便利,但是在法律適用上的確定性和靈活性卻大打折扣。
(一)《著作權法》修訂的評析與建議
在立法程序上,我國屬大陸法系傳統,不可能完全引進美國的立法程序,特別是其“規則制定”程序,要求國家版權局定期調查、聽證與公布部分技術措施例外條款以調和社會經濟發展與法律滯后性之間的矛盾,顯然與我國制度傳統不合。盡管我們的確需要一個開放靈活的協調機制,但是在反規避條款禁止行為的范圍上再做實質性的縮減似乎不太可能,只有借鑒美國立法和歐盟立法的具體規定,在著作權法律規范體系中設置相應的例外條款,尤其是針對接觸控制技術措施的免責條款。2012年3月31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征求意見稿)第65條對技術措施與反規避條款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為保護著作權和相關權,權利人可以采用技術保護措施。未經許可,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故意避開或者破壞技術保護措施,不得故意制造、進口或者向公眾提供主要用于避開或者破壞技術保護措施的裝置或部件,不得故意為他人避開或者破壞技術保護措施提供技術服務,但是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但書”文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一例外條款的出現意味著一個開放靈活的協調機制打破了反規避條款的原有僵局,相應的免責事由得到了法律的確立。爾后,征求意見稿第67條對反規避條款的例外情形做出了具體細致的規定:下列情形可以避開技術保護措施,但不得向他人提供避開技術保護措施的技術、裝置或者部件,不得侵犯權利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權利:1. 為學校課堂教學或者科學研究,向少數教學、科研人員提供已經發表的作品、表演、錄音制品或者廣播電視節目,而該作品、表演、錄音制品或者廣播電視節目無法通過正常途徑獲取;2.不以營利為目的,以盲人能夠感知的獨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經發表的文字作品,而該作品無法通過正常途徑獲取;3. 國家機關依照行政、司法程序執行公務;4. 對計算機及其系統或者網絡的安全性能進行測試。
就征求意見稿中的新增內容而言,意義與作用不言而喻,但仍存在一定的問題:一則,在豁免的范圍上看,較美國、法國等都要窄,也并未從技術措施類型的角度出發進行合理區隔。二則,從立法條文來看,無法明晰此類豁免行為的性質,其與合理使用關系如何仍不明確。這種不確定性既影響了著作權人對自身權利的合理預期,也讓使用者處于動輒侵權的危險境地。再則,網絡傳播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現有的封閉式立法顯然不能羅列全面,無法靈活應對技術發展帶來的新變化,其法律評價的范圍過寬之弊端,勢必使得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可責難性并不強的規避行為被施以否定性評價之后,卻陷入無法執行的窘境。如此一來,公眾無法正確認識到底哪些行為是被法律允許的,即使是有此認識,也無法理解并且甚至承認立法的公正性,這無疑會損害著作權法的權威性。由此可見,立法的腳步絕對不能戛然而止,面對具體的適用情形、方式、范圍等錯綜復雜的實踐問題,在總結、研究和梳理我國著作權法治實踐基礎之上,通過司法解釋等其他法律形式進一步細化反規避條款例外情況的實用性和可行性,既符合我國的法制現實,也保持了法律適用的靈活。
(二)著作權立法外的規范空間
反規避條款有被濫用的危險,而禁止權利濫用作為當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法律概念,也是各國法律普遍規定的基本原則。作為大陸法系的中國,法官并不像普通法系國家的法官那樣有廣泛的“造法”權力,也不可能創造出“禁止反規避條款濫用”的原則,但是司法裁量權仍有一定的作為空間。另外,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立法主要是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基礎,其他的《民法通則》、《合同法》、《電信條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當中也有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相關規定。但是這些法律法規都難以適應數字消費飛速發展導致的對數字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迫切需要,在2010年國家工商總局頒布的《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管理暫行辦法》中盡管對消費者知情權的保障作了較為細致的規定,但是其在立法層級和程序規則方面尚存在諸多不足,其實體規則的滯后性也使得其在數字消費者權益保障上捉襟見肘,尤其是數字消費者的技術權利、技術措施信息知情權等規定幾乎沒有。由此可見,我國數字消費者權益的立法保障尚有較大空間,通過更為明確的數字消費者知情權保障規則,以及更為清晰積極的技術權利賦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弱化反規避條款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