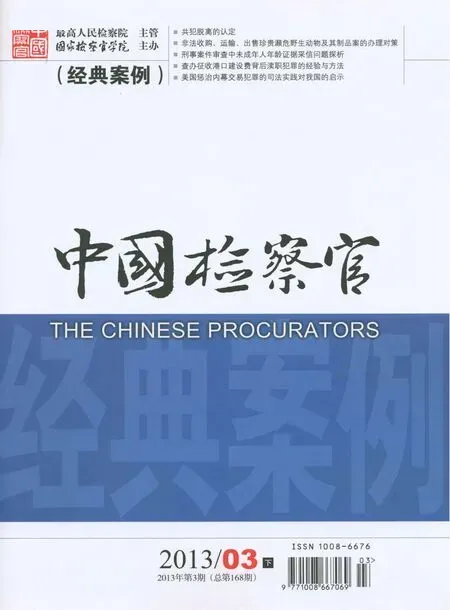冒用他人信息辦理港澳通行證出境的行為認定
文◎余 樂
冒用他人信息辦理港澳通行證出境的行為認定
文◎余 樂*
一、基本案情
2007年8月初的一天,犯罪嫌疑人舒某因幫朋友程某預訂機票,從程某處獲得了其戶口薄和身份證。同年8月6日犯罪嫌疑人舒某以上述戶口薄和身份證,還有自己的照片在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辦理了去香港、澳門的通行證。隨后犯罪嫌疑人舒某持冒用的通行證于2007年8月19日至22日期間,分別從廣東省中山、拱北口岸先后四次出入境到香港、澳門旅游。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觀點:舒某的行為是一般違法行為,不構成犯罪。理由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以下簡稱《出入境管理法》)第 6章附則中第17條“中國公民往來香港地區或者澳門地區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另行制訂。”以及《中國公民因私事往來香港地區或者澳門地區的暫行管理辦法》第26條“持用偽造、涂改等無效的或者冒用他人的前往港澳通行證、往來港澳通行證、港澳同胞回鄉證、入出境通行證的,除可以沒收證件外,并視情節輕重,處以警告或 5日以下拘留。”(以下簡稱《暫行管理辦法》第26條)的規定,舒某的行為按行政處罰處理即可,不以犯罪論處。
第二種觀點:舒某的行為構成偷越邊境罪。理由是:在現行法律法規中,港澳地區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中規定的邊境范疇,舒某冒用他人名義辦理通行證4次出入邊境,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組織、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5條“偷越國(邊)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刑法第322條規定的情節嚴重:……(二)偷越國(邊)境三次以上的”的規定,其行為完全符合偷越邊境罪的構成要件,構成該罪。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舒某的行為已構成偷越邊境罪。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從刑法條文的邏輯性來看,刑法中關于偷越國(邊)境罪的表述按照邏輯結構可以分為三部分:首先是有違反國(邊)境管理法規,偷越國(邊)境的行為存在。本案中,舒某持他人身份證、戶口薄并使用自己照片辦理了港澳通行證先后四次偷越港澳地區,不論是按照 《出入境管理法》、《暫行管理辦法》(特別是第26條),還是其他一些涉及到出入境管理制度的單行法律的規定,這種行為都是被明文禁止的。毫無疑問,舒某的行為符合該邏輯結構第一部分的要求;其次,要構成犯罪,偷越國邊境的行為還必須到達“情節嚴重”的程度,按照解釋的規定,偷越次數達3次以上就屬于刑法意義上的“情節嚴重”,因此舒某的行為也符合這一條件;最后,刑法第322條沒有規定但書或是特別限定,這是一層隱含的內容,因為縱觀刑法條文,針對特定情形規定了特殊法條的也很常見,比如刑法第357七條,就對毒品的范圍進行了劃分;刑法第367條,就專門對淫穢物品作了明確定義,同時還對某一類或某幾類物品進行了排除。而偷越國(邊)境罪條款中并沒有將偷越港澳地區的行為單列出來予以規定,因此,按照刑法第3條“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確定的罪刑法定原則,舒某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
第二,從立法權限角度來看,第一種觀點所依據的《暫行管理辦法》是公安部于1986年12月3日經國務院批準后公布的一個部門規章,其中第26條的表述,在邏輯上已對某一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甚至應該如何處理作出明確的規定,這顯然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8條中“犯罪和刑罰只能由法律來規定”的內容,誠然,立法法的頒布晚于暫行管理辦法,表面上看,不應受立法法約束。但筆者發現,為了不使定罪和量刑成為某人或某些人對其他公民施加暴行的工具,從本質上來說,刑法和刑罰應該公開、及時,而且必須由法律規定。這樣的價值觀已經成為各國立法先驅在制定本國基本法律時不約而同遵守的一條普遍公理,這可以在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立法進程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因此,雖然我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于受政治氣候以及立法技術影響制定并頒布了一些已經生效的規范性文件,但隨著法制進程的加快,在更為完備和先進的法律制定并生效以后,司法人員應該自覺適用新的法律,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綜上,筆者認為暫行管理辦法中關于冒用他人名義偷越港澳地區只作行政處罰處理的條款已經不符合立法法中關于立法權限的規定,雖然尚未失效,但作為負責刑事案件審查起訴的辦案人員應該對舒某的行為大膽地適用偷越邊境罪的條款,認定其行為構成犯罪。
第三,從法律適用角度來看,刑法的效力遠高于部門規章。按照國際以及我國法學界的通說,不同國家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在法律體系中處于不同的效力位置和等級,以此可以分為上位法、下位法和同位法。上位法是指相對于其他規范性文件,在法的位階中處于較高效力位置和等級的那些規范性文件,按理逐次遞減。我國立法法根據法的效力原理詳細規定了屬于不同位階的上位法與下位法和屬于同一位階的同位法之間的效力關系。立法法第79條規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行政法規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規、規章。”作為國家法律體系重要基石的的刑法相對于暫行管理辦法而言,明顯屬于效力高的上位法。因此,如果兩部法律就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規定出現矛盾時,應當優先適用刑法中的規定,刑法明確指出,違反國(邊)境管理法規,偷越國(邊)境,情節嚴重的行為構成偷越國(邊)境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而暫行管理辦法置刑法條文于不顧,依據在刑法面前同樣屬于下位法的出入境管理法明確規定涉及到是否犯罪及刑罰的條款,本身就是不合理也是違反立法權限的。因此,即使以前刑法與暫行管理辦法中相關規定出現矛盾,導致司法人員出現適用法律不規范、不統一的情形,但在立法法這部針對法律之間效力大小的專門法律出臺以后,司法人員就應該站在“規范司法活動,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的高度,堅定不移的在案件辦理中不再引用暫行管理辦法相關條款,認定舒某的行為構成犯罪。
第四,從司法實踐中的具體辦理來看,各地公檢法機關在面對類似本案中舒某的行為時也多以構成偷越國 (邊)境罪處理。經筆者查詢,比較典型的案例有2006年佛山市禪城區法院以偷越邊境罪對借用他人身份證、戶口薄辦理港澳通行證后78次出入香港、澳門地區的歐某作出有罪判決;2011年12月,浙江海鹽縣公安局以涉嫌偷越邊境罪對偷用妹夫身份證辦理港澳通行證6次出入澳門地區的周某立案偵查;市內的案例有2010年巫山縣人民法院以偷越國(邊)境罪對冒用他人信息辦理護照和港澳通行證后120次出入澳門、香港及泰國的小芬(化名)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因此,筆者認為,盡管我國不是英美法系國家,沒有依據判例來適用法律的傳統,但是由于涉及到罪與非罪的界定,既然在司法實務界已經對類似案件的定性大致達成構成犯罪的共識,如果在最高國家機關沒有頒布相應法律或是立法、司法解釋來對本案中類似行為明確排除在犯罪以外的情況下,筆者認為,在司法層面上不宜貿然加以更改,以免在全國范圍內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
綜上,本案中舒某冒用他人名義辦理相關證件后4次出入港澳地區的行為完全符合刑法中關于偷越邊境罪的構成要件,應當按照立法法中有關立法權限以及效力等級的規定,嚴格適用刑法第322條,認定舒某的行為構成偷越邊境罪。
*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檢察院[402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