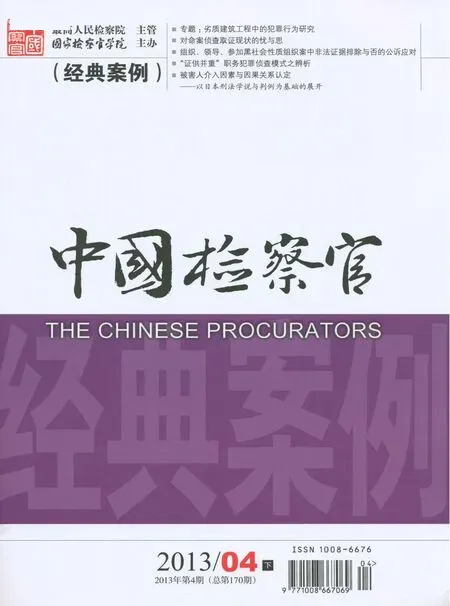危害工程質量安全瀆職行為的刑法考量
文◎關振海 高 岑
危害工程質量安全瀆職行為的刑法考量
文◎關振海*高 岑**
*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法學博士[100043]
**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助理檢察員,法學碩士[100043]
【典型案例一】反映的情況具有典型性的特點,其中有兩個問題還值得做進一步的探討:一是此類案件中是否有適用監督過失理論追究有關人員刑事責任的情形;二是如果存在追究有關人員監督過失責任的情形,那么在具體定罪量刑時應該體現什么樣的刑事政策。
一、規范分析:監督過失與瀆職犯罪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經濟建設得到迅速發展,建筑工程已成為經濟建設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但是一些不法分子為牟取暴利,置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于不顧,在建筑過程中,他們偷工減料、降低工程質量標準或者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工程監管方出于各種原因玩忽職守,對危害行為聽之任之,最終導致了樓房倒塌、橋梁斷裂、鐵路塌陷等一連串重大安全事故,使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嚴重地危害了公共安全。為懲治這種違法犯罪行為,我國刑法規定了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重大責任事故罪等相關罪名。但司法實踐中,囿于各種原因,通常是距離現場越遠,越沒有責任。為了防止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監督過失理論的研究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
(一)監督過失理論的提出
監督過失理論由日本學者提出,意在解決現代工業社會中污染、火災等事故發生時,企業負責人是否有監督過失責任的問題。監督過失概念的提出,源于日本的一個判例:日本森永乳業公司德島工廠是一家生產嬰兒奶粉的工廠,為了提高奶粉的溶解度,自昭和二十八年起,將奶粉中摻入一定比例的第二磷酸蘇打的藥品(安寧劑),該藥品是向當地盛名的藥材商協和產業公司陸續購進的。德島工廠從協和公司購進的第二磷酸蘇打一直用作安寧劑使用而滲入奶粉中,歷時頗久,從未發生任何事故。但自昭和三十年四月起至五月止,協和公司所供的第二磷酸蘇打含有多量砒素的特殊化合物(松野制劑),德島工廠對此特殊化合物不加檢查,將之加入奶粉中出售,造成日本西部一些人工營養乳兒死亡、中毒癥狀。德島工廠廠長及協和工廠廠長被依業務過失致死罪提起公訴。本案一審經過八年的審理,判決不能認定被告人在訂購藥劑時有過失,也不能認定購入藥劑后未加檢查有過失,因而宣判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認為采購物品時應有一種可能混入其他物質的不安感,并肯定森永公司在整個企業方面都有過失。此案發回重審,經審理認為,德島工廠在使用第二磷蘇打作為食品添加物時,應有某些不安感,基于這種不安感,就應有危險的預見,有指定購買純度較高且有品質保證的物品的注意義務。違反此注意義務,造成了嚴重后果,就應負過失犯罪的責任,最后判決被告有罪。[1]
實踐中出現責任事故一般追究直接作業人員的過失責任,認為上層人員、指揮者、決策者負間接責任,這種間接責任也可叫做管理、監督不力責任,如果以“地位越高離現場越遠就越沒有責任”為由而免除監督者的責任顯然有失公正,于是日本等國刑法學者提出監督過失理論,主張監督者同樣應負刑事責任。[2]應當說,該理論較好地解決了上述問題,對于特定涉及公眾生命財產安全的領域可以加強監督者的責任意識,對于維護公眾利益有重要意義。
(二)監督過失理論與瀆職犯罪的認定
監督過失,指監督者自己并不親自從事危險事務,但對直接從事危險事務者負有監督責任的人,在直接從事危險事務的人因過失行為導致危害結果發生時,應當承擔的過失責任。[3]由于業務及其他社會生活上的關系,在特定的人與人之間就形成了一種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這里的監督,是指監督者對被監督者的行為,在事前要進行教育、指導、指揮、命令,在事中要進行監督,在事后要進行檢查。進行這些監督,是監督者的義務或職責,如果監督者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自己的監督義務,導致被監督者產生過失行為,引起了危害結果的發生,監督者主觀上對該危害結果就具有監督過失。責任事故類犯罪的監督過失雖然本身并不直接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但卻對危害結果的發生具有原因力,或是導致危害結果進一步擴大的原因力,因而也具有危險性。[4]
具體而言,運用監督過失理論追究相關人員的瀆職責任應具備以下要素:首先,監督人員應具有監督義務。這種義務一般來源于業務管理法規、行業規章制度等等,是一種客觀義務。如果不具有這種監督義務,便失去了追責的前提。其次,監督者還需具有注意能力,即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履行該項注意義務。何為注意能力?一觀點認為,注意能力就是認識能力。另一觀點認為,注意能力不僅應包括認識預見危害社會結果可能發生的能力,還應包括避免結果發生的能力。[5]我們認為注意能力理論意在從期待可能性的角度限縮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空間,僅具有認識能力但不具有避免能力情形下追責顯然違背了這一點,因而第二種觀點可取。最后,沒有履行監督義務與危害后果的發生還應具備因果關系。即行為沒有盡到相應監管職責對危害結果發生具有原因力。具體有以下兩種情況:(1)如果行為人沒有履行該項注意義務,且履行該項義務能夠阻止危害結果的發生時,其沒有履行注意義務與發生危害結果便具有了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由此具有歸責可能性。(2)如果行為人沒有履行該項注意義務,且履行該項義務也不能阻止危害結果的發生時,則不具有歸責可能性。
案例一中,主體的國有企業身份決定了其兼具社會公共目標和經濟目標,不同于私營企業單純的盈利目的。企業的性質決定了該企業需履行相應的公共職能,以經濟目標支撐社會公共目標,如果因此造成了損失,由國家財政給予補償,因此對于造成的經濟損失,實質上是轉嫁給了國家,其中的管理人員,也肩負了更多的職責。我們認為該國有企業的相關管理人員涉嫌構成國有公司、企業人員失職罪。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15條規定,本罪的立案追訴標準有三種類型:“(一)造成國家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的;(二)造成有關單位破產,停業、停產一年以上,或者被吊銷許可證和營業執照、責令關閉、撤銷、解散的;(三)其他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本案中,基于前期對工程質量監管的過失,以致為了保證工程質量不得不重新返工,由此導致的數百萬元應被評價為這里的“直接經濟損失”。在實踐中,有人提出這里的“直接經濟損失”應屬于發生事故之后產生的損失。但我們認為,事故發生后再根據危害后果追求相關人員的監管責任,只是本罪認定的形式之一。提前發現工程質量存在重大缺陷且具有發生事故的現實可能性時,為了避免這種事故發生而提前采取補救措施產生的費用同樣屬于“直接經濟損失”。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8條有明文規定:“本解釋規定的‘經濟損失’,是指瀆職犯罪或者與瀆職犯罪相關聯的犯罪立案時已經實際造成的財產損失,包括為挽回瀆職犯罪所造成損失而支付的各種開支、費用等。立案后至提起公訴前持續發生的經濟損失,應一并計入瀆職犯罪造成的經濟損失。”
二、政策考量:寬嚴相濟與依法辦案
工程質量事關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一旦出事,則會損害不特定的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造成重大公私財產損失。“豆腐渣”工程俯拾皆是暴露出來的問題,在引發人們普遍恐慌的同時,也使得公眾尤其是司法人員對工程質量瀆職犯罪的關注。其中之一就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把握。降低入罪門檻和提高刑罰幅度成為“從嚴懲處”最多的兩種建議模式。從刑事政策的角度分析,建筑工程質量問題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整治刻不容緩。對于其中負有監管職責的相關人員,在追究其刑事責任時應做到運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依法辦案并行不悖。
(一)從嚴懲治瀆職犯罪
現代意義上的“刑事政策”一詞最早由德國學者費爾巴哈提出,是指“國家和社會據以與犯罪作斗爭的懲罰措施的總和”。[6]此后,中外學者對刑事政策賦予不同內涵,逐漸形成了“廣義的刑事政策”、“狹義的刑事政策”和“最狹義的刑事政策”的區分。[7]本文在刑事法制的范疇內探討刑事政策定義,將其作如下界定:所謂刑事政策,是指國家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等部門根據我國國情和犯罪狀況制定或運用的預防犯罪、懲罰犯罪以及矯治犯罪人的各種對策。[8]
寬嚴相濟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刑事政策,是司法機關正確執行國家法律的重要指針。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核心是針對犯罪的具體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對輕罪案件要“以寬為主,濟之以嚴”;對重罪案件要“以嚴為主,濟之以寬”,即寬中有嚴、嚴以濟寬,嚴中有寬、寬以濟嚴。這是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總結長期以來打擊犯罪、控制和預防犯罪的經驗和刑事司法規律,針對我國目前犯罪態勢而確立的一項基本刑事政策,是現階段刑事司法工作的靈魂。我國歷來對瀆職犯罪采取從嚴的刑事政策。近年來各類瀆職犯罪層出不窮,嚴重損害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政府管理的公信力。與此同時,國家也加強了對瀆職犯罪的打擊力度,具體體現在:
1.增設新的瀆職犯罪。針對食品安全事件的頻頻曝光,《刑法修正案(八)》增設食品監管瀆職罪,專門用來懲治食品領域負有監管職責人員的瀆職行為。
2.出臺瀆職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于2012年7月和8月聯合下發了《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嚴格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若干問題的意見》兩個司法解釋性文件,明確了瀆職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將實施瀆職犯罪并收受賄賂的數罪并罰,明確規定以“集體研究”形式實施瀆職犯罪的,依法追究負有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擴大了“經濟損失”的范圍,嚴格控制職務犯罪案件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適用,等等。
3.明確對瀆職犯罪從嚴處罰。在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文件中明確從嚴把握的傾向。例如《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6條明文規定:依法嚴肅查處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加大對職務犯罪的查處力度,提高偵破率,降低漏網率,有效遏制、震懾職務犯罪,等等。
(二)寬嚴相濟政策與依法辦案的關系
嚴格依法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前提。正如最高檢《意見》中明確指出的:“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須堅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實現政策指導與嚴格執法的有機統一,寬要有節,嚴要有度,寬和嚴都必須嚴格依照法律,在法律范圍內進行,做到寬嚴合法,于法有據。”脫離現行法律的政策把握實際就是一種恣意,實務部門尤其要警惕這種思想,否則就是對法治的破環。例如,瀆職犯罪是結果犯,如果為了從嚴打擊將其規定為危險犯,可以避免公共財產、國家和社會公眾利益“可能”遭受的損失。但同時也導致負有監管職責的人員為其并不具有“確定”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承擔了刑事責任,無疑侵犯該類人員的合法權益。針對有學者從“風險刑法”的角度提出“食品安全監督瀆職犯罪可作為一種危險犯來認定”[9]的觀點,我們認為,“風險刑法”的宗旨并非盲目將法益保護早期化,而是追求風險刑法和刑法謙抑的統一。進入工業社會以來,為了保護社會公共利益,避免危害結果發生后損失的無法挽回,越來越多的立法將法益保護提前至風險或危險的出現,如非法持有槍支罪和醉酒型危險駕駛罪等。這種立法符合現代刑法“法益保護”的宗旨。但是,“不當的”法益保護早期化,也存在擴大刑法干預范圍、違反刑法謙抑性原則的傾向。[10]我們雖然將公共政策作為刑法體系構造的外在參數,但是刑事政策終歸只能依托制度設計技術和作為解釋規范的依據而對刑法產生影響。“風險社會中,不僅作為權威性文本的刑事制定法已為公共政策所滲透,法官關于懲罰必要性的判斷也日益受公共政策影響。”[11]因此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也不斷的為刑罰處罰提供正當化依據,但是無論如何,罪刑法定仍然是底線。
案例一中,因偷工減料導致住房工程出現嚴重質量安全問題,已直接造成了數百萬元的經濟損失,且嚴重威脅到公眾的人身安全。該行為社會危害嚴重,按照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相關瀆職人員予以嚴厲打擊毋庸置疑。但也不能為追求打擊效果而觸犯罪刑法定原則這一法治底線。基于從嚴打擊的角度將瀆職犯罪中的“經濟損失”解釋為“瀆職犯罪或者與瀆職犯罪相關聯的犯罪立案時已經實際造成的財產損失”完全符合立法精神,但將瀆職犯罪解釋為危險犯則與刑法規定相抵觸,有不當擴大瀆職犯罪范圍之虞。
注釋:
[1]黃丁全:《過失犯理論的現代課題》,載《刑事法評論》(第七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75-476頁。
[2]胡鷹著:《過失犯罪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頁。
[3][日]野村捻著:《刑法總論》,何力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頁。
[4]朱興祥、張峰:《監督過失與重大責任事故犯罪》,載《人民檢察》2009年第22期。
[5]郝守才、任彥君:《論監管過失理論及其在我國刑法中的運用》,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年第2期。
[6]蘇俊雄著:《刑法總論》(I),臺灣大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95頁。
[7]廣義的刑事政策,將刑事政策的作用界域擴展至一切與犯罪有關的領域,認為刑事政策是國家與社會以預防和鎮壓犯罪為目的所為的一切手段或方法。狹義的刑事政策,將刑事政策的作用界域擴大到刑罰以及與刑罰具有類似作用的領域,認為刑事政策是運用刑罰以及具有與刑罰類似作用的法律制度預防和控制犯罪的法律政策。最狹義的刑事政策,將刑事政策界定為刑法即刑事實體法的法律政策,是使刑法的實體規定特別是刑罰措施如何更能發揮阻嚇作用的法律政策。參見梁根林著:《刑事政策:立場與范疇》,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頁。
[8]謝望遠:《論刑事政策對刑法理論的影響》,載《中國法學》2009年第3期,第107頁。
[9]盛楊:《淺析“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載《法制與社會》2011年第7期。
[10]謝望原、何龍:《食品監管瀆職罪疑難問題探析》,載《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10期。
[11]勞東燕:《公共政策與風險社會的刑法》,載《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第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