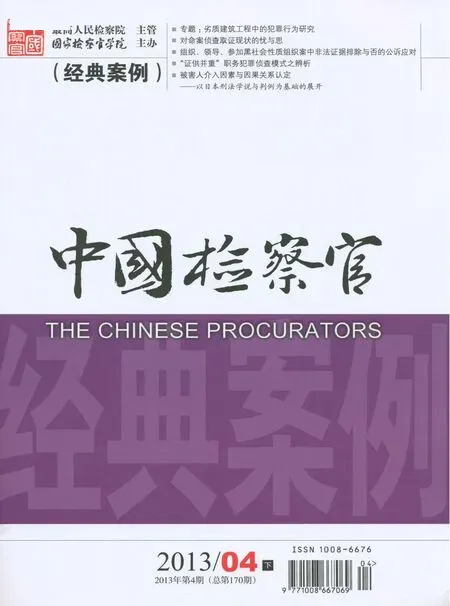保安伙同他人盜走公司銅線的行為定性
戴新寧 汪頤康
保安伙同他人盜走公司銅線的行為定性
文◎戴新寧*汪頤康*
*安徽省祁門縣人民檢察院[245600]
一、基本案情
王某,男,24歲,系某保安服務公司保安員;李某,男,21歲,無業。王某系某保安公司保安員,派駐在某通信電纜有限公司任保安。王某與李某預謀盜竊某通信電纜有限公司的銅線。2000年4月25日當晚,王某與其他保安員調換了值班時間,伙同李某將該公司的三軸銅線盜走,價值人民幣7425元。后兩人先后被查獲歸案。
二、分歧意見
在對該案進行審查起訴時,對于認定王某、李某涉嫌犯罪的事實、涉案財物價值認定及相應案卷證據均為異議,但對如何定性產生了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王某的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李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理由是:王某系電纜公司的保安員,其職責是防火、防盜、防意外事故發生,做好大門過往行人及車輛的檢查登記工作,確保公司財產的安全。王某正是利用了監管和保護公司財產的職責便利與李某共同竊取公司財物,系典型的監守自盜行為,屬于職務侵占行為,應以職務侵占罪追究刑事責任。李某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條件,應定盜竊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王某、李某均構成盜竊罪,理由是:王某與李某在主觀上有共同盜竊的故意,客觀上有共同盜竊的行為。同時,王某實施犯罪之時所利用的是保安員身份條件,不是職務的便利,是工作的便利。故王某與李某二人系共同犯罪,應以盜竊罪追究二人的刑事責任。
三、評析意見
筆者認為,決定本案定性的關鍵點在于認定保安員勾結他人盜竊公司內部財物利用的是職務便利還是工作便利。筆者同意第二意見,認為本案的王某與李某的行為均構成盜竊罪,理由如下:
(一)兩罪構成的行為內容不同
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竊取他人占有的數額較大的財物,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行為。[1]職務侵占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2]
構成盜竊罪的行為表現是竊取他人占有的財物,行為人始終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竊取是指違反被害人的意志,將他人占有的財物轉移為自己或者第三者(包括單位)占有。[3]構成職務侵占罪,客觀上首先要求行為人必須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即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經營、經手單位財物的便利條件;不是利用職務之便,而是利用工作之便侵占本單位財物的行為,不能構成本罪;其次,必須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即行為人利用職務之便實施了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占有單位財物的行為,竊取只是職務侵占罪的行為方式之一。換言之,如果行為人與非法占有的單位財物沒有職責上的權限或直接關聯,僅僅只是利用了工作中易于接觸他人管理、經手的單位財物,或者熟悉作案環境的便利條件,則屬于利用工作條件便利實施的財產犯罪,應當根據行為人具體采用的非法占有單位財物的不同手段,分別認定為盜竊、詐騙或者侵占罪。
從犯罪客觀方面如能分辨出行為人利用的是職務上的便利還是利用工作條件之便的區別,就好界定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的區別。筆者認為,本案王某的行為定性關鍵就是如何理解職務之便與工作之便、明確王某作為保安的法定職責是什么?對此,筆者就“職務”和“職位”的含義及保安的法定職責作如下闡述。就內涵而言,“職務”的基本含義是指職位規定應該擔任的工作。[4]職務是一項工作,不能與“職權”畫等號;亦即不能把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僅僅解釋為利用職權便利。一般來說,“職權”的含義窄一些,它容易僅與擔負單位的管理職責相聯系。“工作”的含義相對較廣一些,既包括在一定單位中擔當管理職責,也包括從事具體的業務活動。就“職務”的外延來說,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一般認為包括主管、管理、經手單位財物等幾種情形。詳言之,“主管”是指行為人雖不具體管理、經手單位財物,但對單位財物的調撥、安排、使用具有決定權。“管理”是指行為人對單位財物直接負有保管、處理、使用的職責,亦即對單位財物具有一定的處置權。“經手”是指行為人雖不負有管理、處置單位財物的職責,但因工作需要、單位財物一度由其經手,行為人對單位財物具有臨時的實際控制權。總言之,即無論是行為人對單位財物的支配、決定權及一定的處置權,還是臨時的實際控制權,均以行為人所擔負的單位職責為基礎,或者均因行為人所擔負的單位職責而產生。
(二)兩罪構成的行為主體不同
盜竊罪的行為主體是一般主體,即年滿16周歲的人。職務侵占罪的行為主體是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人員。同時,對本罪行為主體的認定,不能采取身份說。[5]參考相關的司法解釋,可得知我國司法實踐對職務侵占罪行為主體的認定采用的是職務說。
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雖然盜竊罪和職務侵占罪都屬于竊取型財產罪,但兩者在犯罪構成的行為內容及行為主體上存在較大區別,即職務侵占罪要求行為人必須是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主體是特殊主體;盜竊罪只要求行為人是竊取,主體是一般主體。
《保安服務管理條例》(國務院第564號令)第2條規定保安服務是指保安服務公司根據保安服務合同,派出保安員為客戶單位提供的門衛、巡邏、守護、押運、隨身護衛、安全檢查以及安全技術防范、安全風險評估等服務。據此,我們可以認定,本案的保安王某的法定職責是為某通信電纜有限公司提供門衛、巡邏、守護等安全防范服務。王某并非某電纜公司的工作人員,其法定職務是提供門衛、巡邏、守護等安全防范服務,故其在主體上不符合職務侵占罪的犯罪構成。
綜上,本案的王某作為某通信電纜有限公司的保安,從事的是本單位門衛、巡邏、守護等安全防范工作,與本單位財物“三軸銅線”沒有職務上的權限或直接關聯。在2000年4月25日王某伙同李某行竊,王某利用的是自身工作條件的便利,采取的是與其他保安員調換值班,爭取到有利于秘密竊取的作案時間,而不是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經營、經手單位財物的職務便利條件,與李某合伙實施將公司三軸銅線盜走,其行為完全符合刑法第264條盜竊罪的犯罪構成。故筆者認為,保安王某的行為應定性為盜竊罪,李某應依法作為盜竊罪的共同犯罪處理。
注釋:
[1]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第四版,第873頁。
[2]同[1],第907頁。
[3]同[1],第877頁。
[4]《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商務印書館,第1750頁。
[5]同[1],第9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