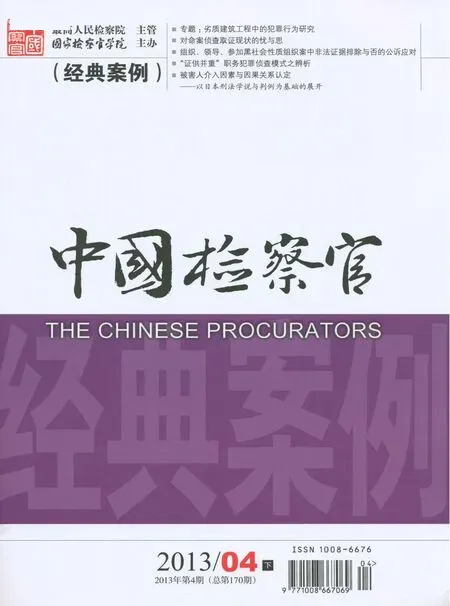從一起強制猥褻婦女案看品格證據的關聯性審查及其規則的完善
文◎蔡震宇
從一起強制猥褻婦女案看品格證據的關聯性審查及其規則的完善
文◎蔡震宇*
*上海市崇明縣人民檢察院[202150]
[基本案情]2009年3月28日21時許,被告人陳某與高某途徑“老李飯店”時,見老板娘屠某獨自一人在店內,遂起意猥褻。兩人進入店內,采用關飯店大門、強拉進飯店、從背后抱住腰部、勒住頸部等強制方法,數次對屠某實施親臉部、頸部、摸胸部等行為。陳某在左手臂被屠某咬了一口后,即放開屠某,與高某離開飯店。
一、本案的相關證據摘錄
犯罪嫌疑人陳某與高某的辯解:我們只是見屠某獨自一人在店內,當時心理比較空虛,在言語上對屠某進行挑逗,說了一些比較下流的話語,過過嘴癮而已,但是絕對沒有動手實施猥褻行為。
證人李某的證言:“老李飯店”是我開的,平時由我老婆屠某經營。2009年3月28日晚上10點多鐘,我接到我老婆電話,叫我快到店里去,具體也沒說什么事情。我走到店門口的時候,看見高某騎在飯店門口的電瓶車上,一副洋洋得意的樣子。我就問高某發生了什么事情,高某講沒什么。于是我又走進店里問我老婆發生了什么事情?我老婆說剛才高某和陳某在飯店里拉著她又摸又親,她跑到外面好幾次都被二人拉了回去。我聽了之后馬上報了警。
證人王某的證言:28日晚上大概十點來鐘,我從外出回家途中經過平時經常吃飯的老李飯店,看見老板娘屠某在店門口與兩名男子發生揪扭。我當時以為可能是兩個男子吃了飯不付錢什么的吧,因為趕著回家,我就沒有上前勸阻。
被害人屠某的陳述:2009年3月28日21時許,我在店里打掃衛生,看見高某和陳某走了進來。言談中,陳某突然從后面用手勒住我脖子,用嘴親其脖子和臉頰,一只手伸到衣服里面摸其胸部。高某則關上飯店大門,上前來用手摸其腰部。其間,我好幾次用力掙脫逃到飯店門口的場心上,但都被二人強行拉回店內。我當時又氣又急,用嘴咬了陳某的左手臂一下,他痛得松手后離開了。高某還沒走,當場對我實施言語威脅。我連忙打了電話讓我老公過來,是我老公報的警。
公安局出具的驗傷通知書證實,屠某系頸部軟組織挫傷。
被告人高某的律師丁某提供了被告人高某與陳某所供職的公司為兩人出具的工作表現證明,證實兩人“在公司工作期間工作勤懇、表現突出、遵規守紀,無違法亂紀行為”。
二、問題的提出
本案中,律師丁某提供了被告人高某與陳某所供職的公司為兩人出具的工作表現證明,證實兩人“在公司工作期間工作勤懇、表現突出、遵規守紀,無違法亂紀行為”。該項證據在英美法上被歸入品格證據的范疇。對于該項證據的審查問題,實踐中主要存在以下三種意見:(1)第一種意見認為,該項證據的取得內容真實、程序合法,應當予以采納。被告人平時表現良好、無違法違紀行為,說明其道德品質良好,連小錯都不犯,又怎么會去犯罪呢?會不會是弄錯了?(2)第二種意見認為,即使該項證據內容真實、程序合法,但與本案沒有直接聯系,不應采納。被告人平時在單位表現良好并不意味著其就不會實施犯罪行為,現實中很多最終被宣告有罪的被告人在平日完全沒有表現其犯罪傾向。反過來說,難道一個小混混一旦占上法庭,他平日里胡作非為的行為難道就可以證明其實施了被指控的犯罪了嗎?一日為娼,就一定會終身為娼嗎?如果這樣的話,還要無罪推定原則干什么呢?像這種容易引起偏見,導致先入為主的證據必須加以排除。(3)第三種意見認為,這項證據雖然不能作為定罪證據,卻可以作為量刑證據。被告人平時表現良好的證據對于證明被告人是否構成強制威脅婦女罪是沒有幫助的,即使是平時一貫道德高尚的人,也不能就此斷定其永遠不會實施犯罪行為。但由于其主觀惡性較小,那么對其的處理也可以相應地酌情從輕,對其進行教育挽回,避免其跌入犯罪的深淵而未能重新社會化。
三、品格證據的審查
(一)本案品格證據的關聯性分析
從律師丁某提交的證據來看,兩名被告人所在的公司出具了兩人在公司工作期間的表現證明,暫且不論這份證據的形式是否合法,[1]從這份證據的內容為可以看出,其在證明被告人工作表現方面是具有證明價值的。換句話說,如果待證事實是被告人工作表現的話,該項證據具有證明性。但從待證事實與本案爭議事實之間的關系來看,其在本案中是否具有實質性呢?本案的爭議事實為被告人陳某與高某是否對屠某實施了強制猥褻行為,但是被告人的工作表現與實施威脅行為之間是否存在邏輯聯系呢?對于辯方而言,提出被告人在工作期間“工作勤懇、表現突出、遵規守紀,無違法亂紀行為”的證明,意在顯示被告人一直是遵紀守法的好市民,不會實施檢察機關所指控的威脅行為。但是這樣的證據所證明的待證事實與案件的爭議事實之間的距離太過遙遠,犯罪行為的發生會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工作表現良好的證明并不能排除猥褻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反過來說,如果檢察機關向法院提供了被告人曾經實施過強制猥褻婦女行為的證據,該項證據在案件中同樣不具有實質性。
(二)證據的可采性分析
如果被告人沒有提出上述證明其工作表現的品格證據,那么是不是這份證據就完全沒有價值呢?其實不然。以上所談論的證據關聯性問題,實際上隱含了一個前提,那便是“在審判程序中”。在美國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人在認罪或被判決有罪之后,便進入 “科刑程序(Sentencing)”。 聯邦最高法院在William v.New York一案確立了科刑程序正當化的基本框架,[2]其中便包括了對被告人相關信息收集的內容。顯然,在科刑程序中,科刑法官所要考慮的實體問題與審判程序中審判法官或陪審團所要考慮的實體問題存在明顯的差異。在審判程序中,審理者所面對的是一個事先被推定為無罪的被告人,其需要的考慮的實體問題是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其將依據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圍繞指控罪名的構成要件進行審查,在此基礎上作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判決。在這一程序中,控辯雙方所被允許提供的證據自然限定在犯罪構成要件的范圍之內。在科刑程序中,審理者面對的是一個已經認罪被判有罪的罪犯,其需要考慮的實體問題是對罪犯課以多少刑罰的問題。其將考慮與罪犯及其行為有關的盡可能多的因素,并在此基礎上對罪犯施以一個適當的刑罰。“科刑法官需要評價‘罪犯的生命和個性’,從中抽取出與‘被告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相關聯的信息。實際上,法院在此種情形下引用了聯邦科刑前報告的形式從而知道緩刑官員收集與諸如‘家族歷史’、‘家庭和鄰居’、‘教育’、‘宗教’、‘興趣和活動’、‘就業’和‘健康’(身體健康和精神健康)等因素相關的信息。”[3]一個惡貫滿盈、罪行累累的大壞蛋與一個誤入歧途、初犯偶犯的小混混相比,對前者課以更久的刑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在這一程序中,對被告人平時工作表現的證據進行審查,從而對被告人本身作出全面的評估,這樣的做法顯然對被告人而言是更為公平的。當然,被告人對此亦享有選擇權。
四、品格證據規則的完善
(一)品格證據規則的立法缺陷
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新修訂的本條文將證據的屬性從“事實”轉變為“材料”,從本條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借鑒了大陸法系的做法,允許所有同案件事實有關材料作為證據被提交到法庭上來,由職業法官來對證據進行審查,并依照自由心證作出判決。但是,這樣的規定在某種程度上會造成庭審過程中因關聯性程度較低的證據被出示,一方面導致訴訟的拖延和庭審爭議焦點的分散,另一方面還將可能造成法官對被告人的偏見。于是,司法機關由針對上述可能出現的庭審困境,出臺了司法解釋。如《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203條規定:“控辯雙方申請證人出庭作證,出示證據,應當說明證據的名稱、來源和擬證明的事實。法庭認為有必要的,應當準許;對方提出異議,認為有關證據與案件無關或者明顯重復、不必要,法庭經審查異議成立的,可以不予準許。”根據該規定,法庭對于那些“與案件無關或者明顯重復、不必要的證據”,有權不予準許出示。
但是這一規定又將產生兩個問題。第一,“與案件無關”如何理解?與犯罪構成有關的事實與案件有關應該是沒有爭議的,但是被告人的品格與案件是否有關呢?被害人、證人的品格與案件是否有關呢?對這一問題的模糊認識,將直接影響到控辯雙方在調查收集證據階段的無所適從,甚至有可能在庭審時因為證據是否與案件有關而引發更多的無謂的爭議,反過來還是影響到了訴訟的正常進程。對于這一點,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只在第268條即第五編未成年人刑事程序中作了原則性規定,此外再無依據。第二,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并未區分審判程序與科刑程序,定罪證據與量刑證據均在法庭調查階段被出示。將與案件爭議事實無關的量刑證據在審判程序中出示,[4]這樣的做法如前所述,將有可能因使法官對被告人產生不公平的偏見。但如果將被告人的品格證據、前科證據等如此重要的量刑證據因與案件實體的爭議事實無關而排除,那么法官在量刑時將同樣會面臨無所適從的困境。于是,量刑證據遭遇了這樣了尷尬:在庭審階段,因與案件爭議事實無關而不得出示;可在庭審結束,被告人認罪或被定罪后,訴訟程序就已經結束而無從出示了。
對此,上海司法系統已經開展相關的改革活動,就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分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主要的改革方向是采用定罪與量刑相對分離的庭審模式,即在法庭調查階段,控辯雙方將定罪證據與量刑證據分開出示;在法庭辯論階段,對定罪意見和量刑意見分開陳述。但是,在現有的訴訟制度框架下,上述改革遇到了難以突破的瓶頸。如在被告人作無罪辯護的案件中,被告人將主要精力至于證明其無罪的方面,而對于量刑方面,其甚至在心理上都存在著嚴重的障礙。辯方明明已經主張無罪了,還要其就量刑輕重發表意見,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更何況,在辯方發表量刑意見的時候,難保法官不會對被告人產生有罪的偏見,這種可能性在程序意義上是存在的。另外,由于量刑證據的出示仍然在審判程序中,對于被告人產生偏見的危險依然沒有消除,反而顯得更加突兀。實際上,庭審模式的改革并未有效避免對被告人產生偏見的危險,而只達到了庭審的脈絡更為清晰的效果。
(二)立法建議
1.單獨賦予被告人提交品格證據的權利,并賦予檢察機關相應的反駁權。雖然品格證據的出示可能會使法官對被告人產生不必要的偏見,但如果被告人已經認識到了該項證據的價值及其可能帶來的危險,那么自然允許其根據自身情況作出選擇。其可以選擇不出示,避免受到偏見的危險;其也可以選擇出示,并以此來竭力證明自己的清白。與之相對應的,在被告人選擇出示品格證據的情況下,檢察機關也有權出示相應的證據進行反駁。
2.引入有限關聯性的概念。即使是相關證據,如果該項證據的證明價值低于其將導致不公正的偏見、混淆爭議或誤導陪審團的危險,或者對于該項證據的質證將導致訴訟不適當的遲延、時間的浪費,或該項證據的提出屬于不必要的重復舉證的,法官有權將該項關聯證據排除。有限關聯性證據制度的引入有助于法官更好地駕馭庭審,避免控辯雙方在細枝末節的小問題上作過多的糾纏,以提升訴訟效率。
3.在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中將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分離。前者審查定罪證據,后者審查量刑證據;前者是后者的必經之路,后者以前者的結果為出發點。這樣的做法使訴訟的爭議問題更加突出,定罪程序解決被告人的定罪問題,量刑程序解決其量刑問題。品格證據在定罪程序中被出示的,就由法官在定罪程序中將該證據作為定罪證據使用,并在量刑程序中將該證據作為量刑證據使用;品格證據在量刑程序中被出示的,就由法官在量刑程序中將該證據作為量刑證據使用。只有在被定罪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進入量刑程序,避免因兩者的混同而導致不必要的偏見、訴訟拖延與時間的浪費,既保證被告人得到公正的審判,又提高了訴訟效率。而對于被告人認罪案件,對于被告人的定罪問題并不是庭審的爭議焦點,反而是各種量刑情節有可能在控辯雙方之間展開激烈的較量,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必要將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絕對分離,只需保持目前的相對分離的模式即可。
注釋:
[1]對于單位提供的書面證明,學界一直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屬于書證,有學者認為屬于證人書面的證人證言,還有學者認為這類書面證明不具有合法性,不屬于證據。
[2]518 U.S.81,116 S.Ct.2035,135.L.Ed.2d 392(1996).
[3][美]偉恩·R·拉費弗、杰羅德·H·伊斯雷爾、南金·J·金著,卞建林、沙麗金等譯,《刑事訴訟法(下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5頁。
[4]對于定罪證據和量刑證據的區分,我國的認識與美國存在差異。在我國,對證據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實體法角度,證據在庭審之前便已經被分成了定罪證據與量刑證據。以品格證據為例,一般在國內被劃入量刑證據的范疇,如辯護意見中會出現“被告人系初犯、偶犯,平日遵紀守法,希望法院能對其酌情從輕處罰”的表述。但是在美國法上,證據是一個程序法的概念,只有在庭審上被出示的,才稱之為證據。由于區分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對證據的認識也相應區分為定罪證據與量刑證據。仍以品格證據為例,若品格證據在定罪程序中被出示用于證明被告人的行為,那么就屬于定罪證據;若品格證據在量刑程序中被出示用于證明對被告人的總體評估,那么就屬于量刑證據。
【本期主講】 重慶市人民檢察院課題組
課題主持人劉昕:重慶市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偵查局局長,重慶職務犯罪偵查業務專家,具有豐富的職務犯罪偵查實踐經驗和深厚的法律理論功底,在《人民檢察》、《重慶檢察》等刊物公開發表文章數篇,主要研究領域為刑事偵查學、刑事訴訟法學、技術偵查等。
課題組成員:鄒望: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南岸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汪葵:重慶市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偵查局綜合處副處長;李玲: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研究室,西南政法大學刑法學碩士,日本亞洲太平洋大學國際政策學碩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日比較法學、少年司法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