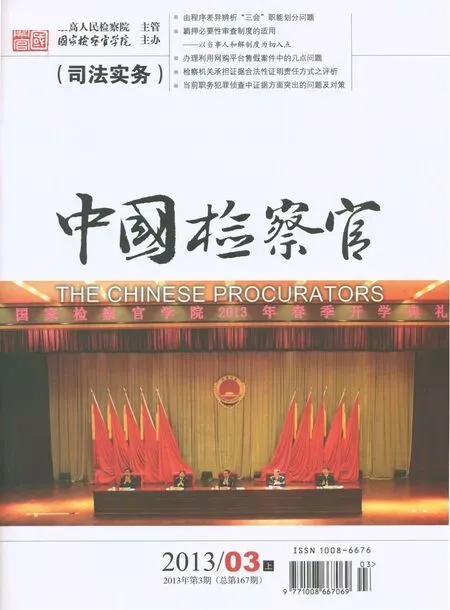檢察機關承擔證據合法性證明責任方式之評析
文◎張 麗
檢察機關承擔證據合法性證明責任方式之評析
文◎張 麗*
*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401147]
兩高三部 《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非法證據排除規定”)規定法院對非法證據,特別是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有疑問時,可以要求檢察機關承擔證明責任。為此,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及修改后刑訴法都明確了控方對于合法取證的證明責任和證明方式,但目前這些證明方式是否有效,則需要我們理性、客觀地分析。
一、提供訊問筆錄
一般來說,即便存在刑訊逼供,也很難從訊問筆錄中看出來,因為訊問人員基本上不會在筆錄中體現刑訊逼供的任何跡象,因此這種方式的證明作用十分有限。
但現階段又不得不承認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仍然意義重大。一方面,訊問筆錄的字里行間有可能透露出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取證的蛛絲馬跡;另一方面,近年發生的冤假錯案告訴我們,在遭受刑訊逼供的犯罪嫌疑人的若干份訊問筆錄中,前幾份的供述一般會漏洞百出,矛盾重重。而從某一份筆錄之后,有罪供述就非常穩定了,往往是刑訊逼供使然。在云南杜培武案中,杜培武面對偵查機關的刑訊逼供,開始“供述殺人的罪行”,“為了不挨打,我不僅僅要按照審訊者的要求說,而且還要盡可能的揣摩他們的意圖。”杜培武的多次供述就相互矛盾。因此通過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來排除刑訊逼供,也是訊問筆錄的重要作用之一。
二、提供訊問過程錄音錄像
修改后刑訴法頒布以前,只要求檢察機關在自偵案件中全程錄音錄像,對于很大一部分由公安機關負責偵查的刑事案件,這一制度尚未成為法律的要求。而目前在職務犯罪案件中,瑕疵證據可能被放大成為非法證據。由于職務犯罪特別是賄賂犯罪的特殊性,往往倚重于嫌疑人的口供,而嫌疑人的言辭證據易變,其不確定性較一般刑事案件更為明顯。訊問過程存在一些瑕疵,如語言不文明、著裝不規范、因技術原因使錄音錄像模糊失真等現象,便可能被肆意放大,成為指責訊問活動非法的根據。
《修改后刑訴法》第121條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錄音或者錄像應當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因此向法庭提供同步錄音錄像將成為一種常態。但現階段這一制度尚不成熟,為保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最大真實性,應盡量縮短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機關的停留時間,實施逮捕拘留后盡快將其送入看守所,在看守所內進行訊問。另外,在庭審中播放錄音錄像一般時間都比較長,如全部播放將會嚴重影響庭審,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應當對播放內容進行選擇,如被告人主張某一次或某幾次存在刑訊逼供的,可以挑選相應的時間段播放內容。
三、通知訊問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
訊問在場人員是指訊問人員以外的其他在場人員,包括記錄人、錄音錄像資料制作人或者訊問聾啞人、少數民族、外國人時提供的通曉聾啞手勢的人員和翻譯人員等,其他證人是指了解審訊情況的相關人員,如看守人員、監管人員等。在實踐中,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一般都是偵查機關的工作人員,他們提供的證言具有多大的說服力可想而知。因為這些人員都被不自覺的印上了偵查人員“同盟的標簽”,即使出庭作證對于法官內心確認的影響作用也不大。雖然這一方法作用有限,但也存在例外情況。在陳某故意殺人案[1]中,被告人稱其唯一的一次有罪供述受到偵查人員的刑訊逼供,并稱當時其岳父在場。在庭審中法庭要求證人出庭作證,其岳父當庭否認看見陳某受到刑訊逼供,法庭認為偵查機關不存在非法取證的問題,此次供述可以當庭宣讀和舉示。因為出庭作證的是其岳父,具有親屬關系,他的證言就比看守人員、監管人員等更具有說服力,對證據合法性的認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
在司法實踐中訊問人員應分為三種:警察、檢察人員、紀檢人員,前二種是我們所稱的偵查人員,第三種是基于辦案的需要進行訊問的人員。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可分為兩種情況。
偵查人員作為第一線工作者,對案件事實的接觸是最直接的,對取證行為是否合法的事實的記憶也是最清晰的。因此偵查人員出庭作證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實,對于有效預防和制止刑訊逼供行為有重要意義。修改后《刑訴法》第57條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出庭“說明情況”。在這里“說明情況”的表述欠妥。筆者認為偵查人員出庭不是要“說明情況”,而是接受質證。那么偵查人員應出庭而不出庭的是否影響相關證據的證據能力或證明力?修改后《刑訴法》第187條第3款的規定通過否定相關鑒定意見的證據能力,可以使得案件鑒定人“被迫”出庭作證。但是對于其他證人尤其是偵查人員應當出庭而沒有出庭的情形,沒有類似的規定。在劉某某故意殺人案中,犯罪嫌疑人在審查起訴階段稱其在偵查階段受到刑訊逼供,公訴機關要求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偵查機關人員多次以工作忙為由予以拒絕,對此公訴機關也束手無策。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使用“辦案機關”而不是偵查機關或部門,而司法實踐中一般將紀檢監察部門也稱為辦案機關,而且該司法解釋明確規定“沒有自動投案,在辦案機關調查談話、訊問、采取調查措施或者強制措施期間,犯罪分子如實交代辦案機關掌握的線索所針對的事實的,不能認定為自首。”因此紀檢人員具有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權力,所以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也應當包括紀檢人員。但是修改后《刑訴法》第57條規定:“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這里使用的是“偵查人員”而不是兩個證據規定中的“訊問人員”,而紀檢部門不是訴訟法意義上的偵查機關,因此紀檢人員也就不是偵查人員,只能將其歸于“其他人員”的范疇。鑒于兩個證據規定和修改后刑訴法對這一問題規定的不明確性,司法實踐中幾乎不存在紀檢人員出庭作證的現象,往往以出具情況說明代替出庭。
在很多案件中偵查機關是將犯罪嫌疑人在紀委交代的“供述”轉化成為訴訟法意義上的證據,而在庭審中也經常出現被告人辯稱其在“雙規”期間受到威脅、引誘甚至刑訊逼供的情況。因此查清紀委調查階段是否有非法取證的情況是相當重要的,但目前由于法律規定的不確定性,實踐中往往很難操作。有必要制定更詳細的細則,將被告人在紀檢部門的“供述”或調查納入到非法證據排除的行列中。
五、提交加蓋公章的說明材料
偵查機關出具附有簽名、加蓋公章的證明文件往往是在沒有錄音、錄像條件的情況下采取的自證清白的方法,司法實踐中十分常見。但實際上,這類材料由于主觀色彩濃厚,在可信性和可采性上大打折扣。在浙江寧波市章國錫受賄案中,公訴機關雖然提交了沒有刑訊逼供、誘供等違法情況的說明,但是法院認定其不足以證明偵查機關獲取被告人有罪供述的合法性。當然,法院認定證據不可采納,主要是由于公訴機關拒絕出示同步錄音錄像,使法庭對被告人供述產生懷疑,進而對情況說明的證明力也就產生了懷疑。因此在認定證據是否為非法取得時,必須綜合全案證據,不能僅憑一紙情況說明就判斷證據的合法性。
在司法實踐中應盡量減少這種材料的使用,即使使用也必須對情況說明的制作形式提出更為嚴格的要求,以增強真實性和可靠性,同時應當結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其他證據綜合判斷。
六、其他證明方式
司法實踐中,還有其他一些方式也可用于證明取證行為的合法性,如犯罪嫌疑人入所體檢記錄、同監所人的證言等。上述證明方式也需要結合其他證據材料進行綜合判斷,才能認定證據是否屬于非法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