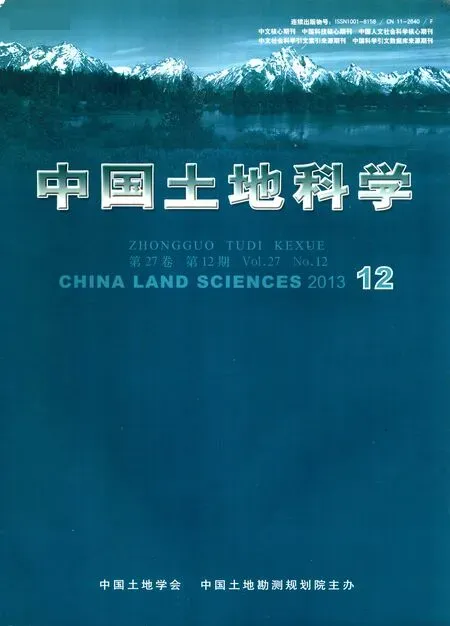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建設對資金的需求及其來源分析
石憶邵
(同濟大學測繪與地理信息學院,上海 200092)
1 新型城鎮化的主要特點
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是世界各國城市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兩個共性問題。近年來,“新型城鎮化”已成為中國各級政府部門、學術界、企業界乃至普通百姓津津樂道的熱題,并被視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1-3]。與舊的城鎮化模式相比,新型城鎮化的主要特點是:(1)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而非物的城鎮化、地的城鎮化。改變過去“要地不要人”的舊城鎮化模式[4-5],扭轉“人口城市化”滯后于“土地城市化”的非集約發展局面,推進“人地互動轉性”的城鎮化,是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核心任務。(2)新型城鎮化的重點是“社會投資驅動型”城鎮化而非“房地產投資驅動型”城鎮化[6]。要以居民的社會福祉最大化而非政府的財政收益最大化為首要理念。要以農民工市民化為主攻任務,為新市民提供義務教育、就業服務、基本醫療、城鎮社保、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務,讓他們分享城市發展成果[7]。(3)新型城鎮化的目標是“生態改善型”城鎮化而非“人為造城型”城鎮化。要以“生態優先”而非圈地造城建鎮為核心目標,扭轉資源高消耗、廢物高排放、環境高污染的工業文明發展偏差,走綠色、低碳、集約的生態文明發展道路。(4)新型城鎮化的實質是內涵型城鎮化而非外延型城鎮化。要注重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提升轉變,從粗放擴張型發展向資源集約型發展轉變,重視和加快戶籍、土地、財稅、投融資、行政等方面的體制和機制的轉型與改革創新,這是新型城鎮化成功的重要基礎。
當前,在土地、淡水、能源等資源約束和環境約束趨緊的條件下,新型城鎮化用地將首重“盤活存量”,即注重提高存量用地在建設用地供應總量中的比重,扭轉城鎮建設對新增土地出讓收益的過多依賴,建立起有利于存量建設用地盤活利用的制度和政策體系[8]。伴隨新型城鎮化發展動力由政府推動為主向市場驅動為主的轉變,過分依賴土地財政的傳統城鎮化模式不可持續。另一方面,人的城鎮化既是一種高成本的城鎮化,也是一項需要“先予后取”的長期性的系統工程[9]。2012年中國還有1.9億農民工尚未市民化,2020年預計為3億人,2030年預計達到3.9億人[10],要完成如此龐大規模的農民工市民化的重任,顯然離不開財政與產業政策的強力支持。
2 新型城鎮化建設對資金的需求分析
2.1 現有估算思路及結果述要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主要又是農民工的市民化。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需求包括使農民工市民化所必須投入的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等方面,因此,新型城鎮化建設對資金的需求也就表現為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需求。
目前國內學術界對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及資金需求有多種估算結果,主要研究成果有:(1)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先生估計,未來10年中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將再有2億農民進入城鎮,加 上現有的1.6億農民工,新增城鎮人口將達4億左右。農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萬元的固定資產投資計算(較低口徑),能夠增加40萬億元的投資需求[11]。(2) 《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0》提出:中國未來需要實現每年2000萬人口進城,通過每人投入10萬元來解決半城市化人口的問題,總體需要資金為每年2萬億元。需要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場來共同分擔,其中:中央政府分擔5000億元,主要用于支付農民工市民化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支出;地方政府承擔5000億元,主要用于支付農民工市民化的住房成本支出;剩余的1萬億元可以通過市場來解決[12]。(3)國家行政學院馮俏彬教授估算得出:按2011年不變價格計算,將現有已在城市居住的15863萬農民工市民化(即存量農民工市民化)的總成本為18091.58億元,其中:隨遷子女教育成本和社會保障成本共計4152.83億元,應由中央政府承擔;社會救助和保障性住房成本共計13938.75億元,應由地方政府承擔;若要在2020年完成存量農民工市民化任務,各級政府每年為此新增的財政支出為2261.45億元[13]。(4)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中國發展報告2010:促進人的發展的中國新型城鎮化戰略》中所做的估測結果是:到2020年,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的最小需求量為16萬億元,其中:道路橋梁64800億元,約占40%;公共交通26700億元,約占16%;水熱氣供應17600億元,約占11%;綠化13000億元,約占8%;污水處理12000億元,約占7%;市容環衛5020億元,約占3%;其他24551億元,約占15%[14]。
上述估算結果要么僅考慮了存量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需求而忽視了新增農業轉移進城人口的資金需求;要么僅考慮了不同區域之間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差異而忽視了不同等級和規模的城市之間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差異,以及不同農民工群體之間市民化的成本差異;要么僅考慮了城市基礎設施投資而忽視了社會資本投資,從而影響估算結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2.2 本文的估算思路及結果
2.2.1 估算方案一:考慮不同區域的差異性 (1)2020年的資金需求總量估算。首先估算存量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需求。2011年全國外出農民工15863萬人,其中東部地區占31.6%,中部地區占36.6%,西部地區占31.8%[15]。到2020年如果使現有外出存量農民工中的65%左右(約1億人)基本實現市民化,按東部地區人均投入20萬元、中部地區人均投入13萬元、西部地區人均投入8萬元計算,得到:東部地區需投入資金63200億元,中部地區需投入資金47580億元,西部地區需投入資金25440億元,三者合計共需投入資金136220億元。其次估算增量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需求。預測到2020年,全國新增農業轉移進城人口14000萬人,其中:東部地區新增農業轉移進城人口5600萬人,中部地區新增農業轉移進城人口4400萬人,西部地區新增農業轉移進城人口4000萬人。到2020年若使其中的1億人(約70%左右)市民化,則東、中、西部地區分別需要投入資金80000億元、40859億元和22856億元,三者合計共需投入資金143715億元。上述兩個方面總計,到2020年若要完成2億農民工的市民化任務,共需投入資金279935億元。(2)2030年的新增資金需求總量估算。同理,首先估算存量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需求。到2030年,其余6000萬存量農民工全部市民化,則東部地區需投入資金37920億元,中部地區需投入資金28548億元,西部地區需投入資金15264億元,三者合計共需投入資金81732億元。然后估算增量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需求。預測到2030年,再使14000萬增量農民工市民化,則東、中、西部地區分別需要投入資金112000億元、57200億元和32000億元,三者合計共需投入資金201200億元。上述兩個方面總計,到2030年若要再完成2億農民工的市民化任務,共需投入資金282932億元。
2.2.2 估算方案二:考慮不同等級規模城市的差異性 (1)2020年的資金需求總量估算。首先估算存量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需求。2011年全國外出農民工15863萬人,其中:在直轄市務工的占10.3%,在省會城市務工的占20.5%,在地級市務工的占33.9%,在縣級市務工的占23.7%,在建制鎮務工的占8.9%,在港澳臺和國外務工的占2.7%[16]。到2020年如果使現有外出存量農民工中的65%左右(約1億人)基本實現市民化(在港澳臺和國外務工的按進入省會城市計算),假設按直轄市人均投入25萬元、省會城市人均投入20萬元、地級市人均投入15萬元、縣級市人均投入10萬元、建制鎮人均投入8萬元計算,得到:直轄市需投入資金25750億元,省會城市需投入資金46400億元,地級市需投入資金50850億元,縣級市需投入資金23700億元,建制鎮需投入資金7120億元,以上5者合計共需投入資金153820億元。其次估算增量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需求。預測到2020年,全國新增農業轉移進城人口14000萬人,其中:直轄市新增420萬人,省會城市新增3500萬人,地級市新增4900萬人,縣級市新增4200萬人,建制鎮新增980萬人。到2020年若使其中的1億人(約70%左右)市民化,則分別需要投入資金為:直轄市7350億元,省會城市49000億元,地級市51450億元,縣級市29400億元,建制鎮5488億元,以上5者合計共需投入資金142688億元。上述兩個方面總計,到2020年若要完成2億農民工的市民化任務,共需投入資金296508億元。(2)2030年的新增資金需求總量估算。同理,首先估算存量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需求。到2030年,若將余下6000萬存量農民工全部市民化,則直轄市需投入資金15450億元,省會城市需投入資金27840億元,地級市需投入資金30510億元,縣級市需投入資金14220億元,建制鎮需投入資金4272億元,以上5者合計共需投入資金92292億元。然后估算增量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需求。預測到2030年,再使14000萬增量農民工市民化,則分別需要投入資金為:直轄市10500億元,省會城市70000億元,地級市73500億元,縣級市42000億元,建制鎮7840億元,以上5者合計共需投入資金203840億元。上述兩個方面總計,到2030年若要再完成2億農民工的市民化任務,共需投入資金296132億元。
綜上,若要在2020年解決2億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按2011年現價計算,則資金需求總規模約為279935—296508億元;若要在2030年再使2億農民工市民化,則 新增資金需求總規模約為282932—296132億元。
3 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資金來源渠道
由上可知,新型城鎮化是高成本的城鎮化,只有依靠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才能籌措巨額的建設資金,進而完成新型城鎮化的預期目標和任務。(1)土地運作。土地出讓收入總體上雖然將趨于減少,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尚未基本完成的地區,其地位與作用仍然不宜全盤否定,關鍵是要優化內部結構,減少增量土地出讓收入,提高存量土地收入占比。(2)債券融資。通過發行市政債、公司債等債券,增加地方建設資金來源渠道[17]。(3)深化稅制改革,逐步建立以持續性的財產稅收益為主的地方財政收入結構。包括開征物業稅,擴大房產稅的征收范圍,一是由城市擴大到郊區、農村,二是由僅對新房征稅擴大到對存量房征稅,增加房地產保有環節的稅收;改革耕地占用稅,將耕地占用稅擴大到農地占用稅,增加土地取得環節的稅收;改革土地增值稅,完善土地流轉環節的稅收。(4)銀行貸款。要注意控制政府性質的土地抵押融資規模,以便防范金融風險。(5)通過政策引導,提高民間資本參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積極性與比重。(6)進城農民工自籌。通過盤活農村資產,完善城鄉產權流轉機制,促使農民工帶資進城,從而增強他們融入城市的初始資本積聚能力。(7)聯合開發基金、信托資金、私募資金、稅收增額融資等其他融資手段,也可作為補充形式,鼓勵嘗試和探索。
4 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配套措施
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主要配套措施是:(1)完善分稅制改革,建立中央與地方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2)構建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的干部政績考核制度;(3)進一步完善征地制度及土地收益分配機制;(4)建立與完善地方政府債務審計機制;(5)推行房產稅、土地增值稅等稅收制度改革,確保地方財政稅源;(6)完善存量建設用地集約利用機制;(7)將農民工納入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體系,并予以重點扶持。
(References):
[1] 陳巖鵬.中央點兵新型城鎮化,重塑經濟增長引擎[N].華夏時報,2012-12-08.
[2] 戰軍.聚焦中國新型城鎮化[EB/OL].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chengzhenhua, 2013-01-05.
[3] 宣曉偉.新型城鎮化的邏輯:現代轉型視角下中國社會結構和關系的再調整[N].21世紀經濟報道,2013-03-04.
[4] 王全寶.城鎮化本質是農民市民化[J].中國新聞周刊,http://news.sina.com.cn/c/sd/2013-03-15/163826543769.shtml, 2013-03-15.
[5] 石憶邵.中國新型城鎮化與大城市發展[J].城市規劃學刊,2013,(4):114-119.
[6] 本報社評.新型城鎮化的目標在于“社會投資拉動”[N].21世紀經濟報道,2012-12-25.
[7] 韓俊.農民工市民化與公共服務制度創新[EB/OL].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106/c40531-19510877.html,2012-11-06.
[8] 高偉.中國新型城鎮化用地首重“盤活存量”[N].經濟參考報,2013-08-26.
[9] 石憶邵.中國新型城鎮化與小城鎮發展[J].經濟地理,2013,33(7):47-52.
[10] 潘家華,魏后凱.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6: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26-28.
[11] 遲福林.用三年時間使有條件的農民工市民化[N].21世紀經濟報道,2013-03-06.
[12] 中國市長協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0[M].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11.
[13] 梁嘉琳,孫韶華,夏保強,等.農民工市民化總成本超1.8萬億[N].經濟參考報,2013-03-04.
[14]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中國發展報告2010:促進人的發展的中國新型城市化戰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35-136.
[15] 彭麗荃.2012年農民工監測報告[A].2013中國發展報告[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111.
[16] 易鵬.底特律破產與中國城鎮化[EB/OL].http: //www.zaobao.com/forum/expert/yi-peng/story 20130720-230527/page/0/1, 2013-07-20.
[17] 丁玉萍.市政債+資產證劵化:金融杠桿撬動城鎮化融資[N].21世紀經濟報道,2013-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