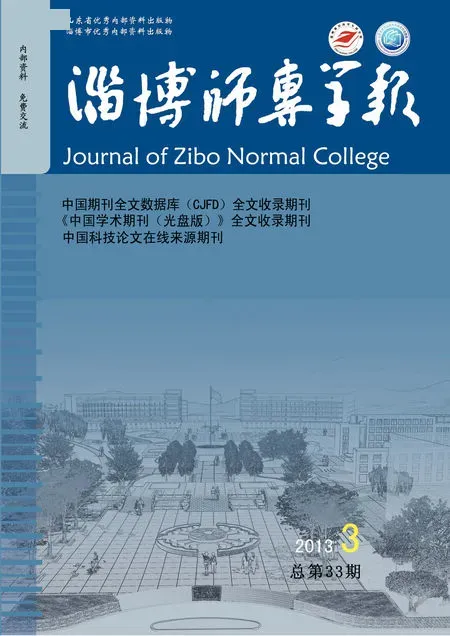兩漢山東墓葬石刻的孝禮文化
楊子墨
(淄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人文科學系,山東 淄博255130)
漢代遵從“以孝治天下”,“孝”是漢代最為重要的社會宗教道德觀念。自漢武帝起,實行舉孝廉的選官制度,在此激勵下,東漢士大夫階層競相追求廉潔、孝行,形成注重名節的社會風氣。面對死亡這一人生倫理大事,世人更是竭盡全力表孝守禮,以彰孝德之心。為此,圍繞墓葬而產生的禮儀文化制度森嚴、內容繁縟、程序復雜,各類墓葬石刻因運而生。古人云:“周禮盡在魯矣”。[1]山東作為齊魯之邦,是儒家文化的發祥地,也是中國孝禮文化的核心地。這里有我國最早的墓碑、墓志、石祠堂、畫像墓,也有全國保存最為完整的墓葬建筑,曲阜孔林為孔子、孔子后裔及孔氏家族的專用墓地,是儒家孝道文化的集中墓葬體現。可以說,漢代山東墓葬石刻為全國石刻的縮影,我們由此可以窺視漢王朝的墓葬石刻形式,體會漢代孝禮文化的博大精深。
一、喪禮與兩漢山東墓葬石刻
死亡,是人生不容回避的問題,如何安葬逝者是社會倫理道德的一件大事。古人將人死之后到安葬以前的治喪活動稱為“喪禮”,對入葬逝者的祭奠則稱為“祭禮”。《禮記·曲禮下》釋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孔穎達注疏曰:“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自古至今,喪葬并不僅僅視為安葬亡靈,它還體現了人們的仁愛及孝道本性,并直接反應了一個社會的倫理規范及政治秩序,正所謂“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2]漢代社會具有嚴格冗繁的墓祭禮儀和豪華奢侈的墓葬建筑,墓葬中包含著各種隨葬器物及建筑裝飾。從考古資料來看,墓葬列置石雕最早見于西漢霍去病墓的石刻組件,有“馬踏匈奴”、躍馬、臥牛、伏虎等等。東漢時期,圍繞喪葬所營造的各類建筑繁縟復雜,有位于墓上的石闕、石獸、石碑,也有置于墓下的畫像石和石棺。它們依附于喪葬建筑,其目的既是頌揚死者,安慰生者,也是宣揚人倫,并且各類石刻以不同形式表現著漢代喪禮文化。
(一)石祠堂
漢代墓祭盛行,世俗認為:“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3]古人在墓前建立祠堂,作為祭奠死者的場所,山東出土的諸多祠堂石刻銘文中均有此記錄,如《汶上路公食堂畫像題記》、《滕州食堂畫像題記》、《曲阜陽三老食堂畫像題字》、《微山食堂畫像殘石》、《微山王成母食堂畫像題記》、《微山祠堂側壁題記》、《微山桓孨祠堂后壁》、《泗水縣陳村畫像題記》、《魚臺文叔陽食堂畫像題記》等銘文中“食堂”,“食堂”即祠堂,信立祥先生就現存資料統計,漢代墓上祠堂至少有“祠堂”、“廟祠”、“食堂”、“齋祠”或“食齋祠”四種名稱,[4]是古人祭祀祖先神靈的墓上建筑。祠堂早在商代就已出現,兩漢時期,祠堂開始流行。至今山東、河南等地還留有漢代祠堂,尤以山東長清孝堂山祠堂、濟寧嘉祥武氏祠最為著名。
東漢永建四年孝堂山祠堂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石祠堂,也是現存唯一一件保存完整的石祠堂。其單檐懸山頂,平面作長方形,室內東西寬3.805米,南北深2.08米,前面正中有八角石柱,與后山墻之間置三角石隔梁,將祠室分隔為兩間。著名的嘉祥武氏祠畫像石經學者研究及復原,其建筑形制、體量大小與孝堂山祠堂近似。另外,1978年和1980年在嘉祥宋山出土兩批零散畫像石經復原后為四座石祠堂,形制規模較小,里面很難容納人。并且,這些祠堂前部既無墻壁又無門扉,似乎可由人任意進出。然而,作為進出口,其敞開的高度又過于低矮,比如嘉祥宋山祠堂進出口高度僅有0.7米,孝堂山祠堂也只有0.86米。顯而易見,如此低矮的進出口,一般人是無法出入并進行活動的。信立祥先生認為:“這種石結構祠堂不過是一種象征性的祭祀建筑,祭祀時祭祀者并不進入祠堂,祭祀典禮活動都在祠堂外進行。”[5]
墓地祠堂是用來祭祀墓主的,一般位于墳墓前。美國學者簡·真姆斯認為“中國東漢時期的享祠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喪葬紀念碑一樣,是一種象征性建筑,它的存在是為了哀悼和紀念死者,使已死去的先輩確信他們沒有被遺忘。”可以說,漢代祠堂是為建立生者與死者和冥世間的聯系而設的。先民試圖通過祠堂這一建筑,使生者可以領悟到死后人們所能達到彼岸的神奇世界。同時,作為“鬼神所在,祭祀之處”[6]的墓地祠堂,將漢“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的精神完整地貫穿于喪葬禮儀之中。
(二)石闕
闕是指立于古代城垣、宮殿、官府、祠廟、陵墓大門兩側的高層建筑物,它多為銘記官爵功績、標注界域或建筑裝飾之用。漢代墓冢前常制神道,神道意為墓路,《后漢書·中山簡王傳》有:“大為修冢塋,開神道”,神道最前方以闕作為標記,故亦稱為“墓闕”。就其建筑用材,闕有木質、石質兩種。遺憾的是,木質闕受歷史侵蝕,已風化為一堆堆丘土。我國現存闕僅為石質,共計二十九處,其中四川二十處;河南、山東各四處;北京一處。除河南登封太室闕、少室闕和啟母闕為神廟所置外,其余皆為用于墓葬墳冢的墓闕。
漢代墓闕常與祠堂并置一起,《水經注》記錄“水南有漢荊州刺史李剛墓……有石闕,祠堂,石屋三間。”“彭山西北有漢安邑長尹儉墓。冢西有石廟,廟前有兩石闕,闕東有碑。闕南有二獅子相對。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兩石羊。”“譙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廟堂,余基尚存,柱礎仍在。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榱櫨及柱,皆雕鏤云矩”等等。山東嘉祥武氏祠也有墓闕。墓闕有闕身、基座、闕頂三部分組成,頂部有單檐和重檐之分。闕面常施各種珍禽異獸、人物故事、祥瑞圖案等裝飾,并題刻闕額及銘文,以標紀制闕者姓名官氏、官職、歷官及墓主行事。另外,在漢代非石闕的畫像上也刻有門闕,它們一是像征世間的門闕以顯示家世富有和地位顯赫,二是將闕想象為天國的“天門”,以對死者起到引魂升天的作用。[7]
(三)石碑
碑是中國古代最常見的一種石刻形式之一,它起源于漢代,有測時、栓牲、下棺等功用。漢代生者為了追念逝者特制石碑立于亡靈墳塋前的正中處,一方面起到標識墓地作用,一方面通過碑文記錄死者姓名、世系、為官經歷和銘贊悼詞,以達到讓逝者名垂千秋的愿望。西漢時,石碑尚未定型,現今發現最早的石碑為山東河平三年的《麃孝禹碑》,其形制古樸僅見碑制雛形。東漢時期,石碑驟然完善并遍及全國,正如劉勰《文心雕龍·誄碑》所言:“自后漢以來,碑碣云起”,“其時門生故吏,為其府主刻石頌德,遍于郡邑,風氣極盛”[8]。近百年的光陰,石碑驟然完善并遍及全國,成為一種影響久遠的石刻形制,其中,墓碑數量首屈一指。漢代立碑并沒有嚴格等級要求,上至達官貴族下至黎明百姓皆可立碑,如《隸釋》卷九有《故民吳仲山碑》。此時,不僅成人可立碑,甚至兒童也可樹碑,蔡邕所書《童幼胡根碑》便是很好例證。
漢代墓碑形制分為圓首、圭首、方首三種類型,圓首碑又細分為平面、暈紋、蟠龍三個亞類。除方首碑外,碑面多有穿,并飾畫像圖案,書法工整典雅。碑文銘贊內容多樣,趙超先生在《中國古代石刻概論》一書中,將其歸為六類:贊頌古代賢圣及前朝帝王功德、贊頌神明的靈異和恩澤、彰揚古代忠臣良將的功業、銘刻當時帝王及將相們的功績、紀念任職官員的德政、表彰孝子節婦等封建道德典范。[9]曲阜孔廟的《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等碑文記錄了孔廟建造、祭祀禮儀之內容,是我們了解漢代祭祀制度的重要文物資料。
漢代墓碑碑文多在千字以上,文體正式定型,已有文有銘亦有序。此時,碑文文體明顯受漢賦影響,起首敘死者姓名、籍貫、祖系及歷官,之后頌揚逝者功德,文末以四言韻文結尾。如《鄭固碑》碑文起首云:“君諱固,字伯堅,蓍君元子也。”而后云:“含中和之淑質,孝友著乎閨門……”文末曰:“其四月廿四日,遭命隕身,痛如之何……乃刊石以旌遺芳”。結尾四言韻文曰:“于惟郎中,實天生德……”。有的墓碑還標注樹碑目的和書碑、刻碑者姓名,如《衛尉卿衡方碑》:“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希書。”碑文文體的定型,是漢代墓葬禮儀碑制成熟的重要內容。漢代墓碑多為門客黨友集資刻贈,它主要表現了客人對逝者的贊譽。正如包華石所指出的“碑文內容表明了客人的動機:這些文字的目的在于贊揚死者在學術和政治生涯中的功績,表達對共同理想的獻身精神,以及提高立碑者自己的聲望。由于這種聲望和漢代的舉薦制度有關,它對一個人的升遷也至關重要。”[10]
(四)石獸、石人
漢代墓上石刻作品具有完善的配套組合制度,它們形成一套完整的墓上石刻體系。除祠堂、墓闕、墓碑外,石獸、石柱、石人等也是陵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著錄漢曹嵩墓:“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祠堂。余墓尚存,柱礎仍在。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榱櫨及柱皆雕鏤云矩,上罘罳已碎。闕北有圭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仆特進費亭候曹君之碑。”漢弘農太守張伯雅墓:“庚門表二石闕,夾封石獸于闕下。冢前有石廟,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側樹兩石人,有數石柱及諸石獸矣。”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冢北有碑……碑東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俱碎。”漢平陽侯相蔡昭墓:“冢有石闕,闕前有二碑……羊虎低傾。”從這些記錄可以看出,祠堂、墓闕、墓碑、石柱、石獸、石人、石闕等石制雕刻作品均為東漢墳冢墓前普遍存在的組合形式。在排列次序上,石柱居首,然后依次為石獸、石人、石闕,最后是置于冢前的石碑和祠堂,山東等地至今仍保留完整的墓上石刻作品。1957年出土于曲阜城東15里防山區書院公社陶洛村的一對石翁,它們以粗獷的框架勾勒出其基本輪廓,不作任何細部雕飾,形象模糊、古樸稚拙。嘉祥武氏祠的石獸體態矮小,造型別致,獸首張口吐舌,多作昂首跨步、挺胸彎腰之姿態,威猛強健。
(五)畫像石
“畫像石,實際上是漢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闕和廟闕等建筑上雕刻畫像的建筑構石。其所屬建筑,絕大多數為喪葬禮制性建筑,因此,在本質意義上漢畫像石是一種祭祀性喪葬藝術。”[11]圍繞喪葬禮儀性質的要求,畫像石以其生動形象的畫面向我們訴說著漢代的喪禮儀式內容及制度要求。
1973年山東省博物館聯合蒼山縣文化館發掘了臨沂蒼山城前村的一座漢代畫像石墓,畫像圖案記錄了漢代社會送葬的相關過程。在畫像中,祠堂前有一門者俯首迎著正朝西前來的車隊。車隊上方有云中飛翔的小鳥,隊前一人騎在馬上,其后一馬車,馬車之后有一羊車,它象征了送葬逝者到達墓地的槥車。槥車是漢代載棺之車,《漢書·韓安國傳》王恢曰:“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顏師古注曰:“槥,小棺也……載槥之車相望于道”。
漢代畫像中有許多“樓閣拜禮圖”,樓閣是墓地中用來供奉祭祀用的祠堂,樓閣內常置有受拜者和匍匐的禮拜者,他們是墓主人和墓主人的子孫。樓閣旁常有標注墓地的雙闕,以及樹木。漢代墓地普遍植樹,樹下停系車馬是墓主的乘具,象征墓主自地下的墓室乘坐來到祠堂,接受子孫的祭祀。而射鳥是表示孝順的子孫在祭祀前,在墓地周圍樹林射獵以為犧牲。另外,在庭院、樓閣、門闕前,常有手持掃帚之人。他不僅是打掃衛生者,還是漢代重要禮儀的代表者。古人稱“擁彗”,彗即是“篲”字,為掃帚。夫人迎接尊貴的客人,常以擁彗表示敬意。《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司馬貞索隱曰:“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樓、闕、馬、車、樹木和射獵他們有機地形成一個整體,向我們展現了漢代祭拜祖先的習俗要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沂南北寨村漢墓吊唁祭祀圖》。而《季札掛劍》則更加形象地表現了漢代墓祭的場景,畫像中左為墳,墳頭上有一樹木,樹上掛著劍。墳前擺著祭品,季札及隨后侍者跪拜行禮。天空有鳥兒飛來,貓頭鷹也站在樹上窺視。
另外,在沂南北寨漢墓中室東璧上橫額上的樂舞百戲圖:眾多伎藝人表演飛劍跳丸、頂橦、走繩、七盤舞、魚龍曼衍之戲、車戲、馬戲,以及敲擊鐘、鼓、磬、鐸,吹奏排簫、笙、竽、塤和撫琴等。多數學者認為,這樣熱鬧活躍的場面是墓主人生前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筆者認為,這也應該是墓葬禮儀的一部分,因為在古代送葬及祭祀的典禮中“樂”是不可缺少的內容。《漢書·周勃傳》:“勃以織簿曲為主,常以吹簫給喪事”,顏師古注疏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統治者以禮樂制度來治理國家,他們以“樂”從屬于禮的思想,以“禮”來區別宗法遠近及等級秩序,同時又以“樂”來融合“禮”的等級秩序。孔子云:“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在舉行祭祀、宴享、朝聘、婚冠、喪葬等宗教和政治活動時,均使用禮樂器。
上述的各類石刻作品,它們以不同的形制及內容體現著漢代喪葬禮儀文化內涵,每一件石刻都有其存在的價值、意義及使命。雖然它們的表現形式不同,但均以喪葬禮儀為目的。墓上有祠堂、門闕、石碑、石獸、石人等石刻組件,墓下雖無此類實物,但睿智的漢代人卻將其以線刻的形式表現在墓室墻壁上。無論是深埋地下永無天日的墓室畫像,還是炫耀于世流傳百代的墓上畫像,它們都有表現升天入仙、車馬出行、樓閣拜謁、歷史故事等畫像題材內容。從地上石闕、祠堂、石碑到地下墓室,它們雖然都是墓葬文化的一部分,卻代表著不同的宇宙世界,地下代表著鬼魂世界,地上服務于現實人間。墓主從人間進入墓地,必須經過車馬長途跋涉,先進入墓闕夾峙的神道才能到達墓址。而從陰間來到世間祠堂,以接受子孫后代的祭祀,亡靈也同樣需要此番長途跋涉。所以,在漢代畫像石中表現車馬出行的題材隨處可見,漢代人以車馬忙碌奔波代表著亡靈在幽明兩界的穿梭。
從墓上到墓下,漢代人對于墓葬建筑的布局、裝飾是如此講究、嚴格、繁縟。冗繁的石刻配件、精美的畫像石雕、豐富的石刻造型,它們以不同的姿態構建著漢代墓葬文化的渾厚與莊嚴,為亡靈塑造一片繁華安寧的凈土。為保持這片寧靜不被賊人破壞,墓室各處采取了嚴密的防盜措施,并在祠堂和墓室題記中以文字提醒、警告甚至詛咒盜墓者,例如:金鄉縣胡集鄉郭山口村魚山漢墓門楣題記“諸敢發我丘者,令絕毋戶后。疾設不詳者,使絕毋戶后”,滕州建初六年食堂畫像題記“盜冢者得毋敗壞”,肥城欒鎮村建初八年張文思為父造祠題記“勿敗□”,滕州永元三年殘石題記“敬白士大夫,愿毋毀傷,愿毋毀傷”,東阿鐵頭山永興二年薌他君石祠堂題記“唯觀者諸君,愿勿敗傷,壽得萬年,家福昌”,嘉祥宋山永壽三年許卒史安國祠堂題記“唯諸觀者,深加哀憐,壽如金石,子孫萬年。牧馬牛羊諸僮,皆良家子,來如堂宅,但觀耳,無得深畫,令人壽;無為賊禍,亂及孫子。明語賢仁四海士,唯省此書,無忽矣”,
二、孝道與兩漢山東墓葬石刻
漢代統治者提倡孝道并強調孝的重要性,圍繞孝所形成的行為和思想反映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由此皇帝推行“舉孝廉”選官制度,民眾以《孝經》為普及典范,“厚葬”成為孝德的重要表現,這一切使人們感觸到“孝”對人生命運的重要性,故此各種表現個人孝悌品行的禮儀民俗備受關注,《鹽鐵論》錄有:“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于世,光榮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發屋賣業”。在此“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的時風下,厚葬之風在社會各階層中普遍流行,人們借用逝者的陵墓建筑、喪葬儀式、隨葬品、墓祭典禮以表達自己的孝心,在墓葬石刻文化中尤以畫像石及銘刻文字尤為突出。
(一)畫像石中的“孝”
漢代人認為,孝可通神明,《后漢書·列女傳》記載姜詩妻的故事時提到:“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12]漢代畫像石中多有孝子圖和列女圖,它們是表現儒家孝悌觀念最為直接的藝術表現形式。據現今發現的畫像石來看,尤以濟寧嘉祥武氏祠中的孝子圖最為集中豐富,畫像中《曾子》、《閔子騫失錘》、《老萊子娛親》、《丁蘭供木人》、《柏榆傷親》、《邢渠哺父》、《董永孝親》、《蔣章訓》、《朱明》、《李善祭主》、《金日殫拜母像》、《三州孝人》、《羊公》、《魏湯》、《孝子趙徇》、《孝孫原谷》、《七女為父報仇》、《帝舜圖》等成為我國直接表現孝道的經典傳統故事的巨幅。
此外,在畫像石中還有許多表示尊老、敬孝的象征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烏和鳩。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烏鴉被賦予了神秘及圣神色彩,“金烏西墜,玉兔東升”烏鴉象征了太陽。它渾身漆黑是黑暗的代表,被視為可以穿越陰間暗室的神鳥,其啼聲陰沉凄涼被定為鬼魂的信差,而其反哺的生活習性又被尊為“孝鳥”。《本草綱目禽慈鳥》中稱:“此烏初生,母哺六十日,長則反哺六十日,可謂慈孝矣。”相傳顏烏母親去世時,曾引來數千烏鴉為他銜土壘幕。[13]宗懔因喪母而悲泣不已,每當痛哭時總有烏鴉聚集鳴啼。[14]美麗的傳說,使“烏鴉”成為人們心中的吉鳥,很多畫像石中都有其身影。微山縣兩城出土的《女黃牽馬圖》畫中一株大樹,樹上羽人、鳳鳥和飛鳥,鳳鳥上刻“蜚鳥”,下刻“烏生”,此“烏生”即為“孝鳥”烏鴉;泰安大汶口的《趙茍哺父》畫中有一對烏鴉作相對哺食狀;《顏烏》畫像中樹上棲息一大鳥,旁隸書榜題“孝烏”。
鳩是吉祥之鳥,為尊老養老之象征。《藝文類聚》引《瑞應圖》云:“鳩,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漢代有授玉杖或稱鳩杖之禮,《后漢書·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鶚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王先謙《集解》引惠棟曰:“《風俗通》云:‘漢高祖與項藉戰京索間,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賜老人也。’”嘉祥武氏祠《董永孝親》圖中董永父親手中所執杖,即為鳩杖。[15]
(二)石刻銘文中的“孝”
漢代人信奉“人死輒為神鬼而有知”的靈魂不滅的生死觀,這使得世人十分重視個人孝悌品行的修養,形成“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谷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16]的厚葬風氣。故使漢代孝子順孫林立,世人為逝者盡孝如禮,對長者竭盡孝行,墓葬石刻銘文也表達了漢代孝行、孝思與孝禮。
《武氏闕銘》、《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執金吾丞武榮碑》、《竹邑侯相張壽碑》、《衛尉卿衡方碑》、《漢博陵太守孔彪碑》、《魯峻碑》、《漢豫州從事孔褒碑》等碑文均記錄有“舉孝廉”的選官內容,從記述情況來看,漢代士人被推舉孝廉后,一般先拜為郎中,然后升任謁者,再拜為縣令或縣長,或升任郡國太守等職。年齡也并非嚴格按照四十歲方可推舉的要求,武斑二十五歲、武榮三十六歲便推舉孝廉。
漢代逝者的裝殮、喪葬儀式、陵墓營建都十分講究。此時,山東墓葬數量眾多、分布廣泛、遍及全省。據不完全統計,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山東地區經過科學發掘、清理的兩漢墓葬近達三千余座,僅臨淄乙烯廠生活區一處漢代墓地就有兩千座之多,主要集中于臨沂、棗莊、濟寧、臨淄等地。[17]其中畫像石就有上萬件,墓碑三十三件,墓闕四件。濟寧是山東漢墓文化的集中地,其中曲阜孔林是孔子、孔子后裔及孔氏家族的專用墓地。兩千多年來,孔氏族人死后多葬于此,從未間斷,成為現今我國年代最久、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氏族墓葬群。林內萬木掩映,墳冢累累,碑碣林立,石雕成群。豐富的孔氏墓碑是國內漢碑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保存完整、數量眾多、形制規整,為研究漢代石碑形制的最佳標本。《孔謙碑》、《孔君墓碑》、《韓勑修孔子墓碑》、《孔宙碑》、《孔彪碑》、《孔褒碑》、《汝南周府君碑額》等已移至曲阜漢魏晉碑刻陳列館。境內墓碑并非孤立于墳冢前,部分墓冢前配置祠堂、石闕、石碑、石獸等石刻組件,它們形成一套完整的漢代墓上石刻體系,為古代陵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現今濟寧嘉祥武氏祠、金鄉魯峻祠仍保存完整。
在厚葬時風的影響下,漢人在墓室形制和結構上都極力模仿現實生后地面住宅,各類隨葬品也是應有盡有,正所謂“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圣人為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于世,光榮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發屋賣業。”[18]如此喪葬必然要耗資巨大,漢代許多石刻中記錄了制作物所付費用。例如:莒南縣孟莊廟的《莒南孫氏闕》銘文記錄其石闕耗資約一萬五千;平邑城北八阜頂《南武陽功曹闕》資費共計四萬五千錢;曲阜防山公社《徐家村北漢墓祠堂》費用上萬錢;現藏法國的山東《文叔陽食堂題記》記錄其祠堂修建共值一萬七千;嘉祥宋山出土的《許安國祠堂題記》中記錄其所作祠堂花費萬錢;嘉祥武氏祠的《武氏闕銘》載武氏祠石闕價十五萬,石獅子四萬。
由此可見,漢代各類石刻花費是何等高昂,難怪漢末造成“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的嚴重現象。而在如此耗資巨大的厚葬背后中,生者是否真正盡以孝心,誠待逝者呢?上述的石刻題記從石匠名師的姓名羅列,到石闕、石獅、祠堂的耗資價位,再到工程的費力長久,生者孝心可謂昭然若揭,而此番孝心也難免使人感到生者那炫耀、吹噓、浮夸的諂媚之態。從現今考古發現,兩漢山東墓葬祠堂和墓室主人多為社會中下層人士。據《武榮碑》碑文記錄,身份最高者是武氏前石室祠主人武榮,他官任執金吾;《武開明碑》中記載武開明曾官居吳郡府丞;武梁官秩僅為百石從事。社會中下層對祠堂和墓闕圖像的重視可能與其能夠供人參觀有關,喪家借參觀之時炫耀財力和孝心,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漢代士人常在墓上祠堂和墓祭銘文中要刻寫名工姓名和所費錢財。
孔子在《論語》中對逝者的喪事、追懷、祭祀有這樣的概括“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焉”,其強調的喪葬是要有誠德厚重之心。兩漢時期,社會遵從儒學文化,以儒家之仁、義、禮、智、信作為人們行善的標準,倡導以孝治天下。此時的喪葬也重“厚”,但這種“厚”是對物質財富的追捧與炫耀,所行之禮隆重龐大,所制之物鋪張奢華,人們追求的是一種孝心的外在物質表現,以“利”為重,欲以厚葬而揚名。難怪王符如此批判到:“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后,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后生之痛者也。”[19]
參考文獻:
[1]左丘明.左傳[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
[2]孟子.孟子·梁惠王[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
[3][6][16]王充.論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4][5][11]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7][15]張道一.畫像石鑒賞[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9.
[8]朱劍心.金石學·說石[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9]趙超.中國古代墓志通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巫鴻.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M].上海:三聯書店,2006.
[12]范曄.后漢書·列女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3]令狐德棻.周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1.
[14]劉敬叔.異苑[M].北京:中華書局,1996.
[17]鄭同修.楊愛國.山東漢代墓葬形制初論[J].華夏考古,1996,(4).
[18]恒寬.鹽鐵論·散不足[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2.
[19]王符.潛夫論箋校正[M].北京:中華書局,1985. (責任編輯:周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