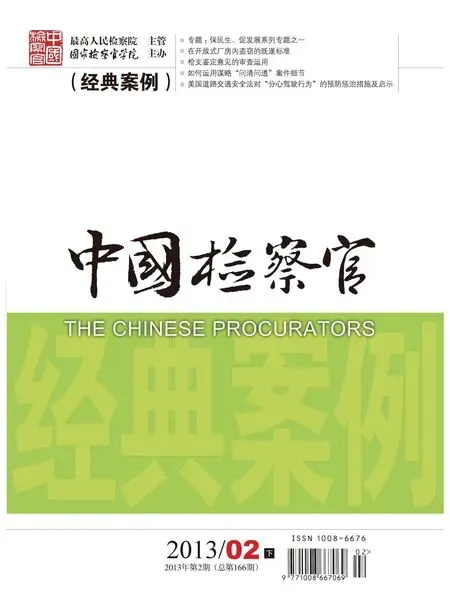毒品犯罪中“以販賣為目的而非法收買”的具體判斷
文◎陳久紅 王東海
本文案例啟示:對毒品犯罪中“以販賣為目的”的判斷要擺脫傳統的“供有則有、供無則無”的口供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堅持從客觀到主觀、從物證書證到言詞證據的邏輯對證據進行審查,以查證屬實的“非法購買”這一基礎事實和毒品的數量、販賣所用工具等相關證據推定行為人“販賣目的”的存在。在行為人沒有明確的證據或證據線索對推定事實構成合理懷疑時,可以認定其具有“販賣目的”,進而構成販賣毒品罪。
[基本案情]2012年11月7日中午1時許,劉某以2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從黃某處購得冰毒896.4克,存放于其承租的房屋內。公安機關通過偵查發現之后,于當日下午5時許將正要外出的劉某抓獲,當場從其身上查獲冰毒一袋,凈重49.6克。隨后,民警對劉某租賃的房屋進行搜查,在臥室的衣柜內查獲用透明塑料封口袋包裝的冰毒17袋 (每袋重量為49.5克到50克不等,連同從其身上查獲的冰毒共計896.4克),并從其臥室內查獲電子秤2臺、封鎖機1臺、透明密封塑料口袋40多個、手機2部等物品。劉某辯稱,購買冰毒是為了吸食,將冰毒分成重量基本相同的18小袋進行包裝是為了方便攜帶,購買電子秤是為了在買菜后方便稱重,封鎖機是朋友暫時存放在其租賃房的。
一、分歧意見
對于該案犯罪嫌疑人劉某行為的定性,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理由是劉某在供述中稱購買毒品是為了吸食,沒有販賣毒品的前科,在購買毒品后沒有販賣行為,也沒有其他證據能夠證明其主觀上具有“販賣目的”。因此,不能認定劉某的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根據查明的事實和證據,劉某明知是毒品且在沒有合法依據的情況下非法持有,數量已達到我國刑法第348條所規定的追訴標準,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論處。
第二種觀點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理由是犯罪嫌疑人劉某購買的毒品數量遠遠超出了其吸食的劑量,并且從其家中查獲電子秤2臺、封鎖機1臺、透明密封塑料口袋40多個。在檢察機關承辦人對其電子秤、封鎖機、透明塑料袋的用途進行訊問時,劉某不能做出合理解釋,因為劉某稱電子秤是為了買菜做飯時核對菜的重量,但在其承租的房屋內沒有廚具,鄰居證實沒見過有人住,房東證實天然氣表的數字和在將房屋出租給劉某時相差無幾;追問劉某哪個朋友將封鎖機放置在其承租屋時,劉某無法提供該人的姓名、地址、聯系方式等。因此,應推定劉某具有“販賣目的”,劉某的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
二、法理釋評
我們同意第二種觀點。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劉某主觀上是否具有“販賣目的”,因為根據1994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 《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和2012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頒布的 《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三)》第1條之規定,“‘販賣’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銷售或者以販賣為目的而非法收買的行為。”如果認定劉某主觀上具有“販賣目的”,則應認定劉某的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反之,則應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我們認為,從劉某的客觀行為來看,應當認定劉某主觀上具有“販賣目的”,其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
(一)前提性的澄清
對本案進行釋評之前,必須解決的一個前提性問題就是“販賣目的”是否要求有相應的客觀行為與之相對應。因為第一種觀點認為,證明劉某主觀上具有“販賣目的”的情形之一就是劉某在購買毒品后實施了販賣行為。對于多數的故意犯罪而言,故意的內容與構成要件的客觀要素具有對應性,即構成要件的客觀要素規制著故意的內容。“但是,目的犯中的目的、傾向犯中的內心傾向、表現犯中的內心經過(心理過程),則不要求存在與之相對應的客觀事實,只要存在于行為人的內心即可。”[1]它是一種主觀的超過要素。雖然“販賣目的”的實現,需要行為人在非法收買毒品之后再實施販賣行為,但是根據《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和《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三)》第1條關于“販賣”含義的界定,只要行為人以實施販賣為目的而實施了非法購買行為,就以犯罪 (既遂)論處,而不需要行為人在實施非法購買毒品的行為之后再實施販賣行為。[2]這種目的犯在刑法理論上被稱為“短縮的二行為犯”,即“‘完整’的犯罪行為原本由兩個行為組成,但刑法規定,只要行為人以實施第二個行為為目的實施了第一個行為 (即短縮的二行為犯的實行行為),就以犯罪(既遂)論處,而不要求行為人客觀上實施第二個行為;與此同時,如果行為人不以實施第二個行為為目的,即使客觀上實施了第一個行為,也不成立犯罪(或僅成立其他犯罪)。”[3]因此,第一種觀點中以劉某在實施非法購買行為之后進而再實施販賣行為來判斷其主觀上的販賣目的是不可取的,該種做法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也與短縮的二行為犯的理論相悖。
(二)認定主觀事實的邏輯與方法
“以販賣為目的而非法收買”中的“販賣目的”是一種主觀要素或者事實,它不像客觀事實那樣可以通過人類感官直接感知或認知,而是“需要通過其他的間接證據所形成的證據鏈并依靠推論(推定)的方法加以輔助顯現。”[4]主觀事實的認定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不但困擾著我國大陸的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同時也困擾著域外和其他國家的學者和司法者,對其認定需要經過外部資料進行判斷已成為共識。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認為,“深藏于內心的主觀事實,不像外表的行為可以直接看見,并直接表述于審判者面前,他人無從窺見其內心,只有從其他情況事實,間接地推論方可得知。 ”[5]德國學者指出,“在查明故意、特定意圖和動機等心理要素時會遇到很多很大的困難,只有從外部事實及心理學上法則進行必要的反推,才有可能解決這些問題。”[6]我們認為,對案件主觀事實的認定,從邏輯上來說,需要擺脫以口供為中心的慣性思維,建立起一種從客觀到主觀、從物證書證到言詞證據的邏輯思維;從具體方法上來說,需要合理運用刑事推定原則。
1.審查案件證據的邏輯思維。司法者需要形成從客觀到主觀、從物證書證到言詞證據、從外圍證據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解的邏輯思維過程。打破傳統的口供為先、以口供為中心、從供到證的思維范式,杜絕僅根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來認定案件的主觀事實。從工具理性的角度來說,物證、書證等客觀證據優于言詞證據。因為言詞證據具有可變、難以固定的特性,“對于每一個提供言詞證據的人,隨著時間、地點和提取的人的不同,言詞證據的內容都有可能發生變化。”[7]特別是對于犯罪嫌疑人來說,基于趨利避害的本能他們很少承認自己的真實意圖,為逃避法律的懲罰而百般辯解成為其第一選擇。與言詞證據相比,物證、書證則以客觀存在的實物及其反映形象證明案件事實,具有客觀性,“物證不會因為證人的存在而缺席。物證不會發生錯誤。物證不會作偽證,只有物證的解釋才可能出現錯誤。”[8]從價值理性的角度來說,遵從從客觀到主觀、從書證物證到言詞證據、從證到供的證據審查邏輯,符合人類的認知圖式,有利于司法人員客觀公正地查明案件事實,是對新刑訴法規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的具體貫徹落實。因為這種審查邏輯是對口供中心主義的超越,可以減少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
2.認定案件主觀事實的具體方法運用。主觀事實因深藏于行為人的內心而難以認定,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難以認定不等于不能認定,因為主觀事實在具備主觀性特征的同時也具備客觀性的特征,即人的主觀意識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它不是純粹的主觀自生的事物,而且,行為人的主觀心理態度會通過其客觀行為外向化、客觀化。這便為化解刑事主觀事實證明的難題提供了有效路徑,即司法人員在認定案件的主觀事實時,應當全面考察行為人的行為以及與行為相關的因素,綜合分析全案證據,根據行為人的客觀行為來反推其主觀心理態度,科學合理地運用刑事推定原則。
刑事推定是訴訟中一種重要的事實認定方法和司法證明方法,是指“裁判者根據已經得到證明的基礎事實,認定存在推定事實。”[9]它是解決主觀事實證明難題的一個有效途徑。雖然說刑事推定不是主觀臆斷,更不是有罪推定,[10]但是它畢竟只是一種事實推定,是一種相對的證明而不是絕對的認知判斷,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沖破罪刑法定原則的危險,對于其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必須嚴格限制。在具體運用過程中,應當從三個方面進行把握:一是用作推定依據的基礎事實必須真實可靠且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具有 “常態聯系”。基礎事實真實可靠,是指基礎事實得到證據的證明,且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的常態聯系,是指“當基礎事實存在時,推定事實也存在的概率極高,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具有近似于充分條件的邏輯關系。”但是,應當注意的是兩者之間“具有高度蓋然性的或然性聯系,而非必然性聯系。”[11]二是在證明標準上,無論是對于司法機關來說還是對處于反駁立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來說,證明標準只要達到高度蓋然性即可,無須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因為,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來說,他們不承擔自證其罪的責任且舉證能力有限,要求其反駁的證明標準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會增加他們提出辯護的門檻、降低成功的幾率;對于司法機關來說,設置和運用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通過轉移證明責任來緩釋嚴格證明的難度,如果要求其證明標準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那么刑事推定的存在基礎就會蕩然無存。[12]三是必須設置反駁程序,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駁權。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針對基礎事實或推定事實的反駁具有具體明確的證據支撐或可調查的證據線索,經查證屬實后構成對推定事實的合理懷疑,那么就應當否定推定事實的存在。
(三)回歸到本案的具體分析
依照上述我們所提倡的審查案件證據的邏輯思維,對本案證據進行審查便應當從搜查筆錄、扣押物品清單、房屋租賃合同、毒品稱重記錄、手機通話清單、尿液檢測報告書、毒品檢驗報告等物證和書證開始,再到劉某承租房的鄰居、房東以及同案人黃某等人的證言,最后再看犯罪嫌疑人劉某的供述。尿液檢測報告書證明劉某系吸毒人員,其與其他物證書證可以聯合證明劉某明知是毒品而非法購買持有這一事實,同案人黃某的指證則進一步印證了該事實。據此,認定劉某的行為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已不存在疑問。這一證據審查和事實認定過程,是對傳統的“供有則有,供無則無”的口供中心主義的超越,有效地擺脫了單一依靠口供這一直接證據認定事實的模式及其容易導致刑訊逼供的弊端,堅守了證據裁判原則。當然,對于本案來說,進行到這一步還沒有完結,因為在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行為中,行為人都會非法持有毒品,只有在犯罪分子拒不供認,又無證據認定構成走私、販賣、運輸、制造、窩藏毒品罪中任何一種罪的情況下,才能認定其行為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這就需要綜合審查案件證據,對劉某的行為進行進一步的判斷,即判斷劉某的行為是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還是構成走私、販賣、運輸、制造、窩藏毒品罪中的其他犯罪。根據上述司法解釋對于“販賣”含義的界定可知,如果劉某具有“販賣目的”,則應當認定其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而對劉某是否具有“販賣目的”的判斷需要科學合理地運用刑事推定原則。
對于刑事推定原則運用時應當把握的三個方面,前已述及,不再贅述。結合本案來說,首先,本案的基礎事實是劉某非法收買毒品,這一事實已經得到案件現有證據的證明,且已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并且,非法收買毒品這一基礎事實和我們所要推定的販賣毒品這一事實存在著 “高度蓋然性的或然性聯系”。因為對于購買大量毒品的人來說,供自己吸食的可能性較小,購買之后往往是為了販賣。其次,在證明標準上,對劉某構成販賣毒品罪的證明并不需要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即對劉某的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判斷是基于其非法收買行為而進行的推定,并不要求劉某客觀上實施了販賣毒品的行為。在證據的把握上也就不要求有交易毒品的毒資、購買人的證言等證明劉某實施了販賣行為的證據。對于劉某反駁證據的把握同樣如此,如果劉某對其販賣事實即“販賣目的”的反駁具有證據支撐,便可否認推定的販賣事實的存在。所謂的反駁事實比如購買毒品是為了吸食,電子秤、封鎖機、塑料袋等不是其本人所有或另有用途等。再次,設置反駁程序就是對案件進行審查時,司法人員需要貫徹直接言詞原則,以現有的證據為基礎,用推定的事實對劉某進行訊問。如果劉某的反駁具有證據支撐或可調查的證據線索,且經查證屬實后構成對推定事實的合理懷疑,那么就應當否定推定事實的存在,只能認定劉某的行為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如果劉某不能提供相關的證據支撐其反駁,或者其無法對司法人員針對推定事實提出的問題做出合理解釋,那么就應當認定推定事實成立,即劉某的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劉某在公安機關的多次供述中,均稱購買冰毒是為了吸食,否認其“販賣目的”的存在。檢察機關承辦人在依法對犯罪嫌疑人劉某進行訊問時,問劉某購買毒品的用途,劉某依然堅稱是為了吸食,承辦人便抓住現有證據繼續對其發問,問其在社區是吃低保的人從何處拿來20萬元人民幣,吃低保怎么還一次性的花費20萬元來購買毒品,每天吸食毒品的劑量,從其租賃的房屋搜出的電子秤、封鎖機、40多個透明塑料封口袋的所有人、用途,為何將冰毒分成重量基本相同的18小袋。劉某辯稱20萬元是之前做生意存下來的,但這一辯解被之后對其銀行賬戶的查詢和其妻子的證言所否定;劉某現年57歲,其購買如此多的毒品用來吸食要吸食多長時間?這顯然不合常理;其辯解電子秤用途是核對做飯買菜時菜的重量,但被房東提供的自劉某承租后天然氣的用量幾乎未動和鄰居從未見到劉某買菜以及在房屋內并未搜查出飯鍋、碗筷等做飯用具這些事實所推翻;其稱封鎖機是朋友存放在租賃房屋,但在承辦人問其朋友的姓名、住址、聯系方式時無法回答;其稱透明塑料封口袋是當天為分裝毒品時買多了,但其提供的購買透明塑料封口袋的地址經查系虛構;其辯稱分裝成18小袋是方便吸食時攜帶,但不可能一次性吸食40多克,也不必分裝成重量基本相同的小袋。據此,我們認為應推定劉某主觀上具有“販賣目的”,其針對主觀上沒有販賣目的的反駁不成立。
三、余論
本案推定劉某主觀上具有“販賣目的”,進而認定其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不但具有學理上的支撐,同時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正如學者所言,刑事訴訟法的該條規定為化解主觀事實的證明這一世界性的難題提供了理論基礎、開了一扇窗。[13]
注釋:
[1]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17頁。
[2]對于司法實踐中將“以販賣為目的而非法收買的行為”認定為犯罪既遂的作法,有學者提出了質疑,認為該種行為應當作為犯罪預備或非法持有毒品罪來認定。參見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7頁。
[3]張明楷:《論短縮的二行為犯》,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3期,第148頁。
[4]高銘暄、孫道萃:《論詐騙犯罪主觀目的的認定》,載《法治研究》2012年第2期。
[5]周叔厚:《證據法論》,臺灣三民書局 2000年版,第22頁。
[6][德]岡特·施特拉騰韋特、洛塔爾·庫倫:《刑法總論Ⅰ—犯罪論》,楊萌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頁。
[7]張軍:《刑事證據規則理解與適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頁。
[8][美]威廉·奇澤姆等:《犯罪重建》,劉靜坤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頁。
[9]樊崇義、吳光升:《論犯罪目的之推定與推論》,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
[10]張旭、張曙:《也論刑事推定》,載《法學評論》2009年第1期。
[11]張云鵬:《刑事推定研究》,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20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14頁。
[12]孫道萃、黃帥燕:《刑事主觀事實的證明問題初探》,載《證據科學》2011年第5期。
[13]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