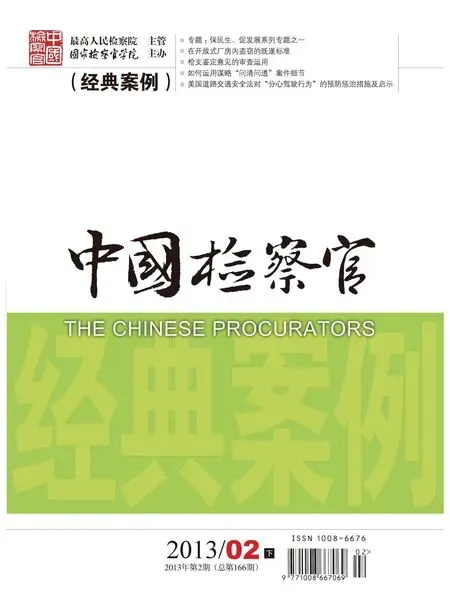刑法立法中的倫理訴求*
文◎徐翠翠
本文案例啟示:盜竊骨灰盒進而敲詐公墓等單位或死者近親屬的,其手段行為構成盜竊尸體罪,目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鑒于此類案件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權利,更嚴重侵犯了社會倫理秩序和善良風俗,因此應以盜竊尸體罪和敲詐勒索罪進行數罪并罰。。
[基本案情]2011年8月12日凌晨,被告人劉某、李某經事先預謀,翻墻進入杭州市蕭山區蜀山街道某某公墓,盜取公墓內某墓穴內的骨灰盒后,將該骨灰盒藏匿于一空墓穴內。當日下午,被告人李某用手機多次致電某某公墓大廳,稱已竊取了公墓內的一只骨灰盒,要求某某公墓拿出現金60萬元贖回該骨灰盒。2011年8月25日下午,被告人李某用手機再次致電某某公墓大廳,獲取了某某公墓負責人的手機號碼后聯系了負責人,與其談妥以8萬元的價格贖回該骨灰盒并約定在蕭山區長途汽車站交易,后被告人劉某、李某在長途汽車站附近被公安民警抓獲。經審理,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法院認定被告人劉某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3000元;被告人李某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3000元。
本案中被告人劉某、李某主要實施了盜竊骨灰盒和利用骨灰盒進行敲詐公墓錢財兩個行為,首先,盜竊骨灰盒的手段行為構成盜竊尸體罪,不構成盜竊罪。其次,利用贖回骨灰盒進行敲詐公墓錢財的目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具體而言:
一、手段行為構成盜竊尸體罪,不構成盜竊罪
骨灰盒,屬于民法上一種特殊的物,其雖然具有一般的財產價值,但更多的具有哀悼、緬懷死者的紀念意義,是具有人格意義的特殊的物,是受法律保護的。這里需要明確的是,對尸體、墳墓等保護是對死者人格的保護,但不是對死者人格權或人格利益的保護,因為自然人一旦死亡即喪失權利主體資格,不再享有人格權和屬于私益的人格利益,這里維護的是保護死者人格不受侵害的公序良俗和其近親屬的人格利益。骨灰盒所體現的法益是社會的公共倫理秩序和善良風俗,而不是財產權益,故而本案中秘密竊取骨灰盒的行為不構成侵犯財產法益的盜竊罪。
刑法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302條規定,秘密竊取尸體或者公然侮辱尸體的行為構成盜竊、侮辱尸體罪。對于該罪中的尸體應作如何認定,理論上和實踐中大致有三派觀點。最廣義說認為,“尸體,既包括整具遺體,又包括尸體的部分、遺骨、遺發,還可包括遺灰、殮物等。 ”[1]狹義說認為:“所謂尸體,指自然人死亡之后所遺留的軀體,尚未死亡的被害人的身體,不是尸體,無生命的尸體,如已蛻化分離的,則為遺骨或遺發,不能稱為尸體,尸體不以完整無缺為必要。”[2]張明楷教授認為:“尸體,是指已經死亡的人的身體的全部或者一部。尸骨或遺骨不等于尸體,但從實質上看,盜竊尸骨的行為也可能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從法律解釋上講,將尸骨解釋為尸體,也不存在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嫌。孕婦腹中的死亡胎兒,即使具有人的形體,也不是尸體;骨灰不是尸體。 ”[3]最狹義說認為:“尸體,是指已死亡之人完整的軀體,但如果尸體已經腐爛成為尸骨,不能認為是本罪所講的尸體。”[4]2002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 《關于盜竊骨灰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答復》指出,“骨灰”不屬于刑法第302條規定的“尸體”。對于盜竊骨灰的行為不能以刑法第302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顯然該司法解釋傾向于對尸體作狹義解釋。筆者認為,在我國大部分地區普遍實行火葬制度的今天,骨灰已經逐漸取代尸體而成為近親屬寄托哀思的物,盜取骨灰盒的行為,同樣侵犯了社會的公共倫理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客體。同時,筆者注意到在司法實踐中盜竊骨灰盒已經不是罕見的個案,在本溪、蕭山、、楚雄、武進、個舊等地均有發生,而大部分法院的做法是以敲詐勒索罪一罪論處,[5]這種做法沒有實現對上述行為的全面法律評價,使得一些嚴重破壞社會倫理秩序的行為逃脫了法律追究。綜上,筆者認為應對尸體作擴大解釋將骨灰包括在內,故而上述盜竊骨灰盒的手段行為構成盜竊尸體罪。
二、目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
刑法在侵犯財產罪一章第274條規定,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目的,對被害人以威脅或者要挾的方法,迫使其交付公私財物的行為。本案中被告人劉某、李某利用贖回骨灰盒進行敲詐公墓錢財的目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具體而言:
首先,本案的犯罪對象有公墓的錢財和骨灰盒,所對應侵犯的犯罪客體為公墓的財產所有權和死者近親屬的人格利益,而后者是公民的人身權中的人格權的組成部分,故而本案中的行為侵犯了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的雙重客體。
其次,本案中的行為符合了敲詐勒索罪的行為邏輯結構:行為人實施威脅—對方產生恐懼心理—對方基于恐懼心理交付財產—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產—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詳言之,被告人劉某、李某利用骨灰盒對死者近親屬具有特殊人格利益作為籌碼,對公墓管理人員進行精神威脅,迫使其交付錢財贖回骨灰盒,手段極其惡劣,嚴重侵犯了公墓的財產權利和死者近親屬的人格利益。
三、類案的量刑處理意見
筆者通過檢索北大法寶里盜竊骨灰盒進而敲詐公墓或死者被害人錢財的二十幾份判決書發現,司法實踐中均以敲詐勒索罪一罪論處的,而且量刑和普通的敲詐勒索罪并無二致。至于法院是認為盜竊骨灰盒不構成盜竊尸體罪,還是依照牽連犯擇一重罪處斷的原則得出的結論,從判決書中無法得知。不過,筆者認為,對上述類案,應以盜竊尸體罪和敲詐勒索罪進行數罪并罰,方能實現對類案進行全面的法律評價,理由如下:
就盜竊骨灰盒進行敲詐勒索錢財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或者違法性而言,運用不同的違法性學說,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理論中,法益侵害說和規范違反說是關于違法性實質的兩種最基本的觀點。法益侵害說是把違法性的本質作為結果無價值來把握,該論從法益侵害的結果中尋求違法性的本質,又稱為物的違法觀,是對于行為引起的法益侵害或者威脅(危險)所作的否定評價,即結果“惡”。其認為違法性的根據在于行為對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脅的結果,只要不存在對法益的侵害那么也就無所謂犯罪。而規范違反說是把違法性的本質作為行為無價值來把握,該論認為違法性的根據在于行為本身的樣態(反倫理性)以及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認為違法的實質在于與國家所承認的文化規范,或者說是國家的社會倫理規范的不相容。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是其違法性的本質,之所以違法是由于行為人違反了對法規范的忠誠義務。目前徹底的結果無價值和徹底的行為無價值出現融合的趨勢,折中說乃主流觀點,因此,在分析行為的違法性時,既要考察行為造成的法益危害,又要考量行為本身的倫理非難性。
上述類案中的行為,不僅造成了財產法益損害的危害結果,比侵犯財產法益更為嚴重的是違反了“事死如事生”的孝倫理傳統,有傷社會風化,給死者近親屬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傷害。在民法上,侵害死者近親屬人格利益,是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而對侵犯最低限度的倫理道德的上述行為,刑法立法是否理應做出反應,以尊重社會倫理訴求呢?偷盜骨灰盒的行為,盡管其本身的財產價值微乎其微,但是百善孝為先,該行為給死者近親屬造成了嚴重的精神痛苦,使得近親屬對死者的敬畏感情遭到了嚴重傷害,這比偷盜他人同樣價值物品的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痛苦要大得多,其應受社會倫理非難性和社會危害性也嚴重得多,故而應對手段行為進行獨立的法律評價,認定為盜竊尸體罪。按照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將偷盜他人同樣價值物品的行為和偷盜骨灰盒的行為在量刑上一視同仁呢?
依據刑法第274條規定,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而2000年5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關于敲詐勒索罪數額認定標準問題的規定》中指出,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以一千元至三千元為起點;敲詐勒索公私財物 “數額巨大”,以一萬元至三萬元為起點。另外,2010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中指出,構成敲詐勒索罪的,可以根據下列不同情形在相應的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1)達到數額較大起點的,可以在三個月拘役至六個月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2)達到數額巨大起點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同時進一步明確,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可以根據敲詐勒索數額、手段等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劉某、李某欲敲詐勒索公墓8萬元,顯然已超過3萬元的標準達到數額巨大,盡管考慮本案中兩被告人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最終判處兩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3000元,仍有量刑羈輕之嫌,究其根源乃是忽略考慮了本案中手段行為的倫理非難性。在進行違法性判斷時,如果完全摒棄行為本身的倫理非難性,那么盜竊骨灰盒的行為和盜竊同樣財產價值的其他物品的行為,在量刑上理應一致,但是,這樣的處理結果顯然違背了刑法的正義價值追求,如本案判決書中僅以敲詐勒索罪一罪論處,是無法實現對類案的全面法律評價的。故而,鑒于此類案件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權利,更嚴重侵犯了社會倫理秩序和善良風俗,應以盜竊尸體罪和敲詐勒索罪進行數罪并罰。
四、余思:在刑法立法中應尊重倫理訴求
刑法結構即犯罪圈與刑罰量的配置,犯罪圈大小體現為刑事法網嚴密程度、刑罰量輕重即為法定刑的苛厲程度。刑法結構主要包括罪刑關系、犯罪圈大小和刑罰嚴厲程度三個方面,其中犯罪圈的合理劃定是保證刑法結構合理的核心內容,那么劃定犯罪圈應該堅持什么樣的標準呢?從應然的角度,一種行為,在刑法上被認為是犯罪行為,那么其也是違背社會倫理規范的惡的行為,反之,違背社會倫理規范的惡的行為,如果嚴重脫逸社會相當性則會被刑法評價為犯罪行為,即罪與惡是一致的。但是,在實然的層面,罪與惡并不總是一致的,罪與惡的統一是刑法立法永恒追求的目標。“對于公民個人而言,當罪與惡的評價相統一時,惡的評價本身會強化刑法在公民心目中的正義形象,對犯罪人的懲罰會使公民感受到來自國家的關愛,刑罰帶給人們的是正義感和安全感;當罪與惡的評價不統一時,惡的評價本身會使公民的頭頂布滿陰霾,宣告一個人有罪傳達出的是國家的蠻橫,對罪犯適用刑罰則會叫人民膽戰心驚、倍感欺凌。”[6]故而,在刑法立法中尊重倫理訴求,是獲得民眾的道德認同,樹立刑法的權威,實現刑法的正義價值目標所不可或缺的,也是刑法的終極人文關懷之所在。故筆者建議,在刑法第302條之后增加一款,作為第302條之一,“盜竊骨灰盒的,以盜竊尸體罪論處,盜竊骨灰盒后對死者近親屬或公墓等單位進行敲詐勒索的,以盜竊尸體罪和敲詐勒索罪進行數罪并罰。”
刑法立法除了要注重對財產權利、人身權利等個體法益的保護,更要注重尊重和體現社會倫理訴求,以更好地實現刑法的正義價值。倫理不僅包含著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以及人與自我之間關系處理中的行為規范,而且也深刻地蘊涵著依照一定原則來規范行為的深刻道理。刑法是一種文化鏡像,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的歷史積淀,是特定國家或者地區文化事實的縮影。在刑法立法中體現倫理訴求,可以實現“罪”與“惡”的統一,法律與道德的協調,從而逐步減少乃至消除司法實踐中“情”與“法”的沖突。我們講“法不融情”,這里的“情”是指個人的私情,而不是指社會倫理秩序和善良風俗,社會倫理卻恰恰應該和法水乳交融的。在刑法立法中尊重倫理訴求,既埋下了“良法之治”的火種,也打下了“守法之治”的根基。
注釋:
[1]趙秉志:《中國刑法適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2頁。
[2]陳家林:《盜竊、侮辱尸體罪若干問題研究》,載《當代法學》2003年第10期。
[3]張明楷:《刑法學》(第 3 版),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第777頁。
[4]陳興良:《刑法疏議》,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頁。
[5]參見 http://vip.chinalawinfo.com/Case/Result.asp?SFlag=11,訪問日期2013年1月27日。
[6]張武舉:《刑法的倫理基礎》,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