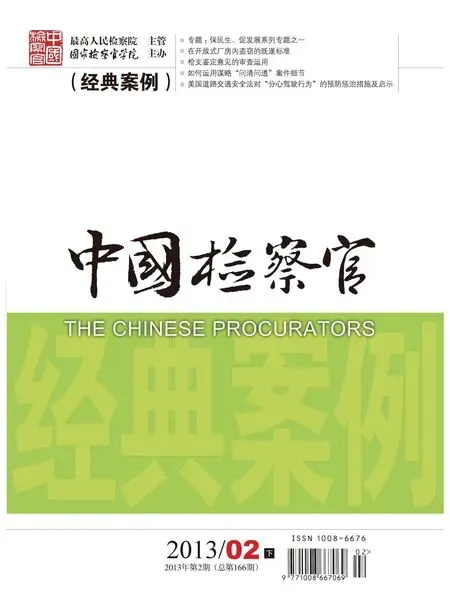介紹嫖娼是否構成介紹賣淫罪
文◎張云波
介紹嫖娼是否構成介紹賣淫罪
文◎張云波*
*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100043]
一、基本案情
某公司老板安排公司員工甲接待外地來的三個朋友乙、丙、丁。甲安排三人入住賓館后,乙提建議嫖娼,丙、丁表示同意,三人請甲幫忙聯系賣淫女,由丙給甲900元人民幣作為支付嫖資的費用。甲知道其曾經去過的某足療店有賣淫女,便電話聯系該足療店經營者戊,說明要帶三名賣淫女去某賓館賣淫,戊表示同意。甲到達該足療店后,戊安排賣淫女A、B、C跟隨甲去賓館,甲向戊支付嫖資900元。甲帶領賣淫女A、B、C到達賓館后,將三人分別帶至乙、丙、丁所在房間,在賣淫嫖娼活動正在進行時,民警將A、B、C、乙、丙、丁六人抓獲,后又將甲、戊抓獲。
二、分歧意見
對于足療店經營者戊的行為構成介紹賣淫罪沒有爭議,但對于甲的行為是否構成介紹賣淫罪,則存在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甲在主觀上具有促成賣淫嫖娼活動得以實現的故意,客觀上幫著聯系賣淫女,聯系到賣淫女后帶至乙、丙、丁所在賓館房間,使得賣淫嫖娼活動得以實現,在賣淫者和嫖娼者之間起到了明顯的牽線搭橋的作用,應當以介紹賣淫罪論處。
第二種觀點認為,介紹賣淫罪是一種有立場的犯罪,即行為人應當站在服務賣淫者的立場、以促成賣淫者實現賣淫活動為目的,雖然甲在賣淫者與嫖娼者之間進行了引見,對促成賣淫嫖娼活動起到積極作用,但其立場是服務嫖娼者、以促成意欲嫖娼者實現嫖娼活動為目的,其行為屬于介紹嫖娼行為,而非介紹賣淫行為,不能以介紹賣淫罪論處。
三、評析意見
(一)介紹賣淫與介紹嫖娼的聯系與區別
所謂介紹賣淫,是指為賣淫者介紹嫖客的淫媒行為,表現為替賣淫者尋找、招徠、介紹嫖客,在賣淫者和嫖客之間牽線搭橋、溝通撮合,使賣淫嫖娼活動得以實現的行為。所謂介紹嫖娼,嚴格意義上講,主要是指為嫖客介紹何處有賣淫者、如何聯系賣淫者或者直接將嫖客帶往賣淫場所的行為。[1]賣淫與嫖娼具有對合關系,無論是替賣淫者聯系嫖客(介紹賣淫),還是替嫖客聯系賣淫者(介紹嫖娼),行為所聯結的都是賣淫者和嫖客,行為目的都是促成賣淫嫖娼活動的實現,行為人所起的都是一種居間作用。所以,從總體上看,介紹賣淫和介紹嫖娼都是一種淫媒行為。但是,二者仍有若干不同點:
第一,服務對象不同,或者立場不同。介紹賣淫者是直接為賣淫人員服務的,站在促成賣淫者實現賣淫的立場上,一般與賣淫者關系比較密切,對賣淫者的情況比較了解,有的直接受雇于賣淫者,有的則對賣淫者有相當強的控制力。介紹嫖娼者則是服務于嫖客的,站在促成嫖客實現嫖娼的立場上,一般與嫖客關系密切,表現為朋友關系或者客戶關系,而與賣淫者往往并不認識。
第二,是否具有營利目的不同。雖然刑法并不要求介紹賣淫罪以營利為目的,但現實生活中典型的介紹賣淫者通常與賣淫者利益相關,無論與賣淫者是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還是受雇傭與雇傭的關系,常常會從賣淫者收取的嫖資里抽取介紹費或者按比例提成。而介紹嫖娼者為嫖客尋找、聯系賣淫女或者是出于共同娛樂的動機,或者是因與嫖客存在生意往來要感謝對方的動機,通常不具有營利目的。
第三,活動頻率不同,社會危害性有異。介紹賣淫者通常與賣淫者形成利益共同體,為追求獲利,其實施的介紹賣淫活動具有經常性、多發性的特點,且常會伴隨有容留賣淫行為,特殊情況下甚至會向組織賣淫行為轉化,社會危害性較大。而介紹嫖娼行為通常具有偶發性、突然性的特點,介紹嫖娼者往往是針對特定的對象臨時起意為其介紹嫖娼,或者應特定對象的請托而為之,一次介紹嫖娼行為實施后何時再次實施不具有可預見性,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
雖然介紹嫖娼與介紹賣淫在一般情況下會存在上述不同,但也不能武斷地認為一切介紹嫖娼行為都不能認定為介紹賣淫犯罪。曾有觀點認為,1994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30條將介紹賣淫和介紹嫖娼區分為兩種行為并規定了處罰措施,但1997年修訂的刑法第359條僅將介紹他人賣淫行為規定為犯罪,這說明立法者的意圖是將介紹賣淫作犯罪化處理,將介紹嫖娼作非犯罪化處理。對此,筆者不敢茍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30條第1款規定:“嚴厲禁止賣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紹或者容留賣淫、嫖宿暗娼,違者處15日以下拘留、警告、責令具結悔過或者依照規定實行勞動教養,可以并處5千元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難發現,此處雖然將介紹賣淫和介紹嫖娼作了區分,但從該文用分號連接的后半部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看,無論是介紹賣淫還是介紹嫖娼,都存在涉嫌犯罪的可能,立法者并沒有排除將介紹嫖娼作犯罪化處理的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法律用語簡潔化的要求,這也可以從200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內容得到確認。該法取消了《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30條的內容,而是直接采納刑法第359條第1款的表達方式,該法第67條規定:“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的,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5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5日以下拘留或者5百元以下罰款。”很顯然,該法取消對介紹賣淫與介紹嫖娼作區分的表述方式不是說介紹嫖娼不再具有違法性,而是出于用語簡潔的考慮,做到與刑法的銜接。
(二)介紹嫖娼行為的定性和處理
其實,無論是介紹賣淫還是介紹嫖娼,都有一般意義上的行為與刑法意義上的行為的區分。不是所有的介紹嫖娼都能認定為犯罪,所有的介紹賣淫也不能都認定為犯罪。學界對介紹賣淫罪的定義有多種表述,但強調更多的是行為人要在賣淫者與嫖娼者之間起到溝通、聯系的居間作用,而未要求行為人一定要站在服務賣淫者的立場或者服務嫖娼者的立場。因此,判斷介紹嫖娼行為能否認定為介紹賣淫罪,關鍵是看介紹嫖娼者是否在賣淫者與嫖娼者之間起到了明顯的居間作用,特殊情況下,還要辨清介紹嫖娼者與介紹賣淫者之間的關系以及是否存在介紹賣淫的共同故意。具體而言,“如果介紹賣淫和介紹嫖娼由二人以上經預謀或勾結在一起分工協作完成,不論是否以營利為目的,營利后分成與否,均可構成共同介紹賣淫犯罪,反之雙方沒有任何關系,兩個行為是完全分開、獨立的,則對介紹嫖娼者而言,不能認為是犯罪。”[2]
從實踐看,介紹嫖娼行為通常存在以下情形:(1)行為人為嫖客提供賣淫者的聯系方式(如將從路邊撿到的招嫖卡片提供給對方),或者為其介紹賣淫嫖娼場所,而與賣淫者或賣淫場所管理者無任何聯絡;(2)行為人親自帶領嫖客到賣淫場所,行為人事先與賣淫者或賣淫場所管理者無任何聯絡;(3)行為人為滿足嫖客嫖娼的意愿,尋找、聯系賣淫者并將其帶至嫖客住處;(4)行為人基于與賣淫者的約定,介紹嫖客與該賣淫者進行賣淫嫖娼活動;(5)行為人基于其與某介紹賣淫者的約定,介紹嫖客通過該賣淫者與賣淫人員進行賣淫嫖娼活動。[3]
對于第一種情形,行為人只是單純地提供賣淫活動的信息,為嫖客提供了便利,并未直接在賣淫者與嫖客之間牽線搭橋、溝通撮合,因而不能以介紹賣淫罪論處。對于第二種情形,應當區別對待:如果行為人僅將嫖客帶至賣淫場所,本人未進入場所,且未參與商談賣淫嫖娼事宜,則不屬于介紹賣淫罪;如果行為人不僅將嫖客帶至賣淫場所,還負責聯系賣淫者、商談嫖資、幫助嫖客挑選賣淫者,那么雖然其事先與賣淫者或賣淫場所管理者之間無任何聯絡,但其在促成賣淫嫖娼過程中起到了明顯的居間作用,無論其本人是否參與嫖娼,都應當認定其涉嫌實施了介紹賣淫犯罪。在第三種情形下,行為人在賣淫者與嫖客之間起到了明顯的居間作用,其行為原本是介紹嫖娼,其行為目的也幫助嫖客實現嫖娼,但在行為過程中其行為卻又演變成介紹賣淫(帶領賣淫女到嫖客處),屬于介紹嫖娼轉化為介紹賣淫的情況,可以構成介紹賣淫罪論。如果行為人是與賣淫女的管理者聯系的,那么其與該管理者構成介紹賣淫犯罪的的共犯。后兩種情形實際上是介紹嫖娼者與介紹賣淫者二者合二為一,行為人表現為具有雙重身份,其行為屬于介紹賣淫與介紹嫖娼相重疊的情形,可以構成介紹賣淫罪。
(三)本案的處理
本案中,甲的行為屬于上述第三種情形。甲應意欲嫖娼者乙、丙、丁的請求尋找、聯系賣淫者,屬于服務嫖客、以幫助嫖客實現嫖娼為目的的介紹嫖娼行為。甲與足療店經營者戊聯系、商量要帶三名賣淫者去嫖客所在賓館得到戊的同意,是與戊進行介紹賣淫行為的意思聯絡,二人形成介紹賣淫的共同犯罪故意。甲將賣淫者A、B、C分別帶至乙、丙、丁所在賓館房間促成賣淫嫖娼活動的實現,屬于甲直接實施了促成賣淫者實現賣淫的介紹賣淫行為。從甲行為過程的整體看,其既有介紹嫖娼行為,也有與介紹賣淫者進行犯意聯絡產生共同犯罪故意進而直接實施介紹賣淫的行為,其介紹嫖娼行為在后來轉化成了介紹賣淫行為,應將其與戊認定為共犯,以介紹賣淫罪論處。
注釋:
[1]劉德權主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觀點集成》(刑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960頁。
[2]劉德權主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觀點集成》(刑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961頁。
[3]參見程敬文、徐偉、孟猛:《吳祥海介紹賣淫案——介紹賣淫罪與介紹嫖娼行為的區別》,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中國刑事審判指導案例4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頁。
【本期主講】
張寶珠,畢業于華東政法大學偵查學專業,現任江蘇省張家港市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偵查二科副科長。自2006年參加工作以來,共主辦、參辦貪污賄賂案件三十余件,其中多起案件受到上級嘉獎。2012年,在該院作為新刑事訴訟法實施試點單位背景下,積極思考,勤于總結,努力為對接新刑訴法出謀劃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