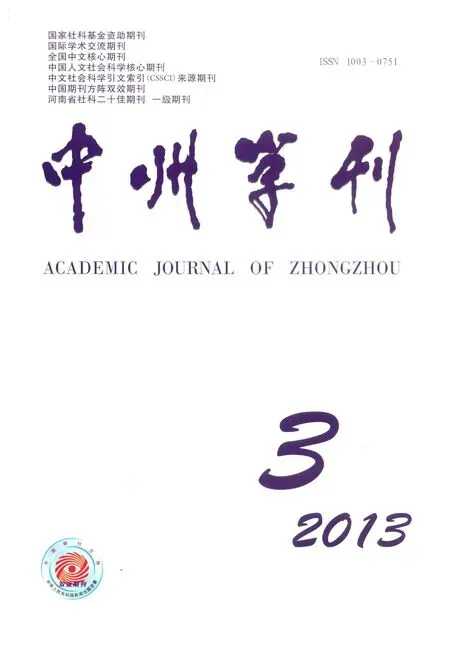從“氏”的本義看氏與姓、氏與族之間的關系*
蔡英杰
《說文》認為氏來自于巴蜀方言,為山崖側(cè)邊附著而將要墮落的山巖。這一說法素來遭人詬病,徐復觀先生即提出質(zhì)疑:“若不能證明初造氏字之人,出自蜀產(chǎn),則何能援巴蜀之特殊字形以造此字。且只要從小篆追溯上去,即可發(fā)現(xiàn)氏字之原形,與許氏所說的山岸欲墮的情形渺不相應。”①那么,氏之本義為何?“氏族”的意義是由本義生出還是源自假借?氏與姓、氏與族之間的關系怎樣?搞清這些問題,并不僅僅只是文字訓詁的問題,而是對于人類學、歷史學都極具意義的事情。
一、氏的本義
《說文》:“氏,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聞數(shù)百里,象形。凡氏之屬皆從氏。揚雄賦,響若氏隤。”②許氏說解之失,上引徐復觀文已指出。除此之外,許氏所引的書證也成問題。氏字起源甚古,甲骨文、金文就已習見,先秦文獻中更有大量用例,許氏找不出符合其說解的例證,故只能以后出揚雄文中的孤例充數(shù)。后世對于氏字之本義意見紛紜,大體以朱駿聲、郭沫若、丁山為代表。
朱駿聲指出了許慎說解之失,但卻犯了和許氏同樣的毛病。《說文通訓定聲》氏字下云:“按許說此字非是。因小篆橫視似篆書山而附會之耳。本訓當為木本,轉(zhuǎn)注當為姓氏,蓋取水源木本之誼。”③朱氏正確指出了許氏說解錯誤的根源在于以篆書之字形附會氏之本義,但朱氏本人卻重蹈了許氏覆轍。他援引《漢簡》引《石經(jīng)》氏之字形作為依據(jù),判斷氏之本義為木本。篆書字形已不可靠,比篆書晚出之《石經(jīng)》字形又怎能靠得住呢?,金文作、、、,與《石經(jīng)》之字形相去遠矣,朱氏之說因此不攻自破。
郭沫若開始從甲骨文字形分析氏之本義,這個方向無疑是正確的。《金文余釋之余·釋氏》云:“氏者余謂乃匙之初文。《說文》:‘匙,匕也。從匕,是聲。’段注云:‘《方言》曰:匕謂之匙。’……今江蘇人所謂茶匙湯匙也……古氏字形與匕近似;以聲而言,則氏匙相同;是氏乃匙之初文矣。”④郭氏之說,徐復觀先生已指出其誤。其一,匙既從匕是聲,則匕乃匙之初文,何得以氏為匙之初文?其二,匕形契文作或,與甲骨文氏作大不相同。氏形下端垂直,若為匙之初文,將何以取物?⑤郭氏雖從正確的方向出發(fā),但仍未能得到氏的本義。其失誤在于,先從語音出發(fā),主觀假定氏乃匙之本字,然后強迫字形就范,把本來形狀與形態(tài)都相距甚大的匕字與氏字認定為相似。對于漢字本義的考釋,必須充分尊重原始文字本身呈現(xiàn)出來的形音義的客觀性,任何主觀的臆斷,都只能與事實的真相愈來愈遠。
丁山認為,氏即示字,示為祭天的圖騰柱,因而氏之本義亦為祭天的圖騰柱。“在氏族社會,以圖騰為宗神,每個家族的閭里之口都立有圖騰柱(Totem Pole)以保護他們的氏族”⑥,因而圖騰柱儼然成為氏族的象征。丁氏之說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其一,甲骨卜辭所稱示者,非為天神,實為人神,即商族之先公先王,因此把示解釋為祭天的圖騰柱并不可靠,遠不如釋作神主有理有據(jù)。其二,甲文(示)與(氏)雖然近似,但分別之際宛然。示之上筆為一平直的橫畫,氏之上筆則為一向右下垂并略微卷曲的斜畫,這一平一斜正是二者的區(qū)別性標志,因而示字之上還可再加一橫畫構(gòu)成,氏字之上則不可再加上一橫畫,示字之下可在豎畫的兩端加點,構(gòu)成八字形的字綴(),氏之下則不能添加字綴。丁氏之說雖不精審,但其見解是建立在武丁時代所有的貞卜例外刻辭基礎之上的,距離事實的真相已經(jīng)不遠了。
要想破解氏之本義的謎底,既要顧及到語言內(nèi)的形音義的因素,又要顧及到語言外的社會發(fā)展的歷史。當此二者能夠相合而不相違,且能彼此互證之時,氏的本義也就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了。
《左傳·僖公五年》:“均服振振,取虢之旗。”⑨又《左傳·閔公二年》:“衛(wèi)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⑩周代天子分封諸侯,“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之旗,是國的象征,也是氏的象征。“取虢之旗”,意味著虢國的滅亡,也意味著虢氏的滅亡。衛(wèi)侯寧愿招致集中打擊,也“不去其旗”,因為這個旗是族旗,也是國旗,是氏族與國家的象征,“去其旗”即意味著衛(wèi)氏與衛(wèi)國的覆滅。《周禮·春官宗伯·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11]周代大夫立家,立家也就是新建了一個氏,所謂“家各象其號”,也就是在旗幟上描繪象征其氏的徽號。《儀禮·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赤巠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鄭玄注:“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12]有氏者才能銘旌,隱含了氏與旗的對應關系,這里的旌(旗),無疑是代表大夫、士所屬的氏族的旗幟,惟其如此,才能發(fā)揮識別作用。
二、氏與姓的關系
《說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從女,從生,生亦聲。《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13]這里包含了兩個重要的信息。其一,在姓產(chǎn)生之時,還處于母系氏族社會,因此部落首領知母不知父,姓源于女性始祖。其二,姓是“因生”而產(chǎn)生,源自于女性始祖創(chuàng)生本族的傳說,表達了對本族生命本原的認同。在原始思維里,自然萬物和人類之間可以相互生成和轉(zhuǎn)換。原始部落的人們認為自己的祖先源自自然界的某一事物,這個事物就成為他們的圖騰,也就是姓。姓的誕生表現(xiàn)了原始人類欲借助某種自然力增強自身力量、提升自身信心的愿望,因而不是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姓多來自于創(chuàng)生神話,三代的夏族、商族、周族的姓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
禹父鯀,妻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帝王紀)[14]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商頌·玄鳥》)[15]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記·殷本紀)[16]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史記·周本紀》)[17]
在夏族的神話傳說中,夏的女始祖修己吞食了薏苡狀的神珠,懷孕生下了夏族的男性始祖禹。夏族以姒為姓,源自薏苡。(上古音,姒,邪母之部,苡,余母之部,反映了語音的變化,在夏族創(chuàng)生神話產(chǎn)生的時代,二字當同音。)在商族的創(chuàng)生神話中,商族的女始祖簡狄吞食了玄鳥之卵,懷孕生下了商族的男性始祖契。商族以子為姓,就源自于玄鳥之卵(鳥卵為子)。在周族的神話傳說中,周的女始祖姜嫄踩了熊的腳印,懷孕生下了周的男性始祖后稷。周族以姬為姓,實源自熊。(上古音,姬,見母之部,熊,匣母蒸部。見匣鄰紐,之蒸對轉(zhuǎn),語音相近。在周族創(chuàng)生神話產(chǎn)生之時,姬、熊當同音。)
現(xiàn)代漢字中,仍保存了一些以女為偏旁的姓,如姜、姞、嬴、姚、媯、妘、姺、娸等,這些都是原始的古姓,這些古姓成為姓源于女性始祖這一歷史事實的活化石。
綜上所述,姓反映的是部落的自然屬性,用于別血緣;氏反映的是部落的社會屬性,用以別族團。遠古部落,都需要有自己部落與其他部落的區(qū)別性標志,但并非所有的部落都有自己的創(chuàng)生神話,因而每個部落都有氏,但并非每個部落都有姓。《莊子·馬蹄》:“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18]上博簡《容成氏》:“容成氏、尊盧氏、赫胥氏、喬結(jié)氏、倉頡氏、軒轅氏、神農(nóng)氏、祝融氏、伏羲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賢。”容成、尊盧、赫胥、喬結(jié)、倉頡、軒轅、神農(nóng)、祝融、伏羲等等,都是遠古部落,這些部落除軒轅、神農(nóng)、伏羲、祝融之外,均有氏而無姓。《國語·晉語》:“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嬉、嬛、依是也。惟玄囂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19]“黃帝之子二十五宗”是黃帝部落聯(lián)盟之下的25個子部落,這25個子部落無疑都有自己的氏,但只有14個部落有自己的姓。這14個部落中,青陽與夷鼓同為己姓,玄囂與蒼林同為姬姓,故實際只有12姓。姓聯(lián)結(jié)血緣,所以黃帝聯(lián)盟屬下的25個部落,只有玄囂與蒼林兩個部落為黃帝后裔,其他部落與黃帝應當沒有血緣關系。五帝當中,黃帝軒轅氏(一說有熊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堯陶唐氏、舜有虞氏,他們的氏,或來自于所居之地,或來自于崇拜對象,要之,都是他們部落的標識。五帝之姓,黃帝、顓頊、帝嚳皆姬姓,堯姓伊祁,舜姓姚(一說姓媯),后世人為的痕跡比較明顯。他們都是古史傳說中著名的部落聯(lián)盟的首領,如果同出一系,這種姓的雜亂現(xiàn)象是無法解釋的。我們有理由認為,在遠古的部落社會中,氏的出現(xiàn)在前,姓的出現(xiàn)在后。作為部落的區(qū)別標識,氏伴隨著部落的出現(xiàn)而出現(xiàn);作為聯(lián)系血緣的紐帶與高貴身份的象征,姓有可能伴隨著一種壟斷權(quán)力的出現(xiàn)而出現(xiàn),姓的產(chǎn)生,應不早于堯舜時期。
夏商二代,只有天子、天子后裔的封國及一些重要方國的首領才有姓有氏。《國語·周語》:“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yǎng)物豐民人也。”[20]剝除皇天賜姓名氏的偽托之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信息:大禹部落以娰為姓,以夏為氏;四岳部落以姜為姓,以呂為氏。《史記·夏本紀》:“禹為姒姓,其后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21]《詩·商頌·長發(fā)》:“韋顧既伐,昆吾夏桀。”[22]姒姓夏部落之十六氏,夏后(夏)為天子之氏,其他十五氏皆為天子后裔封國之氏。《史記·殷本紀》:“契為子姓,其后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同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23]《逸周書·商誓》:“告爾伊、舊、何、父、幾、耿、肅、摯,乃殷之舊官人。[24]子姓殷部落,殷當為天子之氏,來、宋、空同、稚、北殷、目夷、伊、舊、何、父、幾、耿、肅、摯等氏均為天子后裔封國之氏。劉師培《氏族原始論》:“古之所謂有國者,不稱部而稱氏。《孝經(jīng)緯》云:‘古之所謂國也,氏即國也。’吾即此語,推而闡之,知古帝所標之氏,乃指國名,非系號名。如盤古氏,即盤古之國。陶唐為帝堯之國,故曰陶唐氏。有虞為帝舜之國,故曰有虞氏。夏為大禹之國,故曰夏后氏。若夫共工氏、防風氏,則乃諸侯之有國者也。可知古之所謂氏者,氏即國也。《左傳》言:‘胙之土而命之氏。’此氏字最古之義,無土蓋無氏矣。”[25]劉氏所論,大致符合夏商以前的情況。
據(jù)丁山先生考證,甲骨刻辭中所見到的商代的氏族有200多個,這200多個氏包含了多少姓很難考證,但毫無疑問,姓應大大少于氏的數(shù)量。其原因有二:一是許多氏族有氏無姓;二是一個姓可以分化為若干個氏(前文姒姓、子姓的分化可證)。夏代以前,姓在范圍上與氏基本一致,同姓不同氏的情況很少,夏代以后,同姓不同氏的情況明顯增多了。周代實行宗法制,不僅天子可以“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也可以“胙之土而命之氏”,得天子命氏者為諸侯,得諸侯命氏者為大夫。天子、諸侯、大夫如系同一血緣,則為同一個姓,但卻有各自不同的氏。氏乃姓之分支,姓為氏的宗主,由此形成了“姓一定而不易,氏遞出而不窮”的局面。姓是血緣關系的紐帶,用以“別婚姻”;氏是政治權(quán)力的標志,用以“別貴賤”。
春秋以降,由于政治權(quán)力的下移,諸侯逐漸喪失了命氏的特權(quán),氏的“別貴賤”的功用也逐漸喪失。徐復觀先生把春秋以降氏的產(chǎn)生分為四個階段,其中春秋中前期包含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賜氏為特典。第二階段,以賜氏為照例的政治行為。第三階段,貴族自行命氏。第一、第二階段,率按宗法規(guī)定,以王父(祖父)之字為氏。到了第三階段,氏的命名已無宗法統(tǒng)系可言,有以父之字為氏的,有以官為氏的,有以邑為氏的。春秋末期至戰(zhàn)國時期為第四階段,這一時期,由于社會的劇烈變化,不少貴族淪為皂隸,而平民躍升于上層。平民血緣集團的代表人物乃自行命氏,于是有以職業(yè)、以居地為氏的情形出現(xiàn)。[26]氏不僅徹底與宗法制度失去聯(lián)系,而且喪失了作為地位與權(quán)力象征的作用,成為單純的家族血緣關系的標志,氏演變成了姓,姓與氏,變成了二名一實的東西。《史記》屢謂“姓某氏”者,即揭示了以氏為姓這一史實。
三、氏與族的關系
《說文》:“族,矢縫也。束之族族也。從□,從矢。”[27]許氏以族為鏃的本字,誤。族字所從之□,正是標志本部落的旗幟,所從之矢,表示族不僅是以血緣為統(tǒng)系的集團,而且是一個軍事單位。族內(nèi)成員,平時為民,戰(zhàn)時為兵,因此族就是部落,是一個兵民合一的集團。部落平時稱氏,打仗時由部落精壯人員構(gòu)成的軍事單位則稱族。部落、氏、族是統(tǒng)一的,部落名即是氏名,也是族名。五帝時期,形成了部落聯(lián)盟,黃帝、炎帝、蚩尤等皆為部落聯(lián)盟的首領。部落聯(lián)盟下有若干子部落,每一個子部落就是一個族,也是一個氏。
炎帝欲侵凌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制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zhàn)于阪泉之野。三戰(zhàn),然后得其志。”(《史記·五帝本紀》)[28]
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國語·楚語》)[29]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張守節(jié)撰《史記正義》引《龍魚河圖》)[30]
熊、羆、貔、貅、貙、虎為6種獸名,應是黃帝有熊部落中6個子部落的名稱。熊、羆、貔、貅、貙、虎是部落的徽幟,因此這6個部落,也就是6個氏族。九黎,應當是蚩尤統(tǒng)率的東夷部落集團屬下的9個子部落,也就是9個氏族。所謂“蚩尤兄弟八十一人”,應是這9個子部落繁衍分化出來的81個小部落。每個小部落都是一個作戰(zhàn)單位,也就是一個族,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平行的,因此稱為兄弟,并非指蚩尤有81個兄弟。范文瀾說:“九黎當是九個部落的聯(lián)盟,每個部落又包含九個兄弟氏族,共八十一個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領,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個氏族酋長。”[31]九、八十一都泛指其多,未必是確數(shù)。九黎戰(zhàn)敗以后,其勢大衰,但他們還據(jù)有黃河下游和長江中下游一帶的廣闊地區(qū)。到堯、舜、禹時期,他們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聯(lián)盟。這就是史書上說的“三苗”,又稱為“有苗”或“苗民”。
進入夏商,部落首領大都成為侯伯,也就是諸侯,建立了國家。商王朝直接控制內(nèi)的諸侯稱侯,直接控制外的諸侯稱伯,卜辭所謂“某侯”、“某伯”之“某”,既是國名,亦是氏名。商王直屬的部族稱王族,商王諸子所屬的部族則稱子族。如:
己亥貞:令王族追召方。(南明六一六)
已卯卜,充貞:令多子族從犬侯璞(撲)周,古王事。五月(續(xù)五、二、二)
王族,是商王嫡系的部族,王是族名,不是氏名,其氏名當為商。所謂多子族,當為多個子族,它們?yōu)闆]有繼承王位的商王諸子建立的部族,子族一般擁有封國,國名即氏名。如:
“子不”為子族之一。據(jù)考證,“不”即“邳”,其所在區(qū)域在今江蘇邳縣。[32]“不”既是國名,亦是氏名。子族之下,還有小子族。小子族,當為子族族長諸子建立的分族,小子族當有封邑而無封國,他們沒有獨立的氏名,其氏名沿用其宗主——子族之氏。如:
周代實行宗法制,諸侯之子,如果不能成為直接繼承人,五代以后,就要另立門戶。《禮記·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后也。宗其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另立門戶者則要立族命氏,諸侯因而取得了命氏的權(quán)力。《左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以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34]徐復觀先生說:“諸侯以字為氏,是指諸侯對其同姓的卿大夫的命氏方法而言。……以其王父之字為其氏,使其死后的子孫,一面仍得因其王父之字而得知其氏之所自出;同時亦因此而許其另開一支,以團結(jié)其族人,而自相繁衍。……眾仲所說的‘官有世功,則有世族,邑亦如之。’這是指諸侯賜異姓者之氏而言。官是仕于朝廷,邑是仕于都邑。諸侯對異姓者的賜氏,不能按照宗法的身份制度,而改用以勛勞為標準的制度。我們要注意‘世功’兩字。世功,是世世代代有功。世世代代有功,則世世代代相傳下來,必定子孫眾多。但若不賜之以氏,則此世代有功之人,并沒有代表這些眾多子孫的資格而自成一族,以成為以血統(tǒng)為內(nèi)容的固定政治勢力。為了酬庸報功,便賜以他世代所作之官、所宰之邑的名稱,以作為他的氏的名稱,使他的眾多子孫,團結(jié)于所賜的氏名之下而成為一族,而他為之長。”[35]《左傳·昭公十七年》:“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風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36]郯子托名少皞,其實反映的是周代以官為氏的事實。周代之氏,有宗氏,有分族之氏。“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宗氏即小宗之氏,即諸侯別子之后始得之氏。別子之后又有分族,分族所得之氏即為分族之氏。以魯國三桓言之,桓公別子慶父、叔牙、季友之后分別得賜孟氏、叔孫氏、季氏,是為宗氏。孟氏之后分出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氏之后分出叔仲氏,季氏之后,分出公鈕氏、公輔氏,南宮氏、子服氏、叔仲氏、公鈕氏、公輔氏皆為分族之氏。《左傳·昭公三年》:“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晉國大夫叔向的宗氏為羊舌,羊舌氏之后,分出十族,這十族所得之氏,即為分族之氏。《左傳·昭公五年》:“箕襄、邢帶(杜注: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杜注: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杜注: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37]韓氏五族,其宗氏均為韓,分族之氏有箕、邢等;羊舌四族,為叔向兄弟在羊舌宗族下的分族,其宗氏皆為羊舌,分族之氏有銅鞮、楊等。春秋末年,晉國貴族立氏已不需要得到國君的冊命,只要到太史處登記即可。脫離原來的宗族,即可獲得新的氏名。《國語·晉語九》:“智宣子將立瑤為后。智果曰:‘……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及智氏之亡也,惟輔果在。”[38]
春秋中葉以后,宗法制逐漸遭到破壞。總的來看,命氏的權(quán)力已不再掌握在天子或國君手里。[39]春秋末期以后,姓氏合一,平民皆得以有姓,由姓而構(gòu)成宗族,也就是說具有血緣關系的同姓就構(gòu)成了一個宗族。《白虎通·宗族》云:“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恩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40]族是血緣組織,同時也是社會組織。宗族之間平時通有無,相憐恤,亂時則可聚集族內(nèi)力量,抵御外來侵擾。東漢中葉以后,由宗族而滋生出門第,唐中葉以后,門第趨于衰微。
氏字,有人訓山陵欲墮之石,有人訓木之根本,有人訓匙,有人訓示(圖騰柱)。或望文生義,強就字形以說字義;或望音生義,強就字音以說字形;或觀念先行,把外來的理論與漢字字形字義強加比附。凡此種種,都不免有主觀、片面之失。文字是文化的載體,是人們對客觀世界認識成果的沉淀,古文字考釋,如果僅僅著眼于語言內(nèi)部的文字、音韻、訓詁諸因素,不能跟當時社會發(fā)展情況密切結(jié)合起來,就往往流于膚淺而不能深入;古代歷史、文化的研究如果不依靠古文字的考釋,就往往流于主觀,而缺少驗證。只有把二者結(jié)合起來,融會貫通,才能避免主觀性、片面性,得出比較扎實可靠的結(jié)論。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