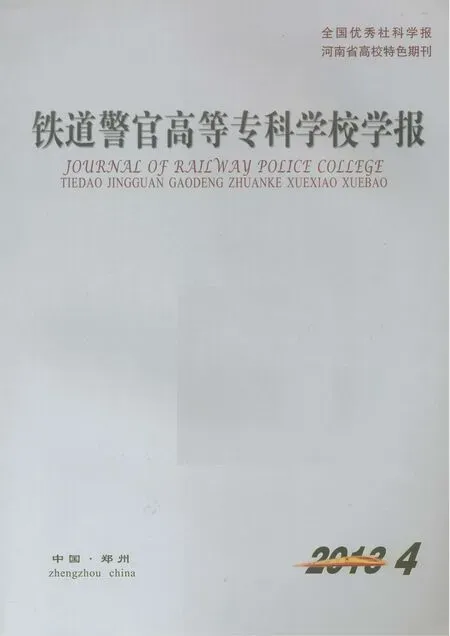以重解學生固有知識的方式確立其法律思維
——法學課程案例教學法新解
李淼
(鐵道警察學院公安基礎教研部,河南鄭州 450053)
以重解學生固有知識的方式確立其法律思維
——法學課程案例教學法新解
李淼
(鐵道警察學院公安基礎教研部,河南鄭州 450053)
在法學課程中,案例教學法具有諸多的優勢。案例教學法在英美國家興盛是基于其獨特的法治文化背景。在我國的法學教育過程中可以借鑒案例教學法,但是卻不能全盤照搬,而應當結合我國現實的背景對這種教學方法進行變通使用,使其發揮最佳效果。重解學生固有知識就是一種對案例教學法的創新使用。
案例教學法;判例教學法;法律思維
一、案例教學法的優勢
案例教學法(Case Method)是19世紀70年代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蘭德爾(C.C.Langdell)首創,時至今日,經歷實踐考驗的案例教學法在美國法學院受到廣泛信服并普遍使用。此教學法通過研究法官的判決來掌握法律原則與法律推理,在教學法上以蘇格拉底問題討論法代替傳統的課堂講授,故又被稱為蘇格拉底方法[1]。我國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引入這種實用型的教學方法的。關于法學教育中案例教學法的概念界定,我國教育界存在分歧,但是仍就其特點達成了基本共識:在案例教學中,教師要創設一種能夠使學生獨立探究的情境而不是提供現成的知識,以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著力培養學生的知識運用、邏輯思維、語言表達和開拓創新等綜合能力[2]。
案例教學法能夠為學生提供一種法律環境,在這種特定環境中進行法律分析,通過對案例的分析和討論,讓學生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運用所學的法學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以使其在教學過程中得到實踐鍛煉,使知識轉化為能力。通過典型案例的呈現,學生經過對典型案例大量相關資料的閱讀、分析、討論與辯駁,不僅能理解與掌握法學理論知識,而且還能使學到的理論鮮活生動起來,學生就此能夠受到啟發,由此及彼,融會貫通,順利實現知識的遷移和認識的提高。案例教學法通過對案例的分析、提問、討論、辯論,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分析能力、邏輯思維能力、法律思辨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同時,也能適應當前國家實行的統一司法考試的需求,促使法學教學模式與統一司法考試的接軌[3]。所以,無論是從實際能力提高的需要、司法實踐的需要、司法考試的需要以及適應法律職業教育目標的需要,案例教學法都不失為一種極佳的教學方法。
二、純粹的案例教學法在我國缺乏相應的背景條件
(一)我國的法律淵源及判決書特點不適合純粹的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具備種種優點,但這種教學方法的產生以及在英美國家的盛行卻有著獨特的法治背景。眾所周知,美國是典型的普通法系國家,主要以判例法為法律淵源,法官的判決就是法律,而他們的案例教學法中的“案例”實際上就是法院的已決判例,所以,Case Method在美國實際上指的是判例教學法;而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法律體系具有大陸法系的特點,在案件的審理判決中,依據的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并不采用“遵循先例”的原則,法院的生效判決并不是以后類似案件的裁判依據,而且我國法院的判決書內容簡單概括,不足以作為分析案情的依據。近年來,我國的裁判文書雖然在說理方面已有相當程度的重視和改進,但還存在很大不足,在事實認定上缺乏對證據的論證和辯駁,說理也不夠充分,缺乏針對性,僅從判決書中無法了解并分析討論具體案情及其法理依據。相反,美國法院的判決書說理透徹、語言優美、結構嚴謹,美國法院的判決非常強調法官對案情的努力思考和清晰的文字描述,重視對認證結果的公開,要求法官在裁判文書中對證據的取舍理由及心證過程進行說明。美國聯邦法院法官中心的《法官寫作手冊》認為:“書面文字連接法院和公眾。除了很少的例外情況,法院是通過司法判決同當事人、律師、其他法院和整個社會聯系和溝通的。不管法院的法定和憲法地位如何,最終的書面文字是法院權威的源泉和衡量標準。因此,判決正確還是不夠的,它還必須是公正的、合理的、容易讓人理解的。司法判決的任務是向整個社會解釋,說明該判決是根據原則作出的好的判決,并說服整個社會,使公眾滿意。”我國法院的判決書則不具備如此豐富的內容,暫時也無法達到與整個社會聯系和溝通的效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國法學教育中的案例教學法不具備絕對效仿美國判例教學法的基礎,我們的案例教學法中的案例選擇也就不能只局限于已決案件的判決,因為這些判決無法提供討論分析的具體內容。
(二)我國的法治文化背景不適合純粹的案例教學法
我國法學教育缺乏實施單純的案例教學法的法治文化背景。法治是在歐洲本土萌芽壯大的,歐洲自古希臘時代就有法治的傳統,之后又較早地形成了法治文化的經濟基礎——商品經濟。后來,法治文化隨著歐洲在北美的移民也擴散到了美國,甚至獲得了更深更廣的發展。所以,法治意識是歐美的根本性文化,而無需人為的移植、栽培。中國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商品經濟的發展比較晚,相對比較落后。中國長期全面地受到儒家文化的支配,而儒家文化常常與法治文化相異、甚至相反[4]。這就意味著由于現實社會中缺乏法治文化環境的熏陶,中國公民本身缺乏法治文化的價值取向和法治的思維模式。要實行法學教育的案例教學法,則需要教育對象具備基本的法律功底以及相應的法律思維,這樣才能適應案例教學法的特點。
(三)我國法學教育的設置階段不適合純粹的案例教學法
美國正式的法學教育始于研究生階段,是已經接受了通識教育的大學畢業生的一種具有職業傾向性的選擇,任何專業甚至包括數學專業的畢業生都可以申請攻讀法學院的研究生,畢業之后通過律師資格考試,他們就可以從事律師這一職業,而法官、檢察官一般要從這些執業律師中選拔,所以美國的法學教育可以說是一種職業教育,一種以培養律師為目標的職業教育;而且在他們看來,法律是一門淵博的社會學,中學畢業的學生沒有任何社會閱歷和經驗,根本就無法透徹地理解法律的精髓,只有隨著年齡的增長,接受了通識教育,積累了社會經驗,思想成熟之后,才能把握法律的博大精深。美國大法官霍布斯曾斷言:“法律的靈魂從來不是邏輯,而始終是經驗。”所以美國的法學教育針對的對象是已經大學畢業的成年人,教育的目標是要將其培養成合格的律師。對于這些具備基本法律功底和成熟思維能力的成年人來講,純粹的案例教學法是卓有成效的。相反,我國的法學教育自大學階段就開始設置,在法律功底全無、思想不成熟、社會經驗也基本為零的狀態下,采取單純的案例教學法,其效果不容樂觀。即使在課堂上生搬硬套地運用這種教學方法,也會使學生一頭霧水,無從下手,最多聽個熱鬧,使案例教學法流于形式,到司法實踐的場合,仍然不知所措。鑒于以上分析,要使案例教學法發揮其應有的優勢,取得良好的法學教育效果,就必須先使學生具備一定的法律基礎,培養出他們的法律思維(要在短期內達到這一目標,就離不開傳統的講授法)。在這樣的前提下,結合運用案例教學法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案例教學法的創新應用:重解學生固有知識
(一)恰當案例的選擇是案例教學法的關鍵
上文已經闡明我國法學教育所能實行的案例教學法有別于美國的判例教學法,更鑒于我國法律的系統性、抽象性、理論性,案例教學法必須與傳統的講授法結合使用。而要保證案例教學法本身的效果,關鍵問題就是要恰當地選擇案例范圍,唯有如此,才能通過對案例的分析討論,解釋成文法的內容,加深對成文法的理解和運用。
目前,關于案例的選擇范圍,有論者認為應當在真實的案例當中進行選擇,認為真實的案例有利于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5];有論者認為所選的案例應當具有時效性,應選擇新鮮的案例[6];另有論者認為,案例教學法中所選的案例既可以是真實案例,也可以是虛擬案例,只要能延展學生的思維空間,提高其思辨能力以及對法律的實際應用能力,實現教學目標,都可以在案例教學中使用[7]。筆者認同第三種觀點。在我國,經過法院判決的案例公開的數量有限,而且真實案例其具體的案情是既定的,在需要例解相關理論時,未必就能搜集到相應的真實案例,這樣就勢必影響到案例教學法的正常開展。而虛擬案例則可以根據課程教學的需要進行相應的創作,把需要對學生進行加強訓練的理論巧妙地糅合到案例當中,以提高學生的分析應用能力。設置虛擬案例,還可以拓展學生的想象空間,增強其學習的興趣和熱情。同時,所選擇的案例,還應包括所有具有法律意蘊的事例,甚至是一些文學作品中的內容,只要能幫助學生提高探知法律事實的能力,使其法律思維能力及法律表達能力得到鍛煉,都可以拿來在課堂上作為案例進行分析討論。因此,在案例選擇的時候,不必糾結于案例真實與否,應當采取真實案例與虛擬案例相結合的方式。除了真實案例與虛擬案例相結合,案例選擇恰當與否的另一重要判斷標準還應當是是否具有針對性。在課堂教學中所選擇的案例要切合所教授的內容,要做到有的放矢,有針對性地開展案例教學,不能脫離教學實際。
“溫故而知新”是學習的一般規律,是孔子對我國教育學的重大貢獻之一,他認為,不斷溫習所學過的知識,從而可以獲得新知識。這一學習方法不僅在古代有其價值,在今天也有不可否認的適用性。人們的新知識、新學問往往都是在過去所學知識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溫故而知新是一個十分可行的學習方法。另外,從人的心理角度來看,人在學習新知識的過程中,對熟知的內容更具敏感度,就好似他鄉遇故知,胸中會產生愉悅感。因此,在案例教學過程中,雖然有針對性地選擇新奇、新鮮的案例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一種途徑,但是,有針對性地選擇學生早期已經掌握的固有知識或者事例,從中導引出現代的法律闡釋,則更能引起學生的共鳴,使其感覺到面對新知識,自己并非毫無準備,原先的固有知識雖然與法律無關,但卻可以為學習法律奠定基礎,無形之中可以增強學習的信心。在法治觀念淡薄、法律思維欠缺的環境中,從學生固有的知識背景里搜尋出具有法律意蘊的蛛絲馬跡,能夠在舊知識與新知識之間、非法治文化與法治文化之間搭建起一架橋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法律功底的先天不足。故此,在法學課程的案例教學過程中,把目光投向學生熟知的內容,重解學生的固有知識,不失為一種獨辟蹊徑選擇恰當案例的方式。當然這種獨特方法的實施也離不開傳統的課堂講授法的配合。
(二)重解學生固有知識之例解
雖然在接受大學階段的正規法學教育之前,學生直接接觸到的法律知識較少,但是在平時的學習與日常生活中,學生涉獵到的其他方面的知識已經相當豐富。筆者在此選出兩例,以期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1.關于寓言故事“殺雞儆猴”的法學解讀
“殺雞儆猴”這則寓言故事盡人皆知,說的是殺掉雞來嚇唬猴子,比喻懲戒一個以警戒其余。這一故事就可以與刑法學中刑罰的功能以及死刑的威懾力建立聯系。當我們在刑法學課程中講到刑罰的威懾功能時,就可以選擇這則寓言故事作為案例進行分析討論,討論刑罰如何發揮其威懾功能以及死刑是否就具有最大的威懾力。所謂刑罰的功能指的是刑罰的制定、裁量與執行過程中對社會可能產生的積極作用,根據對象的不同刑罰的功能可以分為刑罰對犯罪人的功能、刑罰對被害人的功能、刑罰對社會其他成員的功能。在這則寓言當中,雞與猴的主人希望通過對雞“執行死刑”達到威懾猴子的目的,這就相當于期望通過刑罰的執行來威懾其他社會成員,使其遵紀守法,不犯類似的錯誤。在此處,就可以向學生提出問題,主人的目的能否實現,猴子是否會從雞的死亡當中汲取教訓呢?實際上,這個問題就隱含著死刑是否具有最大的威懾力的問題。一般來講,大部分學生會認為刑罰的威懾力與刑罰的嚴厲性成正比,相信刑罰越嚴厲,給人造成的恐懼感就越強,而最嚴厲的刑罰莫過于死刑,那么死刑的威懾力理所當然是最大的。死刑作為最嚴厲的一種刑罰,其威懾力是與生俱來、難以否認的,但是其威懾力是否最大卻是一個不確定的問題。過度適用死刑或者過度強調其威懾力,都將適得其反。意大利犯罪學家菲利早就以實證方法證明出嚴重罪行的周期性變化與死刑的判處和執行數量無關,進而否定了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懾力。同樣,我國明代朱元璋時期“治亂世用重典”的做法也未見成效,這些事實都令人對死刑可以產生最大威懾力產生質疑。
首先,在“殺雞儆猴”的寓言故事當中,雞只是被主人當做嚇唬猴子的工具利用了一把,而雞本身并沒有犯錯,所以主人這種做法本身就欠缺公正性。這就類似于在現代社會中,犯罪的人逍遙法外,而無罪的人成為替死鬼,這種情況下的死刑根本談不上有威懾力,更不要說什么最大的威懾力了。所以刑罰的威懾力只有在公平正義的前提下才能正常發揮其作用。其次,即使我們假定雞跟猴子一樣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但是它們犯錯的原因及其心理特征卻不會完全相同,雞之過與雞之死,對于猴子的行為未必就有警戒效果,或許猴子還會認為雞之死與自己無關,那么對雞使用的“死刑”,對于猴子來說也就談不上什么威懾力了。所以死刑的威懾力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最后,我們再假定雞與猴子犯了同樣的錯誤,假定這個錯誤只是一個輕微的錯誤,當猴子看到只因為一個輕微錯誤,雞就被殺了頭,其心理必然會出現不平衡,不論犯什么程度的錯誤都要被殺頭,那為什么不犯一個更嚴重的錯誤呢?那么這種死刑的執行情況,無疑是在鼓勵犯罪。這也就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刑罰的嚴厲程度應當與犯罪的嚴重程度相適應。通過這則寓言故事,我們就把刑罰的相關理論內容進行了生動形象的例解,消除了學生對這些抽象理論的陌生感,學生理解起來就會更加容易一些。
2.從“阿Q之死”再解讀死刑的威懾力
我們在中學教材中都讀過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在結尾部分阿Q終于被槍斃,小說中這樣寫道:“至于輿論,在未莊是無異議,自然都說阿Q壞,被槍斃便是他的壞的證據:不壞又何至于被槍斃呢?而城里的輿論卻不佳,他們多半不滿足,以為槍斃并無殺頭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樣的一個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他們白跟一趟了……”對于阿Q被執行死刑,無論是鄉下人還是城里人,都沒有感受到死刑的威懾力。在鄉下人看來,阿Q是壞人,為什么是壞人,因為他被槍斃了。在這種邏輯的支配下,根本無法避免自己也成為“壞人”,刑罰的預防功能基本為零。在城里人看來,死刑的執行就是一場熱鬧,好看的話就值了,不好看的話就是白跟了一趟。所以對于旁觀者而言,包括潛在的犯罪人,未必真正會從死刑的執行過程中產生被威懾的心理,相反,人們圍觀圖新鮮和起哄圖樂的心理可能會更重一些。在現實中,人們通過各種傳媒渠道獲悉死刑的判決與執行情況,甚至親眼目睹了死刑的執行場景,但是,大多數人只是直觀地感受到場面的血腥(據個別學生介紹),與己無關的心態使得幾乎所有人對于理論上所推演的死刑抽象的威懾力并無實際感知,即使有些許感知,也比較模糊,并會瞬間即逝[8]。通過這個事例,可以讓學生具體地感受到死刑的威懾力是多么抽象,多么有限,使他們能夠在將來的司法實踐中不過度迷信死刑的威懾力。針對學生們熟知的這些文學作品中的事件,帶領他們進行法律分析和討論,也是一種重解其固有知識以確立其法律思維的方法。所以,在法學課程中,案例教學法完全可以靈活運用,而不必拘泥于某一種形式,為了更好地實現教學目標,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對某種特定的方法加以改造創新,也未嘗不可。
[1]楊莉,王曉陽.美國法學教育特征分析[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1,(2).
[2]鐘俊.論法學案例教學法的改進[J].中國法學教育研究,2010,(5).
[3][5]蘇彩霞.案例教學法在刑法教學中的運用[J].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6,(3).
[4]趙云芬,陽繼寧.法學教育與社會文化整合——兼及我國高校法律基礎課程教學的現狀及改革[J].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2).
[6]朱瑪.法學案例教學法的研究與應用[J].高教論壇,2009,(12).
[7]李凱.案例教學法在刑法教學中運用之展開[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11,(12).
[8]于志剛.關于死刑之抽象化威懾力的側面解讀[J].吉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1).
責任編輯:儀宏斌
D631
A
1009-3192(2013)04-0113-04
2013-01-02
李淼,女,鐵道警察學院鐵路與公安基礎教研部助教,研究方向為刑事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