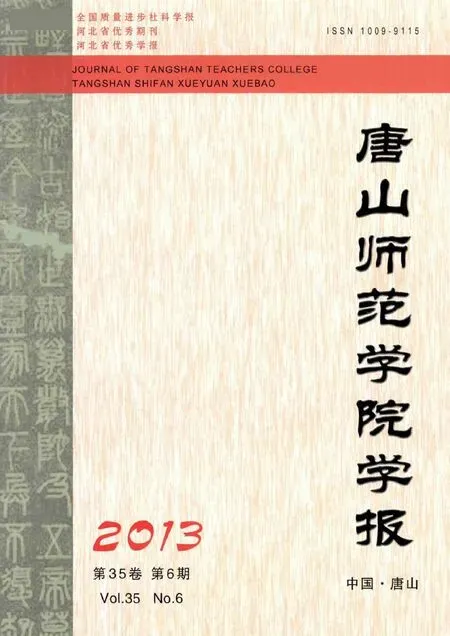論元初江南地區學官群體的形成
盧 琳
(蘭州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1279年蒙古人滅亡南宋,結束了南北對峙局面,完成了統一,但對兩宋時期的儒士群體產生了巨大沖擊。宋末元初的戰爭災害,儒士們不僅遭受顛簸流離之苦,而且元初科舉制度的廢除及四等人制,使儒士群體的社會地位空前衰落,從兩宋時期的社會管理階層淪落到元初游離在政治之外。
元代江南地區的學官群體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著名學者陳得芝在《論宋元之際的思想和政治動向》中論述由南宋滅亡到世祖末年南人儒士思想和政治態度的轉變,并分析出朝廷尊儒和優待士人是促使儒士認同元朝的原因之一,但未涉及學官群體的形成[1]。陳氏還在《耶律楚材、劉秉忠、李孟合論—蒙元時代制度轉變關頭的三位政治家》中論述,從軍事征服到建立適應中原漢地歷史背景和社會狀況的統治制度,是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的必然道路,而要在蒙古統治精英與中原漢族世界之間達到制度文化上的高層次溝通,需要一種特殊的人才來擔當起高層次“文化中介者”的角色,在不同制度文化的沖突中進行調節,從而有效地誘導蒙古人在中原地區建立其統治體制過程中理解和接受中原制度文化,并例舉耶律楚材、劉秉忠、李孟三人的重要作用。文章著眼于整個中原地區社會制度的轉變,并未專注江南地區學官群體這一特殊的社會現象[2]。蕭啟慶在《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中從制度史的觀點分析元代儒士的法定政治、經濟地位,認為元代儒士地位雖比唐宋有所下降,但并未達到“九儒十丐”的地步。此文只綜述元代儒戶地位的演進,未專注江南儒士這一群體[3]。王立平在《元代地方學官》中論述了全國學官的概況,但是北方學官和南方學官在來源、聘任和待遇上有很大差別,這一點作者并未注意到[4]。申萬里在《元代學官選注巡檢考》中考證元政府為解決學官的升遷困難,將儒士出身的學官選注為巡檢,這一現象是元代特殊的社會環境造成的,士人群體在社會處境不利的情況下改善自己生存環境的努力。由于學術界對學官選注巡檢的現象關注不多,文章頗有開創之處[5]。申氏還在《元初江南儒士的處境及社會角色的轉變》中采用社會學的分析方法,探索儒士階層社會角色的轉變,在國內外亦是首次,令人耳目一新[6]。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主要論述元代入侵滅南宋、占領江南地區給儒士階層造成很大沖擊,在科舉不第的情況下,儒士階層出任學官,形成學官群體,并分析學官群體形成的原因及意義。
一、學官制度的確立
學官是設于各路、府、州、縣或學院的教官——教授、學正、山長、學錄和主管學校的錢糧、房產、書籍的直學,《廟學典禮》稱為“提舉學校官”[7,p12],后簡化為“學官”[7,p13]。據顧宏義先生的研究,宋代地方學官、學職的設置、數量、待遇、選舉、考課都已經形成固定制度[8,p117-13]。宋代學官制度的完善對元代的學官制度產生很大影響。金朝在中國北方確定統治地位后,實施科舉制度,并沿用北宋的教育制度,北方的儒學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同樣金朝的學官制度對元初的學官制度的形成產生一定影響。隨著蒙古人入侵滅亡金朝,在北方的統治穩定,即大蒙古國時期,由于四處征戰和對儒學認識的膚淺,導致北方的學官制度蕩然無存,忽必烈即位后,隨著對中原文化認識的深化,逐步實施漢化政策,恢復儒學教育,中統二年(1261年)“諸路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今擬選博學洽聞之士以教導之,據某人可充某處提舉學校官。凡諸生進修者,仍選高業儒生教授,嚴加訓誨,務要成材,以備他日選擢之用”[7,p12]。恢復學校教育,設提舉學校官,管理學校教育,培養人才,這是針對北方在結束戰亂,完成統一后的舉措;至元六年(1269年)
府又對北方各地儒學學官進行整合規范,“外路學校,教授一員,別無另設提舉學校職名,止是隨路、府、州長貳或運司文資官兼充。即目隨路已設學校官,除見欽受宣命人員,擬合依舊存設,其余亦擬行罷去。擬合并散府、上中州,依舊例設立教授一員”[7,p13-14]。對北方各地學官的規范,結束宋末元初戰爭時期學校教育廢止、管理混亂的狀況,為學校教育的進一步恢復和學官制度確立奠定了基礎。上述措施的實施基本上恢復和規范了北方的學官制度,北方學官制度的恢復同樣對江南地區學官制度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江南地區學官制度的確立是在在南宋滅亡后,元世祖時期開始實施,此后一直沿用到元朝滅亡。忽必烈滅南宋后逐步實施漢化政策,為廣泛搜羅人才,下詔“諸路歲貢儒、吏各一人”[9,p246]。這些儒士和南宋時期的官員,很多被任命為學官。這是學官任用的開始,也是學官考核、升遷等一系列制度的開始形成。
首先是學官的任用。一是通過保舉兼考核的形式。至元二十一年(1287),江南非進士人員,如有學問淵博、品行端正之人,可通過保舉的方式,經儒學提舉當面出題考試,按察司考核,優秀者可出任教授。通過保舉兼考試的方法任命學官,不僅表現了江南地區學官任用的靈活性,被保舉的儒士多是名儒、隱士、南宋遺老,同時考核的方法也保證了學官的質量。二是元政府特許學生中的佼佼者出任學官。延祐四年(1317)規定,由本處教授在學生員內推舉才學優長、行無玷缺者,文資正官出題,面試經疑、史評各一道,合格即為直學[10]。在學校學生中選拔學官不僅解決了直學的缺員問題,并且直學是管理本地、書院的田產、祭器、書籍等事務,由學生出任直學促進了學校教育的發展。三是元仁宗設科取士,由于南人屬于第四等人,科舉考試偏重蒙古、色目等北人,江南地區落榜的儒士很多,元政府為安撫儒士,對科舉落第者“恩授”學正、山長、教授等職務,在至正年間成為定制[11]。由科舉不第的儒士出任學官是元政府安撫、穩定江南地區統治的需要,同時對于儒士而言雖不能通過科舉實現進入仕途的政治理想,培養人才也是其退而求其次的最好選擇。
其次是學官的考核和升遷。學官雖是地方卑職,但因擔任著培養人才的重任,因此其考核和升遷有嚴格的制度。從五品提舉,經過三次考試可升為正五品官;從七品負提舉,經過三次考試可升為正七品官[12]。大德五年明確規定,儒學提舉三年任滿,依例于司縣官內任用。路、府、州、縣及書院學官,從直學到學錄、教諭,從學錄、教諭到學正、山長,從學正、山長到教授,任滿或考滿以后,經過層層考試方可升遷。考核的內容多是經疑、古賦等,和科舉考試的內容差別不大。學官的考核、升遷是一套嚴格的系統,并且從直學到教授的升遷,時間長,難度大。這也說明了元政府將南人儒士固定在學官系統,阻礙其進入仕途參與社會管理的目的,也逐步造成學官的數量越來越膨脹,形成學官群體。“元代江南的學官體系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元政權為籠絡江南儒士而設立的,學官的來源、職務、處境、地位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學官只在本系統升轉……因此,江南學官在元朝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6]
二、學官群體形成的原因
首先是宋元更替,社會地位降低,儒士的生存環境惡化。蒙古人在滅南宋的過程中其“嗜殺、屠城”的惡習雖有所改變,但局部性的燒殺搶掠仍有記載,如江西行省南安路上獨縣“入至元,大兵環而臨之者逾七旬,竟以死守屠焉”[13]。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一月,元軍進攻常州,城破,元軍“四門殺人,一城盡死”[14,p59]。可見蒙古人在攻克南宋都城時,嗜殺、屠城的現象依然存在。戴表元在《行婦怨次李編校韻》中描述了臺州地區的情況:“赤城巖邑今窮邊,路旁死者相枕眠。唯余婦女收不殺,馬上婷婷多少年,蓬頭垢面誰氏子,放聲獨哭哀聞天。”[15]從詩中可見戰爭時期的慘狀。同時,戴表元也記錄了逃亡時的情況“越明年,兵聲撼海上,樹郊之民,往往持槁束揾而上,伺塵起即遁。余與公勢不得止,倉皇棄其故業,詣山中可舍者為之歸,蓋其事不能相謀,而流離轉徙,困頓自折,不自意復相出于天臺南峽之麓,自是而行同途,止同游,交同友,客同門,急則傳聲疾呼,老稚攜契,以循須臾之命;緩則握手勞苦,流涕譬釋,以寬離鄉棄土之戚”[16]。戰爭的破壞使南宋遺民流離失所,不得不放棄故土、故業四處奔波,儒士作為南宋遺民中的一個特殊群體,亦不能幸免,同樣飽受奔波流離、生活困頓之苦。加之元朝建立之初,實施嚴格的民族等級劃分,使江南士人失去優越的社會地位,宋金時期被賦予的政治、經濟的特權也不復存在,加劇了江南儒士生活的窘迫。學官作為朝廷正式授予的官吏,并給予俸祿,據《廟學典禮》記載,南北學官的俸祿不統一,南人學官“自至元二十四年(1287)始,每月俸給從國家正俸內支給,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88)以后,不再由國家正俸支給,而從學校養士錢糧內支給”[7,p15]。擔任學官不僅解決了儒士生存的困境,也使儒士群體安定下來,不再飽受顛簸流離之苦。
其次,科舉制度在元代不受重視,入仕無門造成儒士身心的煎熬。唐、宋時期得到完善、發展的科舉制度,在元代表現出實施晚、時斷時續、民族配額的特點。太宗九年(1237年),忽必烈曾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議,“用儒術選士”,即“戊戌試”,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一次選舉人才的嘗試。皇慶二年(1313年)十一月仁宗正式下詔,并于1315年實施了科舉考試[9,p568]。此后在元順帝至元元年(1335年)被中斷,至元六年(1340年)得到恢復,此后推行一直到元朝滅亡。“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北人為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其得者不過州縣卑秩。”[17,p49]可見在元朝統一之初,儒士,特別是南人儒士已游離在核心政治和社會管理層之外,這和兩宋時期,優待士人,社會地位頗高的現象形成強烈反差。科舉制度已不是簡單的生存模式,而是幻化為讀書人精神的寄托,“因為他們總歸是儒生,歷史所決定了的人生角色,使他們永遠不可能超越傳統文人人生理想的思維定勢。不管他們出身如何,成名與否,他們總懷著儒生的雄心,儒生的希望,儒生的牢騷,他們無論如何都擺脫不了糾結于心的科舉情結。”[18]因此對于南人儒士,宋元交替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改朝換代,更是一種文化的入侵和社會制度的變革,而學官制度的形成給予迷茫困頓中的儒士一絲黎明的曙光。雖然學官系統的考核升遷系統繁瑣而漫長,但畢竟對儒士們渴望接近政治,“學而優則仕”的理想近了一步。
再次,南人儒士將學官、學校教育作為捍衛文化、“道統”的精神家園。在古代,儒士不僅奉行“學而優則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還承擔著保存并傳播儒家文化,繼承“道統”的文化使命。元初,在用人方面注重“根腳”,偏重于蒙古人、色目人等,在社會制度層面,蒙古舊俗亦受到重視,因此宋元交替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改朝換代,更是一場文化的變革。儒士作為文化的載體,依然舉起“衛道”的大旗,在學校、書院中保存、傳播以儒家文化為主的的中原文化,“中原文明在蒙元時代雖經歷空前嚴峻的考驗,卻能浴火重生,而且并未偏離原有的發展主線。”[19,p61]中原文明在蒙元時代的經受住考驗,并未斷絕,學官群體起到了很大作用。
最后,學官制度的形成與元政府實施的漢化政策有關。隨著蒙古軍滅亡南宋,實現統一,元世祖實施漢化政策,既而對南人儒士實施優待政策,經濟上,“敕南儒為人掠賣者,官贖為民”[9,p149]。并減免徭役;政治上,遣使在招納漢人儒士,于是大儒元好問、竇默、劉秉忠等人紛紛仕元,這些名儒仕元對普通儒士具有導向作用,加之儒士郝經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主也”[20]。這一重要的政治命題,指出無論漢人還是蒙古人,只要能任用士人,行使圣人之道,換而言之就是以儒家文化為主的“道統”,就能成為中國真正的君主。這一政治命題,為文人仕蒙掃除了思想障礙。
但是學官群體的形成反映了元政府籠絡江南儒士,但又阻止儒士參與中央政權,進入社會管理層的矛盾心態。“元朝天下,長官皆國人是用,至於風紀之司,又杜絕不用漢人南人,宥密之機,又絕不預聞矣,其海宇雖在混一之天,而肝膽實有胡越之間。”[21,p81]元政府為穩定統治,不得不安撫儒士群體,但涉及到中央機密和社會管理杜絕任用漢人南人,對儒士始終保持一種警惕。而學官群體的出現恰是儒士們在社會環境復雜和個體力量單薄的情況下,形成的具有相同處境和共同目的的特殊群體,試圖以群體的力量,通過學校教育保存和傳播以儒家文化為主的“道統”,通過學官的升遷進入仕途,以實現匡正社稷,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學官群體的形成反映了元政府和江南儒士相互矛盾、相互制衡的心態。
三、學官群體形成的意義
首先,學官群體的形成反映了江南儒士社會角色的轉變。兩宋時期,儒士們奉行讀書—科舉—做官的人生模式,進入仕途形成官僚集團,成為中央決策的參與者和地方事務的管理者,在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均享有特權,社會地位頗高。宋元更替,改變了儒士的人生模式,社會地位降低,“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于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于國也’”[22,p20-21]。九儒十丐的說法雖未免夸張,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士社會地位的降低。儒士被固定在學校教書育人,游離在政治之外,從此儒士不再是出卿入相、操勞國事的社會管理階層,而是專心教育,傳播儒家思想的學官,可謂無奈中的心靈寄托。
其次,學官群體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化教育的發展。儒士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學官群體作為儒士的一個特殊群體,是江南地區文化教育恢復和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具體表現:第一,學官群體的形成是導致元代雜劇、散曲、詞賦等通俗文學、市民文學異常繁盛的一個原因,亦是儒士們苦悶、惆悵中的心靈慰藉。《玉鏡臺》《陳母教子》《破窯記》等元雜劇的繁盛既是儒士抒發情感的途徑,同時也促進了市民文學的繁榮。名儒戴表元在1302年被任命為儒學教授,在閑暇之余經常與鄰居王子謙縱論千古,暢談詩書[16]。第二,學官群體的形成對學校教育的發展產生積極作用。周祖謨先生在《宋亡后仕元之儒學教授》一文中考證元初儒士仕元的情況,這些儒士皆出任學官,其中書院山長3人(黃澤、曹涇、胡炳文)、學正1人(劉應龜)、教授10人(戴表元、牟應龍、趙文、馬端臨、張觀光等)、儒學提舉 4人(王義山、白廷等)[23]。這些人中大多都是名儒學者,必將對學校教育和文化的保存傳播發揮了積極作用。
學官作為路、府、州、縣或學院專管教育事務的官員,在宋金時期其學職、數量、考核、升遷等形成一系列完整的制度,對大蒙古國時期,北方的學官制度的形成產生很大影響。但北方的學官數量少,而且在科舉考試恢復后,北方儒士通過考試進入仕途的難度相對較小,因此北方的學官還不能形成一個獨立的群體。而江南地區的學官制度其來源、選任、考核、升遷等方面均比北方嚴格,并且升遷的時間長,難度大,這就使學官被固定在教育系統里,進而形成一個獨立、特殊的群體。學官群體的出現不是簡單的教育系統內部的問題,更突出的表現在儒士群體在元代特殊的社會環境中的生存狀況,因此南人儒士出任學官的原因也頗為復雜,既有迫于生活壓力,維持生計的原因,也與元政府拉攏儒士,鞏固江南統治的政策層面誘導有關,同時也是儒士捍衛文化、“道統”的文人使命相關聯。學官群體的形成對當時江南社會產生重大影響,不僅是儒士在元代社會角色的變異,由社會的核心階層退守到社會的邊緣,社會地位降低。同時學官群體的形成也促進了元代文化教育的恢復和發展,為雜劇、散曲等市民文學的繁榮和書院教育的發展做出貢獻。
[1] 陳得芝.論宋元之際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動向[J].南京大學學報,1997(2):20-25.
[2] 陳得芝.耶律楚材,劉秉忠,李孟合論-蒙元時代制度轉變關頭的三位政治家[J].元史論叢(第9輯),2004(7):1-9.
[3] 蕭啟慶.內北國而外中國[M].北京:中華書局,2007:134-147.
[4] 王立平.元代地方學官[J].固原師專學報,1994(2):19-34.
[5] 申萬里.元代學官選注巡檢考[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5(5):7-10.
[6] 申萬里.元初江南儒士的處境及社會角色的轉變[J].史學月刊,2003(9):21-29.
[7] 王颋,點校.廟學典禮(第1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2.
[8] 顧宏義.教育政策與宋代兩浙教育[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17-137.
[9] 宋濂.元史(第8卷)[M].北京:中華書局,1976:246.
[10] 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第9卷)[M].上海:中華書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3):387.
[11] 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J].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2(6):79-84.
[12] 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第8卷)[M].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3):364.
[13] 劉將孫.養吾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5卷)[M].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14] 鄭思肖.鄭思肖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59.
[15]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四庫叢刊初編本,第28卷)[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180-191.
[16]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四庫叢刊初編本,第11卷)[M].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79-101.
[17] 葉子奇.草木子(第3卷上)[M].北京:中華書局,1959:49.
[18] 周柳燕.中國古代戲曲的科舉情結[J].藝苑縱橫,2002(2):78-85.
[19] 蕭啟慶.內北國而外中國[M].北京:中華書局,2007:61.
[20] 郝經.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7卷)[A].郝文忠公文集[C].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2134-2897.
[21] 葉子奇.草木子.(第4卷下)[M].北京:中華書局,1959:81.
[22] 謝枋得.謝迭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卷)[M].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23] 周祖謨.宋亡后仕元之儒學教授[M].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3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