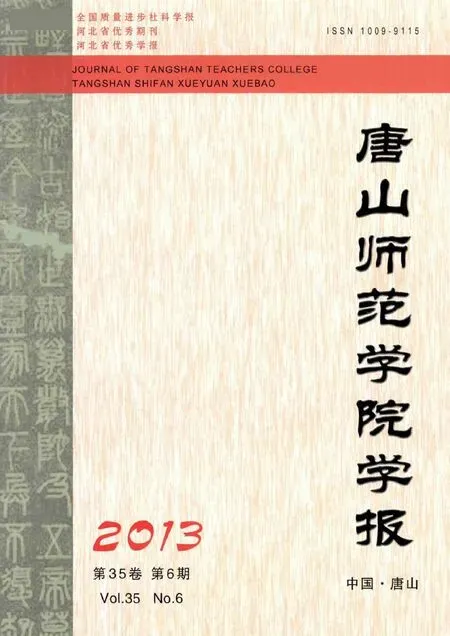法律發現的“前世”與“今生”
——以歷史法學到概念法學的變遷為線索
張志文
(山東交通學院 文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357)
政治學法學研究
法律發現的“前世”與“今生”
——以歷史法學到概念法學的變遷為線索
張志文
(山東交通學院 文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357)
歷史法學代表人物薩維尼倡導“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致力于拉近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歷史法學所力主的“法是被發現”主要是從法的產生角度也即立法立場來分析的。作為歷史法學派的延續之一,概念法學傾向于構建嚴謹的能夠涵攝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法律體系。在它的視域中,法官只需從法律體系中發現法律即可完成對案件的判斷,從而將司法者囚禁在了概念的城堡里。這種理論上的幻想遭到耶林等社會法學者的批判也在情理之中了。
法律方法;法律發現;歷史法學;概念法學
在時下學界的研究中,作為獲取針對個案所要應用法律的方法,法律發現基本上是在司法的場域中被認識和表達的。不過,如果從學源的角度去追溯對法律發現的使用,就會看到在立法的藩屬內也有它的身影。例如,薩維尼就主張“法律系發現的,并非制定的,其成長之本質乃系一無意識的、自然的過程”[1]。所以說,對于法律發現的研究不外乎從兩種意義上展開:一是從法的起源角度理解,認為法律不是被制定的,而是被發現的;二是從法律適用的過程進行理解,換言之,是從時下的法律體系中尋找能夠適用于當下案件的法律規范或解釋性命題的活動[2]。只不過是出于對“立法中心主義”的不滿和人類理性局限性的承認,旨在交涉理性和選擇理性并致力于實現社會公正的司法審判活動被賦予了更多的期待。隨之,法律發現,這個雖起源于立法但是被學界公認的術語,卻更多從司法的角度被闡述。可以說,立法立場的法律發現如今已經鮮有提及了。基于此,本文嘗試通過以歷史法學為切入點,詳細剖析立法立場的法律發現觀,并進而以歷史法學到概念法學的流變為背景揭示法律發現的立場變遷,期望能夠對法律發現理論有個全景式的了解。
一、法律發現的“前世”:以歷史法學為切入點
在對立法立場法律發現觀介紹之前,有必要對歷史法學進行些許的說明。在我國臺灣學者李鐘聲看來,由于與西方歐美學者的論證目的不同,歷史法學可以表述為三種形式:沿革法學派、法律史學學派和民族法學派[3]。沿革法學派從事于法律規定之史的考證,是研究法制史的學派。法律史學學派是以科學的歸納方法研究法律史,以探討法律進化的發展途徑,它主要主張法律是由地方習慣逐漸凝成,所以法律具有民族性,且隨著民族的進化而演進。民族法學派是由德國學者所形成,力主法律的發現說,偏重于法律在民族史上的連續性,主張法律是民族精神的表現,民族精神是基于民族的共同意識,法律潛存于民族的共同意識所形成的習慣之中,所以,法律源于民族共同意識而呈現于習慣。可見,立法立場的法律發現主要是由歷史法學派之一的民族法學派來貢獻的。該學派的首要原則,是認為法律是發現的,而不是制定的。其主要有以下幾點:
1. 為什么需要發現法律
薩維尼將發現法律的理由歸結為“內”和“外”兩個方面。先看“內”,主要是指基于法的本質的認識。在18世紀的歐洲,自然法支配著當時的法律與社會意識。自然法強調人的理性,主張法律原則是普遍的和固定不變的,代表性法典的產生是自然法風靡一時的有力佐證。不過,“當日益上升的國民意識與人文主義的文化更新一起攻擊專制國家的機械性立法時,受排斥和受監護的感覺在德意志導致啟蒙之自然法的崩潰”[4,p147]。薩維尼旗幟鮮明地充當了批判自然法學的“先鋒官”。在薩氏看來,法律的本質“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生活著的人本身。”具體來說,法律如同一個民族所特有的語言、生活方式和素質一樣,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機能和習性,在本質上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具有我們看到的明顯的屬性。由于民族的共同信念,這些屬性才能融為一體,同時,也是“一種民族內部所必需的同族意識所致”[5]。概言之,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體現。
對此,應從法律的存在樣態和存續時間兩個層面進行把握。從存在樣態上講,“法律以及語言,存在于民族意識之中”。生存的、活動著的民族精神產生了實在法。于是,在法律的形成路徑上,“每處都是由習慣和一般信念,然后才靠法理學發展而來的。因此,法律的形成每處都依賴民族內部默默起作用的力量,而不是依靠立法者的武斷意志。”可見,法律與社會共存,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再者,從存續時間上,“對于法律來說,一如語言,并無決然斷裂的時刻;如同民族之存在和性格中的其他的一般性取向一般,法律亦同樣受制于此運動和發展”[6,p9]。只是在不同時期同一民族法律的表現形態不盡相同,或為習慣法,或為經過人們設計過的實在法。故而,“民族精神”創造法律達致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原始階段,法律借助于民族精神的內部必然性默默地生長。隨著文化的進步以及民族內部事務的復雜化和精細化,處理事情的方式也由共同表決轉向了不同階層的分工處理。挖掘、整理民族意識中的法律就落在了法學家的手里。這就進入到了文化上的高級階段。總的來說,“法律與自然界的生物甚至人類一樣,是借助于內部的必然性、按照其自身法則有機地生長的。它們都受看不見的手的支配”[7]。
再分析“外”,對編纂法典的反對。在理性建構主義光環的輻射下,人們對事物的理解陷入了“早期的擬人化的思維方式之中”。這種認知進路重新復活了那種把所有具有文化意義的制度的起源都歸結為發明或設計的傾向[8]。于是,法律、宗教、語言等都是經由人審慎思考而建構起來的文明產物,人們有能力根據生活的理性來重新設計或改變已有的制度。這種主觀對客觀理性加工的過程,在薩維尼的視域中,是對民族精神的扭曲和虐待。因此,僅是出于更高政治目的要求立法者有意為之的立法活動“容易變成對法的徒勞無益的損害”。在這里,薩維尼對立法所采取的是一種實證主義的態度,他認為立法就是主權者將自己的意志宣布為法律的活動,而法律自然也就是被明確宣布為立法者的意志了。然而,對于立法的作用,薩維尼也沒有一概反對。在某些特定規則存有含混不清、令人生疑的情況下,制定一項法律,或者從事某項立法活動,就可將種種不確定性和疑慮一掃而光。對于這一性質的立法,薩維尼說古羅馬的裁判官告示就是一典型例證。因此說,薩維尼所反對的是那些武斷的僅憑理性沖動而實踐沒有法典訴求的立法活動,那些能夠展現且完全維護民眾自身意志的立法并不處在被反對的行列。
以德國為例,薩維尼從立法理論的角度說明了法典編纂的條件以及之于現實的不可能。首先,就內在內容來說,法典應該保障最大限度的法的確定性和適用的安全性。而實現上述任務的關鍵就在于法典內容的完備性,即法典應該符合對任何一個法律問題都能夠做出回答的期待。不過,這種愿景被千變萬化的社會實際所沖淡。所以,“所有的新法典均放棄了追求此種外在的形式完美性的一切企圖,而且,找不到任何替代之物。”另外,以幾何學藝術清楚表達的根據已知條件推導未知數據的“主導公理”在法學領域卻難以施展拳腳,原因在于難以分辨到底哪些法律概念和規定為公理,以及這些概念之間內在聯系和親合程度。若執意編纂法典,表面上由法典控制的司法,事實上是用法典以外的代替真正控制權的東西來規定的。其次,在形式上,法典必須將其內容用極其精確的形式進行表述,而不能產生歧義和混亂。這個目標的實現依賴于起草法律者對其所從事法律的充分研究,若沒有表達的技巧,法典編纂工作將面臨失敗的風險。基于此,薩氏總結到,“當一個民族處于其精神發展的年輕階段的時候,他們對于其自己的法有著清晰的認識,但是,對于法典則缺乏相應的表達的語言和邏輯技巧。”[9,p193]
2. 在哪里才能發現法律,也即法的產生淵源
在薩維尼看來,法律應起源于行為方式,或者說,習慣法也就是行為方式的產物。法律首先應內存于人類的信仰和習俗之中,而并非法律制定者僅靠一己之力就可獲得。法律亦如藝術一般,是文化的自然體現和土生土長的產物,只能去發現而不能通過理性的立法手段來創建。
恰如前述,法律的成長總是伴隨著“民族”演變浮動的節奏前進。于是,薩維尼說,“民族的共同意識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從民族共同意識中去發現法律是薩氏法律發現觀的場域所在。不過,薩維尼承認,關于民族共同意識或民族精神的產生和發展,“是一個無以歷史地回答的問題。”換言之,薩維尼只是堅信民族精神的客觀存在,但是并沒有做出細致的考察。也許是出于論證的需要,薩氏只接受這樣一個結論就展開對法典編纂支持者的反擊。
如要實現對民族共同意識的了解,我們不得不從歷史主義的發端說起。歷史主義自19世紀初葉遍布于歐洲大陸以后,導致大部分學者追溯歷史主義的發軔,紛紛以歷史主義作為探究和建構自己理論的背景淵源,而締造此一傳統的先鋒當屬赫德(Herder)。赫氏對18世紀的哲學家所秉承的靜止的、單調不變的歷史觀進行了批判,認為“史家應注意特殊的歷史形式和他們的發展,不應任意以自己時代的標準去批評不同的時代,尤其對異時代之異文化須具有同情的了解”[10]。在他的歷史思想中,“發展”的觀念顯得尤為關鍵,并將其視為“一種形成或成長的連續過程,尤其著重起源的追溯”。對于18世紀末開展的如火如荼的民族主義,赫德將他的歷史觀置于民族的歷史之中,強調“民族起源,主張史家應該探究早期的民族史,由此可以反映純粹的民族精神。”在赫德的作品《人性史哲學的理念》中,“民族作為歷史規定的生活傳遞者,依照神的計劃依次更迭;在語言,亦即與民族血脈相連的詩歌中,Herder聽到了‘民族的聲音’”[4,p352]。可以說,“民族”促進了市民階級國家意識的覺醒;而已經覺醒的知識分子更注重在民族精神中找尋自身的立足點。兩者之間是互相促進的關系。“當民族與民族文化被視為普世歷史任務的執行者時,中歐市民階級的國族意識亦正在興起。逐漸抬頭的知識分子在自身發現作為文化國族的國民,并經歷了表達民族精神的文化創造。”于是,法律“現在也不應再被視為國家立法者的合理創作,反之,它似乎應被視為由民族集體潛意識中‘悄然’孕育出來之整體文化的一部分,……這種觀念經由Herder的傳播影響到薩維尼,并對歷史法學派中的日耳曼旁支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然而,在薩維尼這里,民族精神并不是一味地在歷史的回溯中求證,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是開放、動態的變化的過程,這與羅馬法有著莫大的關系。畢竟,“羅馬法完美地體現了羅馬民族的精神,這表現在羅馬人無需具備任何法律教養,僅具平常良好之感覺,即可體認法律的精粹”[9,p277]。盡管薩維尼表現出了對羅馬法的極力推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并沒有被羅馬法的具體內容所束縛,也就是說,并不是將“民族精神”的內容局限在羅馬法詳實的論證之中,更多的是從技術層面而非價值的角度表示了對理性普世主義的反對。所以說,薩維尼的民族精神“實際上體現在技術層面上。”因此,與立法者創造法律進而實現價值不同,法律人主要去發現規則,無論規則“在國內還是國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申言之,法律人的重要職責“就是發現和整合本國族的民族精神,將其從普通國族成員樸素的感情和行為中升華為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則體系”。
3. 發現法律的路徑選擇
既然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那么它的發展不是跳躍式的,其命運也不是個別革新者單憑理智決策就可掌控的,而是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演化的結果。因此,薩維尼并不期望能從改革性的立法產生良好的法,而是期望從某一個受過科學培養的和從事工作的法學家等級能產生良好的法[11]。這也就是說,發現法律的主體是職業法學家階層。在薩維尼看來,法學家有兩種素養是不可或缺的:一是歷史素養,另外則是系統眼光。由此也引申出發現法律的兩種路徑選擇:系統的方法和歷史的理解。
為何法學家要具備“系統眼光”,這是因為在薩維尼的心目中法典應當具備系統性和完備性。在《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的結尾,薩維尼表達了對系統性的關切。“……而且,一部法典乃是一部更為龐大的作品,要求具有更高程度的有機的統一性,對此無人會否認。”從實踐的層面來講,作為社會存在整體中的一部分,法律的“很多單一形式各自聚集為某些特定的制度,如婚姻、財產、繼承等,它們的調節建立在一些簡單的、在人民當中活靈活現的基本觀點之上。……提出、界定這些制度,并按其內在的相互關系,把它們納入一個體系,這就構成法學家在哲學方面的工作”[9,p31]。體系化的方法主要是各種法律現象之間具有的內在一致性和相互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將單個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規則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12,p261]。這也就是系統方法的操作流程。
再來說歷史的方法。正如科殷的論述,主宰著婚姻、財產、家庭等這些制度的基本觀點是在歷史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只有進行歷史的觀察才能開拓它們的指導思想。法律科學將會在它們的歷史的發展中密切跟蹤注視它們,同時借此認識它們的本質;因為這種對發展的觀察,將會令人一目了然,到底在一種制度里什么東西已經死亡,另一方面,什么東西還生機勃勃,并且還發揮作用。”所以歷史的觀察又是完成系統認識的基礎。“嚴格適用歷史方法乃是對于德國法的諸般缺陷的真正彌補,由此,由現代的傲慢和無知加諸純正的羅馬法的玷污,將被一掃而凈。”[9,p346]故而,薩維尼宣稱,歷史才是通達對于我們當下情境的理解之途。
可以說,在薩維尼的研究策略上,做到了歷史和體系的方法首尾一貫的結合,開創了德國法形成的新途徑。其晚年巨著《現代羅馬法的體系》即是明證。“以歷史的方法為先導——因此拋棄了以往的實用法學的方法——來考察古代的法源,并且,對那些也同樣適用于19世紀的社會經濟需求和政策目標的各種概念進行了明確化,對普通法進行了一般類型化,從而開辟了體系性法原理學的道路。”[13]歷史的方法為法的形成提供了素材;體系化的方法則為其搭設了正當的科學形式。發現法律的形式要素就包含兩個方面:邏輯成分和歷史成分。總之,歷史的方法和體系的方法是歷史法學發現法律的主要路徑選擇。換言之,法律正是“由歷史經驗中發現并經過邏輯整理表現出來的。”
二、歷史法學派的“分野”(流變)
盛極一時的歷史法學持續了近百年,并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重蹈了18世紀自然法的“厄運”,批判它的聲音不絕于耳。正所謂“禍起蕭墻”,恰如龐德所言,歷史法學派中的一些論者轉向了實證主義,另一些論者則改用經濟觀去解釋法律史或者轉而采用歷史唯物主義,還有一些主張必須對歷史與歷史法學派作出明確界分的論者則放棄了歷史法理學,只信奉一種純粹描述的法律史學和一些純粹描述的法律學說[14,p15]。對于歷史法學分崩離析的原因,龐德是這樣總結的:“乃是與19世紀各個領域普遍否棄歷史哲學思想和恢復對人類努力之功效的信念的狀況相應合的。”由此看來,法律發現在“立法”立場上駐足的時間并不長。應該說,以薩維尼為代表的歷史法學既造就了“立法”立場的法律發現也為其后來的立場變遷埋下了伏筆,下面就以“民族”作為引子論析歷史法學的“分野”。
雖然歷史法學是作為對自然法學的一種反動思潮而登上歷史舞臺,但前者只是在理論觀點和主張上與后者相左,而本質上是一樣的。歷史法學“僅僅在自然法的內容上加上了人文主義、國民意識等內容,使其更為豐富、更加適應社會現實”[15]。在胡果、薩維尼的經營下,歷史法學“把社會構想成一個按照與生物進化相類似的歷史演進而發展的有機整體。”“在這個因每個民族而各具特色的整個進化過程中,定會表現一種自身的邏輯,一種悄然躍動的精神。這是正處于萌芽狀態,并且同時會使一個民族全部歷史文化的事業具有統一性和意義的‘民族精神’。”[16,p193]
之于薩維尼,“民族”一詞更多地是從象征意義上使用的。“民族并非歷史性之國族的政治與社會現實,充其量只是一種理想的文化概念:經由共同文化教育而結合的精神與文化社群。”[4,p381]正是在這一“民族”概念的觀照下,薩維尼轉向了對羅馬法的研究。在薩維尼看來,羅馬法被視為是“德意志法律生活的重要元素”。在對材料的處理上,薩氏的靈感“來源于康德的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模型要求”,即言之,自然法學派的錯誤在于其預設的理論前提,而自然法學派的理性主義方法“卻可以保證在實踐基礎上收集出來的法律素材形成一個具有邏輯一致性的合理的法學體系。”于是,他采用了體系性(哲學性)與歷史性相結合的處理方式。這種研究方法既兼顧了法學的邏輯性,同時也沒有忽略以“批注——詮釋”的方式透視其實用性。不過這種研究策略并沒有一貫遵從。薩維尼對羅馬法體系化處理的關注顯然多于其對法律歷史的研究。也正是因為此,他所采用方法的不足逐漸顯現。這表現為兩點:其一,嚴格的體系性風格使得對羅馬法的研究擺脫了傳統的雜亂而顯得更加的條理、規整,“但可惜卻也略去了現代運用的實用批注”,從此有意地傾向于從體系內挑選古代羅馬史料的價值與貢獻。其二,薩維尼所展示的體系化方法并不完善。“作為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勢必應該由基本概念、規則和原則建構成一個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整體。”故而,薩維尼的追隨者在他止步的地方開始了后續的對歷史法學的超越。歷史的方法在后繼者眼里一文不值,而體系化的方法卻被發揮到了極致。
普赫塔在繼承其師(薩維尼)觀點的基礎上,將嚴格概念形式主義推到了支配地位,構建了“概念金字塔”。在普赫塔這里,法律也是源自于民族精神,其形成和發展是一個無形的過程。他將民族界定為“一般未經訓練養成之理解的表面現象,此等理解無法掌握非具體可見者”[4,p386]。其實,法的系統性也正是源自于其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恰如葉士朋所言,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由于法是民族精神這個有機整體的體現,因而具有系統性。“法律制度或許有一個‘靈魂’,有感覺或者指導性原則,賦予它們以統一性并使法律制度獲得系統性的表達,從一般的原理推導出其他原理,這正是普赫塔所說的‘概念的金字塔’”。無論是薩維尼還是普赫塔均認為法學家乃是發現法律的主導者。普赫塔這樣來論證自己的“概念的譜系”:“法律家應該透過所有——參與其中的——中間環節向上與向下‘追尋’概念的來源,質言之,應該清楚地向上一直追溯每個法的‘來源’到法的概念,再從這個最高的法的概念向下推導直達個別(主觀的)權利為止。”[4,p38]也就是說,藉由定義式的概念作為媒介,賦予法律制度統一性并以系統性的方式進行表達,將能夠推導出其他原理的一般原理列為起點,這樣最具體的法律條文都可從公理體系的最高點推論出來。他所依據的是“后期歷史法學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論的演繹方法,即不從各種法律、命題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從概念中演繹出教條式的命題和判例”[17]。
雖然在論證問題的起點上薩維尼與普赫塔并無二致,但是后者對前者的超越主要是表現為對法學家作用的使用和法律體系化的理解上。在薩維尼那里,法學家的工作僅在于對習慣、習俗法的發現、挖掘并將其體系化。而普赫塔則更進一步,“法學家不僅要將既有的法律素材予以體系化,還要積極地利用這個體系中發現的原則和規律去創造新的法律。不僅新的法律可以從原則中推導出來,而且新的法律概念也可以從既有的概念中創造出來,因為新的法律規則和概念都源自法律體系的邏輯結構”[12,p266]。因此,“法學家不再只是充當民族精神的喉舌,道出民族意識中什么應該成為法”。另外,普赫塔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了概念體系的構建上,并構造了一個精美的體系。作為該體系的掌控者,法學家僅是受限于“內在的邏輯觀照”,發揮其主觀學術創造性,由概念中推導出具體的法律條文。不過,這種強調從思維、理論到法律實踐的理性法理論的演繹方法被以耶林為首的利益法學批評為“倒置法”,也為后來歷史法學派中的“潘德克頓法學”的興起奠定了方法論基礎。另外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從普赫塔開始,歷史法學并不像初始那樣堅決地反對法典的制定,轉而積極地促進法典編纂工作。這是因為,“在文明發展的高級階段,習俗法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小,而制定法和法律科學的作用越來越大”。
可以說,正是由于普赫塔的“概念理論”和支持法典編纂觀念加速了概念法學的形成和傳播,并使其在理論和實踐兩層面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體現。在理論上,繼普赫塔之后,耶林將概念法學推上了頂峰;在實踐上,以溫德沙伊德為核心代表人物的“潘德克頓法學”得以法典化。
首先,來分析理論層面。提及耶林,能夠想到的是他的目的論或利益論,也即是,法律必須從其所追求的目標和保護的利益來理解。之所以如此,在于他認為概念法學或結構法學是無意義的,遠離了社會生活,并嘲諷其為“法學概念的天堂”。然而,在最初,耶林卻不是這樣認為的,而是抽象概念法學的狂熱追隨者。應該說,到了耶林生活的時代,羅馬法的體系化工作已在薩維尼等人的倡導和助推下開展得如火如荼,內容已經被系統地整理和吸收了。如何自由地利用羅馬法成為羅馬法體系化工作完成之后另一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此,耶林深刻認識到:“對羅馬法的研究的核心不是對羅馬法實質內容的盲從,而應該汲取羅馬法的方法本質。”[12,p270]于是,耶林延續和發展了普赫塔關于法律科學即“概念性理論”的“造法”功能和制定法的理論,嘗試擺脫羅馬法實際內容的影響,創造出誠如自然科學對社會駕馭那般的時代所需要的法律。
耶林借鑒了當時的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來構筑自己的“概念方法”。這種方法要求,“首先,將法律規則和法律關系分解為單個的要素;其次,從眾多的單個規則中提煉出法律科學的基本概念;最后,通過將這些要素和概念的內在關系進行組織和整合,構建一個新的具有內在邏輯關系的體系”。這樣一來,在耶林的法學理論中,“法律現象的內在規律性認識不再完全依賴于歷史文獻和社會效應,它也可以單純從既有的法律知識體系中創造出來。換言之,法律不再僅僅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也可以是一種邏輯的衍生品”[12,p271]。至此,法學不再留戀于對歷史材料或給定現實的組織或解釋,而是轉變成一門憑借智力推介或邏輯演繹就可對材料進行塑造的智識性活動,而客體的實證特征則在所不問。可以說,概念法學理論框架已經出現,至于這種理論的實踐效應則留待潘德克頓法學來發揮。
其次,從實踐角度分析。到了19世紀中葉,法學中那種對以往羅馬法關注的熱情逐漸消退,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構建一個現代實用的法律體系成為學者們研究的興趣點。歷史法學派所堅持的反對法典編纂的觀點似乎與那時的社會潮流有些不合時宜。加之普赫塔和耶林等概念法學理論的“推波助瀾”,以及19世紀中葉后的德意志諸條例和法典在同盟國中的順利實施,這些都促生了“潘德克頓法學”。
“潘德克頓法學”體系是由海斯(Heise)創立,其代表人物當屬溫德沙伊德。他對德國法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主要有二:其一,在《潘德克頓教科書》中,溫德沙伊德全面總結了“潘德克頓法學”的理論。該書對潘德克頓法學的概念、法律結構體系、歷史基礎等進行了詳細論證。其二,溫德沙伊德也直接參與并主持了德國民法典的制定。他是1888年民法典第一草案的實際起草人,所以民法典第一草案也被稱為“小溫德沙伊德”。“潘德克頓法學”的法典化最為明顯的標志表現在《德國民法典》的文體和概念上。“不僅法典的結構體系,而且法典的具體內容,都充分體現了潘德克頓法學派的概念精確、體系一致和邏輯自洽的思想”[12,p272]。因此,依靠法律構成技術的潘德克頓法學從法規中抽象出概念,這即是其創造性的體現,但是概念的操作一旦脫離了自己的目的,法學也就演變成了游離于實際生活之外的邏輯游戲。如此主張成為后來的自由法學及利益法學譏諷的對象。
可見,從普赫塔開始,在耶林的作用下概念法學的傾向漸次出現;溫德沙伊德作為“潘德克頓法學”的集大成者更是助推了概念法學的形成。概念法學以精密的自然科學為榜樣。“概念法學用嚴格而完美的學術將法與社會、法與現實徹底割裂開來。”曾經是普赫塔思想擁躉和潘德克頓法學嫡系的耶林后來“背叛”了概念法學,尖刻地嘲笑普氏等建造的“概念天堂”,成為了反對概念法學的旗手。在耶林看來,概念法學盲信邏輯、熱衷于抽象概念的游戲,忘記了法律對社會生活應當承擔的使命。與普赫塔強調規范的制定和適用僅靠理性依循概念就可完成不同,耶林認為目的才是整個法的創造者。“而目的是由歷史、社會和政治決定的,是不斷變化的。”所以,必須結合社會生活來解釋法律,法的目的應成為法學基本的指導原則。受耶林的影響,利益法學的倡導者赫克更是直陳概念法學的痛處,成文法典并不像概念法學一廂情愿認為的那般完善,漏洞的存在是在所難免的,如此一來,法官就充任立法者助手的角色彌補法律以滿足社會的各種法需要。
總之,歷史法學通過排斥立法者實現了法的“非國家化”。在歷史法學那里,法律不再局限在自然法理性所圈定的范圍內,而是一個國家和社會總體文化的組成部分。它“使人們意識到現行法與其產生歷史的、社會文化的作用條件之間的相互聯系。被美化了的概念賦予這個產生過程以這樣的稱謂,即‘民族精神’。因此,包含于一切法律規范中的政治的形成與決策的基本特征就顯現出來了”[18]。既然法的成長實質上是一個無意識的過程,那么與習慣相比較,立法的重要性顯然處于從屬的地位。所以,“法是被發現的,而不是被制定的”是出于“立法”立場的考量。作為歷史法學的“分野”之后的產物,概念法學則繼續著體系化的思維邏輯,將法學看成是純粹概念演繹的產物,對法進行著“非現實化”的加工。以往那種如薩維尼那般的對羅馬法的關注已經消散,現在轉向了側重于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礎之上構建一個現代的法律體系。像歷史法學所主張的從“民族精神”中發現法律的做法被純粹的邏輯思維所取代。立法者單憑邏輯就可建構的概念金字塔可以為司法者提供裁判一切糾紛的規范。法官只需循著概念思維發現法律裁判案件即可萬事大吉,而無需擔心規則是否允當或缺失。于是,發現法律成為了法官裁判糾紛的利器。綜合來看,基于對法典化運動的反對,歷史法學所倡導的“法律發現”拉近了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而概念法學視域中的“法律發現”似乎又使法律遠離了社會現實,將司法者囚禁在了概念的城堡里。這種理論上的幻想和邏輯上的惡性循環遭到耶林等人的批判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法律發現的“轉型”及原因評析
大致而言,薩維尼的歷史法學在其弟子的經營下將邏輯自足的觀念推向高峰,后來單純是為了維系法律的邏輯一致性、體系性,又將社會事實或者法律目的拋之腦后,使得潘德克頓法學流于概念法學。法律發現也正是在這一流變的過程中實現著立場的變遷。我們就以薩維尼、普赫塔、溫德沙伊德三人見解為切入點透視這種“轉型”,而后分析主導這種現象背后的因素。
恰如前述,薩維尼的法律發現觀主要是從立法立場進行闡述的。他認為法律的產生并非出于立法者獨斷的意志,而是由某種內在潛移默化的力量來促生的。“法律之形成,猶如習慣法之形成,先是肇始于習慣和通行的信仰,然后由于法學的淬煉,而底于成。”[19,p60]對此,臺灣學者林文雄將薩氏的觀點總結為以下幾點:一是法是被發現的,而不是被制定的;二是從原始社會的簡單的法發展到近代社會非常復雜的法,民族的意識不再直接地自我顯現,而它必須經由法律家的手將法的技巧巧妙地顯示出來;三是法律沒有普遍的妥當性或適用性。因此要追隨民族精神的發展,必須進行法的歷史研究[20]。具體來說,第一點詮釋了歷史法學派法律發現觀的立場和態度;第二點暗示了發現法律的主體即為法律家;第三點指明了發現法律的方法,強調歷史研究之于法律發現的重要性。不過,在這里需要明晰的是,薩維尼立法立場法律發現觀的提出主要是針對當時的德國是否制定法典這一問題而出現的。但是,我們卻不能想當然地認為薩維尼只是專注于立法立場的法律發現。其實,按照楊仁壽的說法,從前面的三點中也可得出薩維尼對法官職責的理解,“在于發現法律,適用法律,絕不容以自己的智慧來創造法律”。我們之所以堅持薩維尼是立法立場法律發現觀的倡導者主要是緣于他對法律本質的框定。縱使薩維尼由于首次系統提出了法律解釋的“四個因素”(語法、邏輯、體系、歷史)而被譽為當代法學方法論奠基者,但是這套解釋理論的出發點仍然沒有擺脫立法者的思維,“法律解釋者必須從立法者的立場出發,以一種藝術性的方式對法律進行重述”。因為“法官不能做任何修飾法律的工作,即使是改善有缺陷的法律也不行,因為那是立法者的職務。”
到了普赫塔這里,法律發現的立場也就隨著“概念金字塔”的構建開始出現了搖擺。在概念的譜系中,“法律條文并不是彼此并行不悖的有約束力的規范,而是符合理性的相互關聯并互為條件的體系”,這種構造理念“體現出了清晰的形式概念主義的維度,由此構成了形式邏輯體系之下的概念金字塔”[21]。如此層次分明、邏輯嚴密的法律秩序體系也使得法官適用法律的過程變得單純簡單。裁判法律問題時,“只須將有關的法律概念納入這一體系中,歸納演繹一番,即可獲得解答,此與數學家以數字及抽象的符號,按照公式為純粹形式的操作,并無不同。”可見,普赫塔在其師薩維尼既有羅馬法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一方面著力汲取羅馬法中的可與數學相媲美的確實性構建“概念金字塔”,在這一前提下另外又將關注的觸角伸向了司法,認為法官遵循發現的邏輯即可完成對糾紛的裁判。
行至溫德沙伊德,由于理論上來自概念法學的滋養和實踐上制定完善民法典過程中的決心和所累積的信心,法律發現不但完成了立場的轉移,另外獲得了更加充分的闡釋。溫氏認為,法官的職責,“乃在根據法律所建立的概念體系,作邏輯推演,遇有疑義時,則應探求立法者當時所存在的意思,予以解決。”[19,p60]對此應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首先,對法律自足性的強調和國家制定法的尊崇使得社會生活中發生的任何案件均可依邏輯方法從現有的法律中找到答案;其次,對于解釋法律的標準,溫德沙伊德認為應以探求立法者的意思為最終的旨歸,這里既指立法者明白表示的意思同時也暗含著立法者所未預見的法律問題。最后,在法律存在漏洞時,法官“可通過理論構成的方法加以解決,將利益衡量隱藏在邏輯的外衣之下。若結果與立法當時的意思矛盾沖突,亦牽強附會地謂立法原意本應如此。”所以說,立法者的原意統治著法官思維的整個過程:若遇明確法律直接邏輯推演即可;對需解釋的法律和存有漏洞法律的“加工”也被披上了貫徹“立法者原意”的外衣,其目的是為了排除利益衡量和目的考量,否認司法活動的造法功能。這樣以來,在“立法者原意”的護佑下,不僅清晰的法律同時需解釋和存有漏洞的法律也都是被發現的結果。發現法律的過程成為了純粹理性的認識活動。總之,在概念法學勾勒的法學藍圖中,立法者依靠邏輯推演制定的成文法典實為司法者發現法律的唯一淵源;司法者只要遵循發現的邏輯就能完成對糾紛的判斷。法律發現到了概念法學這里完成了由“立法”向“司法”的轉型,以后對它的提及也更多從司法者的角度進行闡揚。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在這種立場變遷的過程中,體系化的思維方式使得法學依靠自身邏輯就能建構起完備無缺的足以指導社會實際的規則;實證哲學的影響也讓原本醉心于將權威或偽哲學家的思辨作為認知之源的看法轉向了用經驗或觀察的方法來確定事物的本質。下面我們詳細分析這兩點是如何起著主導作用的。
其一,將基于羅馬法研究而引申的體系化方法推向了極致。作為自然法學派崩潰之后的產物,歷史法學急于掙脫理性統治所框定的藩籬,于是將突破口放在了羅馬法的研究上,并從中提煉出了體系化的思維方式。在薩維尼看來,“羅馬法的根本價值在于以其特有的純凈形式,蘊含了永恒的正義規則,因而賦予自身以自然法的秉性,而其具有的實際懲罰功能,則又使其具備實在法的功能”[6,p22]。除了這種實用性之外,他還對羅馬法的清晰莊嚴與優美贊賞有加。他贊揚“古典時期羅馬法學家的卓越典范,不僅認為他們的作品有重大的歷史貢獻,甚至認定他們表達了超越歷史局限的法律真理,因此才能逾千年仍被肯定、適用”[9]。而這一點正是因為羅馬法本身所具有的嚴謹的概念和精于計算的法律適用方式之于其“衰敗季節”所起的重要作用,而那時的法學家并沒有如薩維尼所處的德國那般急于制定法典,因為羅馬法學家認為,“每一條原理原則都可以適用于實際的案件,而每一個案件也都可以根據法律規則進行裁判;其從一般到個別,倒過頭來,再由個別至一般的游刃有余中,他們的精純技藝是無可否認的”。
于是,在《中世紀羅馬法史》中,薩維尼以“六卷”的筆力,希望透過羅馬法在歐洲歷史上的持續影響,以羅馬法對歷史的處理方式來影射當時的德國對待現行法的態度。而這主要是側重于歷史的論述。在《當代羅馬法體系》中,薩維尼將更多的筆墨耗費在了思想的建構上,推導出了羅馬法的指導原則,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的思想、理論和關于法律的概念。也正是在《當代羅馬法體系》中,薩維尼將系統的方法與歷史的方法進行了結合。可是,在歷史方法的使用上,他卻由于選取古代羅馬法而不是日耳曼法律作為研究的素材而遭到強烈的抨擊。正如臺灣學者林端所說:“歷史法學壓根兒不是為了法律史而法律史,毋寧說它的法律史的研究本身,即是展現了一個比先前的法學更高的科學原則。”歷史法學所處理的是法律學說與個別法律制度之間的歷史,即所謂“內在的”法律史,而對于法律與歷史的、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等基本問題卻避而不談。究其原因,“一方面,‘民族精神’這一概念就已經意味著放棄對這種關系(指的是法律與歷史、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做具體描繪的可能性:其非理性的、浪漫主義的民族與民族精神概念,并非把民族當作一個行動的單位看待,而是看作一個以神秘主義方式創造的有機體”[9,p46]。另一方面,薩維尼的羅馬法研究卻和其倡導的民族精神相形漸遠。“羅馬法,事實上比其他法律更少是創造的‘民族精神’的產物,它是法律人的法律,甚或是專家學者的法律。”而他們所進行的“歷史研究”主要是探討封閉的法律結構與解釋學的詳情,至于當時的環境對于法律建構所具有的意義則在所不問。
這樣一來,原本作為對抗理性主義的自然法學,歷史法學扛起了“歷史”的大旗,可是后來的發展卻與真正的“歷史問題”漸行漸遠。歷史法學“獨特的融合歷史的與系統的研究方式,使其‘歷史主義’出現無根且無由貫徹的特性,剩下來的主要仍是法律素材系統性的處理工作,這事實上與它要對抗的自然法思想所具有的形式的理性主義的觀念并無二致,使其最后發展成‘非歷史的’法律實證主義,竟然成為‘不可避免的必然結果’”[9,p105]。因此,在薩維尼等人的開拓和經營下,羅馬法體系的所有細節都得到了分析,“根據這一體系,所有的規則和原則都具有內在一致性,而且每一條規則和每一項原則也都成為了一個和諧整體的一部分。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理想法律體系的圖景;按照這一圖景,各國的法學家至少可以把其法律世界的某個部分置于理性秩序之中”[14,p38]。通過分析,薩維尼認為羅馬法學家的精湛的法律體系構造技術是在能夠確認法律自主性存在的前提下,保證法律連續性和進步性的關鍵。“通過概念方法和體系化方法,羅馬法學家有效地做到了法律技術與社會發展的統一。”在歷史法學派之前,法學家憑借自然理性來回答法律應當是什么的問題;而這之后,則通過以羅馬法研究為基礎所建立的理想法律體系中去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了。法學的任務也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悄悄地發生了轉移。“法學作為一種自主性的知識體系,可以確保司法審判時從法律概念和公理中推理出司法裁判的結果。在司法活動中,宗教、社會和政治的因素都不是法學家要考慮的因素。”[12,p295]
其二,緣于實證主義的影響。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得人類的認知模式發生了轉向,盡可能以精確的數學語言或純粹的實驗方法來確定行為的合法性成為了新的認識論的理想。實證主義正是導致這種認識傾向出現的原因。在實證主義看來,思想目的、價值或政治目的等問題不是經驗可以解決的。它衡量事物的標準被限定為實在的、事實的或經驗上可以被描述的。因此,在法學領域,實證主義“既反對將法與宗教和道德聯系起來,亦反對將它們與哲學類型的思辨一視同仁。”[16,p184]主觀主義或道德論的任何形式在實證主義這里遭到了拒絕。以客觀的和可以驗證的方法獲取法律知識成為研究的主流。
在這種認識方式的影響下,各種學派開始了對“實證之物”的探討。按照葉士朋的歸納,主要有歷史實證主義、概念實證主義、社會實證主義以及法條實證主義。以薩維尼為代表的歷史法學將產生于民族精神的法視為實證的,這種法以可觀察的客觀的形式顯現出來;概念實證主義認為,“那種一般的、抽象的、嚴格建構和聯貫一致的,不依賴實體立法的多變性而始終有效的法律概念才是實證的”;依據社會學的規則對法學進行研究被稱之為社會實證主義,而法條實證主義則側重于法律本身的研究,解釋法律并使之更加完整。總之,上述這些學派皆拒絕道德論或主觀主義的任何形式,將研究法律的切入點定位在了客觀的和可檢驗的標準上了。可見,實證主義促使法學擺脫了理性主義和神學法學的影響,這樣以來,法學就有了和其他學科一樣的普遍性和堅定性,積累和實現著自身的確定性。
法學實證主義總結了歷史和概念實證主義的成果,主張現有的法秩序是一個由法條和制度組成的封閉體系,該體系獨立于生活現實之外。在這一前提下,司法審判活動采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從法律體系中推導出正確的判決。這就要求,封閉法律體系中的“這些概念不僅具有所有時代均承認的體系性、教育性或語義學上之整理歸類的價值,藉此,其如同數學符號一樣可以促進專業學術上的理解,例如在課堂或學術性的判斷論證時;此外,其具備直接的真實性”[4,p417]。另外,為了保證現實生活中的案件能夠在封閉體系中找到合理的判決標準,該體系必須是無漏洞的。在法學的概念體系中而不是實證的法律條文體系中,體系沒有漏洞的目標得到了實現。“概念在概念金字塔中的定位與符合邏輯的體系脈絡,始終可以透過‘有創造力的建構’,邏輯一貫地填補實證法律的漏洞。持續不斷地推敲琢磨法學概念以達于完全的體系正義,正在滿足此一要求。一旦學術對概念的工作達到目標,那么任何可能想象的法律事件均可將之涵攝于某一定理或概念下,如是操作亦已足夠。然而,法官之法的發現工作必然就局限于正確涵攝的邏輯性工作。”[4,p418]
總之,實證主義在反對理性主義法學和基督神學的過程中發揮了“旗手”的作用。“法學實證主義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方面,法學是產生法的科學;法學在實現產生法的使命時是自治的——它不依賴于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22]以薩維尼為代表的歷史法學正是對第一層面內容的寫照;概念法學則是第二層面內容的延續和發展。毫無疑問,法學實證主義使得法學家必須將自身局限于純法律的斟酌,倫理、政治、社會方面的因素不在此列。利用給定的法律材料,從個別中引申出一般的事物,并從一般中引申出特殊的裁判結果。在法學實證主義所構筑的“圍城”里,法學和法律的自主性成為追逐的目標,而法學的任務也僅在于完成體系化法學的構建。“這個任務對于法學自身的完善來講,并沒有什么重大的危害,但是如果對法律和法學自主性的過分強調,乃至將法律體系和法學體系視為一種封閉的體系,那么在理論和現實中都會產生很大的危害性。”[12,p299]
四、法律發現的“今生”:司法立場的評點
在概念法學將法律發現僅僅視為在抽象法律體系中的邏輯推演時,耶林、赫克等學者呼吁法律適用更加關注社會目的、利益的做法也頗具有突破性。“因為一個只依據形式邏輯的標準所構成的體系,其將切斷規范背后的評價關聯,因此也必然會錯失法秩序固有的意義脈絡,因后者具有目的性,而非形式邏輯所能涵括。”[23]因此,在大多數的案件中,法官是不能夠嚴格地依法律獲得裁判結果的,那么就只能探究法官裁判時的事實動機如何。如此,規范性法學又被評價性法學所取代。可是,在評價標準的取舍上又會陷入選項較多而無所適從的窘境。法律發現剛剛掙脫概念法學的“虎口”,又不幸落入了社會法學為其預設的“狼窩”。調諧兩者之間的關系成為首當其沖的關鍵,為此應著眼于以下兩點:
其一,承認法典或成文法對法官發現法律的約束作用。雖然司法判決的過程并非概念法學所描繪的那般“純粹”,按照權力分立和法治國原則的要求,法官要受到法律的約束。一般來說,法官判決的任務不外乎將法律的內容具體運用到待決案件中,所以法典之于法官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實現了法律知識的系統化。將眾多的法律材料匯總成篇以系統化的法典形式表述出來,一方面可以使法官更快地有區別地獲取法律知識;另一方面也利于法官職業的專業化。其次,能夠確保法的確定性。通過法典可以獲取改善的法的確定性,“不僅指法官的行為變得更好預知,相關人能更好地適應未來的法院司法,在一般可獲得的法典中,可查閱那些必須被考慮到的權利與義務;獲得改善的法的確定性還意指,法官行為的正確性”[24]。此“正確性”存在于與法律的一致性之中,是可以被審查的。最后,增強判決的合法性。法典編纂減少了判決直接依據基本法律原則進行判案的可能。以基本法律原則為基礎而編纂的規范有能力使判決結果在內容上合法化。因為,“依據規范同時意味著依據法律原則,規范承載著法律原則。規范把法律原則的判決指示傳送至法律判決。”所以說,在成文法中發現法律應為法官司法的首選。
其二,法官考量價值的自由應以對相關程序的遵循為前提。嚴格將法官約束在法律字面含義上的做法受到了懷疑并得到了證實。服從法律并意味著反對法律概念的含糊性或堅持法官必須嚴守法律。法官不是“法律的嘴巴”(孟德斯鳩語),毋寧說是創造性地對待法律。可是,法官“創造性”的發揮也是有條件的。換言之,成文法權威的承認為法官發現法律框定了基本的路向選擇,而在通向判決的過程中,法官的“創造性”也被套上了“緊箍咒”,主要有二:一是形式要素的約束。正如拉倫茨所言,只要法律、法院的判決、決議或契約不能全然以象征性的符號語言來表述,解釋就始終必要。“解釋不是計算題,而是一種有創造性的精神活動。”在解釋方法的選擇上,應遵循語法、體系、歷史、目的、合憲解釋的順序,“這類規則指引的法律范圍,可能確保減少法官選擇的可能性,因而增強法律對他的約束”。另外,來自先例的約束。先例是法官在長期的司法活動中被提出、改變、后又被確定的判決原則。它的存在使得法官在案性區分、詞意確定等事項上省去了諸多麻煩,因此也是被事實上所承認和遵循的。所以偏離固守的先例,法官需耗費更多的口舌來論證其判決。二是非形式主義的約束。如法官所習得的有關法律理論,既可為法官司法提供必要的理論支持同時也限制了發現法律的技術選擇。再如,法官完全從法律、司法先例中獲知成文法的指示進而能夠直接確定某個證詞的確定程度、某個罪犯具體判決結果是否公正是不太能夠實現的,往往是通過察看和詢問別的法官在面對類似情況時是如何采取策略來印證和支持自己的選擇。這種非形式主義的約束雖說并沒有像形式主義因素那樣被學者所提及,但是確實在法官發現法律中的過程時刻存在并約束著他們的行為。
[1] 楊仁壽.法學方法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27.
[2] 劉治斌.司法過程中的法律發現及其方法論析[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06,24(1):35-43.
[3] 李鐘聲.法理學大綱(上)[M].臺北:三民書局,1999:132.
[4] 弗朗茨·維亞克爾.陳愛娥,黃建輝,譯.近代私法史(下) [M].上海:三聯書店,2006.
[5] 徐愛國.破解法學之謎——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學流派[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141.
[6] 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許章潤,譯.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9,22.
[7] 陳慧.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法學家——薩維尼的生平與學說簡介[J].德國研究,2003,18(4):54-59.
[8] 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鄧正來,等,譯.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一卷)[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5.
[9] 許章潤.薩維尼與歷史法學派[M].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10] 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24.
[11] 科殷.林榮遠,譯.法哲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31. [12] 曹茂君.西方法學方法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3] 大木雅夫.范愉,譯.比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92.
[14] 羅斯科·龐德.鄧正來,譯.法律史解釋[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
[15] 何勤華.德國法律發達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85.
[16] 葉士朋.呂平義,蘇健,譯.歐洲法學史導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17] 何勤華.歷史法學派述評[J].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36 (2):25-31.
[18] 魏德士.丁曉春,吳越,譯.法理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207.
[19] 梁慧星.民法解釋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5:60.
[20] 林文雄.法實證主義[M].臺北:三民書局,2003:5.
[21] 沈志先.法律方法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5.
[22] 霍爾斯特·海因里希·雅克布斯.王娜,譯.十九世紀德國民法科學與立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
[23] 卡爾·拉倫茨.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49.
[24] 阿圖爾·考夫曼,溫弗里德·哈斯默爾.鄭永流,譯.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75.
(責任編輯、校對:王學增)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Legal Finding: The Changes from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 to Concept Law as a Clue
ZHANG Zhi-we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Shandong Jiaotong University, Jinan 250357, China)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 Savigny advocates that law is the embodiment of national spirit which aims to narr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social life. The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s view that “law is to be found” is mainly gene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ve position. As one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 the concept law is to build the rigorous legal framework that could cover the overall social life. In its view, the judge only needs to find the law from the legal system to make the judgment that the judge is imprisoned in the castle of concept. It is reasonable that the theory fantasy is criticized by the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 representative Jhering.
legal method; legal finding;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 concept law
D90.05
A
1009-9115(2013)06-0076-09
10.3969/j.issn.1009-9115.2013.06.021
2013-02-02
張志文(1980-),男,山東臨清人,講師,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法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