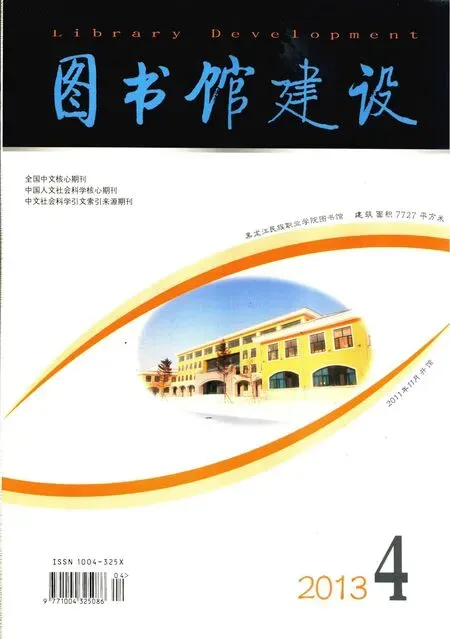弱勢群體圖書館權利保護及其限度*
沈光亮 (洛陽理工學院圖書館 河南 洛陽 471023)
對弱勢群體權利給予傾斜性保護是民主國家通行的做法,現代國家紛紛通過法律對弱勢群體的權利進行保護,并在具體實施中給予更為細化的政策保障。我國目前正大力推進公共文化事業建設,通過提供普遍均等的文化服務滿足個人精神追求和個人發展能力提升,讓更多的國民享受社會文化發展成果。圖書館權利作為公民基本文化權利的重要內容,對兒童、老人、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給予特殊照顧,這亦逐漸成為國內圖書館界的通行做法。在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權社會里,對弱勢群體的圖書館權利傾斜性保護為何成為社會共識?在對弱勢群體的圖書館權利保護中應遵循什么樣的原則?這是圖書館界應予以了解和明確的。
1 社會公正與弱勢群體權利保護
社會公正源于利益平等。平等是指“人們在社會上處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享有同等的權利”[1]。具體說來,平等就是不同社會主體在一定歷史階段的交往過程中處于同等的社會地位,在社會領域享有同等權益、履行同等義務的理念、原則和制度[2]。在我國,無論在理論闡述之中,還是在日常話語里面,人們通常還使用“公平”這一概念來表達與平等相近的意義。《辭源》對“公平”的解釋是“處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3]。至于合情合理,則可視作“在一種分配中,沒有任何一個人羨慕另外一個人,那么這種分配就稱之為公平分配”[4]。由于公平具有明顯的主觀性,很難設計出客觀的評價標準,而平等較之公平相對容易衡量。
不論是平等還是公平,都側重于物質分配或利益分配上的平等化。我國國民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愿望訴求,平均分配思想可謂根深蒂固。但簡單的平等思想顯然既不現實,也不利于勞動能動性的發揮。在促進國家經濟實力快速發展的思想指導下,按勞分配一直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原則。按勞分配承認了勞動主體的能力、體質、環境等事實差別,但社會客觀存在的弱勢群體在按勞分配社會中處于事實上的不利地位,進而容易造成社會差距不斷擴大。隨著我國和諧社會建設的不斷深入,按勞分配逐漸暴露出加大社會差距、影響社會穩定等不足。為此,我國政府逐步調整社會分配思想,即由“唯平等論”依次向“平等與效率并重”、“效率優先、兼顧平等”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穩步發展及社會和諧。
社會公正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政治宣言,社會中每個人不同的天賦、能力、性格等形成的綜合能力是有差別的。僅有形式上的平等并不夠,不管是機會平等還是過程平等,都無法保證結果平等,平等的濫用只會導致多數人以社會整體的名義損害弱勢群體的合理權益。社會利益分配的平等只是相對的,它既要體現多勞多得的生產規律,同時也要從社會道德和執政正義上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這就是著名的“差別原則”,即“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相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5]24。
弱勢群體也叫社會脆弱群體、社會弱者群體。按照學術界達成的基本共識,所謂弱勢群體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礙及缺乏經濟、政治和社會機會而在社會上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每個人都有自謀生活、自我生存的權利,當弱勢群體僅靠自己的能力難以生活、生存下來的時候,有向社會主張生活、生存的權利,政府必須履行保障公民正常生活、生存的責任[6]。法治社會通過對公共控制以實現對公民人權和基本自由的保障,通過矯正分配秩序對弱勢群體予以特別的保護,避免弱勢群體的實質性權利受到侵害,防止社會利益分配的不公[7]。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大多數國家都給予了社會弱勢群體某種制度上的救助與傾斜,而且一般情況下,隨著社會繁榮程度的提高,對弱勢群體的保障程度也在相應增大。
2 弱勢群體圖書館權利保護
現代圖書館秉承對全社會開放的理念,承擔實現和保障公民文化權利、縮小社會信息鴻溝的使命[8]。在我國,并沒有圖書館權利的權威界定,根據相關研究成果和國內政策相關內容表述,目前國內學界一致認為:圖書館權利就是公民依法享有的自由、平等、公平地利用圖書館的權利[9-11]。圖書館權利被視為公民基本文化權利的重要內容,接受圖書館服務是公民享有圖書館權利的具體方式,全體社會成員包括弱勢群體都有權利享有普遍均等的圖書館服務。國際圖書館協會和機構聯合會將圖書館權利享有中的弱勢群體界定為那些在使用傳統圖書館服務或資料上處于劣勢或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利用傳統圖書館服務的人群,包括聾啞人、肢體或發展性殘疾人、社會福利機構中的老年人、居家不能外出者、囿于醫院或監獄中的人和流浪者等[12]。《圖書館與知識自由宣言》強調圖書館“應該平等地為所有用戶提供信息、設備及服務,不允許種族、信仰、性別、年齡歧視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歧視”[13]。可見,圖書館權利平等也即圖書館服務平等。世界已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其先后制定的250多部圖書館法規中,強調或申明“提供平等服務、保障知識自由”是現代圖書館服務的重要理念。
在效率優先思想指導下,我國圖書館服務長期存在一些諸如簡單追求效率、忽視社會公正的現象。首先,表現在公共圖書館設置呈城市中心化。占我國人口多數的小城鎮和農村圖書館資源較為稀缺甚至是空白,農村居民難以享有圖書館服務。其次,社會居民接受圖書館服務有地區性限制。目前多數公共圖書館僅對本地戶籍居民辦理借閱證,有些雖然取消了戶籍限制,但在借閱證的辦理上仍保持一定區別,大量流動居民無法利用圖書館或受到區別對待。再次,圖書館服務資源向接受能力較強的讀者傾斜。讀者群被人為劃分成不同等級,圖書館服務遭受不平等對待。最后,圖書館服務管理色彩濃重。服務內容和項目往往是政府的“規定動作”或者是管理者的想象甚至一廂情愿[14],公益性推進還多停留在階段性社會工程層面,長期穩定的弱勢群體圖書館權利保護的運行體制還沒有真正建立。
公共圖書館服務不僅表現在有形物質載體的文獻信息傳播上,更體現在無形知識的傳承上,其實質是民主政府為公民平等享有基本文化權利、共享社會文化成果提供的制度保障。為保障弱勢群體能夠共享圖書館服務,我國政府及其相關機構從法律、政策及其實施上不斷對圖書館服務機制給予完善并對弱勢群體給予傾斜性特殊保護。我國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明確指出“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15],還針對婦女、老人、兒童和殘疾人等弱勢群體分別制定了相關社會保護法律。我國簽署的國際性公約、國家機關和地方立法機構或政府制定實施的相關規范性文件(如《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省(自治區、市)圖書館工作條例》、《北京市圖書館條例》等)也包含眾多弱勢群體圖書館權利保護的內容。
我國2006年發布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中,首次明確提出“切實維護低收入和特殊群體的基本文化權益”,“保障和實現城市低收入居民、殘疾人、老年人和農民工等群體的基本文化生活需要”[16], 標志著政府開始從實踐層面努力提升弱勢群體平等參與社會文化生活的機會和能力,使他們真正地融入到整個社會發展中去,實現社會全體公民的共同發展。我國相繼開展了一系列文化惠民工程,如鄉鎮綜合文化站和基層文化陣地建設工程、農家書屋建設工程,此外,還開展了諸如“知識工程”、“文化工程”、“送書下鄉工程”等文化援助活動,旨在積極構建普遍均等的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提高公共圖書館服務的社會覆蓋程度。同時,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對公共圖書館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項目所需經費予以補助或獎勵,要求公共圖書館公共空間設施場地免費開放,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免費提供,“在實現均等普惠的公共服務基礎上,逐步增設多樣化服務,重點增加對未成年人、老年人、農民工等特殊人群的對象化服務”[17]。努力滿足殘疾人、老年人、進城務工者、農村和偏遠地區民眾等的特殊需求,以體現民主社會的包容性[18]。
目前國內公共圖書館面向弱勢群體主要提供以下幾方面服務:第一,提供“無障礙”的圖書館設備、設施,如設置殘疾人通道、配備老花鏡,設置兒童閱覽室和盲文閱覽室。雖然國內關于圖書館區分服務仍有一定的爭論,但對圖書館針對弱勢群體開設專門服務空間的做法都一致認同。業界多對那些為了方便管理而限制讀者權利的做法給予拷問,同時也反對片面地將“公平、平等、自由”作為所有圖書館服務行為價值的評判標桿[19],那樣只能是一種形式上的平等,最終受損的是讀者權利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圖書館權利。第二,為弱勢群體提供知識援助和信息推送服務,如送書上門、設置流動服務點、開辟外來工借閱專區或分館。第三,開展有針對性的文化教育活動,如面向農民工、老年人、低文化者、低收入者等弱勢群體的電腦培訓、職業介紹、文化講座等。第四,提供免費的公共場地,如將圖書館研修室、活動室、報告廳等場所免費租借給社會公眾,開展大眾文化休閑活動。
一些圖書館針對弱勢群體服務提出了專門的規范要求,除了給予弱勢群體制度傾斜外,還通過倫理的方式給予弱勢群體從生理到心理、從物質到精神、道德方面的關懷和幫助[20],在滿足弱勢群體文化需求的基礎上,還滿足弱勢群體的人格尊重需求,提高享有文化服務的自信心。但從總體上看,目前我國公共圖書館弱勢群體服務長效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針對弱勢群體的服務對象重點在老年人和殘疾人等生理性弱勢群體上,對農民工、下崗職工等社會性弱勢群體服務的力度都不大,且多是臨時性安排。在開展弱勢群體服務時,其常常會選擇那些物力和財力投入都不大且又被大多數圖書館選擇的對象,這就導致了大部分公共圖書館服務對象的不全面和不均衡化。
3 弱勢群體圖書館權利保護限度
對弱勢群體圖書館權利給予傾斜性保護源于對人權的尊重和社會正義,其實質是通過制度安排將社會群體的利益分配向利于弱勢群體的方向調整,以保障弱勢群體獲得同樣的發展機會和精神生活[21]。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和社會弱勢群體權利保護意識還較薄弱,因此,國內學界基本認為我國對弱勢群體圖書館權利的保護還有待進一步加強。但事情都有其兩面性,任何權利皆應受到限制。權利的享有不是隨心所欲的,它要受到權利屬性、功能、條件等因素的影響,行使權利者的自由意志是在法律的框架內實現的,更要依賴于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22],同時還要受到道德規范的約束。
3.1 法律限度
法律規定了權利的特定范圍和條件;法律通過權力、義務對權利進行限制。任何人包括弱勢成員在享有圖書館權利時都要“保守國家秘密,愛護公共財產,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15]。 相關圖書館專門性法規中也多包含了讀者義務的內容。此外,所有的權利和權限都是相互的,沒有人可以比別人享有得更多,一個人所擁有的權利應以不損害他人的正當權利為界限,這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權利自然而然地被要求尊重和認同他人的平等權利。對弱勢群體圖書館權利的保護不能超過圖書館的服務能力,更不能以犧牲其他群體的圖書館正當權利為代價,這即是弱勢群體圖書館權利保護所必須堅持的合理和利益均衡原則。弱勢群體的圖書館權利必須是符合規范的,否則任何人都沒資格訴求[23]。只有弱勢讀者在追求正當的、正確的、合適的圖書館權利時,才可以期待得到圖書館員和其他讀者的尊重并給予支持或滿足。
3.2 社會限度
社會權利分配的價值訴求應該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現實社會中,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以及一國內部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人群之間,由于經濟實力和信息技術的應用水平等方面的不同,造成現實中圖書館資源的擁有存在客觀上的貧富懸殊[24]。圖書館服務多數要受時間、地點、場合和設備等條件限制,公共圖書館服務不可能滿足所有弱勢群體的需求,弱勢讀者的圖書館權利行使如果超過圖書館的服務的限度就屬不正當行使或濫用,圖書館有權對濫用的讀者權利進行限制[25]。弱勢群體圖書館權利的保護必須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即享受圖書館服務的特殊待遇時應該“有理、有利、有節”,否則就會走向反面。
3.3 道德限度
道德是基于人的本性的一種善惡評價,權利的實現不僅要合乎法律規范,同時也要合乎道德規范,社會輿論、人們的信念、傳統習慣等道德規范同樣對圖書館權利的實現產生一定的約束力量。與社會強制力量相比,道德往往會在更大范圍內發揮作用,它能使人們在尊重對方的利益最大化愿望、彼此利益相容并相互促進的情況下實現不同權利主體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因為公平與終極價值、道德評價、文化素養和個體情感等有著深刻的聯系,因此弱勢個體的道德水平和對圖書館服務公平的判斷不可能有統一的標準,只能是相對的。同樣,弱勢個體在實踐圖書館權利時,首先取決于其道德水平。例如,以前通行的辦證押金更多的是圖書館要求讀者作出信用承諾,其效力更多體現為一種道德約束,如果一個人連最起碼的信用和道德都不講,區區一點押金又能有什么用?就社會正義而言,權利優先于道德。杭州圖書館館長褚樹青明確表示,管理者和其他讀者無權拒絕流浪者甚至乞丐入館,當其他讀者不愿接納弱勢群體時,可以放棄自己的權利并選擇離開圖書館[26]。
4 結 語
一個公平的社會不應讓社會成員為偶然的、不是由他自身原因所造成的貧困和疾患負責[5]28。因此,在社會利益和社會權利的分配過程中,給予缺乏權利保障的弱勢群體以適當的關懷和傾斜性的特殊保護是一個正義社會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27]。但是,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被認為是具有一種基于正義、或者說基于自然權利的不可侵犯性[5]96,這就要求在圖書館權利保障的過程中,綜合考慮和平衡各方面權利,使各方權利達到一定程度的均衡狀態[28]。政府和圖書館管理者應通過采用一定的方式及程序,劃定不同社會群體的圖書館權利限度,協調權利關系,以排除權利糾紛或沖突,使各社會群體的圖書館權利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即便某一圖書館服務個體的圖書館權利受到侵害,也能通過權利救濟得以恢復或補償,最終維持一個良好的圖書館服務秩序。
[1]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988.
[2]唐澤霜.聚焦精髓:談圖書館精神中的平等精神[J].圖書館, 2005(5):23-25.
[3]陸爾奎,方 毅,傅運森,等.辭源[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647.
[4]伊特韋爾, 米爾蓋特, 紐 曼.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M].陳岱孫, 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1996:59-60.
[5]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
[6]邱 本.市場法治論[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 2002:314.
[7]覃有土, 韓桂君.略論對弱勢群體的法律保障[J].法學評論, 2004(1):60-64.
[8]中國圖書館學會·圖書館服務宣言(2008)[J].圖書館建設, 2008(10):1
[9]李國新.圖書館權利的定位、實現與維護[J].圖書館建設, 2005(1):1-4.
[10]程煥文, 周 旖.圖書館邁向圖書館行業自律時代[J].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 2006(10):118-123.
[11]劉茲恒, 陳 潔.關于圖書館權利的一點認識[J].圖書館雜志, 2005(8):3-5, 43.
[12]吳 桐.國外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包容理念與實踐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情報資料工作, 2010(3):24-27.
[13]國際圖聯《圖書館與知識自由宣言》[EB/OL]. [2013-01-06].http://wenku.baidu.com/view/b8c8321c227916888486d712.html.
[14]吳理財.公共文化服務的運作邏輯及后果[J].江淮論壇, 2011(4):143-149.
[15]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EB/OL].[2013-01-06].http://law.npc.gov.cn/home/ begin1.cbs.
[16]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EB/OL]. [2013-01-06].http://wenku.baidu.com/ view/ c12803c289eb172ded63b70d.html.
[17]關于推進全國美術館、公共圖書館、文化館(站)免費開放工作的意見[EB/OL]. [2013-01-06].http://www.gov.cn/zwgk/2011-02/14/content_1803021.htm.
[18]于良芝, 邱冠華, 許曉霞.走進普遍均等服務時代:近年來我國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構建研究[J].中國圖書館學報, 2008(3): 31-40.
[19]王宗義.圖書館精神與社會公平的辨證解讀[J].圖書館雜志, 2005(8):6.
[20]李俊奎, 梁德友.論弱勢群體倫理關懷的幾個理論問題:概念、維度與依據[J].社會科學輯刊, 2009(3):32-35.
[21]成中英.論東方德行倫理和西方權利倫理的結合[J].浙江學刊,2002(5):24-29.
[22]陸列奇.權利的限度[D].長春:吉林大學法學院, 2003:34.
[23]朱貽庭.權利概念與當代中國道德建設研究[J].倫理學研究, 2005(4):5-7.
[24]付立宏.關于數字鴻溝的幾個問題[J].圖書情報知識, 2003(2):7-11.
[25]謝少俊, 韓 毅.圖書館讀者權利的自由度及限制尺度[J].圖書情報工作, 2009(15):58-60,73.
[26]杭州圖書館走向開放 彰顯公平[EB/OL].[2013-01-06].http://news.sohu.com/20110402/ n279510722.shtml.
[27]江 婭.尋找保護弱勢群體的理論依據[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6):53-57.
[28]李昊青.淺析信息法學研究方法中的價值與效率維度[J].圖書館學研究, 2008(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