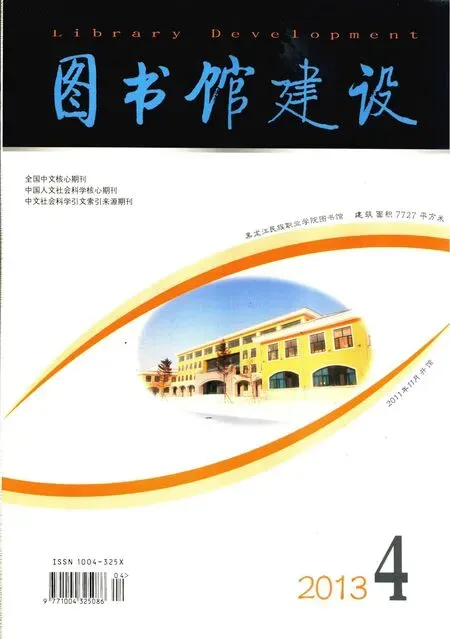基于著作權法視角的圖書館口述文獻工作探析
周曉燕 (南陽理工學院圖書館 河南 南陽 473004)
口述文獻(Oral Documentation Collection)是指用文字、圖形、符號、聲像等方法(或者相互結合)把口述內容固化在特定的介質上(如甲骨、青銅、縑帛、簡策、石頭、樹木、紙張、膠片、磁性或數字載體等)而生成的資料。現代意義上的口述文獻工作肇始于圖書館,圖書管理員是第一批口述文獻管理與研究隊伍的組成部分[1]。雖然有學者認為目前我國圖書館開展口述文獻工作的條件尚不成熟[2],但是這項工作的確在被日益推廣,可謂方興未艾。例如,國家圖書館[3]、新疆建設兵團黨校圖書館[4]、汕頭大學圖書館[5]等都一定程度地開展了這項工作。口述文獻工作不只受到專業性原則和業務標準的調制,更是受到制度規范的活動。事實上,在現代口述文獻工作的早期,著作權保護就是圖書館所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1]。相對于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的圖書館,我國圖書館對口述文獻工作中涉及的著作權矛盾與利益沖突還沒有深刻的認識,更不可能將其當成圖書館著作權保護的專門領域開展充分研究。然而,著作權不斷擴張的趨勢及社會上頻繁上演的有關口述文獻的著作權紛爭與訴訟事件應當引起圖書館的重視與警覺。口述文獻的收集、整理和開發利用滲透著著作權法的理念及其制度內涵,圖書館應針對其特點和規律建立完善的著作權管理體系與著作權危機防范機制。
1 口述文獻的著作權歸屬問題分析
探討口述文獻工作涉及的著作權問題的關鍵是要界定相關的權利主體、確認其創作貢獻、厘清相關的法律關系,為此必須認識口述文獻著作權的創作方式,而這又以了解口述作品的著作權特征為前提條件。口述作品的非實物載體性及口述文獻后續整理、研究、開發的參與主體的多元性,決定了口述文獻工作中存在著交叉聯系、相互影響、彼此制衡的多種類型、不同性質的復雜的著作權法律關系。
1.1 口述作品與口述文獻
《伯爾尼公約》第2條第1款中關于“講課、演講、講道和其他同類性質作品”指的就是“口述作品”。我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4條第4款中“口頭語言形式表現的作品”與其相對應。“獨創性”是口述作品得到著作權保護的必備條件之一,陳述語、感嘆語、問候語、詢問語等實用性語言并不是“作品”[6]。與其他作品類型相比,口述作品的最大特點是未經任何物質媒介“固定”,使得其在司法活動中存在“證據適用障礙”,這是美國、盧森堡、塞浦路斯等許多國家沒有對其提供著作權法保護的最重要原因[7]30。但是,口述作品是在作者頭腦中構思、加工而成的,是凝結了智力勞動的成果,體現著創造性,如果因為沒有被“固定”就不對其保護,很容易被他人剽竊和復制,并將其當成非法營利的借口。目前,部分國家的著作權法已經有了新的調整,不再以“固定”作為口述作品得到保護的前提條件,而只是當成司法程序中的一種證據要求。口述作品的創作與存在特點決定了對其提供保護的高難度性,于是將其及時固化在物質介質上成為口述文獻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也有利于后續的研究、保護、傳承工作的開展。在速記、錄音、錄像和數字化復制等技術的支持下,沒有加以“固定”的口述作品將越來越少[8]37。
1.2 口述者與口述訪談者
口述文獻著作權的歸屬并不清晰,關乎此類問題的糾紛最常見。以創作法律關系為標準,口述文獻可以劃分成“敘述式口述文獻”和“訪談式口述文獻”兩種類型。無論哪種類型的口述文獻,口述內容都是其核心部分,口述者都能夠享有并主張著作權,然而參與者(輔助人、合作人、受托委人)的身份、地位、創作貢獻卻有很大差異,這是口述文獻著作權歸屬的復雜性所在。在敘述式口述文獻中,參與者只做了輔助性工作,如提供場所和記錄設備、記錄口述內容、提供其他組織工作和咨詢意見等。按照《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3條的規定[8]337,這些活動不具有創作成份,不應被視為創作。因此,參與者不能享有口述文獻的著作權。在訪談式口述文獻中,參與者的身份主要是訪談者。訪談者需要事先搜集研究資料、擬定訪談主題、設計訪談框架、提出訪談計劃、準備訪談設備,并通過提問、引導等互動方式執行訪談。這樣,訪談者的活動就具備了創造性,訪談者與口述者是合意創作者,應共享著作權,即民法理論中的“準共同共有”,應當按照《著作權法》第13條有關“合作作品”的規定歸屬著作權[9]。正如里奇指出的,訪談文獻是雙方共同參與制作的產物[10]。至于委托創作情形下口述文獻的著作權歸屬問題,根據《著作權法》第17條的規定,則要考量口述者和訪談者之間是否有約定和約定的具體內容。一般認為,自傳性口述文獻的署名權不適用于合同約定。因為,如果自傳性口述文獻署名為訪談者、執筆者,那么就不能稱其為“自傳”,這屬于“事實不能”。
1.3 口述訪談者與圖書館
在圖書館口述文獻工作中,口述訪談者與圖書館存在著職務創作法律關系,訪談者實際上是圖書館的代理人,訪談具有職務性質,這決定了訪談者和圖書館之間的權益分配的法定模式。對于職務作品著作權的歸屬,各國法律規定的不盡相同。除了荷蘭之外的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都規定職務作品的原始著作權歸作者所有。英美法系大多數國家及大陸法系個別國家的法律規定,職務作品原始著作權歸單位所有[7]183-184。大部分東歐國家法律則規定,職務作品的著作權原則上歸作者所有,但作者所在單位在其工作范圍內以及國家在某些情況下,都可以代其行使權利[7]183-184。按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圖書館職工履行職責創作完成的口述文獻屬于《著作權法》第16條第1款規定的“普通職務作品”[8]329,著作權歸圖書館職工所有,圖書館在業務范圍內有優先使用權。兩年內,未經圖書館許可,圖書館職工不得許可第三人以與圖書館相同的方式使用口述文獻。需要注意的是,圖書館為制作口述文獻數據庫研發的計算機軟件,按照《著作權法》第16條第2款第1條的規定屬于“特殊職務作品”[8]329,圖書館內部的開發者只享有署名權和獲得獎勵權,其他著作權(包括財產權和除署名權之外的精神權利)全部歸圖書館所有。
2 圖書館口述文獻工作中的著作權問題
著作權問題存在于口述文獻采集、整理和開發利用的全過程。與其他類型文獻工作相比,口述文獻工作中的著作權問題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涉及的著作權項較多,除了復制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圖書館已經比較熟悉的財產權外,還會與圖書館工作不相干的匯編權、廣播權、攝制權、翻譯權、展覽權等財產權利以及發表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等精神權利發生聯系。另一方面,圖書館往往是口述文獻及其衍生作品的著作權共享主體之一,但是圖書館行使自己的權利時又受到口述者享有的權利的限制。圖書館和其內部參與口述訪談、記錄、整理、研究的職工之間的著作權利益平衡問題也是不可回避的。此外,許多口述文獻及其衍生作品極具開發潛力,增值空間較大,增值方法多樣,能否對第三人利用著作權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管對圖書館同樣是一個考驗。
2.1 口述文獻采集中的著作權問題
對圖書館最具挑戰性的著作權問題就是有圖書館訪談者參與的互動訪談式口述內容采集,因為圖書館對其中涉及的著作權問題比較陌生。例如,訪談者用速寫、錄音錄像等方式將口述內容“固定”,必會涉及復制權(包括數字化復制權)。如果訪談者在記錄過程中加入了自己的思想、立場、情感、傾向,勢必造成口述內容被篡改、變造;或者錄制設備故障,使“固定”后的口述文獻出現信息缺失,甚至可能侵犯口述者享有的修改權或保護作品完整權。顯然,圖書館對口述內容的“固定”屬于對口述者享有的著作權的直接行使。另外,基于網絡的跨地域、跨時空利用網絡攝像機、網絡視頻會議系統的口述訪談,通過博客、微博、電子郵件推送采集口述文獻在美國等國家的部分圖書館已實現[1]。在此情況下,口述者自己直接行使了信息網絡傳播權,但是圖書館必定要將口述內容收集、儲存在相應的設備中,這同樣是一種復制行為。無論是以速寫、錄音錄像或者數字記錄方式,還是通過網絡采集口述文獻,都主要涉及對口述者享有的復制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保護,而且這里面還涉及口述者是否享有“選擇權”問題。例如,有的口述者就只同意筆錄其口述內容,反對錄音[11]。對此,美國口述歷史協會制定的《口述文獻原則和標準》規定,訪談者必須尊重口述者的意見,口述者有權拒絕訪談者的建議[12]。所以,圖書館在采集口述文獻中保護著作權的關鍵問題不在于只是履行“告知義務”,而是要在告知采集的方法、特點、目的之后,與口述者進行充分溝通,按口述者的意愿辦事。
2.2 口述文獻整理中的著作權問題
著名口述史學家P·湯普森認為,“整理”是整個口述文獻工作最重要的組成部分[13]。口述文獻的整理有兩種類型:其一,技術整理。即對口述文獻進行分類、標引、編目,并制作相應索引、目錄、文摘等工具。世界上最有影響力、最具通用性的口述文獻技術整理工具是美國口述歷史學會的《口述歷史編目手冊》(Oral History Cataioging Manual)。其二,內容整理。可以將其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對口述內容補充、更正、稽核、甄別,去偽存真、去蕪存菁,這屬于口述史研究的范疇。口述史整理研究可能產生新的作品,而這種新作品的著作權可能只歸屬于整理者,也可能由口述者與整理者共有。口述史研究盡管不是圖書館的主要工作范疇,但亦會有所涉及。二是只對口述內容進行簡單的拼接、編輯、訂正等學術邏輯和文法的整理加工,并將口述內容轉換成文字或者數字形式,這是圖書館整理口述文獻的重點。在此情形下對口述文獻的整理必須是“原始性”的或者“原真性”的[14]。例如,隸屬于英國國家圖書館的英國國家口述資料館將所有錄音磁帶上的聲音(包括寒喧、重復、咳嗽等)都嚴格按照原始聲音轉錄成文字[15]。圖書館整理口述文獻涉及的著作權問題最為復雜,因為具體的整理行為究竟是屬于“口述史研究”,還是“原真性加工”,往往不容易區分。這又是一個必須明確界定的問題,關乎圖書館、口述者及其他主體對基于口述作品、口述文獻的衍生創作成果的著作權益的分享。
2.3 口述文獻開發中的著作權問題
彰顯口述文獻重要價值的做法就是加大開發利用力度,主要方式包括出借出租、編研出版、影視改編、陳列展覽、專題研究及進行多媒體、數據庫等數字化開發等。例如,美國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的訪談抄本都按照受訪者名字的字母或者訪談主題順序實現了互聯網絡查詢和檢索,而且個別訪談抄本都已在網上全文發布,讀者可以通過網絡任意下載口述抄本。對于訪談的磁帶,圖書館可以根據讀者需要提供出租服務[16]。美國一些口述文獻研究機構也專門提供錄音、錄像資料轉錄和整理的有償服務,其中以康涅狄克大學圖書館口述歷史辦公室(Oral History Office, University of Connectivut)最具特色,其享有最高的聲譽[1]。圖書館開發利用口述文獻受到口述者享有的復制權、出租權、翻譯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專有權的控制,如果圖書館許可第三人對口述文獻進行小說、影視、戲劇作品等藝術創作或者出版,還要受到發表權、改編權、匯編權、廣播權、攝制權、翻譯權等權利及圖書館是否享有“再授權”權利的制約。圖書館在與口述者的談判中,應爭取盡可能多的權利,最好是得到專有使用權,甚至受讓著作權。否則,圖書館開發利用口述文獻的價值將大打折扣。由于圖書館可能成為口述文獻及其衍生作品著作權的共享主體之一,所以圖書館在行使自身權利時要注重對口述者合法權利的保護,在權利無法分割行使或者權屬不明時,更要恰當把握行使權利的“尺度”與“方法”,不能以犧牲口述者的利益作為實現圖書館利益的代價。
3 基于著作權保護的圖書館口述文獻工作
就我國法律法規來看,在明確界定口述文獻的著作權,對于尚未形成信息產品的原始口述資料,如何確定其著作權等方面存在法律障礙,至今沒有解決辦法[12]。在此立法狀況下,圖書館應以現行法律法規既定的著作權原則為依據,建立健全口述文獻工作中的著作權保護規范,尤其是不能忽視對法律風險評估與合同約定的著作權管理方法的運用。圖書館還要積極采取措施,培養、提高口述文獻工作者的著作權保護素質,建設專業化的著作權管理隊伍。
3.1 制定和健全著作權保護規范
要使法律法規的精神得到落實,必須在《著作權法》所確立的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圖書館保護著作權的自律性規范。例如,美國口述歷史學會于1968年制定了《口述文獻原則和標準》,1979年出臺了《口述文獻評價準則》,現行版本是2009年9月制定的《口述文獻的通用原則和最優實踐》,這些行業規范對口述者、訪談者的權利、義務、法律責任、權利許可與轉讓和放棄等作了規定,還提供各種標準的法律授權樣本,具有較強的指導性和實用性[11]。我國圖書館口述文獻工作起步相對較晚,尚無行業性的政策或者指南。以現行法律法規為依據,借鑒美國《口述文獻原則和標準》的相關內容,綜合各種觀點與實踐,口述文獻工作應遵循的著作權規范主要包括:其一,程序合法。將訪談的內容、時間、地點、方式(筆錄、錄音、錄像、數字記錄等)以及使用方式(編輯整理、開發利用等)與限制、優先權、版稅等問題告知口述者,并征得其同意,即取得授權。例如,按照美國《著作權法》第101條規定[17],圖書館將口述內容以速寫、錄音錄像、數字設備等方式“固定”,必須經過合法授權。否則,屬于非法活動。其二,簽字生效。對于口述內容整理、加工、編輯后形成的口述文獻經口述者審查簽字才能定稿。其三,證據保全。對錄音帶、錄像帶和底稿、光盤、照片、速記本以及其他收集到的材料要完整保存,整理出來的文字結構要保持原來采訪流程的順序,這不僅是出于對進一步研究與開發利用的考慮,在發生糾紛時還可以作為主張權利和應訴抗辯的佐證[18]。其四,利益共享。如果對口述文獻的開發利用有經濟收益(出版發行、調閱收費、影視改編或與此有關的其他收益),應與口述者合理分享[14]。其五,履行義務。與口述者和第三方開發利用者訂立完備的著作權合同,認真履行合同約定,嚴格按合同辦事。其六,談判磋商。如果口述者要行使與圖書館共同享有的不可分割的權利,圖書館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而應主動與其協調,達成一致。其七,權限控制。例如,美國圖書館普遍對數字化口述文獻的使用設置了諸多權限,防止非法復制和傳播[1]。其八,內部管理。建立圖書館內部著作權管理制度,清晰界定圖書館與其職工之間的著作權法律關系。
3.2 評估不同業務中的法律風險
雖然圖書館對于每項口述文獻工作都會事先制定詳細的計劃,其中包括應對可能出現的著作權糾紛與訴訟的預案,但是比較于對其他類型文獻的搜集、加工、整理、儲存和利用,口述文獻工作仍然具有較高的法律風險。其一,法律法規不健全。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及其配套制度對口述作品、口述文獻的闡述存在“盲點”,這也是有的學者認為國內圖書館尚不具備開展口述文獻工作條件的理由之一[19]。其二,口述文獻工作本身的著作權特點。例如,圖書館出于業務的需要不得不對口述內容編輯、加工并在一定范圍內“公開”,這種管理權勢必會與口述者享有的發表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復制權等權利發生沖突。其三,缺乏著作權管理經驗。由于口述作品、口述文獻、口述文獻工作中的權利主體多而相互關聯,絕大多數圖書館缺乏專業著作權管理人才,難以判明其中的法律關系,更別說制定科學的處置策略。其四,外部風險管理難度大。圖書館對經其授權的第三人(包括文學、影視、戲劇、曲藝的創作者和電子書商、錄音錄像制作商、數據庫開發商與出版者等)利用口述文獻的行為很難監控(即使訂立有相關協議),如果因為第三人的過錯造成侵權,作為口述文獻提供者的圖書館自然會被牽連其中。對于我國圖書館,口述文獻工作是著作權保護研究與實踐探索的新領域,圖書館要對其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風險認真研究、掌握規律,積累防范和化解風險的經驗,建立健全預判和預警機制。鑒于口述文獻工作的特點,圖書館希冀建立一套針對所有業務類型的風險評估模式并不可行,因為每種類型的業務有不同的著作權特點與管理要求,需要開展專項的風險評價。
3.3 以著作權合同約定權利義務
在口述作品、口述文獻著作權的法律法規不健全的背景下,合同的價值凸顯,其目的是將事后的權益分配和矛盾處理變成事前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界定,從而利于主張權利、助于防范糾紛、便于調解審理。合同可以是許可使用合同,也可以是轉讓合同,但一般應具備編輯和使用的限制,著作權歸屬、優先使用權、版稅、資料的預期處置方式和各類傳播方式及電子發行等項[20]。合同涉及的權利內容應盡可能寬泛(如復制權、信息網絡傳播權、匯編權、廣播權、翻譯權、攝制權、放映權、展覽權,以及發表權、修改權等),同時要約定圖書館是否享有轉授權。對于口述文獻及其衍生作品存在的合作創作、委托創作問題,合同中更要明確界定圖書館與口述者的權利、義務和法律關系。除了權利的歸屬和行使外,合同還要包含《著作權法》第24條、第25條規定的其他內容。合同對隱私權保護等法律問題也要有所觸及,雖然這與著作權保護無關。總之,合同條款應細化,忌籠統和粗略,這樣有利于對圖書館權益的保障,如“李宗仁與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口述作品糾紛案”就是典型案例[21]。合同不宜采取口頭或其他形式訂立,而應是書面合同,并且口述者必須簽字。在相關口述作品著作權糾紛中,有的當事人認為,其沒有在合同書上簽字,合同對其不產生法律效力[22]。合同模式同樣適用于圖書館與其內部職工(口述訪談者、整理者,軟件開發者等)之間的權利、義務與法律責任的約定,因為圖書館未與其內部職工簽訂著作權合同而導致的訴訟案件在我國圖書館界已有發生[23]。與其他著作權使用合同不同,圖書館應特別要求口述者在口述文獻合同中訂立“真實性條款”。因為,如果口述者的言論涉及到對他人的傷害、誹謗、誣蔑、詆毀、隱私或者泄密等而引起法律問題,圖書館作為參與者,自然脫不了干系。訂立“真實性條款”是圖書館重要的自我保護措施,對口述者也會起到警示作用。
3.4 提高工作人員的著作權素養
口述文獻工作增加了一個新變量,即歷史的見證人和在場者──口述者,使得流程中增加了兩個新的維度,即口述者與歷史現象間的關系、口述文獻工作者與口述者之間的關系[24]。這對口述文獻工作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學者認為,口述文獻工作者集圖書館工作者、檔案工作者、歷史工作者、新聞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等身份于一體[25]。對于口述文獻工作,并非只要有熱情就能做好,不經過相關的專業訓練是無法勝任的。例如,對于怎樣在尊重和保護著作權的前提下對口述內容以速記、將錄音轉成文字的方式固定下來,如何把握“口述史研究”與“原真性加工”的界限,如何向第三人授權使用口述文獻及其衍生作品等問題,大多數圖書館工作者是不清楚的。20世紀50年代初,為了保證口述文獻的工作質量,美國肯尼迪總統圖書館就曾專門訓練和雇傭了一批資深的圖書館員、歷史學家來承擔有關任務,這時期的口述文獻工作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來說都有很大的提高[16]。1968年后,美國匹茲堡等大學的圖書情報學院開設了“口述歷史與口述傳統”課程,講授口述歷史從口述到各種記錄格式的發展、口述歷史館藏的開發與管理[26]。目前,在線口述文獻知識培訓服務也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貢獻最大的是美國口述歷史學會于1995年創辦的“口述歷史論壇”(H-Oralhist)[27]。至于著作權素質對于圖書館口述文獻工作者的意義,早在1968年,Zacher就認為,口述文獻工作要求圖書館員補充新知識、掌握新技能,積累著作權保護經驗[28]。為了解決我國圖書館口述文獻著作權管理人才匱乏的問題,除了開展著作權保護普及教育外,可以借鑒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部分圖書館的做法,創造條件逐步設置“著作權圖書館員”(Copyright Librarian)[29]崗位,由專人負責此項事宜。
[1]楊祥銀.當代美國口述史學的主流趨勢[J].社會科學戰線, 2011(2):68-80.
[2]蔡 屏. 我國圖書館在現有條件下開展口述歷史工作的局限[J].圖書館建設, 2012(1):39-42.
[3]國家圖書館中文資料組.國家圖書館關于征集“非正式出版文獻”的公告[EB/OL].[2011-01-11].http://www.nlc.gov.cn/syzt/2008/0709/article27.htm.
[4]趙維景.口述歷史:圖書館特色館藏建設的新領域[J].科技創新導報, 2012(12):216.
[5]張 衛.口述歷史收集與整理工作的意義與注意事項:以威寧縣地方文獻收集為例[J].圖書館建設, 2011(3):27-28.
[6]王 倩.談口述檔案著作權問題的特殊性[J].檔案, 2011(1):15-17.[7]鄭成思.版權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0.
[8]李明德, 許 超.著作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9]董瑜芳.試論口述歷史中的版權問題[EB/OL].[2011-12-17].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I.php?NewsID=4217.
[10]里 奇.大家來做口述資料:實務指南[M]. 2 版.王芝芝, 姚 力,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5:15.
[11]傅光明.口述史:歷史、價值與方法[J].甘肅社會科學, 2008(1):77-81.
[12]鄭松輝.圖書館口述歷史工作著作權保護初探[J].中國圖書館學報, 2010(1):104-110.
[13]王杉勝.淺談口述資料的搜集與整理[J].新疆地方志, 2007(3):16-18.
[14]曹幸穗.口述史的應用價值、工作規范及采訪程序之討論[J].中國科技史料, 2002(4):335-342.
[15]李小江.口述歷史與檔案工作[J].中國檔案, 2006(1)55-56.
[16]楊祥銀.美國總統圖書館的口述歷史收藏[J].圖書館雜志, 2000(8):60-64.
[17]李明德.美國知識產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53.
[18]陳俊華.圖書館開發口述歷史資源探索[J].圖書情報工作, 2006(6):126-129.
[19]蔡 屏.我國圖書館在現有條件下開展口述歷史工作的局限[J].圖書館建設, 2012(1):39-42.
[20]尹培麗.口述資料及其著作權問題探究[J].圖書與情報, 2011(3):53-56, 84.
[21]薛鶴嬋.口述檔案的知識產權研究[J].蘭臺世界, 2009(6):31-32.
[22]王 云.口述“紅旗渠”修筑者獲著作權[EB/OL].[2012-02-11].http://www.news.ifeng.com/society/1/detai/2012-10/22/184169540-shtml.
[23]秦 珂.圖書館工作中區分職務作品和法人作品的法律適用界定[J].圖書情報工作, 2010(10):129-132.
[24]任中義.口述史學及其規范性研究[J].洛陽師范學院學報, 2012(3):92-95.
[25]張 燕.基于口述史的檔案編研發展策略分析[J].山西檔案, 2010(5):19-21.
[26]匹茲堡大學圖書情報學院課程[EB/OL].[2012-11-16]. http://www.sis.pitt.edu/-lsdept/descrip.ht.
[27]美國口述歷史論壇[EB/OL].[2012-11-16].http://www.h-net.org/-oralhist/.
[28]口述史在二十一世紀所起的文獻作用[EB/OL].[2012-12-07].http://www.archives.sh.cn/docs/200802/d155517.html.
[29]陳傳夫, 汪曉方, 符玉霜.國外版權圖書館員崗位設置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國家圖書館學刊, 2009(2):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