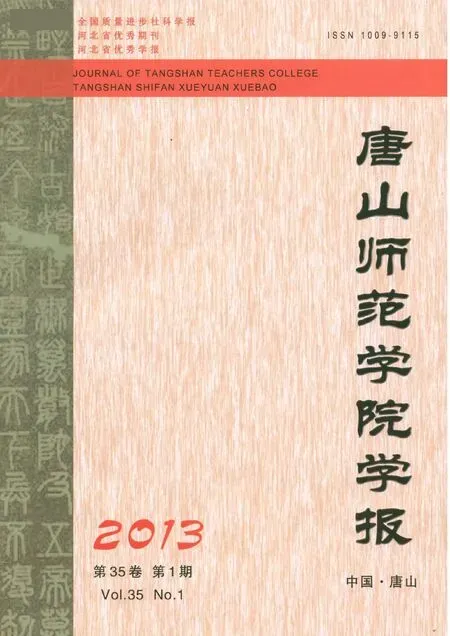從認知隱喻的角度解讀狄金森“死亡”詩中的張力
趙振華
(桂林航天工業學院 外語系,廣西 桂林 541004)
隨著Lakoff和Johnson認知隱喻理論的提出,隱喻研究突破了傳統修辭學的領域,上升到思維和認知的高度。隱喻無處不在,日常生活表達中充斥著大量的隱喻[1]。詩歌中的隱喻能意象盎然,張力四射,是詩人善于運用隱喻的意象性,對客觀事物的描述中添加和融入了自身對主觀世界的感受和認識,使隱喻認知不斷加深和升華的結果[2]。狄金森是美國文學史上頗具有傳奇色彩的女作家,她一生之中留下了1 800多首詩歌,其中有三分之一的詩歌是對“死亡”的詠頌。Henry James評論說狄金森的“死亡”詩代表了她詩歌創作的最高成就。Lakoff和Johnson的隱喻理論為研究狄金森的“死亡”詩歌提供了全新視角。
一、認知隱喻學對詩歌張力的解讀
從亞里士多德至今的2 000多年里,隱喻一直被局限于修辭學研究,屬于詩學和文學研究的范疇。隨著20世紀80年代Lakoff和Johnson的著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的發表,隱喻研究進入了認知和思維的新時代。Lakoff和Johnson認為隱喻是一種認知手段,一種思維和行為方式,是概念從一個認知域向另一個認知域映射的過程。Lakoff在2004年北京的講座中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認知隱喻觀,并重點討論了詩歌中的隱喻。他認為詩歌中的隱喻之所以能充滿張力是因為“詩人所做的不是給經驗以新的概念化,而常常是以新奇的方式去描述業已形成的經驗概念”[3]。
詩歌作為一種獨特的語言藝術,它包涵著詩人豐富的思想、情感和意境,給讀者一種特有的心理享受。在詩歌中有許多高度陌生化的隱喻,它們和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常規隱喻不同,通過尋找相似點的傳統方法來理解隱喻是比較困難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在語言層面上,應從認知和思維的高度對其進行分析,否則就難以體驗詩歌隱喻中的無窮張力。如果說隱喻是詩歌的靈魂,那么張力可以說是詩歌的氣質。隱喻作為詩歌最重要的表現形式,其張力大小被用作衡量隱喻表現力和感染力的重要標準。概念隱喻理論認為隱喻認知感的強度,即張力的大小取決于源域和目標域的距離及其映射方式,即兩域之間的距離越遠,人們感知的張力越強烈;映射的方式越遮蔽其引發的心里沖擊就越大。隱喻不是整體的系統映射,而是部分映射。由于概念體系地存在于人的大腦中,隱喻中的兩個概念域都有其自成體系,是包含有子集的集合體,Lakoff & Johnson將這些子集稱為蘊含(entailment)。隱喻的張力就是通過突顯、忽略和遮蔽的方式從經驗范圍內選擇部分蘊含而形成的,它來源于相距遙遠的兩事物的和諧映射。詩歌之所以可以創造出無窮的張力,正是因為詩人將概念從源域映射到目標域時,應用非常規的隱喻映射,巧妙的突顯源域和目標域中的某些子集,將看著本不相干的、距離遙遠的兩個域并置到一起,產生了豐富的隱喻意象,強烈刺激讀者的感覺,喚起讀者腦海中的意象,使其心靈感受到巨大的沖擊力,激發讀者的想象力,產生無窮的隱喻張力。
二、狄金森詩歌中死亡“隱喻”的特點
狄金森存世的500多首“死亡”詩可謂是其對美國文學獨特貢獻之一[4]。她通過其特有的想象和意象,表述自己對死亡的理解,通過具體生動的身體感覺來描繪死亡感受,使抽象的概念具體化。詩歌中的隱喻從各個角度研究了死亡,并表達了她的真情實感,表現出無限的隱喻張力。
下文以狄金森“死亡”詩歌中的幾首代表作為例,分析其隱喻中的強大張力。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He kindly stopped for me—
The Carriage held but just Ourselves-
And Immortality.
We slowly drove--He knew no haste
And I had put away
My labor and my Leisure too,
For His Civility—
We passed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Recess—in the Ring—
We passed the Fields of Gazing Grain—
We passed the Setting Sun—
Or rather—He passed Us—
The Dews drew quivering and chill—
For only Gossamer, my Gown—
My Tippet—only Tulle—
We paused before a House that seemed
A Swelling of the Ground—
The Roof was scarcely visible—
He Coraice—in the Ground—
Since then--’tis Centuries--and yet
Feels shorter than the Day
I first surmised the Horses’ Heads
Were toward Eternity—
狄金森在這首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中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哀婉動人的唯美畫面。詩人受和藹可親的紳士——死神的邀請,和永生(immortality)一起坐上他的馬車,穿過學校,越過田地,看到夕陽西下,感到夜里衣薄體寒,最后到達一座仿佛墳墓的房屋,然后再一同走向永生。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一些概念隱喻,如DEATH IS DESTINATION (END OF JOURNEY)和 DEATH IS DEPARTURE。在這兩個概念隱喻中生命是一次旅程,死亡是這一旅程的終點,人死后會有 coachman和 footman幫助死人踏上旅程,然后聽候上帝的裁定,好人升入天堂(paradise),壞人被打入地獄(hell);還有DEATH IS THE END OF A DAY人的一生被比作一天或年,而夜晚的黑暗代表著死亡(DEATH IS DARK);HUMAN DEATH IS THE DEATH OF PLANT這一隱喻概念中借用了人和植物的某些相似點,植物的凋零被映射到人類的死亡[5]。狄金森巧妙的將這些概念巧妙的融入詩中,通過巧妙地突顯兩個概念域中的某些子集,使得原本相距甚遠的兩事物得到和諧的映射,突破了常規隱喻的表達。通過讀這首詩我們感覺到了詩歌中強大的張力,她對死亡的經驗的描述并沒有限于死亡的片刻,而把它視為通往永生的必由之路。詩中的死神沒有恐怖丑陋、猙獰的面孔。狄金森把死亡描述成一位風度翩翩、和藹有禮貌的紳士。在人生的旅途中,這位紳士邀請作者為伴,走向永生。狄金森對死亡的描寫不但含蓄隱晦而且十分飄渺。她巧妙地運用隱喻使原來令人痛心疾首的哀傷變得朦朧,充滿詩意。詩中沒有生離死別的痛苦,一切盡融入敘事者超然的回憶中。詩人只是在敘述一天的行程。詩人用一日比喻一生,學校象征童年,豐收的稻田象征青年,沉落的太陽象征晚年,最后到達的是那座形同墳墓的房屋,即到了人生的最終歸宿。詩人把人的一生描述得各得其所,警示活著的人要學會珍惜人間的友情、親情、愛情,經歷人間的酸甜苦辣,當死亡真正來臨之際,也就能做到毫無畏懼地坦然面對。
《我死時聽到了蒼蠅的嗡嗡聲》是狄金森的代表作之一[6]。一般人看來,死亡是萬分痛苦、不能忍耐的事,狄金森卻不以為然。詩是以第一人稱寫的,描繪了詩人躺在床上即將遠離喧囂的人世,旁邊圍滿了前來告別的親朋好友。
I Heard a Fry Buzz—When I Died
The Stillness in the Room
Was like the Stillness in the Air
Between the Heaves of storm—
The Eyes around--had wrung them dry
And Breaths were gathering firm
For that last Onset—when the King Be witness--in the Room—
I willed my Keepsakes--sign away
What portion of me be
Assignable.—and there it was
There interposed a Fly
With Blue—uncertain stumbling Buzz
Between the light—and me—
And then the Windows failed—and then
1 could not see to see—
Lakoff和Turner在其研究中總結出死亡是身體反應的概念隱喻(DEATH IS BODY REACTIONS)時,歸納了一些常用的隱喻表達,如“Close one’s eyes, breathe one’s last,draw one’s last breath, expiring zero heart beat, no brainwaves, to kick the bucket, out of pain”等[2]。狄金森巧妙地將這些動作投射到死亡這一目標域上,還運用“意識和體力的減弱直至停止”來喻指人的死亡。彌留之時已不能感觸到其他事物,而只能聽到蒼蠅的嗡嗡作響。蒼蠅這一意象是這首詩的一個亮點。蒼蠅是生命轉瞬即逝的標志,蒼蠅來臨預示著死亡的臨近,蒼蠅的嗡嗡聲反而更反襯了屋里的寂靜。這首詩成功地運用了蒼蠅這一意象,通過隱喻生動描繪了詩人如何從有知覺、有意識到無知覺、無意識的死亡狀態。詩人自始至終保持著對死亡客觀冷靜的態度,對死亡經驗描述是奇妙、不可思議的,是活著的人無法了解的感覺。似乎死亡是一種美妙的體驗,是通向永生的橋梁。臨死的情景被她描繪得淋漓盡致,猶如身臨其境。
事實上,死亡的經驗一個人一生只能體會一次,沒有特殊的敏銳和超前的悟性是很難如詩人般繪聲繪色地描述自己彌留的感受的。狄金森正是憑著自己的直覺,巧妙運用這些隱喻,這一非常規的表現形式擴大了詩歌的內在感染力,表現出了極大的張力。
狄金森的另一首小詩《Apparently with no surprise》:
Apparently with no surprise
To any happy flower,
The frost beheads it at its play
In accidental power
The blond assassin passes on,
The sun proceeds unmoved
To measure off another day
For an approving God
The look of Death
在這首詩中,狄金森巧妙地運用DEATH IS THE END OF A YEAR這個概念隱喻。這個死亡概念隱喻是英文中特有的,在漢語中基本上不用。作者將死亡比喻成冬日,也能看出作者對死亡的坦然態度,對待死亡就像四季輪回般。冬天是一年中最末的季節,詩人用它喻作死亡,即DEATH IS WINTER。冬天的到來,即意味著死亡的臨近。冬天具有極大的破壞力,它和死亡的本質接近。嚴霜(Frost)在詩中就是殺戮者(assassin)。一朵小花被嚴冬砍下頭顱,生命就此終結,周圍卻對此無動于衷,沒有震驚,沒有悲傷。整首詩彌漫著陰霾、恐怖的氣氛。蒼白的太陽帶來的不是溫暖,自然界中的事物失去了美好的一面。嚴冬的殘忍、小花的無辜可憐、周圍事物的冷漠都躍然紙上,讓讀者感覺到詩中隱喻的巨大張力。
詩歌作為一種藝術的表現形式,它反映人們的生活和思想,并給予讀者心靈上的愉悅。詩歌的張力來源于它非常規的表現形式——隱喻。無疑詩歌就是隱喻化的語言。通過運用概念隱喻理論對狄金森“死亡”主題詩歌進行分析,我們更能深刻體會她的獨特視角和意境。狄金森用極其豐富的隱喻對死亡這一主題進行了探索,刻畫出不同的死亡意象,向人們展示了她神秘而又豐富的內心世界。
[1]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1-23.
[2]Lakoff G., Mark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143-145.
[3]Lakoff G. Ten Lecturures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y Lakoff[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158.
[4]常耀信.美國文學簡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112-125.
[5]趙振華.“死亡”概念隱喻——基于英漢語料的對比研究[J].桂林航天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2(3):53-55.
[6]江楓,譯.狄金森名詩精選[M].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1997: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