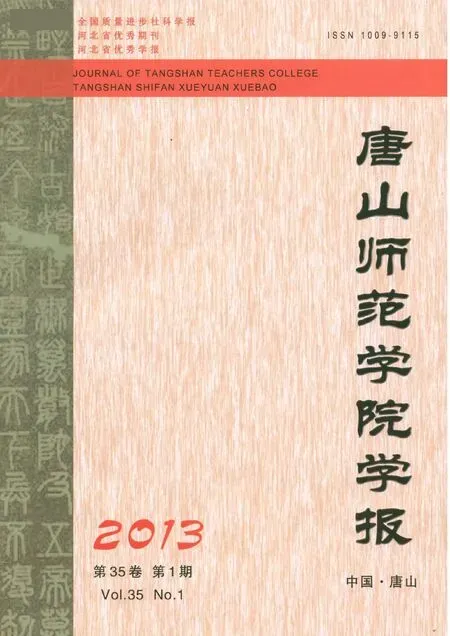基于城市融入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的思考
謝章明,解登峰
(皖西學院 思政教學部,安徽 六安 237012)
一、問題提出
在當前社會轉型、發展轉軌的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作為社會特殊群體,目前已超過1個億,其社會權益的保障、身心健康的維護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豐富是民生工程中的重點工程。在身心健康方面,新生代農民工時常面臨城市和農村雙重邊緣化的境地,社會認同極易發生偏差,常對社會普遍懷有一種疏離感和責任匱乏心態,如果處理不當,會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促進人的心理和諧,加強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1]已成為黨和政府的重要政策方針。心理和諧是個體心理健康的重要標志,而且個體的心理和諧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必要基礎。“和諧社會”的典型特征就是,構成社會的各個團體及個人,他們之間存在一定的差別(可以表現為社會地位、經濟收入的水平、個人行為方式以及個性特點等方面),但彼此之間又能夠和諧相處[2]。
隨著我國衛生保健工作的發展,其工作內容從單純的身體疾病的防護拓展到綜合的身心健康預防和保護體系,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維護成為今后我國農村衛生保健工作的新方向。2001年1月26日北京回龍觀醫院開辦了全國第一所農民工心理健康學校,有效開展了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工作。為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更具有針對性、實效性,心理健康服務工作應由專業機構和人員遵循心理健康規律向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心理促進工作[3]。
二、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會認同感,提升融入度
一方面,城市經濟繁榮與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發展呈現弱相關現狀,另一方面,由于與鄉土生活的長期割裂,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是城市人與鄉村人的身份歸屬產生了困境和偏差。社會身份認同,指一個社會成員意識到自己是某一個社會群體或社會類屬中的一員。個體通過對特定群體的價值感和情感的認識,會形成“群體我”和“群體自尊”,能夠促進個體生活的奮斗目標。可見,如何化解新生代農民工這種“扎根”與“歸根”的搖擺心理,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在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城市社會認同感,是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的核心內容。
1. 破除二元身份分類法,確定合理的身份認同感
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過程中,新生代農民工與占有優勢社會公共資源的城市青年相對比,極易產生自卑心理,害怕被定義為“鄉下人”;然而,在回鄉生活時,又會對社會公共資源相對缺乏的農村產生不適應。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感的困惑源自于社會類化過程中的二元化心理機制,即要么“是”,要么“不是”。長期的城鄉發展不均衡化,經濟差距增大帶動文化心理差距的增大,經濟的落后就預示著文化的落后,自然而然地,人們就形成了“鄉下人”和“城里人”的刻板印象。“鄉下人”是落后的標志,甚至是“臟亂差”的代名詞;“城里人”是文明發達的標志,是工作愉快、生活幸福和待遇優厚的群體。實際上,隨著我國經濟實體的多樣化,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分化出來,這種刻板的二元化分類已經不適應群體的類別化。
新生代農民工屬于我國現有經濟體制的產物,既不同于城市工人也有別于舊時的農民。在地域上,他們是我國城市生活群體的重要部分;在社會保障上,他們還是農村農民的身份;在時間歸屬上,他們會結束城市漂泊的日子,返鄉生活。這種境遇會造成個體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不連續感,從而不斷地適應新的社會環境,造成身份認同的困境。采用多元化的群體類別化分類是擺脫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困惑的關鍵要素。多元化群體類別化是結合具體情境,運用多樣化參照標準進行同質性分類。新生代農民工具有一定的文化教育水平,具有在城市工作的實踐經驗,在認知能力上與城市青年相似;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有土地情結,農村土地是他們固有的物質財富,因而在情感上與農村農民具有一致和相同之處。另者,新生代農民工和城市市民都有維護城市和諧發展的社會責任,是城市生活中不可忽視的群體。如果采用差異性比較,新生代農民工會出現群體歸屬的矛盾感和邊緣感,而在多元化群體類別化視角下,采用同質性比較就容易產生群體的科學定位。
2. 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心理融入度,以促進城市生活和諧感
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進城農民工在身份地位、社會權利、價值觀念等方面向市民轉化,實現城市文明的再社會化[4]。新生代農民工有別于父輩時代的農民工,不僅繼承了父輩們的努力工作的勤勞本質,而且在工作條件和報酬上有了自己新的需求,具有較強的城市化傾向,在價值觀念、消費形式和社會認同方面趨于市民化,尤其在自己子女教育上,希望子女能享受城市的優良教育資源,這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有融入當前城市生活的心理需求。增進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生活的適應力,除了在體制上給予一定的保障以外,應從心理層面上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城市一員”的角色融入度。許傳新、許若蘭從社會距離的視角研究新生代農民工心理融入度,發現性別、是否獨生子女、城市生活體驗、社區參與程度、相對剝奪感對其與城市居民的社會距離感有顯著性影響[5]。
大多數流入城市的農民就業渠道主要是靠親緣、地緣為主的社會關系,通過非正式途徑就業,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邊緣人”的身份認同危機[6]。增進城市社區與新生代農民工之間的交流和共事,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內封閉性成為必要。Mussweiler的選擇性通達模型認為,在目標和標準同樣的社會實踐中,不同群體間會產生同化效應,即當個體面對社會比較信息時,其自我評價朝向比較目標的現象[7]。依據此模型,當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公民在廣泛范圍內接觸和共同完成某項任務時,其價值觀和意義感與城市居民相似。因而,在生活教育等基礎領域,擴展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市民的互相參與的平臺,有利于促進農民工對城市規則以及文化系統的進一步了解,增強城市生活的和諧感。
三、靈活多樣開展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工作
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工作旨在應用心理學的原理、方法和程序預防或消除癥狀或適應不良的行為,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質量。國外的心理服務固然有許多引人矚目的成功理論、方法與體系,但只有當它們與本國文化和國情相融合之后才能顯現其適宜性[8]。首先,要結合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開展心理健康服務工作。其次,要因地制宜開展心理健康服務工作,因為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工作性質不同,聚集地相對比較分散,較為集中于建筑工地等勞動力密集和服務性行業集中的地方。再者,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的社會效益應給予科學評估,合理配置人員和設置機構,科學測量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
1. 以多元文化視閾指導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
新生代農民心理健康問題的出現究其原因是文化的變遷產生的心理沖突。城鄉文化的沖突是客觀存在的,折射到新生代農民工身上是心理沖突和社會認同的困惑。新生代農民工心理結構的變遷處于“從家延伸”和“返回家”的雙重拉力過程,從而產生揚棄傳統的農村文化還是全面吸收現有的城市文化的心理沖突。每座城市的文化特征比較一致,都秉承開拓進取的現代精神,追求公平民主、注重效率、提倡競爭、注重合理消費和生活品質的提升等。城市文化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但傳統文化是深入人的許多隱性心理的,也無時不影響著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和行為。因此,運用多元文化視閾,強調實際的文化語境,深入了解當地農村社會文化和現有的城市文化之間的差異,實現文化意義的調和,是促進個體或群體的心理和諧的首要條件。
新生代農民工原有的農村文化由于地域的不同,呈現多樣化和區域化特征,在面對心理健康問題時都有自己的調控方式。景懷斌從“信仰——養性”思路出發,發現中國文化背景下的群體具有以儒家、道家和佛家為中心的心理健康問題的調適方式。在民間方面有“緣”的觀念和“報應”思想,并且有算命和巫術等形式的心理調適方式[9]。在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時,合理運用西方心理健康服務的身心調適理念和技能的同時更需要注重新生代農民工固有的文化情境,處理好城市文化的理性和農村文化的感性之間的差異性,協調之間的沖突。
2. 因地制宜開展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
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工作的構建是一項系統的工程。我國心理健康服務工作起步相對比較晚,面臨著專業人員缺乏、規模運行機制不健全等不足,如果要建立新生代農民的社會支持和心理援助系統,需要多方面協作、整合社會各方面資源,政府、非政府民間組織、企業雇主以及各種社會主流媒體應多方位開展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服務范圍不僅注重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問題,而且要關注他們的發展問題。
在暢通和完善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的預警機制、危機干預機制、信息溝通機制和資源整合機制的同時,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環境的分布,積極開展“社區心理健康服務”“企業心理健康服務”和“新生代農民工心理自助活動”。社區心理健康教育是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新生代農民工的聚集地之間進行多樣體育活動、文化活動和心理健康知識普及活動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活動需求,提高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素養和職業技能水平,提升自我心理調適能力,如開展集體體育活動,建設社區圖書館和電影院,建立心理健康宣傳欄等。另者,進行企業心理健康服務工作,企業文化的建設為新生代農民工創設良好的人文環境,既注重競爭和效率,也注重合作和和睦,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價值感和自我效能感。自助團體也是一種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的很好途徑。從多元文化的視閾,新生代農民工是最了解自己的群體,能夠運用同一文化意義的心理健康問題的調適手段,容易產生心理上通情。因而,發展、監督這些自助團體將有助于深化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工作。
3. 科學評估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的社會效益
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是我國心理健康服務組織體系的重要組成,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部分。心理健康服務組織體系建設,要貫徹精神衛生工作中“預防為主、防治結合、重點干預、廣泛覆蓋、依法管理”的原則,建立“政府領導、部門合作、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保證心理健康服務工作重點逐步轉向社區和基層[10]。
在我國社區和基層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國家應組織或委托心理健康教育專家和心理健康教育實際工作者共同研究制定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工作的評價與督導指標體系,對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服務工作進行社會效益方面的科學評估。關注心理健康服務的學者應注重考察心理健康服務的開展程度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生活滿意度的聯系,注重考慮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與心理健康服務人員數量之間的合理配備,注重總結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問題的類型以及心理健康需求范圍,注重考慮政府、社區、企業和社會各方力量的心理健康服務資源整合程度和有效性,科學驗證社會公共資源投入、心理健康問題所造成損失和心理健康服務受益之間的關系。
[1]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51.
[2]王登峰,黃希庭.自我和諧與社會和諧[J].西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1):1-7.
[3]黃希庭,鄭涌,畢重增,陳幼貞.關于中國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建設的若干問題[J].心理科學,2007(1):2-5.
[4]何曉紅.論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礙[J].前沿,2005(10):228-231.
[5]許傳新,許若蘭.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社會距離實證研究[J].人口與經濟,2007(5):39-44.
[6]李良進,風笑天.試論城市農民工的社會支持系統[J].內蒙古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3):12-16.
[7]Mussweiler T. Comparison processes in social judgment:mechanism and consequences[J]. Psychological Review,2003(3): 472-489.
[8]徐華春,黃希庭.國外心理健康服務及其啟示[J].心理科學,2007(30):1006-1009.
[9]景懷斌.傳統中國文化處理心理健康問題的三種思路[J].心理學報,2002(3):327-332.
[10]徐大真,徐光興.我國心理健康服務體系模式建構[J].中國教育學刊,2007(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