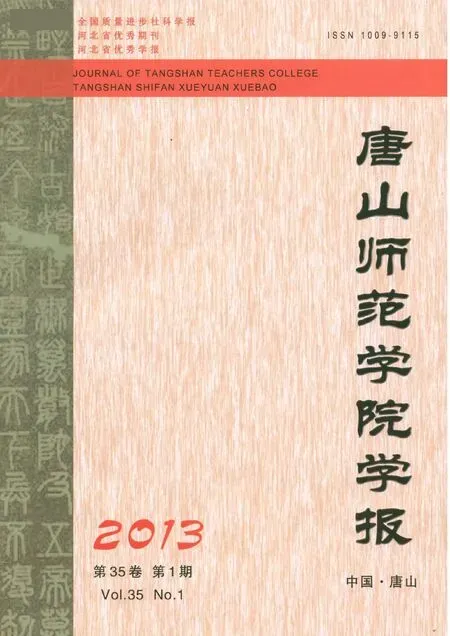“文明對話”解決“文明沖突”的可行性
—— 基于伽達默爾語言觀的視角
瞿 磊,李 璐
(揚州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0)
“文明對話”解決“文明沖突”的可行性
—— 基于伽達默爾語言觀的視角
瞿 磊,李 璐
(揚州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0)
語言問題是伽達默爾解釋學中一個重要內容,從伽達默爾的語言觀正確看待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的觀點,贊同用“文明對話”來解決文明間的沖突。基于伽達默爾語言觀的視角來分析“文明對話”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伽達默爾;語言;文明對話;文明沖突
一、語言的興起和嬗變
早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就提出了關于人的本性的經典定義,他認為人是具有理性(logos)的動物,即人是具有邏各斯的動物。邏各斯在其原初意義上并非理性、思想,而是語言、言談,這是一種活生生的、主——客體沒有分離的語言[1,p147-148]。
在《克拉底洛篇》中,柏拉圖討論了以下兩種與語言有關的理論。柏拉圖認為,一旦我們擁有客體,我們一方面就可以說,語詞是被賦予客體的;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語詞是為客體而發明的。照第一種看法,客體是被賦予的一個名稱。照第二種看法,語詞并不是被構成而且被賦予給客體的,而是為客體發明的。這就是柏拉圖約定俗成的語言理論,這表明了語詞是為客體而發明的,并且語詞也是可以隨意改變的。他討論以上兩種理論的目的在于強調知識對語言的在先性,因為他的重點放在理念這種非語言的知識上。
威廉·馮·洪堡乃是被伽達默爾稱為“現代語言哲學的奠基人”。洪堡認為,語言在本質上是人的語言,人在本質上是一個語言的存在物,語言的力量包含在使得“有限的手段無限使用”[1,p151]之中,必須將語言看作是脫離任何特殊內容的形式。對他來說,每一種語言都表達了一個世界,正如每個語詞都表達了一個內容。
洪堡以后的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對以后的語言科學,尤其是對語言哲學影響更大。自《普通語言學教程》問世以后,語言學界普遍接受了他的關于“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這一看法。他的語言符號系統的工具主義語言觀在現在的語言哲學和語言科學中居于統治地位。
正是基于上述情況,伽達默爾才著手對語言哲學中形形色色的現代語言觀進行了批判,如結構主義、分析哲學等流派,從而揭示了語言的非工具特性,形成和創立了自己的語言觀。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作為現代解釋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哲學解釋學為中心探究人類的理解問題,而語言問題則是伽達默爾所建立的哲學詮釋學的中心問題。伽達默爾詮釋學的語言不是語言學意義上的工具、手段,語言在此具有本體論的意義。人生活在語言中,且只有通過語言才能真正認識自己、理解自己、建構自己。他從語言這一中心出發強調“對話”的意義及其在語言中所反映的關系和真理的顯現,試圖以此恢復單純的以現代科學方法論為指導的精神科學自身探索真理的領域。
二、伽達默爾的語言觀
伽達默爾把語言作為核心問題進行探究,實際上是在探究“理解怎樣得以可能”的問題。他認為,理解是在語言中的理解,理解的基礎并不在于使某個理解者置身于他人的思想或直接參與到他人的內心活動中。他說:“所謂理解就是在語言上取得相互一致,而不是說使自己置身于他人的思想之中并設身處地地領會他人的經驗。”[2,p48]人與人之間的經驗差異所導致的彼此思想之間的距離,使得人們不能“設身處地”,或者說根源于不同生活過程所導致的語言之間的意義上的差異。然而,這種差異可以在語言這一共同的事件中得到溝通和理解。語言正是談話雙方進行相互了解,并取得一致意見的核心,整個理解過程乃是一種語言過程[2,p490]。在海德格爾的影響下,伽達默爾對理解的語言性質給予了特別的強調,認為“我們的整個世界經驗以及特別是詮釋學經驗都是從語言這個中心出發展開的”。在他看來,語言包容了人類世界的一切經驗。一方面,人只有通過語言才能理解存在并獲得世界;另一方面,世界只有進入語言才能成為人們的世界。在此意義上,人們認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
1. 不同語言之間的理解——翻譯
兩個不同語言的人之間只有通過翻譯和轉換才能進行談話,否則雙方間的了解便變得很難。翻譯需要通過語言把其中的意思表達出來,語言作為相互了解的媒介,在翻譯中必然存在著翻譯者對原先文本的解釋,這是翻譯者對原先文本所包含的文化視域與自己文化視域的銜接,翻譯者必須考慮二者之間的距離。伽達默爾認為“這種距離是永遠不可能完全克服掉的”[2,p490]。所以,翻譯過程就是理解和解釋的過程,就是在語言中達到某種妥協,或者說使一種視域融合過程。但是,翻譯者不可能完全把作者的意思表達出來,必然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只能說是再創造。換句話來說,翻譯所涉及的是解釋,而不是重現[2,p492]。翻譯者也很痛苦地意識到自己所解釋出來的意思與原作者所想表達出來的文本意義之間的差距,翻譯者會在反復斟酌和磋商中去尋找最佳的解決辦法。通過翻譯使理解成為可能,翻譯總是解釋,或者說是對文本的創造而不是重現。正如伽達默爾所說,“一切理解都是解釋,而一切解釋都是通過語言的媒介進行的,這種語言媒介既要把對象表達出來,同時又是解釋者自己的語言”[2,p496]。
2. 相同語言之間的理解——對歷史流傳物的理解和談話
流傳物有文字流傳物和一般流傳物之分,伽達默爾重點論述對文字流傳物的理解。他認為,流傳物的本質通過語言性而作為標志,并且“以文字形式所流傳下來的一切東西對于一切時代都是同時代的”[2,p498]。因為這種同時代性,在直接面對文本的理解中就相應地擴展了自己的視域,并且這種視域擴展是兩方面的——本文通過理解者的理解實現的當前意義與理解者視域向本文的擴展。本文所講述的內容在理解者面前展開一個豐富的世界關系,理解者通過對本文的理解實際上是對本文所作的傳達的參與。伽達默爾認為,本文總是能使總體得到表達,并且本文整體意義的表達與解釋者是分不開的。另外,對文字流傳物的理解,實際上表現解釋者所具有的普遍世界關系之間的雙重放大和交往,并且解釋者在解釋過程中的視域擴展顯現原有的世界關系的當前意義并不是任意的,他的解釋必然受到本文視域的限制。另一方面,解釋的創造性還應表現解釋者對當前世界意義的強調,從而突出文字流傳物的某一方面。這種突出應具有某種程度上的遮蔽性,即突出本文某一方面的意義而舍棄另一些意義,從而又使解釋過程變為文字流傳物在當下意義的拓展具有一定的方向性。
伽達默爾認為:“談話是相互了解并取得一致意見的過程。”[2,p491]語言是談話者進行相互了解并對某事物取得一致意見的核心。這種一致意見的取得是談話者分別把對方的意見置于自己的意見和猜測之中的過程,并且通過這一互動過程雙方不斷進行理解并發生視域融合。那么,在一定意義上說,這是雙方在尋找著一種共同語言,表達了對存在物的真理性認識。他認為:“對事物統一的意見的講說”,作為“事物的真理存在于話語之中”[2,p525]。這就是說,談話不僅使理解得以實現,并且在語言中達到事物的完全意義的涌現和認識真理的實現。
3. 語言理解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傾聽
伽達默爾說,關于傾聽這個主題,他“提出被人們稱為生活世界的思維者的理解”,亦即傾聽,具有對生活世界的普遍意義。他認為,在傾聽中存在著人的真正自由,因為傾聽者必然是“清醒與喚醒的”,否則,便不是傾聽。傾聽總是和理解相伴著,沒有傾聽的理解與沒有理解的傾聽都是不存在的,因為傾聽者總是在內心里根據自己的視域進行重新理解,所以當一種語言說出來后,這種言說就不屬于他自己了,而屬于對他的一種傾聽。伽達默爾認為,傾聽的本質是“將言談的所有段落在一種新的統一方式中來理解”[3,p19]。正是在傾聽中存在著一種無聲的回答式的對話性理解,閱讀文本也一樣,閱讀者發生著與作為傾聽者一樣的事情,閱讀實際上也是種傾聽,傾聽具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所以,伽達默爾說:“我們必須學習傾聽:相互傾聽,這也同樣適用于單個的人以及他與他人的共同生活,適用于各族人民。”[3,p23]歸根到底,一切傾聽都是通過語言的對話與理解。
三、從伽達默爾語言觀看現代的文明沖突與對話
伽達默爾特別強調對話在相互理解過程中的意義,對話包含著“言說”與“傾聽”這兩個對立面及其相互轉化。把握理解的語言性的關鍵在對話的結構中。在此,在解釋學視角下分析“文明對話”代替“文明沖突”的可行性。
亨廷頓認為,冷戰后的世界由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所構成。他指出:文明是人類的終極部落,文明的沖突就是全球規模的部落沖突,21世紀將是世界各文明激烈沖突的時期[4,p334]。他還強調自己所屬的西方文明要受到其他文明的挑戰,特別擔心儒教文明(實際上是指中國)與伊斯蘭文明(主要是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可能聯合起來對西方文明構成最嚴重的挑戰。
杜維明則有不同的見解,認為21世紀將是文明對話的時代,用“文明對話”代替“文明沖突”,并認為儒家傳統將在這種文明對話中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他還認為文明與文明之間,首先需要承認、尊重彼此文明的存在,這才能互相包容,互相參照。文明對話的目的不是說服對方,更不是把自己的思想強加于別人,而是更好地傾聽,這其中也是儒家恕道的體現,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這種恕道思想又與基督文明恰恰相反,基督文明認為“己所欲施于人”,那么這兩種文明思想之間就存在著碰撞,需要進行理解與對話,以消除隔閡,更好地去理解彼此的所屬文明,豐富自己的文化資源。
雖然各種文明不盡相同,但可以進行對話,基督教和佛教、回教進行對話,在對話的過程中,儒家文明可以起到一個中介作用,有儒家式的基督徒,儒家式的佛教徒。儒家式就是說要關心政治,參與社會,注重文化[5,p19]。這并不是說由儒家的思想來統合,它是起一個中介、溝通的作用。可以把儒家思想,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思想,通過“文明對話”的方式嵌入到其他文明中去,讓其他文明慢慢了解到異文明的思想與主張,從而讓雙方能達到相互一致,消除“文明沖突”。費孝通也十分贊成用對話的方式來解決文明的沖突,加深文明與文明之間的了解與溝通。他認為,文明對話的最高境界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意思是說每個文明對自己文明內部的價值,特別是其核心價值,是持認同的態度,對于異文明彼此要互相學習、互相包容,那么這就可以呈現出一個多元文化融合的世界,“天下大同”便成為邁向和平文化的靈感。
伽達默爾認為,在對話中對話雙方不是試圖進入到另一個人的心境,而是各自通過對話表明自己,依靠參與討論的主題達到一種相互交流和理解。在理解的過程中,對話的言語交流使對話者雙方都得到了改變,各自的視域都會得到調整或修正。就像文明與文明一樣,通過“文明對話”可以相互了解到各自文化,這樣在自己的文明中就會融合其他文明的思想,更加理解這個文明的思想,減少文明的沖突,迎來的是世界的和平。他也認為從對話的終結處走出來的“自我”已不再是原來的“舊我”,而是一個“新我”,一個比原來擴大了的自我。同時,這個過程又是可以無限延展的,對話,融合,再對話,再融合,循環往復,以至無窮。只要人們付出努力,“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荀子·正名),文明間的對話就會成為可能,文明間的沖突就會減少。
伽達默爾曾引用過柏拉圖的一句話:“只有與自己的友愛,才能使與他人的友愛成為可能。”傾聽他人是仁愛的提升,與他人的友誼、團結就是真正的善與幸福。孔子說:“仁者,人也”(論語·中庸),“仁者,愛人”。伽達默爾的偉大不僅僅在于他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更為重要的是他為走向文明深處的人類開啟了一個永恒的卻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海德格爾晚年在編輯自己的著作全集時留下這樣一句話:“他的著作是‘道路’,而不是‘著作’。”人們同樣會看到伽達默爾及其思想將永遠行走在語言的路途中。
[1] 嚴平.走向解釋學的真理——伽達默爾哲學述評[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2]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3] 成中英.本體詮釋學[M].北京:北大出版社,2002.
[4]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5] 朱漢民.杜維明:文明的沖突與對話[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
(責任編輯、校對:孫尚斌)
The Feasibility to Solv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y Using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Based on Gadamer’s View of Language
QU Lei, LI Lu
(School of Marxis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0, China)
The problem of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adamer’s hermeneutics theory. Samuel Huntington’s concept of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rom Gadamer’s view of language is a right way to solve the clashes. The importance and feasibility of civilized dialogues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damer’s language theory.
Gadamer; language;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089.2
A
1009-9115(2013)01-0113-03
10.3969/j.issn.1009-9115.2013.01.031
2012-08-23
瞿磊(1988-),女,安徽天長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