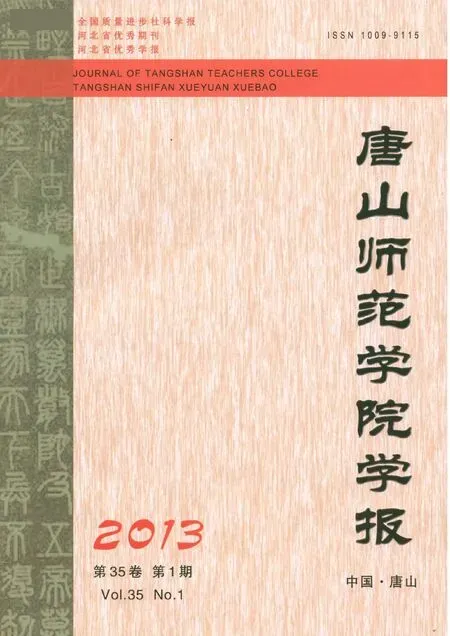非理性決策中的情緒加工及其影響因素
—— 以最后通牒任務為例
張 振,劉 凱,楊邵峰
(天津師范大學 心理與行為研究院,天津 300074)
非理性決策中的情緒加工及其影響因素
—— 以最后通牒任務為例
張 振,劉 凱,楊邵峰
(天津師范大學 心理與行為研究院,天津 300074)
傳統經濟學當中的“理性人”假設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挑戰,研究者提出了不平等厭惡理論、互惠性理論和雙系統加工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非理性決策及其特性進行了闡述。目前關于非理性決策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從實驗前誘導的情緒狀態、情緒調控策略等與情緒加工相關的視角進行;今后關于非理性決策的研究應致力于突破以往模型研究的局限,對非理性決策的神經機制進行探討,并向實際應用發現發展。
非理性決策;負性情緒;最后通牒任務
在日常生活中,決策貫穿了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人們所有的行為都是決策的結果。傳統經濟學理論的“理性人”假設認為經濟決策的主體都是充滿理性的,既不會感情用事,也不會盲從,而是精于判斷和計算,其行為是理性的[1]。在經濟活動當中,主體所追求的唯一目標就是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但“理性人”假設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與挑戰,因為它并不能完全預測人們在現實生活當中的決策和行為。也就是說,人們的決策和行為并不是完全按照得失收益權衡來進行的。國內外學者對非理性決策進行了數十年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并提出了一些解釋非理性決策的理論。對已有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和梳理,不僅可以肯定先前研究的成績,而且能夠從中發現目前研究的不足和缺陷,這將有助于推進新的、更深入的研究。
一、非理性決策及其研究范式
理性決策是依據傳統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提出的,而非理性決策則是相對于“理性人”假設提出的,因此所有違背“理性人”假設的決策模式都可以稱之為非理性決策。非理性決策的研究范式包括框架效應、偏好反轉、獨裁者任務和最后通牒任務等等。本文主要討論通過最后通牒任務度量非理性決策的實驗研究。
最后通牒任務源于博弈理論。標準的最后通牒任務需要兩名玩家參與,其中一名玩家(提議者)提議如何分配給定數目的金錢(如10元),另一名玩家(反應者)決定是否接受分配提議。如果反應者接受分配提議,那么兩個人將獲得相應的金錢;反之,如果反應者拒絕分配提議,那么兩個人什么也得不到[2]。被試通常充當反應者的角色。依據“理性人假設”,參與最后通牒任務的個體應該接受任何一種非零的分錢提議,這樣才能使被試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但是大量研究結果表明,被試通常會拒絕那些低于總額20~30%的提議,即使拒絕分配提議意味著被試什么也得不到[3][4]。因此,最后通牒任務中拒絕行為就違背了傳統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被研究者稱為非理性決策。
二、非理性決策的理論
最后通牒任務當中的非理性決策與傳統“理性人”假設不符,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興趣。一些研究者通過大量實驗研究得出豐富的結果,并有學者提出一些解釋非理性決策模型。
1. 不平等厭惡理論
不平等厭惡理論假定人不喜歡并試圖回避不平等性,代表理論包括Bolton和Ockenfels、Fehr和Schmidt的理論。Fehr等在1999年提出了一種依據不平等厭惡解釋非理性決策的理論。Fehr認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至少有一部分人是關注結果公平性的[5]。Fehr將公平性模擬為一種服務于自我的不平等厭惡,假如某個人不喜歡那些不公平的結果,那么這個人就是厭惡不平等性的。不公平厭惡驅使人們為了獲得更公平的結果而拒絕那些不平等的結果,即使這樣做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厭惡不平等性理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如何測量或判斷結果的公平性性。Fehr認為,公平性判斷依賴于一個基線,而這個基線是建立在社會比較之上的。不平等厭惡模型就是建立在社會比較和損失厭惡的心理學證據之上的。不平等厭惡模型的主要假設有兩點:第一,生活中除了完全自私的個體之外,還存在一些厭惡不公平結果的個體。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時,當這些人的收益低于他人收益時,他們會感到不公平;而當其收益高于他人時,這些人也會感到不公平。第二,一般而言,自己收益低于他人收益時所體驗到的不平等體驗更為強烈。
2. 互惠性理論
互惠性是指人們會獎賞友善的行為,并懲罰不友善的行為。社會學家Gouldner指出互惠原則在文化當中的普遍存在性和重要性不低于亂倫禁忌。互惠性理論包括Rabin在1993年和Falk與Fischbacher在2006年提出的理論。其中Falk和Fischbacher的理論認為互惠性包括正性互惠(獎賞友善行為)和負性互惠(懲罰不友善行為)[6]。互惠性理論認為,互惠行為可以理解為個體對友善/敵對行為的反應,個體體驗到的友善/敵對程度越大,其獎賞或懲罰這種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大。判斷行為的友善性主要依據行為所導致的結果及實施行為的動機或意圖。互惠性理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評價行為的友善性。在評價行為友善性時,互惠性理論不僅考慮行為所導致的結果,而且將行為意圖也納入其中。也就是說,行為的友善與否并不僅僅由其結果來決定,相反人們主要依據他人的行為動機來決定對待他人的方式。以犯罪行為為例,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的懲罰并不相同。
3. 認知——情緒雙系統模型
近年來,很多研究者都相繼提出了雙系統加工理論:基于直覺的啟發式系統(heurist system)和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統(analytic system)[7-10]。認知——情緒雙系統模型認為人的決策行為受認知和情緒兩個系統的支配,其中情緒系統是直覺的、自發的、快速的;而認知系統是慎思的、控制的、緩慢的。情緒系統通過自發的情緒反應(如憤怒、厭惡、高興等)影響人們的決策行為。而且,認知系統和情緒系統同時對決策或推理過程起作用,當兩個系統的作用方向一致時,決策或推理的結果既符合理性又遵從直覺;而當兩個系統的作用方向不一致時,兩個系統存在相互競爭的關系,占優勢的系統則控制行為結果。Sloman認為,當兩個系統作用方向一致時,行為結果并不會體現出兩個系統的存在;只有兩者作用方向相反時,才可能出現決策過程中的非理性行為。Kahneman則認為,在雙方的競爭中,情緒系統往往會獲勝,而這正是很多非理性決策的根源[11]。最后通牒任務中的拒絕行為正是由于情緒系統在決策過程中占主導地位,進而驅使個體拒絕接受分配提議這種理性化的抉擇。
三、非理性決策的情緒加工及其影響因素
1. 非理性決策中的情緒加工
很多研究者都認為,最后通牒任務中的拒絕行為是由個體體驗到的負性情緒(憤怒、厭惡等)引起的,而且這種假設也得到了大量研究證據的支持。例如,Sanfey等在2003年進行了第一個最后通牒任務的fMRI研究,其中被試需要充當反應者完成多次最后通牒任務。研究目的就是為了探討非理性決策中的情緒加工過程,研究結果表明不公平分配提議會導致前腦島的激活,而前腦島常常涉及到厭惡等負性情緒的加工;而這些腦區的激活程度與分配建議的公平性、被試施加非理性決策的可能性之間存在顯著相關[12]。隨后,Van’t Wout等進行了一項皮膚電研究,試圖進一步探討決策過程中的情緒加工。研究發現:不公平分配提議能夠引起更大的皮膚電活動,而且皮膚電活動強度能夠預測被試拒絕不公平分配提議的可能性[13]。他們的研究結果擴展了Sanfey研究所得到的“前腦島激活與拒絕不公平提議之間存在相關”的結論,為情緒在非理性決策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Boksem和Cremer采用腦電技術探討了非理性決策相關的ERP成分,研究結果表明,不公平提議會引起更大的MFN成分,而且那些具有更高公平關注偏好的被試會表現出更明顯的效應[14]。Hewig等的研究也表明,不公平提議能夠引起更大的ERP成分,而且MFN的波幅能夠預測不公平提議的拒絕[15]。情緒動機理論認為MFN可能反映了個體對負性反饋引起的情緒動機意義的評價,因此研究者認為MFN波幅反映了被試所體驗到的負性情緒,MFN波幅越大,被試體驗到的負性情緒也就越大,他們就越可能拒絕不公平提議。
2. 誘導情緒對非理性決策的影響
很多研究結果都表明被試面對不公平提議時會體驗到強烈的負性情緒,而實驗前誘導的負性情緒必然會對被試本身體驗到的負性情緒產生影響。一些研究者認為,誘導的負性情緒與被試體驗到的情緒效價一致,能夠增強被試所體驗到的負性情緒的影響,因而會導致非理性決策的增加。例如Harle等采用情緒圖片誘導被試的悲傷、愉悅和中性情緒,要求被試完成最后通牒任務,研究結果表明悲傷情緒要比中性情緒或積極情緒更能顯著增加非理性決策的比例[16]。Andrade等采用電影片段使被試體驗到憤怒情緒和高興情緒,然后檢驗了誘導情緒對非理性決策的影響。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憤怒情緒能夠顯著增加不公平提議的拒絕比例,即非理性決策的頻率。這些研究都證明了負性情緒在非理性決策當中的主要作用[17]。隨后,Moretti等采用情緒圖片分別誘導了厭惡情緒、悲傷情緒和中性情緒,試圖考察不同負性情緒對非理性決策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研究發現,實驗前誘導的厭惡情緒要比悲傷或中性情緒更能促進非理性決策的發生[18]。因此,即使同為負性情緒,厭惡和悲傷對非理性決策的影響也是存在差異的。
另外一些研究者則認為,實驗前誘導的負性情緒會干擾或打折被試面對不公平提議時的情緒體驗,進而使得被試做出較少的非理性決策。Bonini等最新的行為研究支持這種觀點。實驗要求被試在兩種房間內完成最后通牒任務,其中一間房間內充斥著厭惡性氣味(厭惡性條件),另一間房間則沒有厭惡性氣味(控制條件)。實驗結果表明厭惡性條件當中的被試更少地選擇非理性決策[19]。Bonini提出了一種無意識的折扣觀點來解釋實驗結果,即厭惡性條件當中的被試將不公平提議所引起的厭惡體驗錯誤地歸因于房間內的氣味上,進而削弱了本身厭惡體驗對非理性決策的影響。而Mancini等采用光刺激使被試產生痛苦體驗,結果發現這種痛苦體驗能夠使被試接受更多的不公平提議,而且痛苦強度能夠預測中等不公平提議的接受率。他們將此解釋為,個體的痛苦體驗可能會驅使個體做出更為自私的選擇,因此軀體狀態和體驗在高級人際互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20]。
3. 情緒調控策略對非理性決策的影響
既然情緒是導致非理性決策的關鍵因素,那么個體的情緒調控方式、策略必然會影響到非理性決策。人們在現實生活當中體驗到強烈負性情緒時,也會采用多種方式來宣泄、調節這些負性情緒對其決策、行為的影響。目前研究者主要關注書寫表達負性情緒的信息、分心策略、認知再評價策略和反芻策略對非理性決策的影響。例如,Xiao和Houser對標準最后通牒任務進行了變化,即被試在拒絕分配提議的同時,可以選擇向提議者反饋一些書面信息。研究結果發現,當被試能夠通過其他方式(如書寫表達負性情緒的信息)表達負性情緒時,非理性決策的頻率會顯著降低[21]。
情緒調控是人們日常生活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主要的情緒調控策略有分心策略、認知重評策略和沉思策略。研究發現,分心策略和認知重評策略能夠降低負性情緒的影響,進而使個體做出更多的理性決策;而沉思策略則會加劇負性情緒的影響,進而使得個體做出更多的非理性決策。恰當的時間延遲同樣是有效管理負性情緒的一種途徑。一般而言,當個體與誘發情緒體驗的客體相分離后,個體體驗到的負性情緒就會逐漸消失,因此“做出決策之前先停下來,冷靜一下”這種普遍的做法似乎非常有效。但是,Wang等人的研究結果表明,時間延遲對情緒調控的影響會受到延遲時間內被試認知方式的影響[22]。
通過對上述關于非理性決策概念、理論及影響因素研究的總結與梳理,我們發現目前研究存在以下幾點不足:第一,以往研究所采用的情緒誘導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別,包括情緒圖片、視頻剪輯、硫化物氣體等等。不同情緒誘導方式必然會影響到最后的實驗結果,因而使得很多研究結果出現分歧。第二,大多數研究都集中于探討負性情緒對非理性決策的影響,而忽視了親社會情緒(如同情、羞愧、憐憫等)對非理性決策的影響。今后的研究應更加關注親社會情緒對非理性決策的影響,這樣有利于親社會情緒和親社會行為的研究。第三,目前非理性決策方面的研究多只簡單考慮情緒因素,并沒有將社會情境等因素納入其中。由于非理性決策是社會互動過程中的行為,因此今后研究應考慮不同社會情境對非理性決策的影響,以及情緒狀態和社會情境之間的交互作用。
總之,今后的研究應從不同情緒狀態與社會情境等方面研究非理性決策的原因、發生機制等,進而解釋情緒、社會情境等影響非理性決策的內部機制。
[1] Von Neuman J., Morgenstern O.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Guth W., Schmittberger R., Schwarze B.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82, 3: 367-388.
[3] Camerer C. F. Behavioral Game Theor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M]. New York, 2003.
[4] Yamagishi T., Horita Y., Takagishi H., et al. The private rejection of unfair offers and emotional commitment[J]. Proc Nalt Acad Sci, 2009, 106: 11520-11523.
[5] Fehr E., Schmidt K. M.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3: 817-868.
[6] Falk A., Fischbacher U. A theory of reciprocity[J].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2006, 54: 293-315.
[7] Frank M. J., Cohen M. X., Sanfey A. G. Multiple systems in decision making: A neuro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18(2): 236-254.
[8] Sloman S. A. The empirical case for two systems of reason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6, 119: 3-22.
[9] Barrett L. F., Tugade M. M., Engle R. W.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eory capacity and dualprocess theories of the mind[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4, 130: 553-573.
[10] Paivio A. Mind and its evolution: a dual coding theoretical approach. Mahwah[M].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7.
[11] Kahneman D. A perspective on judgment and choic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3, 58: 697-720.
[12] Sanfey A. G., Rilling J. K., Aronson J. A., et al. The neural basi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J]. Science, 2003, 300: 1755-1758.
[13] Van’t Wout M., Kahn R. S., Sanfey A. G., et al. Affective state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J].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2006, 169: 564-568.
[14] Boksem M. A., De Cremer D. Fairness concerns predict 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 amplitude in ultimatum bargaining[J]. Social Neuroscience, 2010, 5: 118-128.
[15] Hewig J., Kretschmer N., Trippe R., et al. Why humans deviate from rational choice[J]. Psychophysi- ology, 2011, 48: 507-514.
[16] Harle, K. M., Sanfey, A. G. Incidental sadness biases social economic decisions in the Ultimatum Game[J]. Emotion, 2007, 7: 876-881.
[17] Andrade E. B., Ariely D. The enduring impact of transient emotions on decision making[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9, (109): 1-8.
[18] Moretti L., di Pellegrino G. Disgust selectively modulates reciprocal fairness in economic interactions [J]. Emotion, 2010, 10: 169-180.
[19] Bonini N., Hadjichristidis C. Mazzocco K., et al. The role of incidental disgust in the ultimatum game[J]. Emotion, 2011, 4: 965-969.
[20] Mancini A., Betti V., Panasiti M. S., et al. Suffering makes you egoist: Acute pain increases acceptance rates and reduces fairness during a bilateral ultimatum game[J]. Plos one, 2012, 6(10): e26008.
[21] Xiao E. Houser, D. Emotion expression in human punishment behavior[J]. Proc Nalt Acad Sci, 2005, 102(20): 7398-9401.
[22] Wang C. S., Sivanathan, N. Narayanan, J. et al. Retribution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The effects of time delay in angry economic interactions[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1, 116: 46-54.
(責任編輯、校對:劉玉娟)
The Emotion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Taking Ultimatum Game as an Example
ZHANG Zhen, LIU Kai, YANG Shao-feng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China)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y faces more and more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its Rational Man Hypothesis. Then,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Inequality Aversion Theory, Reciprocity Theory and Dual-process Theory which explain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its feature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cludes induced emotions,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so 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reak the limit of previous traditional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begin moving towards practical use.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negative emotion; ultimatum game
B849
A
1009-9115(2013)01-0155-04
10.3969/j.issn.1009-9115.2013.01.044
2012-05-10
張振(1989-),男,河南安陽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認知神經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