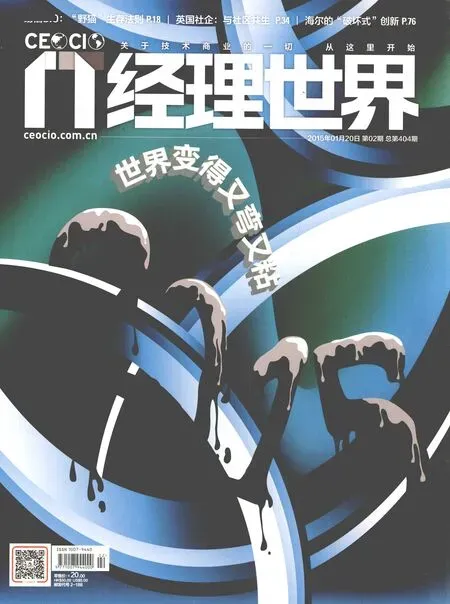微博覆蓋的核心要素
魏武揮
一條微博發出后,就等于是把一句話扔到了一個浩瀚無邊的數字世界,任何一條微博理論上都存在n層級轉發的可能乃至于可以覆蓋到上億微博用戶,但同時也存在這個可能,沒有任何人關心。影響一條微博被轉發的因素到底有哪些,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的研究員唐潤華先生在2011年10月的時候曾在他的微博上寫道:
影響一條微博轉發數的因子,按權重排序:1、博主本身的粉絲數、2、轉發者的粉絲數;3、話題的吸引力;4、微博的發布時間;5、微博的表現技巧。
在這五個因子里,前兩個屬于同一個性質:傳播節點的大小。有所不同的是,第一個屬于博主自身慢慢運作出來的,屬于主動性結果,而第二個則很難控制。在沒有有償發布的情況下,你不知道哪個轉發者會轉發你的微博。后三個又與第一個相同:博主主動性結果,無論是內容還是時間,都是可控的。
唐研究員很明顯認為第一點最重要,我基本認同。他認為第二個因子也很重要,我再次表示認同。但他的認同和我的認同都還不足以證明什么,我們需要一個好的例子來做比較分析。但一年多過去了,始終沒有發現好的案例,直到古城鐘樓這個微博號突然爆紅的那一天的到來。
古城鐘樓的微博是每兩個小時報一次時,報時用的語言符號是:鐺。這是一個看上去相當無聊的微博,它除了這個“鐺”以外不會發布任何微博,而且保證時間點的準確。1月7日上午,這個微博大概有2萬多粉絲,但一天不到的時間,就迅速攀升到10萬多,到我寫作此文的時間——1月9日——這個無聊的微博已經有40萬粉絲了。
不過這個無聊并非它首創,我在微博上又發現了一個名為“big_ben_clock”的微博(事實上,twitter上的大本鐘早就在那里報時了)——有網友告訴我,連這個bigbenclock都不是第一個無聊的。不過沒有關系,我們已經獲得了兩個無聊得幾乎類似的微博,換而言之,唐研究員所提到的五個因子里,后三個幾乎是一樣的。
這是一個近乎完美的比較案例,完美得就像實驗室里的東西,它天然就幫觀察者刨除了一些變量。我做了一個小小的信息收集,,“古城鐘樓”的第一聲鐺是2011年10月26日,而“big_ben_clock”第一聲BONG是2010年7月30日。后者顯然無聊得更早。到1月7日引爆點出現之前,兩個微博所擁有的粉絲其實都差不多:2萬多。
然后就有一個同樣有點無聊的用戶發了一條微博,他說:“發現一個史上最無聊又最有毅力的微博!@古城鐘樓”。這條微博當天獲得了13萬次的轉發。這位用戶并非大號,連v字都不是,怎么會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力呢?一個最關鍵的傳播節點是:蔡康永,這位老兄可是有2000萬粉絲的主。
蔡康永作為第一個引爆節點后,又吸引了眾多粉絲數可能沒那么多但已屬大v的微博進行轉發。在短短的一天時間里,古城鐘樓粉絲數暴漲,隨后新浪運營方介入,作為熱點話題后,再次推動古城鐘樓的粉絲數。在它一路上揚到40萬粉的同時,也帶動了big_ben_clock的粉絲數,后者目前保有7萬粉絲量。
這個案例能告訴我們的是:在同等內容的情況下,一條微博或者說一個微博賬號的受歡迎程度取決于是否有大號參與。大號參與與否的結果完全不同。但如果不是做有償發布的話,大號是否轉發,屬于一個非常隨機的事件,或者說,是博主本身無法控制的。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結論,在大多數微博營銷案例中,購買大號轉發,是一條常規之道。而靠內容創意取勝,屬于偶發事件——因為好的創意內容實在是太難得了。
除了商業上的一個結論外,我們或許還能推出一些和商業無關的社會意義上的結論:微博究竟是不是草根的狂歡場?至少這個案例不是。表面上一個無聊微博草根不能到再草根,但如果沒有本就擁有話語權的社會名人(蔡康永)的幫忙,它最多只能做到big_ben_clock的程度。在微博這個場域里,基本上不存在什么話語平權,名人照樣是名人,絲依然是絲。
在本專欄上一期文章《技術人格》中,我已經提到:“虛擬世界不再是‘像現實世界,而是現實世界本來就有很大的‘虛擬成分,所謂虛擬世界只不過還原了那種現實罷了。”現實社會中那種金字塔式的話語結構,在虛擬世界中不可能被顛覆。2010年7月,韓寒在微博上喂了一下,招來1萬多條評論和5千多條轉發,你喂一個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