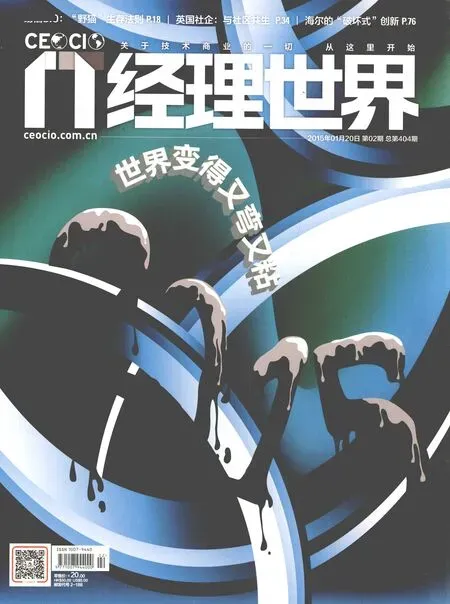泰勒制催生“惡之花”?
胡泳
富士康的系列自殺曾經震驚國人,有媒體稱富士康追求效率、漠視人性的管理為“泰勒主義的惡之花”。假如要清算富士康的“原罪”,等于變相否定泰勒的管理成就,從而也就等于在拷問管理的“原罪”。因為管理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其標志性事件,正是弗雷德里克·泰勒發起的“科學管理”運動。
泰勒是工廠工程師出身,他希望能知道一部機器或一個工人使用規定的材料和方法,在受控條件下完成某一生產過程、制造某一部件,需要和應該用多少時間。從1881年開始,他進行了歷時20多年的一系列試驗,制定了一套協調一致的工廠管理制度,又從這種管理制度出發,發展出最后以“科學管理”聞名于世的管理哲學。
泰勒一直是人本主義者憎恨的對象,他們指責泰勒的科學管理方法將工作“非人化”,并把管理變成了簡單的衡量。但這種認識可能過于簡單而膚淺。泰勒管理哲學的真正內涵比這些原則要深刻得多,他的主要觀點是,只有勞資雙方協作在所有的共同工作中應用科學方法,才能使整個社會得到最大的福利。1911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泰勒說:“從實質上說,科學管理是任何公司或產業中工人方面的一種切實的精神革命——是這些工人在對待工作職責、對待同事、對待雇主的一種徹底的革命。它同樣也是管理當局(工長、監工、企業主、董事會)的一種徹底的精神革命——是他們對待職責、對待同事、對待工人、對待所有的日常問題方面的一種徹底的精神革命。”
自從20世紀泰勒的思想在企業中扎根,人類對于高效率的胃口似乎就再難饜足。以泰勒為先導,管理由一種應急之策轉變為更全面、更長期的方式,這對人類的經濟福利產生了巨大影響。把人當作“機械人”來安排動作,說來有違人性,但對提高勞動生產率卻能奏效。
泰勒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符合那個時代要求的。20世紀早期的美國勞工絕大多數未受過教育,不善表達自己,也對工廠體系不習慣。對他們來說,嚴格規定的工作步驟是切實有用的。
科學管理是時代的產物,而時代總是在變化的。當勞動大軍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教育,工會開始在公司經營中擁有了發言權,泰勒的理論就開始顯得不合時宜了。人本管理初露端倪始于1965年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提出了“開明管理”的概念,并闡釋了商業“協同”的思想,他提倡管理者與其“團隊”分享權力并追求“持續改善”。
人本思想抓住了工作場所人性表現的核心所在:人生而具有生產力和主動性。哈佛商學院教授克里斯托弗·巴特利特和倫敦商學院教授薩曼特·高歇爾在人本管理理論的扛鼎之作《個性主義的公司》中指出,公司的力量不僅在于員工的能動性,而且在于“對個人價值的堅定信賴”。要將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挖掘到極致,而不是要求人像機器一樣。
泰勒的遠見以及后來者對他的思想的強烈反彈,反映了當代生活的一個巨大悖論:泰勒奉為神明的工作效率所帶來的物質利益,我們每天都在享受,然而我們始終痛恨、抵制、反抗效率崇拜給所有勞動者所系的心理鎖鏈。
然而,盡管我們為人本管理所吸引,這種管理方法在當今的企業實踐當中仍然是喧囂大于實質,形式大于內容。事實上,不論是股票市場,還是全球經濟,都在繼續獎勵能帶來效率提高的管理行為,而效率正是泰勒給我們留下的最大遺產。
在管理學家加里·哈默看來,“現代管理理論的發展無非就是對兩樣東西的追求:讓管理更加科學,讓管理更富人性色彩。認為對后者的追求比對前者更開明,這是一種完全錯誤的看法。”科學管理在提高現代人的生活水平上也許發揮了任一其他主張都難以企及的作用。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對此這樣評價:對過去100年生產力的迅速提高,技術專家把功勞歸于機器,而經濟學家卻把功勞歸于資本投資。只有極少數的人認識到,功勞應該歸于把知識應用于工作。發達經濟國家正是由此被創造出來的。
泰勒是把知識應用于工作的先驅。今天的生產和服務,仍然大部分按照泰勒的思想在運行。和亨利·福特一起,泰勒成為效率和工業實力的化身。但他的問題在于,整個“科學管理”的設計過于理性,沒有給作為人的工人留下任何位置。對他來說,工人和公司的關系是一種直截了當的經濟交易:我出錢,你出活。意義,認同,賦權,這些都與泰勒式的概念無關。在等級制管理日益坍塌的今天,這構成了他“惡名”的全部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