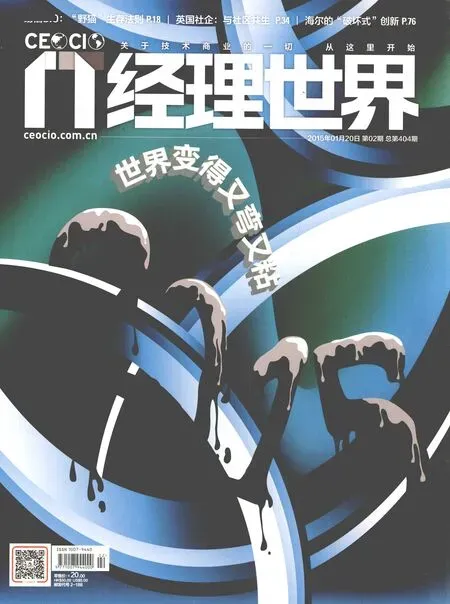華大基因:年輕配方
劉燕


早晨9點左右,站在華大基因位于深圳鹽田區北山道的白色大樓前,看著幾千名員工陸續走進辦公樓的情景,你很難再聯想起巨資拍攝的大片中,總是和基因工程相生相伴的科幻場景。要不是他們沒有著一身統一工裝,這里更像是深圳工業區隨處可見的代工廠門前。
這個隱匿在大大小小加工廠房中的科研機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基因組測序中心。但它還相當年輕——1999年楊煥明、汪建等幾位海歸科學家,為了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在北京創建了華大基因。僅僅14年時間,華大基因完成了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國部分的1%,水稻基因組計劃、家蠶基因組計劃、SARS研究、大熊貓等多項基因組科研項目,同時,建立了大規模測序、生物信息、克隆、健康、農業基因組等測序技術平臺。目前華大基因在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共有5000多名員工,還與15000個合作伙伴建立了業務關系。同時,華大基因有全世界最多的基因測序儀——140多臺分布全球。在世界頂級科學雜志發表高質量學術論文的數量,幾乎占到中國發表總數的30%左右,2012年已經發表38篇,相當于研究院每個月產出3篇科學研究報告。
根據公開資料,2007年~2009年,華大基因的收入分別是4000萬元、1.2億元和4億元。在2010年華大基因的收入突破10億元。2011年,華大基因主營業務收入更是高達20億元。旗下子公司——華大基因科技服務有限公司,經過兩輪融資后估值高達33億元。
華大基因螺旋式上升的發展軌跡中,始終伴隨著很多猜測和不解。而在汪建和他的管理團隊眼中,只有年輕人才能稱得上是最強大的秘密武器。
游擊戰斗的那幾年
3個科學家,華大基因的創立者楊煥明、汪建和于軍,滿懷理想,在中國把基因組學研究成果帶到了國際舞臺。在這一過程中,華大基因的身份一直在發生變化,曾受惠于國家基金,也一度進入國家體制,最終選擇回歸獨立之身,尋求內生式創新基因。
1999年9月1日,人類基因組計劃第五次會議召開,楊煥明在這次會議上舉手表意,代表中國承擔1%基因組計劃。在此之前,楊煥明、汪建、于軍等幾位中國科學家,在張家界開會擬定了中國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戰略構想。緊接著,他們開始尋求經費和政策支持,幾經周旋,政府創建了北京基因組中心,掛靠在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并以此中心名義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HGP)遞交加入申請。但在當時官方對真正開展這項計劃態度并不十分堅定的情況下,幾位科學家決心成立自己的研究中心,最終在順義區政府給予的50萬元啟動經費支持下,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正式注冊成立了。正是在華大基因第一個研究中心,北京空港工業區B區6號樓3層,楊煥明、汪建等人開啟了民間研究機構承擔基因組計劃的測序任務。
他們在舉手的瞬間,也許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個多么艱難的過程。當他們在2000年完成華大基因第一件大事后,發現對機構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感取代了情緒上的興奮。
一邊繼續搞科研一邊尋找出路,直到2006年新一代高通量DNA測序儀推出,使測序提速百倍以上,讓汪建感覺基因組學發展將迎來新機遇,想要在生物技術領域干出一番事業必須趕上這波。但開展基因組學研究的愿望并未得到官方的積極回應,汪建等人決定離開國有體制,帶著科研人員南下,在深圳成立了華大基因研究院。
這個看起來不可思議的選擇,推動華大基因開始構建“產學研”一體化模式。起初,汪建打算集中手頭上的經費專門用于基因測序與分析,并用兩億元購買測序設備,至于最終能發展到什么程度還沒有明確目標。不過,2008年,華大基因在《自然》雜志上成功發表的一篇學術論文,作為突出成績被深圳市政府重視起來。現任華大基因助理院長的張勇,對當時的情形印象深刻,“區領導來到華大基因做現場辦公,明確了華大基因是一個在做事的機構,但也要講經濟,提出華大基因必須把科研成果產業化的要求”。
于是,除了研究院本身,華大基因成立了華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華大基因健康服務有限公司、北京六合華大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華大方瑞司法鑒定中心、華大方舟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等一系列營利性公司,而分支機構也快速遍布各地,杭州、西藏、香港、歐洲、印度等地都有了華大基因的分公司或實驗室。用科學研究支撐技術的先進性推動產業創新,產業轉化后又反哺科研,這套創新機制聯動起來,使華大基因在2009年之后進入超速增長期。2009年,華大營業額是4億元,2010年超過10億元。2010年7月,華大歐洲、美洲分部成立,8月份這兩家分部的收入已超過千萬元。
以往,華大基因研究院代表的是華大的全部,而現在,它是華大最重要的創新孵化器,與產業化密切相關的核心部門。“如果不實現產業轉化,華大就是一個瘋狂發文章的機構,只是一個科學上領先的研究機構。”張勇說。
華大軍校練兵
看上去,華大基因滾雪球式的飛速發展,應該歸功于它介乎企業和科研機構之間,實現了自己一套產學研一體化的模式。但在汪建看來,華大研究院那些敢想能干的年輕人,才是華大基因真正的殺手锏。
2008年7月,產前診斷研究員陳芳從深圳大學碩士畢業,由于參加了華大基因與深圳大學合作培養人才計劃,畢業后她就來到華大基因的研究院。
不看重學歷、不問學習成績、對各種類似優秀學生干部等證書更是只字不提,與其他同事一樣,她也曾感嘆于“一家明星科研機構,面試居然如此輕松”。
但真正的考驗在后面。剛被招進研究院,等著陳芳的是持續兩個月的上崗前培訓。一周基礎知識教學,一周實驗平臺培訓,一周臨檢項目培訓,第二個月就要跟著技術導師入組實驗室平臺,開始觀摩和學習真正的實踐技能。
沒料到的是,結束了兩個月的培訓后,在最后的上崗考核中,由于實驗技術技能中一個步驟銜接出差錯,陳芳沒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整個測試,需要重修半個月,才取得每個新人真正進入華大前在“華大軍校”所需要的“金槍證”。
面試的快速通道和實踐性培訓之外,華大基因最重要的是給人才提供成長平臺。“傳統實驗室模式,一般都是一個導師帶兩三個學生,三四年做三四個課題。華大把研究和產業結合,一年光課題就有8000多個,每個人每年怎么也能做七八個。”張勇說。
在通過上崗培訓考核后,陳芳非常幸運地被一個新項目組選中。這個項目組試圖采取無創方式,改變對唐氏高危孕婦使用的傳統羊水穿刺篩查方式,避免以往羊水穿刺帶來的1%的流產風險,還能提升篩查準確率。
接受更大考驗的時候來了,面對全新領域,除了幾篇學術論文別無其他可參考信息,跟著老師在實驗室反反復復地做實驗。“傳統的科學研究,就是假說導向的,但華大做項目時就不做假說。在生物領域,鎖定一個目標失敗的幾率比成功大太多。華大從不先設定它的結果,而是從數據挖掘的角度去做。任何數量的樣本研究都會產生巨大的數據,在這其中一定有有用的東西,當然也有失敗的,但成功率相對高。”在張勇看來,這是華大基因的研究院與其他科研所最大的不同之處。
陳芳第一次體驗到一種挫敗感:即使已經做到了100個樣本也不代表第101個樣本一定會測試成功。“我甚至有了輕度抑郁癥的傾向,那時候每天睡4~5個小時,腦子里只有實驗,看到別人又有新東西做出來就著急,自己的實驗出一點問題就會質疑自己。”陳芳說。
創新方法論
華大基因研究院這些年輕人,有學生物的、學數學的、學計算的、學物理的,有高中畢業就投奔公司而來的,也有按部就班拿到大學研究生文憑的,盡管受教育背景不同,但他們來到研究院都可以找自己有興趣的領域,也可以主動申請任何項目,他們上班不用打卡,也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
聽起來,這就是一個搞創新的自由之地。在這里,每天都能冒出無數新想法,但事實上,一個想法從產生到最終落地成為一個項目,研究院有一套立項機制嚴格把關。
2009年底,陳芳跟著小組把項目做到商用轉化階段后,她開始認真思考一個問題:“盡管我們希望通過這個項目能幫助孕婦做到早發現,但實際上在胎兒成形后進行的篩查都屬于消極干預,有沒有可能把這種診斷再往前一點?比如婚前、受孕前。”
帶著好奇心,她開始查閱資料,發現一年之前,華大基因就在研究相關技術,并在《Cell》雜志上成功發表植入前診斷方法的文章,而且在幾次業務討論會上,她也留意到有同事在別的項目應用中開發這項技術。
這個意外發現,使陳芳有了動力和信心。于是,她開始著手進行小規模樣本調查,然后寫了10多頁的報告。報告提交到研究院之后,研究院召集技術開發、市場開拓、臨床檢驗團隊的老師們,一起探討新項目的可行性。“找不同部門的老師就是想從不同維度去考量項目是不是可以嘗試,用什么方法去做以及未來可能達到什么效果。”
這種協同創新的模式,在研究院內部也一直在完善的過程中。
在此之前,華大基因的研究院成立了一個技術開發團隊,分別覆蓋了華大基因所有研究項目的領域范圍,專門研究基礎核心技術開發,搜集世界上科研趨勢及最新研究技術,然后提供給研究院去實踐。起初由10個人組成,現在,他們開始按照領域,被縱向劃分到不同平臺小組,以便在新項目立項前能夠給出合理、專業的評判和建議,使得創新想法能夠更快速高效地在內部得到回應。
而市場部門的工作人員,把大量的精力都用在搜集產業需求方面的信息,反饋給科研人員,供科研人員挑選合適、可行的項目去做。像陳芳在運作新項目前,也能從市場部這里聽到市場需求點在哪里,項目做出來以后可能產生的效應是什么等等反饋和建議。
第一次約談后的第三天,陳芳收到老師們的反饋,對她的項目提議,大家并沒有反對,反而給了很多方向、實施上的具體意見。接著,她根據建議開始了小規模樣品測序,把相關實驗結果以及項目具體實施方案全面擬出來。十多頁的文檔變成了幾十頁,她要接受項目立項、項目規劃以及財務主管們的考核,她必須說服這些人,才能夠“通關”去實現她的項目。
每天遇到問題就找同事們討論,有時解決不了,她就寫郵件向國外分支機構或合作科研機構的老師們求助,有時一天來回30多封郵件。前前后后3個月時間,陳芳終于組建了自己在華大基因第一個3人項目組,并拿到上百萬元的經費支持。在今年,這個比無創診斷更進一步的項目,已經轉移到臨床檢驗團隊的同事手中,由他們繼續跟進臨床商用轉化,目前正與多家醫院進行合作意向以及具體實施方案的討論。
“研究院聚焦在生育、癌癥、個人基因組、農業育種四個領域,華大基因項目立項、成果判定的標準,就是要符合大的民生需求,對人類健康有幫助,有很強的科學性,符合生命科學研究的基本邏輯,還有就是要有起碼的技術作為實現項目成果的基礎。”主管研究院的徐訊說。年輕人當然有很多完全出于個人興趣的想法,只要符合這幾個大方向,項目審批的幾個環節就是朝著“如何讓項目更完善”的目標去的。
成千上萬的小項目里,也有不少在探討中直接升級為大項目。華大基因科研人員施玉健剛開始在做自閉癥相關研究時,了解到這個疾病被界定為具備遺傳基礎的疾病,發病率高并且還無法做到及早發現和干預,一般只能在4歲以后才能確診,但治療上已經非常困難了。
在多次反復實驗后,施玉健對父母生殖細胞形成時所發生的胚系突變與自閉癥風險之間的關聯,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邊研究,邊與技術開發、市場團隊進行持續半年左右的深入探討,越來越覺得不應該只是朝著發篇論文的目標做,應該成為一個更大的項目。
要做大項目必須有足夠量的樣本,華大基因領導層開始介入尋找資源支持。2011年10月13日,華大基因說服了美國“自閉癥之聲”合作,雙方合作創建全球最大的自閉癥患者基因組數據庫。一年后,雙方項目小組聯合在《Cell》上發表了基因胚系突變與自閉癥風險之間關聯性研究成果的文章。大量新的自閉癥易感基因的發現,將為未來自閉癥的早期篩查診斷、治療等打下基礎。目前已經設立了早期篩查的項目。
一個項目在華大基因的研究有幾條路:單純的發表期刊論文,科學發現向產業化轉化,或者由產業需求拉動科研創新。“但有一些很純粹的科學性研究,實在太偏門了,不可能實現產業化,那我們會選擇放一放。現在華大基因對產業化的要求還是挺高的,從發展的角度上說,還是會追求變現。”張勇說。
年輕的力量
20歲的趙柏聞,華大基因研究院“人類認知能力的基因組學分析”科研項目的團隊帶頭人;
李英睿,北大生命科學院的才子,曾曠課到華大“打黑工”———不要工錢只干活,后來被華大基因錄用,現在是華大基因首席科學家;
羅銳邦在剛滿20歲時,已在《自然·生物技術》上發表論文;
《自然》雜志評選出2012年度科學界十大人物,37歲的王俊成為唯一一位入選的中國人。
在華大基因研究院,青年才俊的故事已經被講爛了。平均年齡26歲,科研人員差不多是23~24歲,幾乎所有人都是剛畢業就來了。在徐訊看來,“中國紅軍長征時很多都是20歲上下的青年,為什么他們可以承受這么大的責任,因為人在這個年齡階段是最富有創造力的。但在當下的現實社會中,他們反而沒有一個自由的平臺施展潛力”。 為此,在篩選人才的過程中,華大基因的內部研究院不會把不具備相關實踐經驗和成果作為過濾掉人才的理由。相反,即便成績優異卻對科研沒有積極態度的人,被認為是最不符合研究院用人標準的。
同時,華大在體系內部重視教育來幫助年輕人成長。華大學院,有授予學位的權利,并與華工、武大、華科、電子科大、東大、華師、川大、青島大學等國內高校合作創辦創新班,累計招生137名。與哥本哈根大學簽訂協議聯合培養基因組學和生物信息學博士生;香港中文大學與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合作成立“香港中文大學—華大基因跨組學創新研究院”,計劃共同培養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代謝學、臨床遺傳學、臨床基因組學、計算機生物學及生物信息科學領域的全方位科研人才;與奧爾胡斯大學簽訂協議共建Clinical Genetics Center,聯合培養博士生。
華大基因的研究院從幾個人發展到現在的1000多人,早已經從50后、60后、70后的組合中更迭到80后甚至是90后。
不過,華大基因也有困惑。“有不少公司用10倍的價格挖人,我們也有百分之十幾的流失率。”張勇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體會:人不是以前那種一根筋了,比較苦比較累、錢少、沒有執著的熱愛,也就走了。
除此之外,擺在徐訊和華大基因面前的,是一個正在規模不斷增大的研究院,它需要摸索、提煉一個更加體系化的管理機制,使原先在“小而美”的研究院中打造出來的自由創新氛圍能夠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