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稅“妙招”的法律風險
文/周月萍 上海市協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郝肖贊 上海市協力律師事務所律師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繼續做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新國五條”細則)被業內不少專家解讀為房地產調控實質性的加碼和升級。從長遠來看,這一旨在打擊投機的政策本意,最終會在民間釀成何種避稅版本?又會引來哪些社會及法律問題?筆者從法律視角一一探析。
可預期的避稅版本和法律怪象
“新國五條”中“按轉讓所得的20%計征”的規定將使稅負成為老百姓二手房交易沉重的負擔,因為產生的稅負最后很可能轉嫁給購房者,促使購房成本增加。為了避開二手房轉讓過程中產生的大筆稅費,很多購房者會絞盡腦汁,試圖通過各種手段進行避稅。這種主觀上為了達到避稅目的,而不惜采用各種虛假方式的現象,勢必會擾亂視“雙方真實意思表示”為王道的市場交易規則,甚至違背傳統的社會倫理道德觀念,誘發各類不穩定因素及系列法律問題。
手段一:通過“陰陽”合同避稅
所謂“陰陽”合同,是指二手房買賣雙方簽署兩份合同,一份合同是真實成交價格,另一份合同是為了規避個稅的虛假成交價格。以一套原價100萬元,實際成交價格200萬元的二手房為例,如按新政計征20%的個稅,則賣方需繳納20萬元稅;如通過簽署“陰陽”合同,將成交價格改為150萬元,賣方只需繳納10萬元稅,比以真實價格成交少繳10萬元,而買家只需以現金形式補足“陰陽”合同間的差價部分50萬元即可。
但從目前上海個稅實際征繳情況來看,稅務部門會對明顯低于市場價格成交的二手房進行價格評估,如發現成交價格低于評估價格的,交易雙方必須按照評估價格進行征繳。因此,“陰陽”合同規避個稅存在法律風險。
另外,因為在房產交易中心備案登記的成交價格低于實際成交價格,如果買家五年內再次出售,因為其登記的購買價格低于實際成交價格,導致再次轉讓時所得稅的增加。因此,對購房者而言,賣方實際上是通過壓低成交價的方式,增加了買方將來再次轉讓房產時的成本,這無疑有損購房者利益。
手段二:通過假離婚再復婚避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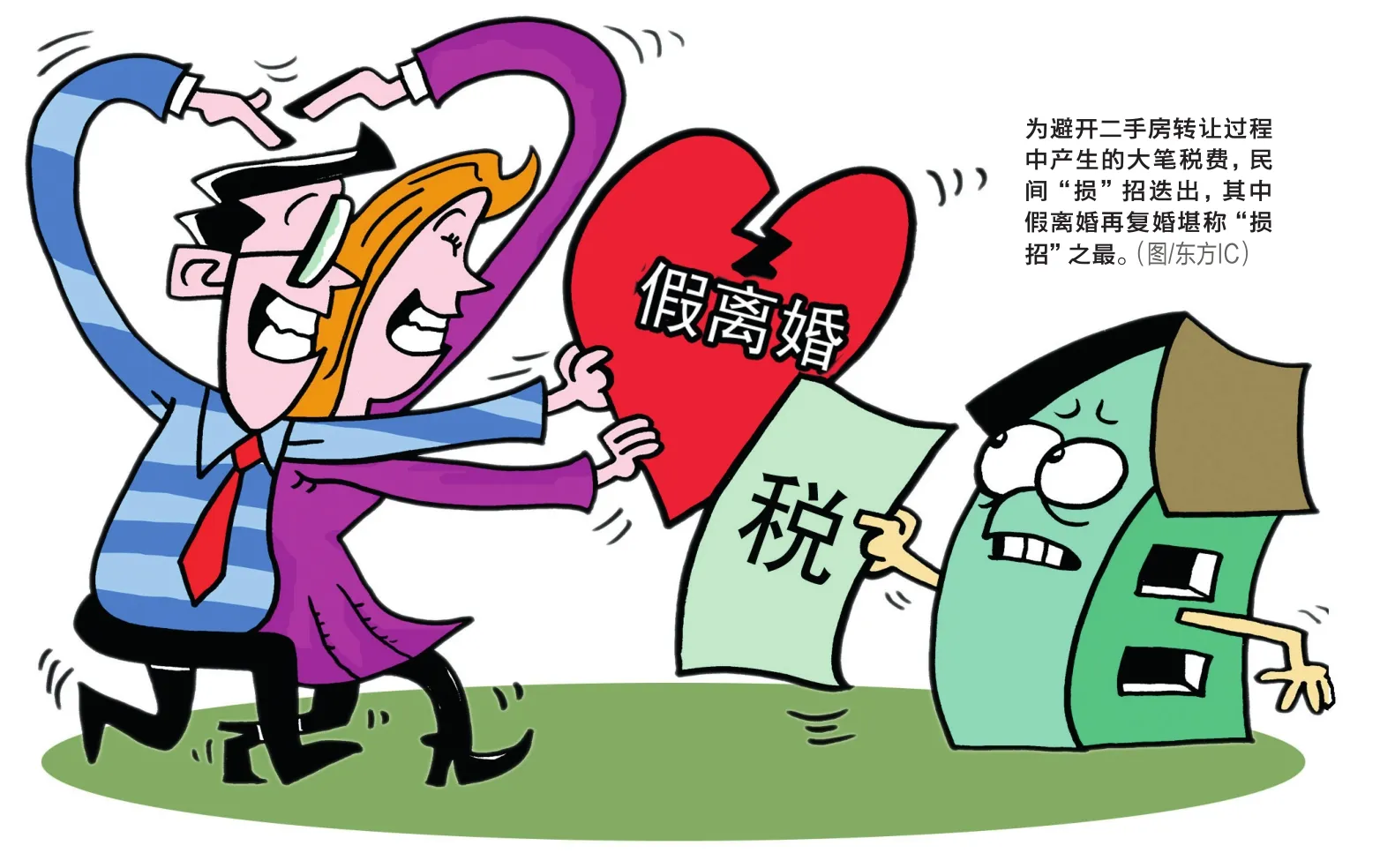
各種避稅辦法中,最“損”且號稱最簡便有效的一招,則是通過離婚、結婚實現。
這種避稅方法共分三步,第一步,買賣雙方夫妻離婚;第二步,賣方房主與買方異性結婚,房產證上加上對方名字,然后離婚,房屋歸買方異性;第三步,買賣雙方夫妻各自復婚。這樣一來,二手房過戶的總費用只需要結婚、離婚費及房產證更名的費用,表面上看可以節省幾萬乃至幾十萬元的過戶費用。
這種暗度陳倉、曲折復雜的避稅方法,看似可行,但由于牽扯到互不相識的夫妻,期間變數過多、太過復雜,需要冒的道德風險太大,在這個離婚率居高不下的社會,萬一離婚后,對方拒絕復婚了,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得不償失了。因此,這種有悖傳統的道德倫理和社會秩序觀念的假離婚,實不可取,否則,房事和房市真都要亂了。
另外,為了避稅而假離婚后,如果“不幸”弄假成真,假離婚變成真離婚后,之前夫妻雙方簽訂的財產分割協議均非一方或雙方真實意思表示,這勢必導致社會糾紛及訴訟案件的增多,產生社會不和諧因素,實不可取。
“新國五條”新政出臺后的相關建議
針對“新國五條”細則是否會“誤傷”改善性需求和剛性需求的擔憂,及因此可能會出現的各種避稅手段導致的一系列社會及法律問題,筆者認為,樓市調控細則已包含在新政中,但還需各地政府“翻譯”成可操作的具體條款。20%個稅政策的實施細則應該盡早清晰化,以避免市場對新政的恐慌或不理解,出現不理性地扎堆買賣房產現象,并導致房地產市場價格不降反升,違背新政本意。
另外,各地政府在出臺實施細則時,應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不同城市“量身定做”相應的配套政策,以避免在樓市調控中“誤傷”剛需及改善性需求。對剛需及改善性需求的購房者應實行“定向寬松”,譬如繼續嚴格執行2006年國家稅務總局《通知》中關于確保納稅人合法權益的規定。諸如,“對出售自有住房并擬在現住房出售1年內按市場價重新購房的納稅人,其出售現住房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先以納稅保證金形式繳納,再視其重新購房的金額與原住房銷售額的關系,全部或部分退還納稅保證金”;“對個人轉讓自用5年以上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個人所得稅”等,切實達到抑制投機性需求、支持合理需求的政策目的。
自古以來,中國的老百姓們素有先安居后樂業的傳統思想觀念。自我國房改以來,大量商品房的涌入的確解決了一部分人的安居夢想,但由于受各種因素影響,商品房價格節節攀升,現已是高處不勝寒,足以讓普通的工薪階層及家庭傾其大半輩子心血。
為解決百姓們樸實而艱辛的安居夢想,國家亦在不斷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力度,“新國五條”細則第四條亦提出“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規劃建設”。但地方政府如何將這些政策落地,仍是目前中央及地方政府重點關注的議題。只有解決了普通百姓的安居問題,才能緩和房產市場供求矛盾,并最終使房價回歸理性。
對于“新國五條”帶來的稅負影響及短暫的市場震蕩,筆者呼吁,市場各方需理性對待,拭目以待新政及后續政策的出臺;作為地方政府層面,筆者建議盡快出臺實施細則或征管細則,盡量縮短政策銜接的過渡期,以促進市場穩定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