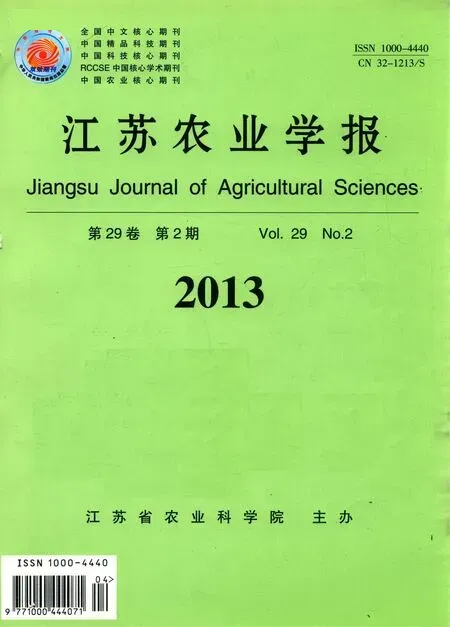藍藻自然腐解特性研究
趙懸懸, 朱光燦, 許麗娟, 呂錫武
(1.東南大學能源與環境學院,江蘇 南京210096;2.東南大學無錫太湖水環境工程研究中心,江蘇 無錫214135)
近年來,太湖流域地區經濟飛速發展,人口、企業數量與日俱增。與此同時,大量未經處理的生活污水和工業污水不斷注入太湖,使得太湖水體富營養化愈加嚴重,最終導致太湖水華產生。2007 年太湖藍藻大暴發,藍藻形成的水華大量堆積在湖面,導致無錫城市供水危機并嚴重破壞水體生態[1-2]。目前,太湖藍藻的處理仍以機械或人工打撈為主,這種方法能大量去除湖泊藍藻水華,降低水體營養水平,可在水華藍藻大量堆積的區域快速達到改善水環境的目的。但是打撈只是權宜之計,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主要原因在于,機械或人工打撈上岸的藍藻含水率大于99%,常規的掩埋等措施難以處置,最終導致藍藻大量存積,并經自然腐解形成陳藻。陳藻藻液具有高有機物、高氮磷含量和腐敗發臭的特點,長期堆積會對周圍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目前,國內外對陳藻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對陳藻的形成過程及處理技術等方面的研究較少,直接導致人們在陳藻處理方式上的盲目性。
鑒于上述情況,本試驗擬開展藍藻自然腐解特性研究,探究藍藻腐解過程中有機物降解、氮磷積累和葉綠素降解等方面的規律,并提出較為適宜的陳藻處理及資源化利用方式,為工程實踐提供指導。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材料
自然腐解試驗所用的藍藻取自宜興市周鐵鎮符瀆港藍藻打撈站,含固率為7.3%,藻漿中主要污染物指標:化學需氧量(COD)77 500.0 mg/L,總氮3 247.5 mg/L,總磷273.5 mg/L,NO3--N 464.0 mg/L,NH4+-N 840.3 mg/L。試驗自2011 年9 月23 日至10 月23 日。
1.2 試驗方法
試驗所用的裝置(圖1)為有機玻璃制成的圓柱體容器,直徑0.35 m,高度0.50 m,有效容積40 L。容器上部設有1 臺攪拌器,轉速可調,腐解過程中轉速保持在3 r/min,取樣前調至15 r/min并保持30 s,取樣時停止攪拌。藻漿由容器頂部一次性投入25 L,之后每3 d 取1 次樣,進行水質分析。由于本試驗所用的容器敞口面積較小,因而忽略水分蒸發的影響。
1.3 分析項目及方法

圖1 腐解試驗裝置圖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reactor
1.3.2 葉綠素含量測定 葉綠素-a 采用丙酮提取-分光光度法測定。
1.3.3 微量有機物GC/MS 測定 用0.45 μm 濾膜過濾后測定微量有機物,采用THERMO FISHER(賽默飛世爾)公司的Thermo Scientific 分析儀器,其型號為:Triplus TraceGC ITQ1100,毛細管型號為Thermo TR-5ms,30 m×0.25 mm×0.25 μm。
進樣口溫度:250 ℃;載氣流速1.2 ml/min,恒流不分流進樣;柱溫:初溫40 ℃,保持3 min,以8℃/min升至250 ℃,保持3 min,以30 ℃/min升至280 ℃,保持3 min;傳輸線溫度:250 ℃;離子源溫度:250 ℃;溶劑延遲4.5 min;質量掃描方式為全掃描;質量范圍為35 ~350 amu。
1.3.4 藻毒素測定[3-5]總微囊藻毒素-LR 含量(TMC-LR,即胞內與胞外MC-LR 之和)和胞外微囊藻毒素-LR(EMC-LR)含量采用高效液相色譜(HPLC)法測定。
藻毒素提取:將取得的樣品按5%比例加入冰醋酸,混合過夜,用0.45 μm 濾膜(有機)過濾,濾液用于TMC-LR 含量測定[EMC-LR 測定樣品直接用0.45 μm 濾膜(有機)過濾,濾液備用];將濾液通入已活化的Supelco 固相萃取(SPE)柱中以富集微囊藻毒素(MC-LR),濾液過柱速度不大于5 ml/min;而后依次用40 ml 去離子水、20 ml 10%甲醇溶液、20 ml 20%甲醇溶液淋洗SPE 柱,去除MC-LR 之外的雜質;用0.1% 三氟乙酸-甲醇溶液5 ml 分3 次洗脫SPE 柱,將MC-LR 溶出,置于5 ml 帶刻度錐滴管中;應用MTN-2800D 型氮吹儀將錐底管中液體蒸發至0.2 ml,再用0.1% 三氟乙酸-甲醇溶液定容至0.4 ml;將定容后的樣品用0.45 μm 針頭過濾器過濾,濾液放入樣品瓶,-20 ℃保存待測。
2 結果
2.1 化學需氧量(COD)變化規律
COD 的變化情況如圖2 所示,可以看出,隨著腐解時間的推移,藻漿中的COD 逐漸降低,且呈現出“前期慢、中期快、后期穩”的規律。至試驗結束時,COD 已 由 進 料 時 的77 500 mg/L 降 至46 260 mg/L,降解率達到40.3%。腐解試驗前6 d,由于水解酸化作用的進行,藻漿的pH 值由6.80 下降至5.49(圖3),此時大分子有機物并未完全分解為易降解的小分子有機物,因而COD 的降解速率相對較慢;腐解試驗6 ~24 d 期間,腐解系統整體處于缺氧狀態(溶解氧濃度約0.4 mg/L),局部處于厭氧狀態(溶解氧濃度小于0.2 mg/L),藻漿的pH 值由5.49上升至6.93(圖3),一定程度上表征著自然腐解系統水解酸化階段的結束。此時可以觀察到腐解系統內藻漿出現膨脹且有氣泡產生,大量小分子有機物分解轉化成甲烷、CO2等氣體逸出,導致COD 下降速率加快;試驗24 d 后,COD 趨于穩定,保持在48 280 mg/L左右。COD 的變化規律說明藻漿在自然腐解過程中有機物存在一定的降解,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陳藻后續處理的負荷。

圖2 藻漿中化學需氧量(COD)隨腐熟時間的變化Fig.2 Change of 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during decomposition of cyanobacteria liquid
2.2 葉綠素a 變化規律

圖3 藻漿中pH 值隨腐熟時間的變化Fig.3 Variation of pH during decomposing period of the cyanobacteria liquid
葉綠素a 是表征浮游植物生物量最常用的指標之一,是藻類細胞重要組成成分。藻漿中葉綠素a的變化規律如圖4 所示,可以看出,試驗啟動時,藻漿中葉綠素a 的濃度高達113.5 mg/L,試驗周期結束時降至最低(15.3 mg/L),去除率達到86.5%。與COD 的降解不同,葉綠素a 的降解呈現“前期快、中期慢、后期穩”的規律。腐解試驗1 ~6 d,葉綠素a 的降解速率最快,其濃度呈線性降低。試驗6 ~21 d,降解速率逐步減慢,但葉綠素濃度仍穩步降低。腐解試驗21 d 后,葉綠素a 濃度趨于穩定,保持在16.0 mg/L 左右。有研究表明,生物監測中葉綠素a的濃度與藻類密度有著良好的線性關系[6]。據此可認為藻漿自然腐解過程中,葉綠素a 的降解規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藻類密度的下降情況,即藻類密度在腐熟過程前3 周迅速下降而后趨于穩定。另外,由圖4 還可以看出,腐解試驗結束時葉綠素a 并未降解完全,這部分葉綠素可能是由非藻類的浮游植物產生的。

圖4 藻漿中葉綠素a 濃度隨腐熟時間的變化Fig.4 Change of chlorophyll-a during decomposition of cyanobacteria liquid
2.3 氮、磷變化規律
如圖5 所示,從試驗啟動至24 d,藻漿中NH4+-N含量始終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由840.3 mg/L增長至2 079.0 mg/L,之后趨于穩定,保持在2 095.8 mg/L 左右,這一階段腐解系統呈現整體缺氧而局部厭氧的狀態,隨著腐解過程進行,藻類殘體中的有機氮會生成NH4+-N[7]。加之,試驗期間藻漿的pH 處在5.49 ~6.95 的偏酸性區間,不利于NH4+-N 形成NH3釋放到空氣中,因而出現NH4+-N 的大量積累。與NH4+-N 的變化不同,NO3--N 的變化呈先增后減的趨勢。從試驗啟動至3 d,藻漿中的NO3--N 濃度由464.0 mg/L增長至576.8 mg/L,這一階段腐解系統內部存在一定量的溶解氧,部分NH4+-N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轉化為NO3--N,因而NO3--N 濃度有所升高。之后至試驗結束,NO3--N 濃度不斷下降至10.6 mg/L。這一階段腐解系統整體處于缺氧狀態,NO3--N 在反硝化作用下不斷減少。
如圖6 所示,整個試驗過程中,藻漿中總磷的變化甚微,平均濃度為314.1 mg/L,少量的增長可能是由水分蒸發所致。相比之下,總氮存在著較為明顯的減少趨勢,從試驗啟動至18 d,藻漿中總氮濃度由3 247.5 mg/L降至2 782.5mg/L,之后趨于穩定并保持在2 764.4 mg/L左右。總氮的減少主要通過兩種方式:(1)NH4+-N 水解形成NH3;(2)NO3--N 反硝化形成N2,兩種氣體釋放到空氣中造成氮素的流失。藻漿中NH3的生成反應受到pH 抑制,因而NO3--N 反硝化生成N2所引起的氮素流失成為總氮減少的主要形式,這通過對比NO3--N 與總氮減少量可得到證明。
浙江專員辦順應轉型趨勢,突出管理思維,聚焦事前事中環節,努力在問題研究的深度、政策建議的高度和系統糾偏的廣度上下工夫,不斷提升財政金融監管的權威性。

圖5 藻漿中NO3--N 和NH4+-N 含量隨腐熟時間的變化Fig.5 Changes of NO3--N and NH4+-N contents during decomposition of cyanobacteria liquid
2.4 藍藻腐解前后有機組分GC/MS 分析
藍藻腐解前后藻液中揮發性半揮發性有機組分定性分析結果見表1。可以看出,新鮮藻漿中存在63種有機物,包括羧酸類10 種,醇、酚及酮類物質8 種,烷烯烴類2 種,酯類14 種,胺類11 種,其他18 種,其中相似度大于70%的有39 種。自然腐解30 d,藻漿中存在40 種有機物,包括羧酸類6 種,醇、酚及酮類物質7 種,烷烯烴類2 種,酯類3 種,胺類9 種,其他13 種,相似度大于70%的有20 種。

圖6 藻漿中總氮、總磷含量隨腐熟時間的變化Fig.6 Changes of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contents during decomposition of cyanobacteria liquid
由表1 還可以看出,經過自然腐解,藻漿中酯類物質大量減少,說明酯類屬于易降解有機物,可在自然腐解過程中發生水解作用,并產生了酸、醇等物質。另外,自然腐解過程對微量有機物去除率較低,只有36.50%。殘存微量有機物中,已被確認為致癌物的有1 種,促癌物、輔致癌物有2 種[8-10],被列入中國環境優先污染物“黑名單”的有2 種[11]。對比表2 中峰面積的結果可知,經過自然腐解處理后藻漿中易降解有機物基本得以降解,而難降解物質的去除率也可達到60%以上,并且這一過程中并無新物質產生。綜合分析認為,藻漿通過自然腐解過程,可生化性有所提高,為后續處理與資源化利用提供了條件。
2.5 微囊藻毒素變化規律
由圖7 可知,新鮮藍藻的微囊藻毒素主要存在于藍藻細胞中。隨著腐解過程的進行,藍藻細胞逐漸破裂,細胞內藻毒素不斷溶出,致使胞外藻毒素(EMC-LR)的含量逐漸增大。EMC-LR 含量與總微囊藻毒素(TMC-LR)含量的差距不斷減小。當腐解進行到第9 d 時,EMC-LR 含量達到最大(415.89 μg/L),與TMC-LR 含量已相差很小,說明此時藍藻細胞內的藻毒素達到最大程度釋放。由圖7 還可以看出,藻漿中的TMC-LR 逐漸被降解,至試驗結束時,其含量已由進料時的494.26 μg/L降至11.39 μg/L,降解率達到97.7%。與COD 的變化規律相似,TMC-LR 的降解亦呈現出“前期慢、中期快、后期穩”的規律。腐解0 ~9 d 內,TMC-LR 降解速率較低,原因可能是細胞內的藻毒素未能充分溶出從而導致降解速率較為緩慢。腐解9 d 之后,藍藻細胞內的藻毒素達到最大程度釋放,TMC-LR 降解速率也隨之增大。24 d 后,TMC-LR 含量達到穩定,保持在12.39 μg/L左右。由藻毒素的降解規律可以看出,藻漿自然腐解過程對TMC-LR 有著顯著的降解效果,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陳藻資源化利用的安全性。

表1 新鮮藻漿與腐解藻漿有機組分定性分析結果對比Table 1 Comparison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organic components between fresh cyanobacteria liquid water and decomposed cyanobacteria liquid

續表1 Continued table 1
3 討論
對比圖2、圖4、圖5 及圖7 可知,化學需氧量、葉綠素a、NH4+-N 及TMC-LR 分別在試驗進行到24 d、21 d、24 d、24 d 時達到穩定。其中有機物、NH4+-N及TMC-LR 在同一時間達到穩定并且遲于葉綠素指標的穩定,可考慮用三者之一的穩定時間來表征藻漿的腐解期。本試驗過程平均水溫為25.9 ℃,此時藻漿的腐解期為24 d。

圖7 藻漿中藻毒素含量隨腐熟時間的變化Fig.7 Change of microcystin-LR content during decomposition of cyanobacteria liquid
腐解試驗結束時,藻漿已基本形成陳藻,其有機質及氮磷含量較高,其中COD、總氮、總磷的濃度分別達到46 300 mg/L、2 765.8 mg/L、304.1 mg/L。對于陳藻的處理要充分考慮有機質及氮磷的資源化利用并選擇合理的方式。從有機質利用的角度出發,宜選擇厭氧發酵,因為厭氧發酵可以在降解有機質的同時生產出生物能源或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從氮磷利用的角度出發,宜選擇農肥灌溉。研究表明在氮缺乏的地區施用藍藻生物肥料對水稻的生長和增產有利[12];姜繼輝等研究發現施用藍藻發酵液和新鮮藍藻的土壤總氮、有效磷和有機質含量顯著增加[13]。
對比厭氧發酵與農肥灌溉技術,筆者認為宜將后者作為陳藻處理的首選方式。原因有兩個方面:首先,陳藻中氨氮濃度過高不利于其厭氧產沼氣,Walter 等[14]研究表明高濃度的氨態氮(NH3-N)抑制了厭氧發酵產甲烷,在消化過程中,當氨氮增加到2 000 mg/L 以上時,甲烷產量降低;其次,相比于農肥灌溉,厭氧發酵投資較大,對技術的要求較高,運行管理也較為復雜。
[1] 朱 喜. 太湖藍藻大暴發的警示和啟發[J]. 上海企業,2007,7(2):7-13.
[2] 祖慧琳,朱 煜,鄭典元,等.太湖藍藻水華污染對黃顙魚遺傳多樣性的影響[J].江蘇農業科學,2012,40(4):37-40.
[3] 張立將,尹立紅,浦躍樸. 水中微囊藻毒素高效液相色譜檢測與前處理條件優化[J]. 東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5,35(3):447-452.
[4] CHEN W,LI L,GAN N,et al. Optimization of an effective extraction procedure for the analysis of microcystins in soils and lake sediments[J]. Environ Pollut,2006,143(2):241-246.
[5] MORENO I M,MOLINA R,JOS A,et al. Determination of microcystins in fish by solvent extraction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J]. J Chromatogr A,2005,1080(2):199-203.
[6] 于海燕,周 斌,胡尊英,等. 生物監測中葉綠素a 濃度與藻類密度的關聯性研究[J]. 中國環境監測,2009,25(6):40-43.
[7] 盛 東,徐兆安,高 怡. 太湖湖區“黑水團”成因及危害分析[J]. 水資源保護,2010,20(3):41-44.
[8] 鄭曼英,李麗桃. 垃圾滲液中有機污染物初探[J]. 重慶環境科學,1996,18(4):41-43.
[9] 朱惠岡,俞順章. 飲水中致癌、致突變物(上)[J]. 環境保護,1985(3):28-30.
[10] 朱惠岡,俞順章. 飲水中致癌、致突變物(下)[J]. 環境保護,1985(4):21-23.
[11] 周文敏,傅德黔,孫宗光. 水中優先控制污染物黑名單的確定[J]. 環境科學研究,1991,4 (6):9-12.
[12] TRIPATHI R D,DWIVEDI S,SHUKLA M K,et al. Role of blue green algae biofertilizer in ameliorating the nitrogen demand and fly-ash stress to the growth and yield of rice(Oryza sativa L.)plants[J].Chemosphere,2008,70:1919-1929.
[13] 姜繼輝,嚴少華,陳 巍,等. 太湖藍藻發酵后沼渣和沼液的肥效研究[J]. 江蘇農業學報,2009,25(5):1025-1028.
[14] WUJCIK W J,JEWELL W J. Dry anaerobic fermentation[J].Biotechnol Bioeng Symp,1980,10:4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