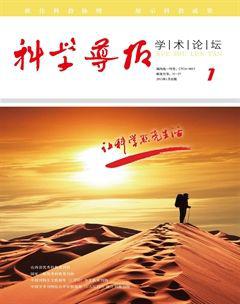李煜詞的“水"意象情感境界的深化
陶星
【摘要】李煜在政治史上是亡國之君,但在文學史上他卻被稱作“詞中之帝”。對于李煜詞作的風格與情感境界,歷來的評論者多認為其前期偏于享樂淫靡,而后期的作品則境界甚高。在本文中,以李煜入宋以來詞作中的“水”意象作為切入點,分析了他在生命最后的短短三年內,詞作風格與情感境界不斷深化的歷程。
【關鍵詞】“水”意象情感境界悲情世界命運
詞之體式起源于唐末,但就思想境界而言,這些初期的詞作卻多流于側艷,所謂“兒女情多,風云氣少”。但相較其后的五代南唐,卻從情感境界方面對詞有了一個全新的發展,特別是后主李煜在眾多詞人中脫穎而出,被稱為“詞中之帝”。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李煜打破了花間詞派的樊籬,使得詞的意境得以開拓。
李煜一生詞作不多,《全唐詩》總計收35首。據筆者統計,其詞作中涉及“水”的僅11處,雖然不多,但“意象”之所以為“意象”,其中一個重要特質就是它被詞人賦予了多重內涵。從某種意義上說,意象內涵的不同也反映了詞作所傳達的情感境界的不同。在本文中,筆者之所以選取“水”作為探究對象,就是因為在眾多意象中只有“水”與李煜的生命關系最緊密,而且我們可以從其詞作的“水”意象中了解他后期詞作風格與情感境界的褪變,因此本文從“眼中之水”、“心中之水”、“生命之水”三個層次對李煜筆下具有多重內涵的“水”意象進行探討。對李煜詞作的評價,過去的評論多以公元975年為界,認為他亡國前期的作品內容多綺靡之詞,終不脫花間氣,而從975年受降到978年被殺這僅僅3年的時間里,其詞作成就之高卻被王靜安評日:“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作為皇帝,李煜是不幸的,史書記載他“悒悒以國蹵為憂,日與群臣酣宴,愁思悲歌不已”。面對內憂外患的國家,以他的性格品質,想不亡國都很難,所以亡國之君的命運應該是一個必然。但作為詞人,他的命運卻似乎是帶有一絲偶然,入宋以來的詞作,其言呼號悲泣,其情一往而深。目睹而今的國破家亡,當時的他自然而然地便會回憶起從前的生活,體現這種情懷的詞作如《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這首詞是李煜入宋后的作品,全詞但寫夢中往事,當年之繁華,今日之凄婉,二者一虛一實,一夢一醒,相較之下,也只能對夢空恨,徒自落淚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恨僅僅是一種對往日帝王生活的回憶與懷念,對那種所謂快樂生活難以重來的哀悼與悲嘆,往事已矣,如流水般一去不返,而淚水卻不住的流,也許現在的李煜也只能從那一滴滴淚珠中回味從前的花月春風了。
過去是享受著奢侈的帝王生活,雖有憂愁,也多是“閑愁”,而今則由天上墮落人間,過起了囚徒的生活。說到回憶,李煜是“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除了宮廷生活,確實也再無可回憶的了。但正是因為缺少閱世經歷,才使得他無論生活還是作詞都以一己全情去投入,也正因如此他的感慨也較常人為深:言語受到限制,活動受到約束,這些被李煜看在眼里,也印在心里。李煜經歷了一段囚徒生活后,其情感已不在是僅僅對過去生活的眷戀,而是升華到了對家國天下的悔恨,如此情懷如其詞《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是李煜入宋后第二年(977年)正月所寫。全詞但寫喪家亡國之痛,從“春花秋月何時了”到“只是朱顏改”數句,對永恒的自然與無常的人事進行了三次對比,最后結語落在“一江春水”。故國已逝,家鄉已遠,只有那秋月長在,東風時來,雕欄玉砌之外只有那哀愁悔恨如春水一般長流不盡。
李煜入汴后“日夕以淚洗面”(李煜寄金陵舊宮人信中語),同樣是對往事的哀悼,同樣是傷春悲秋,此情此感人人本具,何以唯獨后主之詞便“高妙超脫,一往而深?”筆者認為,乃是因李煜不僅僅是以一顆赤子之純心來感知外界事物,以全情真意來書寫自身身世的凄婉,而是以個人感受寫盡宇宙萬物蕓蕓眾生共有的悲慨。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的那樣:“后主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比如其詞《相見歡》: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李后主在這短短的36字的小詞中卻將人世間一切美好事物最終的歸宿都寫盡了。在詞中作者用一個“謝了”,說的何等直白,花謝本是正常之事,但在詞中讀來卻給人一種突然之感,令人恍然間若有所失,而這種下沉之感與“水”之向下流的質性又是相同的。在這里詞人用了一個喻指,他用“林花”謝了代指世間一切無常而美好的事物走向衰亡,接下去“胭脂淚,相留醉”,胭脂淚”是一切的美好,既令人沉醉又令人心碎。面對衰亡,后主不是一個強者更無法與之抗衡,他只能眼睜睜看著這一切,包括自己的淚水與長恨向江水東流一樣,一去不返。
以李煜而言,如果說他前期的詞作是移情入景,那后期的詞作則是觸景生情,正如前文所述,李煜詞中的“水”意象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水了,而是他內心長期蘊藏著的一種情感,一種境界在與客觀意象相接觸時的外化,而這種含有悲劇色彩的外化同時也為我們傳達了一些悲劇意義。
李煜從小生活在深宮內院,再加之生性風流,閱世不深,因此無論遇事待人,乃至南面主事均以真心待之。況且他本就對政治避之猶恐不及,面對不可回避的登基,他是多么希望能像流水一樣隨遇而安,隨緣自在。只可惜,在那樣的身世下,他的這種純情之夢必然是一種幻想。從他當太子時就為兄弟所猜忌,當了皇帝后又為宋所欺壓,最后甚至淪為階下囚,凡此種種都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渴望安寧自由而終為命運所縛的悲劇人生。
參考文獻
[1]張璋,黃畬.全唐五代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全唐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詹安泰.李璟李煜詞,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