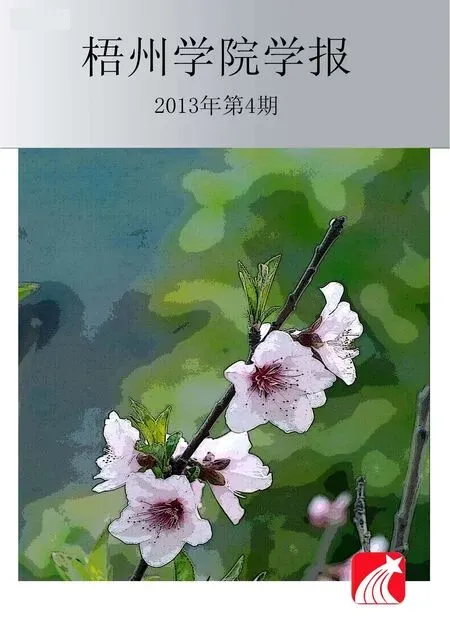中國與東盟國家國內法關于核心勞工標準的法律比較
植文斌,蔡菲菲
(1.2.梧州學院法律與公共管理學院,廣西梧州543002)
中國與東盟國家國內法關于核心勞工標準的法律比較
植文斌1,蔡菲菲2
(1.2.梧州學院法律與公共管理學院,廣西梧州543002)
隨著國際社會對于勞工權利保護意識的增強,國際性的勞工保護運動的發展、企業的社會責任及勞工權利保護問題逐漸成為消費者購買產品時考慮的因素。而中國企業的海外市場拓展近年來也受到勞工權利保護名義下的貿易投資壁壘的阻礙。隨著中國企業對東盟國家直接投資浪潮的興起,東盟國家的勞工權利保護、勞工標準和勞動待遇等問題也勢必成為影響中國企業投資的利益實現。該文嘗試通過對中國與東盟國家國內法關于核心勞工標準的法律進行比較分析,對中國投資者和投資企業如何合理利用東盟國家勞動力資源進行討論。
核心勞工標準;東盟國家;中國;國內法
一、核心勞工標準的含義和發展
勞工標準是由國際勞工組織(ILO)創設,用于衡量勞動者在勞動就業方面的受保障程度,由多項國際公約和建議書構成。目前公認的勞工標準就是在該組織通過的200余項公約的基礎上設立的,也被稱為核心勞工標準[1]。核心勞工標準包涵了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禁止童工勞動、禁止強迫勞動、同工同酬和消除就業歧視等領域的勞工標準[2]。
國際勞工標準正式確立應朔及國際勞工組織成立,繼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作為國際聯盟的一個附屬組織設立,1946年12月14日國際勞工組織成為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該組織的宗旨是:“促進充分就業和提高生活水平;促進勞資合作;改善勞動條件;擴大社會保障;保證勞動者的職業安全與衛生;獲得世界持久和平,建立和維護社會正義。”
近代意義上的勞工標準理論起源于上世紀50年代的經濟法理論中,1951年就有國外的學者指出任何勞動立法都會導致雇主利潤的減少,這里的勞動立法可以視為現在意義上的勞工標準,而雇主的固有缺陷則屬于“市場缺陷”,而勞工標準就是為了克服這個“市場缺陷”而產生的。而到了1996年,有學者提出了勞工標準的外部性,認為當勞工待遇提高時,勞工不僅僅給企業帶來更多效用,還給社會帶來更多效用。隨后一些學者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下更提出了勞工標準的外溢性特征,即在世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居民很關注發展中國家居民的工作條件,后者工作條件的提高能滿足前者的某種愿望。然而國際勞工標準的矛盾從上世紀90年代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開始產生,90年代初期,企業的社會責任運動興起。首先是美國勞工及人權組織發動“反血汗工廠運動”,后演變為“企業生產守則運動”,直接目的是促使企業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勞工標準的支持者認為最低勞工標準是有必要的。如果達不到最低的標準,一方面勞工的待遇和經濟狀況將會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會沖擊部分工業化國家的制造業基礎,工業化國家的工人將失去大量的工作機會。而勞工標準的反對者認為,降低勞工標準并不一定意味著低工資和惡劣的工作環境,一個企業、一個行業或者說一個國家的工業競爭力不可能一直依賴于低工資或低下的勞工待遇和環境,無法證實勞工標準的不同對貿易產生明顯的作用。
隨后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世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兒童權益公約制定的SA8000于1997年10月公布,成為全球首個道德規范國際標準[3]。但從總體來說,無論是SA8000或者是更早之前出現的企業社會責任,這些認證體系的宗旨目的都是為了在保證產品可供交易的同時,確保人道主義和勞工權利的實現。可以看出,國際勞工標準是后兩者的核心內容和主要制定依據。
2004年5月1日,美國和一些歐盟國家單方面推行SA8000,藉此設置貿易壁壘,打擊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引發了新一輪對于國際勞工標準問題的國際博弈和爭議。因此對中國與東盟國家國內法關于核心勞工標準的對比進行研究,對于研究中國在對東盟國家的投資戰略,維護中國在東盟國家投資的利益實現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國際貨物貿易安全有重大的意義。
二、中國與東盟國家國內法關于核心勞工標準的法律比較分析
1.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于童工年齡規范方面的法律比較
依照中國《勞動法》定義,童工是指未滿16周歲,與單位或者個人發生勞動關系從事有經濟收入的勞動或者從事個體勞動的少年、兒童。而青少年工人是指任何超過上述定義的兒童但年齡不滿18歲的工人。而越南則規定:“勞動者必須是已年滿15歲,并且有勞動能力已訂立了勞動合同者。勞動使用者可以說營業,機關、組織或個人;勞動使用者如系個人,須已年滿18歲方可雇傭。”[4]而柬埔寨則沒有規定童工的年齡限制,只在學徒合同一篇里規定了勞動部門應規范一些行業不允許低于18歲的人成為學徒,而學徒要工作2年后方可轉成工人,因此造成了柬埔寨有近150萬年齡在14歲以下的童工。新加坡《就業法》第68條規定:(1)禁止工業企業或非工業企業雇傭兒童;(2)當工業企業只雇傭同一家庭成員時,可以雇傭兒童;(3)非工業企業可以用年滿13周歲的兒童并根據其能力安排輕活[5]。縱觀東盟10國的勞動法,其對于童工問題方面的規定基本有以下特點:第一,15周歲以下為童工;第二,不禁止或僅部分禁止雇傭童工;第三,在家庭成員允許或有效進行監護下,允許企業雇傭童工;第四,存在若干強制條款要求僅雇傭18歲以上成年人,如越南規定雇傭方是個人的必須雇傭18歲以上工人,還有其他國家規定若干工種只能雇傭18歲以上工人;第五,青少年工人視為成年工人。
東盟國家勞動法與中國勞動法主要分歧在于:首先是童工年齡的界定,中國勞動法規定是未滿16周歲則為童工,東盟國家一般認為是未滿15周歲,部分認為是13周歲;其次是中國勞動法采用的是勞動者年齡一刀切的方法,對雇傭未滿16周歲的童工是絕對的禁止,而東盟國家的勞動法則存在許多的例外條款,如家庭成員的允許和監護等條件,甚至如柬埔寨允許雇傭童工的行為;最后是勞動合同類型,中國只承認正式的勞動合同,但是東盟國家除了勞動合同外還存在學徒合同。
造成東盟國家和中國在童工問題上巨大分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中國是《1973年最低就業年齡公約》(第138號)和《1999年禁止和立即行動消除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公約》的締約國,這些國際條約對于童工問題的規定已經通過法律納入和轉化,成為我國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和其他法律法規和規章;第二,中國1994年通過《勞動法》的時候,已經改革開放了15個年頭,雇傭工人的企業大多是機械化或者需要大量熟練工人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而東盟大多數國家還存在大量的家庭作坊和手工作坊式的企業,因此造成用工訴求的分歧;第三,中國長久以來處在和平發展的國內外環境之中,成年勞動力充足,有提高童工年齡標準的條件,而一些東盟國家,如柬埔寨,則經歷了長久的戰亂,成年勞動力缺乏,不得不在生產中使用童工;第四,東盟國家的家庭作坊和手工作坊型企業長久以來有著手藝傳承的傳統,師傅和學徒的勞動關系作為這些國家的傳統得到承認,對民族手工藝的傳承發展是有好處的,是適合東盟國家國情,符合東盟國家歷史的。
2.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于勞工就業條件方面的法律比較
菲律賓勞動法律強行性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每個星期工作5天,每天不得少于60分鐘的就餐時間,對醫務人員有特殊規定,并規定在國家發生戰爭、嚴重事故和自然災害時特殊崗位人員可以被要求工作,但必須給予額外補貼。在工資發放上,規定了必須保護勞動者的福利,禁止削減工資和取消福利。規定了勞動者的最低工資,但農業和非農業工人的最低工資由地方工資與生產力理事規定[6]。越南關于就業條件的規定在勞動時間上有其獨特之處,越南法律規定了三種工作時間:一般工作時間、約定時間、夜間工作時間。一般工作時間為一天不超過8小時,一周不超過48小時,雇傭者有權要求勞動者于周六周日工作,但必須事先通知勞動者;約定時間指的是勞動者和雇傭者可以約定增加勞動時間,但一天不得超過4小時,一年不得超過200小時;夜間工作時間限制為從22時到次日6時或從21時到次日5時,按氣候來決定。此外越南對加班和夜間勞動的工資發放進行了詳細的規定。文萊勞動法在工作時間上并沒有按小時來計算,但規定雇主必須每周為勞工提供不少于5天半的工作時間。另外文萊還規定在沒有家屬陪同下的勞動合同期限不得超過12個月,有家屬陪同的情況下不得超過3年,在文萊法律還出現“受供養人”、“家屬”、“移民工人”等就業條件的要素或者限制。新加坡的法律有雇傭者不得要求雇員連續工作6小時而沒有休息時間的規定,也規定了8小時工作制和雇員就餐時間不得少于45分鐘,另外新加波還制定了全國統一的最低工資標準和詳細的休假安排。而它的勞動法對于工作時間和工資的規定較東盟各國全面,對工作時間、休假、加班安排、最低工資標準等方面進行了規定,值得注意的是,勞動法規定工資的支付方式為貨幣支付,采取月薪制,而東盟各國大多采取的是日薪制或周薪制。
總體來說,中國和東盟就就業條件方面的法律規定并無較大差異和沖突,主要體現出以下幾個共同點:第一,對工作時間進行了詳細的規范;第二,都賦予了勞動者休息的權利,但東盟這方面的規定比較細致,還包括了勞動者每天連續工作的時限以及就餐的時間等;第三,對要求勞動者加班的行為也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對加班的時間中國采用的是法定上限,而越南規定雇傭者和勞動者可以約定時間;第四,都普遍制定了最低工資以及加班工資等關系勞動者工作待遇的規定。
對于中國和東盟國家在就業條件上的若干差異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東盟國家國土面積和人口較少,因此能對一些勞動者細致的要求進行滿足,所以東盟關于就業條件方面的立法相對于中國顯得詳細而富有人文色彩。但是由于中國國土面積寬廣,人口眾多,不能一一考慮全國各地勞動者對于氣候、風俗、信仰而產生的就業條件的訴求,在全國性的勞動法中充分體現各地差異明顯是不現實的。這需要中國國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對本地區的勞動者就業條件相關規定進行細化和變通,而且由于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在中國的勞動法里特別強調了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的原則。
3.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于就業平等與反歧視方面的法律比較
新加坡對于就業平等與反歧視的勞動法律主要集中在對女性雇員的特殊保護上,特別是制定了詳盡的婦女產假期的休假和工作報酬的規定,例如規定分娩前4周加分娩后8周或者從分娩前28天且不遲于分娩日12周內為產休假,而且在一定條件下經雇傭雙方同意可以延長,但女性雇員在分娩前受雇不足180天的,產假期內不享受報酬,以及其他的一些特殊保護制度。柬埔寨在其勞動法第12條原則性規定除了法律另有規定,任何雇主不得基于種族、膚色、性別、信條、宗教、政治觀點、出身、社會血統、工會會員身份或工會活動的因素作出雇傭、限定和分派工作、職業培訓、提拔、晉升、報酬、給予社會福利、處分或終止雇傭合同的決定,否則這個決定可以撤銷。其他東盟國家的憲法、勞動法在這方面的規定也是大同小異。中國的《勞動法》在就業平等和反歧視方面主要有以下的規定:(1)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2)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在錄用職工時,除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3)殘疾人、少數民族人員、退出現役的軍人的就業有特殊規定;(4)除了對婦女的生理特征進行特殊保護外,我國還禁止婦女從事一些較重較危險的工種作業[8]。
綜上所述,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就業平等和反歧視方面的法律差異主要有以下特點:第一,對婦女保護力度不同,中國勞動法律體系對婦女勞動權益保護更為全面和重視,這主要是婦女在中國和東盟國家中社會地位差異所決定的;第二,東盟國家中存在大量的民族沖突,宗教沖突和宗教內部的教派沖突,而中國這方面問題并不嚴重,因此東盟國家多數采取高壓的法律和政策,而中國則采用溫和的扶持少數民族的法律和政策;第三,一些東盟國家的就業平等和反歧視法律會以家庭或者血統為對象,而中國則僅僅對勞動者個人進行保護,這是由于東盟國家大量家庭作坊和手工業作坊存在而導致的。
4.東盟國家的學徒工保護法律制度
由于東盟國家存在著大量的家庭作坊和手工業作坊式的企業,因此東盟國家的勞動法中一般都直接或間接設立了學徒工合同的內容,甚至獨立成章,由此可見學徒工這一個特殊雇傭關系在東盟國家中是有歷史延續和現實必要性的。
越南的學徒工制度在其勞動法內稱之為勞動授藝制度,帶有職業培訓的色彩,要求授藝機構要依法登記、納稅并允許其收取學費。越南的授藝制度主要面對13歲以上的學藝者,必須具有合格的健康條件,但是勞動傷兵社會部規定的部分高危職業不允許招收學藝者,向傷兵、病兵、殘疾人、少數民族或在有許多人缺少就業機會、失業的地方設立授藝機構和工廠及家庭形式的傳統授藝機構可享受稅收的優惠。營業者有義務使學藝者提高技術水平,提供培訓,在授藝和培訓期間安排學藝者進行工作的,無須登記但不得收取學費,學藝時間計入工齡;學藝期間參加生產活動的學藝者可以與營業者協商獲取報酬。營業者系為了使用而招收學藝者的,在學藝合同中應約定學藝者在學藝期間按營業時間進行工作,營業者保證學藝者學藝完成后簽訂勞動合同。
菲律賓的特殊工人分類除了學徒工還有實習生制度,兩者的區別在于:(1)學徒工必須年滿14周歲以上,而實習生則必須年滿15周歲;(2)學徒工合同期限為3個月到6個月,而實習生為3個月之內;(3)學徒工必須具備基礎的職業理解能力,對實習生并無具體規定。學徒工和實習生均可以在雇主處享受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費用包括在學徒工和實習生的補貼當中,學徒工和實習生的工資不得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75%。
而柬埔寨勞動法中的學徒合同也具有其獨特的特點:第一,其締約雙方均要求為個人,即“師傅”和“徒弟”;第二,學徒合同必須在締約后2周進行公證,否則合同不受保護;第三,沒有設立學徒的最低年齡限制,但設定了最高年齡限制,必須為21歲以下,在受藝工作領域內沒有2年以上工作經歷;第四,學徒合同最多只能訂立2年的授藝培訓期限;第五,師傅和培訓主管不得與未成年女性學徒同居一室;第六,設立了師傅和培訓主管禁止從業的條件;第七,規定如雇傭60個工人以上的企業或個人雇傭的學徒不得超過總雇傭人數的十分之一。
學徒工制度具有以下的特點:第一,面對的對象都是未成年工人,甚至是兒童;第二,授藝的個人和機構提供的服務都屬于培訓性質,但帶有傳統的手藝傳承的色彩;第三,學徒工享有的權利均比普通工人低,就業條件和勞動待遇都比較低;第五,都具有法定的期限,但各國對于期限的設置差異較大。因此筆者認為東盟國家的學徒工制度只應存在于手工業領域,對于需求大量熟練工的中國企業不應使用學徒工制度。一方面可以保持中國企業的國際形象,避免在勞工標準問題上遭遇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另一方面也確保企業的有序運行,規避使用童工的風險,避免因為生產安全事故而造成經濟損失和社會責任的缺失。
從SA8000來反觀中國及東盟國家的勞工標準立法,無疑中國和東盟國家國內法確立并可以實現的勞工標準和勞動待遇都較SA8000的要求低。通過用SA8000的童工、強迫勞動、生產安全與健康、反歧視、工作時間和工資這幾個方面的核心勞工標準的要求與東盟和中國現有法律法規進行比較,不難發現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核心勞工標準與SA8000存在著以下的差距:第一,東盟國家的勞動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不反對、甚至支持使用童工,較為典型的是柬埔寨的勞動法律,而這方面中國做得比較完善;第二,東盟國家存在學徒工和家庭工等類似契約勞動的強迫勞動形式,而中國一些企業則采取扣押身份證和押金等方式強迫勞工勞動,這都是不符合反強迫勞動的要求的;第三,東盟國家和中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不注重生產安全和健康,職業病和職工公害病的比例較高,很少有企業制定了完善的安全與健康培訓及制度;第四,東盟國家對于勞動信仰的尊重比較重視,但是對于婦女勞動者的歧視則比較嚴重,而中國沒有詳細的條文去保護勞動者的信仰和風俗,僅僅是原則上加以肯定。這些都是中國及東盟國家在核心勞工標準上不能滿足SA8000的主要方面,仍需通過經濟發展、法律和社會制度的完善來逐步改善。
通過審視中國及東盟國家所謂的廉價勞動力優勢,不難發現以下幾個共同點:生活福利低下,生產條件低下,生產環境惡劣,勞資雙方地位差距過大。因而中國在勞工權利保護方面被許多發達國家的公民、組織甚至政府所攻擊,已成為中國對外貿易和海外投資發展的雙刃劍。雖然中國國內的勞動者已經從國民經濟的增長中受益,但是另一方面不可忽視的是中國勞動待遇和勞工權利的發展速度遠遠落后于經濟增長速度,勞工標準問題和勞工權利貿易壁壘的出現使中國以勞工為代價打造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時代提前結束。而作為整體勞工待遇低下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以及勞工待遇問題遠遠比中國更為嚴重的東盟國家來說,勞工權利保護以及勞工標準提高問題將成為區域性、綜合性的難題。
三、中國與東盟國家在核心勞工標準問題上的挑戰和對策
隨著中國及東盟國家等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發達國家市場以及國際市場中競爭力的增強,沖擊了發達國家的同類產品在國內外市場的地位,同時發展中國家通過豐富廉價的勞動力還吸引了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與資金,一些發達國家認為這是導致其國內失業加重的主要原因。在此客觀背景下,發達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出口在較低勞工標準下生產的產品是一種傾銷行為,要求制定國際上統一的勞工標準,把勞工標準問題納入國際投資和貿易秩序中。西方發達國家企圖將國際投資貿易與勞工標準掛鉤的行為,其本質和實際目的是利用發展中國家現存的較低的勞工標準以及短期內無法在保證發展的情況下提高勞工標準的現實,以貿易制裁為手段,抑制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盟國家在世界貿易中的優勢,是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樹立的“藍色貿易壁壘”。
由此可見中國及東盟國家相對較為低下的勞工標準及勞動待遇以及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勞工標準上的差異將導致以下危機:第一,這將影響中國及東盟國家企業對外貿易,中國及東盟國家的出口國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而倡導并施行SA8000為代表的國際勞工標準的國家也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這造成了中國及東盟國家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障礙,影響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于世界市場的開拓,甚至即將影響中國及東盟國家企業已占有的國際市場份額;第二,較為低下的勞工標準及勞動待遇將影響中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安全。鑒于中國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的經濟地位,中國成為資本輸出國,對東盟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將成為中國出口型企業開括新的贏利空間的必然選擇,其中大部分的投資企業也是從事對發達國家的出口貿易業務。而發達國家更為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國際勞工標準也成為很多國家公民接受的企業行為準則,出口企業必須贏得市場地民眾認同成為了企業和產品在國際市場立足和發展的重要條件;第三,東盟國家較中國更低下的勞工標準,將導致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外移,短時間內造成經濟和就業上的緊張局面,雖然這樣的產業轉移是一種良性轉移,從長久來說是有益的,但是就業崗位流失過快會引發一定的社會矛盾;第四,中國的對外出口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到東盟國家之后,如果適用東盟國家低下的勞工標準,消費者無疑會更加質疑這些產品中包含勞動者待遇因素,從而引發藍色貿易壁壘,影響中國對外貿易的安全以及對外投資的收益。
因此,中國在加入并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大環境下,在對東盟國家進行投資活動的同時,應從下幾點來應對國際勞工標準帶來的挑戰。
1.增強與東盟國家的交流與合作,在不斷提高自身國內的勞工標準的同時,與東盟國家合作制定綜合性方案和階段性對策,允許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采取分階段的逐步提高,達到自由貿易區內部勞工標準的統一,促進自由貿易區勞工標準與國際勞工標準的接軌。
2.中國應利用世貿組織成員國身份積極參與世貿組織就勞工標準等問題的談判,使中國、東盟各國甚至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利益體現在國際投資貿易秩序當中。
3.加快中國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國內產業更新。在國際投資中應注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對外轉移以及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引進,擺脫在低檔勞動密集產品出口上與東盟國家的內部競爭,避免貿易摩擦,從自由貿易區內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
4.雖然美國和一些歐盟國家強行推行SA8000有著保護勞工權益以外的經濟和政治目的,并據此設置了一些貿易壁壘,但是毫無疑問SA8000正逐漸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一些著名的國際企業如沃爾瑪、麥當勞、肯德基、雅芳等紛紛加入這一認證,并表示會優先考慮通過這一認證的供貨商,對其全球范圍內的分銷商、分包商等也提出了符合SA8000的要求。這些企業在中國和東盟國家擁有大量的投資,中國在東盟國家投資的企業也與這些企業有著密切的貿易關系,因而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制定一些政策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積極進行SA8000的認證,有利于提高自由貿易區的整體競爭力。同時,SA8000其作為一套民間組織制定的勞工標準,對各國企業不會產生強制約束力,企業接受其標準并申請認證完全是出自自愿,其次SA8000不存在時間表的問題,這為中國及東盟國家的企業提供了充分的調整余地。而政府在面對SA8000成本高昂、削弱了中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的現實中,可以給予一定的財政和稅收激勵政策,因為企業在勞工標準上與國際接軌不僅僅企業獲益,而且可以改善政府的貿易政策和整體形象,也可以保障和提高勞工權利。另外中國和東盟可以嘗試通過民間勞工組織交流的方式,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推行適合中國和東盟國家統一的勞工標準,用市場手段來促進中國本地企業和海外投資企業提高勞工標準和勞動待遇。
參考文獻:
[1]國際勞工局理事會第292屆會議紀要[R].2005(GB292).
[2]佘云霞.自由貿易與勞工標準問題[J].廣東社會科學,2009 (1).
[3]Friedman.M,The SocialResponsibility ofBusiness is to In crease its Profits[N].The New York Times,1970-09-13.
[4]米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經濟貿易法律指南[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318.
[5]蔡磊.新加坡共和國經濟貿易法律指南[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367.
[6]陳云東.菲律賓共和國經濟貿易法律指南[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134.
D912.5
A
1673-8535(2013)04-0061-07
植文斌(1986-),男,廣西容縣人,梧州學院法律與公共管理學院教師,法學碩士,研究方向:法學理論。
蔡菲菲(1980-),女,廣東揭陽人,梧州學院法律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經濟法。
(責任編輯:高堅)
2013-06-06
廣西高等學校科研一般項目(200103YB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