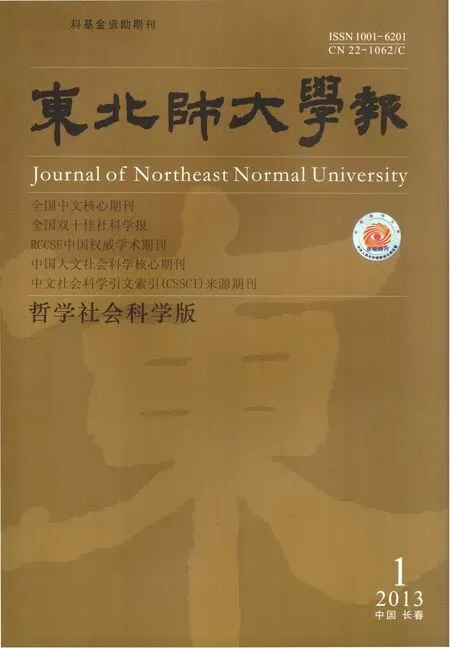精神生活的形上情結(jié)
楊淑靜,丁惠平
(1.東北師范大學(xué)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吉林 長春 130024;2.江蘇省社會科學(xué)院 《江海學(xué)刊》雜志社,江蘇 南京 210000)
精神生活是人內(nèi)在的精神訴求,或者說是人自身具有的堅(jiān)固的形而上學(xué)情結(jié)。正是精神生活的形上情結(jié)才使人的精神生活不斷獲得愈益明確、愈益清晰的理論意識,這種自覺的理論意識直指現(xiàn)時(shí)代精神生活的物化現(xiàn)狀。精神生活的物化不僅嚴(yán)重銷蝕了精神生活本應(yīng)具有的自覺意識,同時(shí)對精神生活內(nèi)蘊(yùn)的形上訴求也造成了嚴(yán)重的威脅,因此,必須在精神生活獲得自覺意識的同時(shí)進(jìn)行精神生活的物化批判,這既是葆有精神生活形上訴求的理論努力,同時(shí)也是精神生活形上情結(jié)的內(nèi)在理論張力。
一、精神生活的理論自覺
現(xiàn)時(shí)代,精神生活的典型特征就是韋伯意義上的“祛魅”,即精神生活的祛魅化、世俗化,“宗教發(fā)展中的這種偉大歷史過程——把魔力從世界中排除出去……使世界理性化,摒除作為達(dá)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1],對于此種精神生活現(xiàn)狀,馬克思也做過相關(guān)論述,“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2]275隨著啟蒙以理性取代宗教和神話,世界本身去神秘化了,現(xiàn)實(shí)已撕去了被神話和宗教包裹的溫情脈脈的面紗,人們已經(jīng)能夠按照事物的實(shí)際情況理性地看待事物本身了,而對事物本身的認(rèn)識就是精神生活不斷自我澄明的理論表征。
現(xiàn)代社會的典型特征是祛魅化、世俗化,而祛魅化和世俗化的時(shí)代就是人類精神覺醒的時(shí)代。以往的時(shí)代,是宗教統(tǒng)治的時(shí)代。在宗教的統(tǒng)治下,人類喪失了自己,或者還沒有獲得自己,人類的精神生活還處于蒙昧狀態(tài)。宗教時(shí)代的精神生活是依其所是的樣子被接受的,生活與認(rèn)識的統(tǒng)一是不證自明的,“對此,我們已不再感到奇怪,因?yàn)槲覀兞私獾剑覀冞^去的同類是在現(xiàn)實(shí)宛如被蒙上面紗的條件下生活的。”[3]1-2隨著路德宗教改革的推進(jìn),徹底反宗教的斗爭開始了,宗教斗爭使人們認(rèn)識到了宗教的本質(zhì),人們已經(jīng)能徹底地撕碎宗教鏈條上那些虛構(gòu)的花朵,而反宗教斗爭最強(qiáng)烈的莫過于啟蒙運(yùn)動(dòng),啟蒙運(yùn)動(dòng)破除了宗教、神話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打破了宗教神學(xué)的絕對權(quán)威,人作為理性的人不斷崛起。啟蒙作為理性的倡導(dǎo)者成了現(xiàn)代性的發(fā)源地,理性是現(xiàn)時(shí)代的時(shí)代特征,理性的人徹底擺脫了宗教的幻想,使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了,人從天國回到了人間,找到了人的真實(shí)本質(zhì),找到本質(zhì)的人能夠圍繞著自身和自己的太陽旋轉(zhuǎn)。“今天,那種想要認(rèn)識一切的驕傲以及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人、從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的妄自尊大,叩響了所有的大門。”[3]3回到現(xiàn)實(shí)的人能理性地面對此岸世界的真理,人不再迷茫了。現(xiàn)時(shí)代的人類,由于啟蒙運(yùn)動(dòng)對人的理性和主體性的張揚(yáng),已經(jīng)獲得了清晰明確的時(shí)代意識,人們已經(jīng)能自覺地反思精神生活問題了,就像黑格爾在《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中講到的那樣“我們不難看到,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是一個(gè)新時(shí)期的降生和過渡的時(shí)代。人的精神已經(jīng)跟他舊日的生活與觀念世界決裂,正使舊日的一切葬入于過去而著手進(jìn)行他的自我改造”[4]。以往的時(shí)代,生活本身是被遮蔽的,因此,現(xiàn)時(shí)代就要不斷地使人的生活解蔽、并不斷的自我澄明。
人類精神生活的理論自覺是精神生活形上性的內(nèi)在理論要求。正是因?yàn)槿祟愑袑γ篮蒙畹南蛲匀祟惒挪粩嗟胤此甲约旱木裆睢W韵掌穑F(xiàn)代的頭腦已經(jīng)意識到,關(guān)于世界中有神存在的觀念已經(jīng)喪失,人們已經(jīng)開始不斷地尋求自己精神生活的內(nèi)在理論訴求。克爾凱郭爾和尼采認(rèn)為西方社會被引向了絕對的虛無主義,但是,對他們來說,這個(gè)世界作為總體仍是一種精神化了的存在。“領(lǐng)悟一種狀況是導(dǎo)向支配該狀況的第一步,因?yàn)椋瑢徱曀屠斫馑麊酒鹆烁淖兯拇嬖诘囊庵尽坏┏蔀檫@種狀況中的一個(gè)主動(dòng)參與者,那我就自然地想要干預(yù)這種狀況與我自身生存之間的相互作用。”[3]20也就是說,我們一邊在生活,一邊在看我們對生活的意識,我們思索這個(gè)世界應(yīng)該怎樣理解,我們懷疑每一種解釋的正確性,在每一個(gè)生活與對生活的意識表面一致的地方,背后都隱藏著真實(shí)的世界與我們所知的世界之間的區(qū)別,“人是精神,人之作為人的狀況乃是一種精神狀況”[3]3,這恰恰表征了精神生活形上訴求的內(nèi)在理論要求。黑格爾在艱深晦澀、抽象的哲學(xué)著作《小邏輯》中談到“世界精神太忙于現(xiàn)實(shí),太馳騖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內(nèi)心,轉(zhuǎn)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園中”[5]31,回歸家園就是回歸精神生活的內(nèi)在性,就是回歸精神生活的形上性,也就是人應(yīng)尊重人自己,并應(yīng)自視能配得上最高尚的東西。“對人而言,生命活動(dòng)的較高的開端必然始于人的精神生命,堅(jiān)定不移的信念信仰、人文化成的道德倫理、不懈追求的價(jià)值理想、正義感與生命激情的內(nèi)心涌動(dòng),才能使人以高尚的開端創(chuàng)造真正屬于人的生活”[6]。我國當(dāng)代著名哲學(xué)家馮友蘭先生也有言“哲學(xué)是使人作為人能夠成為人”,成為“大寫意義上的人”,而“大寫意義上的人”就是不斷追求并踐行崇高的人,也即成為堅(jiān)守精神生活內(nèi)在訴求的人。
二、精神生活的物化批判
人類獲得了精神生活的自主性,但與此同時(shí),這類驕傲與自高自大所遇到的挫折又引起了一種可怕的虛弱感,即人們的精神生活已經(jīng)不再具有一種超越的神圣價(jià)值(這種神圣價(jià)值或者是以上帝這樣的人格神、造物主、意志主宰的形態(tài)存在,或者以天命、天理、良知等形態(tài)出現(xiàn)),人要重新尋求自己精神生活的終極關(guān)懷、價(jià)值源頭和生活意義。尋求本身就是對精神生活現(xiàn)狀的反思和批判。
精神生活的現(xiàn)狀是:它被嚴(yán)重物化了。在世俗化時(shí)代,占主導(dǎo)地位的思維方式是物質(zhì)性思維方式,即工具理性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使市場的運(yùn)行邏輯成了人們?nèi)粘I畹倪\(yùn)行邏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談到由于工具理性的猖獗導(dǎo)致目的合理性領(lǐng)域和價(jià)值合理性領(lǐng)域的分裂,價(jià)值理性領(lǐng)域被目的合理性領(lǐng)域侵蝕了,造成了“持久算計(jì)的世界”以及“多神和無序的世界”。在目的合理性領(lǐng)域中,人們只需要服從社會的法律法規(guī)就可以了,但人的最終目的不是服從外在的約束,而是要尋求使自己崇高起來的意義和價(jià)值,事實(shí)領(lǐng)域在面對人自身的這一內(nèi)在要求時(shí)沉默了,這個(gè)艱巨的任務(wù)只能在“價(jià)值合理性領(lǐng)域”完成。所以,合乎邏輯的推論是:個(gè)人的價(jià)值追求必須訴諸于價(jià)值合理性行為領(lǐng)域。這必然會導(dǎo)致如下的結(jié)果:首先就是價(jià)值的多神化,或者說“終極價(jià)值的多元化”;第二就是價(jià)值的爭斗,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價(jià)值追求,都堅(jiān)持自己的價(jià)值信念,從而造成多元價(jià)值的相互沖突。韋伯所揭示的是精神生活物化的典型特征,即“如此被貶抑、被拉到物的水平上的人,已經(jīng)失去了人性的實(shí)質(zhì)”[3]42-43,但他只是提出了問題,并沒有在理論上解決此問題。哈貝馬斯明確了此問題,用他的表述就是:“系統(tǒng)侵蝕生活世界,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即物化時(shí)代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的性質(zhì),它只能滿足個(gè)人的欲望和現(xiàn)實(shí)利益的實(shí)現(xiàn),無法滿足人們精神生活終極關(guān)懷的價(jià)值訴求,它根本就不能代替?zhèn)鹘y(tǒng)社會的道德和宗教,就像許紀(jì)霖先生說的那樣,“在中國社會,一個(gè)很有趣的現(xiàn)象便說明了這樣的一個(gè)問題:‘越是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生活富裕的地區(qū),廟里的香火越是旺盛,各種祭祀活動(dòng)和宗教儀式越是隆重。當(dāng)神圣性從人們門前被驅(qū)逐出來之后,又從后門溜回來了’”[7]8,精神生活嚴(yán)重物化了。馬克思說“資產(chǎn)階級在他已經(jīng)取得了統(tǒng)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guān)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cái)財(cái)嗔税讶藗兪`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他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guān)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xiàn)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lián)系了。”[2]274西美爾在《大都市與精神生活》中也提到了同樣的觀點(diǎn),“金錢只關(guān)心為一切所共有的東西,那就是交換價(jià)值,它把所有性質(zhì)和個(gè)性化都化約在一個(gè)純粹的數(shù)量層面”,“知性關(guān)系把人當(dāng)作數(shù)字來處理”,“正是貨幣經(jīng)濟(jì)使得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都充滿可權(quán)衡、算計(jì)、清點(diǎn),以及把質(zhì)的價(jià)值化約為量的價(jià)值”。不論是韋伯、馬克思、西美爾、哈貝馬斯,亦或是許紀(jì)霖,進(jìn)行的都是自覺意義上的精神生活物化的現(xiàn)狀反思。
精神生活的物化批判,根源于人類自我意識的不平靜,這種不平靜在黑格爾的哲學(xué)中變得清晰起來。黑格爾通過自我意識的自否定,確定了絕對理念的辨證法,“當(dāng)精神一走上思想的道路,不陷入虛浮,而能保持著追求真理的意志和勇氣時(shí),它可以立即發(fā)現(xiàn),只有[正確]方法才能夠規(guī)范思想,指導(dǎo)思想去把握實(shí)質(zhì),并保持于實(shí)質(zhì)中。這樣的進(jìn)展過程表明其自身不是為了別的,而是要恢復(fù)絕對的內(nèi)容,我們的思想最初向外離開并超出這內(nèi)容,正是為了恢復(fù)精神最特有的最自由的素質(zhì)”[5]5。絕對理念的辯證法使一切不合理的因素都消化在自身的理論體系內(nèi),也即“心靈深入于這些內(nèi)容,借他們而得到教訓(xùn),增進(jìn)力量”[5]5。正是自我意識的不平靜,人才能在精神生活形上性內(nèi)在的辯證張力中,對精神生活的物化現(xiàn)狀進(jìn)行批判,而這種批判本身同時(shí)也是對形上性的一種內(nèi)在葆有。只有自我意識的辯證法才能拯救精神的形上性,蔑視辯證法,必然會陷入形而上學(xué)的深淵(恩格斯語)。
精神生活的理論自覺促進(jìn)了人們對精神生活物化現(xiàn)狀的批判,對精神生活的物化批判也是精神生活形上性的內(nèi)在理論張力,歌德寫到“人類將變得更加聰明,更加機(jī)靈,但是并不變得更好……”這就表達(dá)了精神生活內(nèi)在的理論要求,“聰明”和“機(jī)靈”意味著精神生活獲得了理論自覺,而“不好”表達(dá)的則是精神生活物化的現(xiàn)狀。理論自覺是形而上學(xué)的內(nèi)在理論要求,而批判則是精神生活形上性的內(nèi)在理論張力。人們之所以有這種批判意識,是由于人們認(rèn)為自己應(yīng)為這種現(xiàn)狀負(fù)責(zé),因?yàn)樗梢员挥心康牡丶右愿淖儯梢灾匦滤茉斓酶咏谌诵牡脑竿藘?nèi)心的愿望就是精神生活形上性最直接的表達(dá)。
三、精神生活的形上訴求
人類獲得了精神生活的理論自覺,這是精神生活形上訴求的內(nèi)在理論動(dòng)力,正是這種理論自覺,使人們能夠揭開現(xiàn)實(shí)的面紗,意識到精神生活物化的現(xiàn)狀。精神生活的形上性不僅具有揭示精神生活物化現(xiàn)狀的理論要求,同時(shí)還具有批判精神生活物化的內(nèi)在理論張力。這就是精神生活的形上情結(jié)。
世俗化時(shí)代的典型特征是精神生活的物化,但精神生活的物化不能證明沒有文化和精神生活,而是文化和精神生活發(fā)生了世俗化轉(zhuǎn)向,這就是精神生活形上性的辯證法。現(xiàn)代文化(在本文中,筆者是在一個(gè)意義上運(yùn)用“精神生活”和“文化”兩個(gè)詞的)的典型特征是:大眾文化、流行文化、平民文化替代精英文化,即現(xiàn)時(shí)代是一個(gè)英雄主義隱退的時(shí)代,是一個(gè)大眾造星的時(shí)代,芙蓉姐姐、鳳姐和網(wǎng)絡(luò)明星,證明了精英文化的隱退,“超女”、“快男”作為文化事件,是文化平民主義誕生的精神宣言。精英文化是智性的、啟蒙的,訴諸于人們的理性和想像,而世俗文化則是反智性的、反啟蒙的,它直接訴諸于人們的感官和直覺[7]26。造星運(yùn)動(dòng),大眾文化、平民文化一方面證實(shí)了精神生活物化的現(xiàn)狀,但同時(shí)也揭示了人們的精神生活獲得了自主性和獨(dú)立性,人們獲得了精神生活的自覺意識,這也符合恩格斯所說的“歷史總是以退步的形式實(shí)現(xiàn)進(jìn)步”、“片面性才是歷史的真正原則”。有的學(xué)者說我們已經(jīng)進(jìn)入了“心時(shí)代”,“心時(shí)代”昭示了精神生活的新樣式,用流行的話語來說就是“看電影比吃飯重要”、“請人吃飯不如請人出汗”、“意思比意義更重要”等等。“看電影”、“出汗”、“意思”是精神生活的內(nèi)在要求,是精神生活形上訴求的理論表征。
以物欲為標(biāo)志的時(shí)代,若無人類精神生活的形上訴求,將會是時(shí)代最悲壯的情景[8]。在80年代,個(gè)人的獨(dú)立曾是人人羨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它卻成了個(gè)人不堪忍受的巨大壓力。城市里的人徹底原子化了,《大話西游》以“活在當(dāng)下和現(xiàn)在”為核心內(nèi)容塑造了現(xiàn)時(shí)代人類精神生活樣式的經(jīng)典傳奇,在這個(gè)意義上來說,郭德綱和周立波都是“無厘頭”、“大話時(shí)代”的弟子。就像趙本山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shí)候講的那樣,“現(xiàn)時(shí)代,只要快樂就行,我就能把快樂帶給你們”,快樂就是人類內(nèi)在的精神追求,是物化時(shí)代精神生活最狂放的吼叫。快樂是精神生活形上性最直接的表達(dá)。人類精神生活從一開始就尋求從內(nèi)部決定生活方式,而不是從外部接受一種普遍的、像圖表一樣中規(guī)中矩的生活方式。盡管由這些生機(jī)勃勃的沖動(dòng)所指引并賦予特征的生活在現(xiàn)時(shí)代并非絕無可能,但是他們還是在觀念上與之對立的。由此看來,我們就能解釋像羅斯金和尼采那樣的人物對于現(xiàn)時(shí)代的深切憎恨,這些人只能在非模式化的個(gè)人表現(xiàn)中找到生活價(jià)值,而這些表現(xiàn)無法化約為準(zhǔn)確的等價(jià)物,最后,他們只能走向絕對的相對,走向精神生活的虛無主義。康德所說的“歷史中的這樣一個(gè)現(xiàn)象永遠(yuǎn)不會被人遺忘,因?yàn)樗沂玖巳诵灾杏袀€(gè)美好的事物的萌芽以及達(dá)到這種事物的能力。而在此之前,沒有一個(gè)政治學(xué)學(xué)者曾經(jīng)從先前的歷史事件的過程中推論出這一點(diǎn)”。雅斯貝斯在《時(shí)代的精神狀況》中也發(fā)出了這樣的吶喊,他認(rèn)為即使是在“體育運(yùn)動(dòng)中,仍然包含著前進(jìn)升華的要素作為對僵化的現(xiàn)狀的抗議,這種要素雖然不是共有的目標(biāo),卻是無意識的愿望……人所達(dá)到的境界要超出他在生活秩序中所完成的,他要通過表現(xiàn)那指向整體的意志的國家來達(dá)到這種境界”[3]60,75。“無意識的愿望”和“生活秩序的境界”一方面表達(dá)了人類精神生活的理論自覺,另一方面也表達(dá)了精神生活的物化批判,而這既是精神生活形而上性的內(nèi)在理論要求,同時(shí)也是其內(nèi)在的理論張力。
黑格爾堅(jiān)守“人應(yīng)尊敬他自己,并應(yīng)自視能配得上最高尚的東西”,而最高尚的東西就是人的精神生活所希冀的東西,就是馮友蘭先生的“作為人成為人”,就是尼采的“高山之巔、冰雪之間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這本身就是對精神生活形上訴求的理論表征。精神生活具有內(nèi)在的堅(jiān)實(shí)的形而上學(xué)情結(jié),這是系在人類精神生活鏈條上一朵純潔無瑕的、永不凋謝的花朵。
[1][德]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7:79,89.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卡爾·雅斯貝斯.時(shí)代的精神狀況[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
[4][德]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上卷[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9:6-7.
[5][德]黑格爾.小邏輯[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0.
[6]胡海波.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生命精神[J].東北師大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8(3):10.
[7]許紀(jì)霖.世俗時(shí)代與超越精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8]涂良川.馬克思“感性活動(dòng)”的形上意蘊(yùn)[J].東北師大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1(6):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