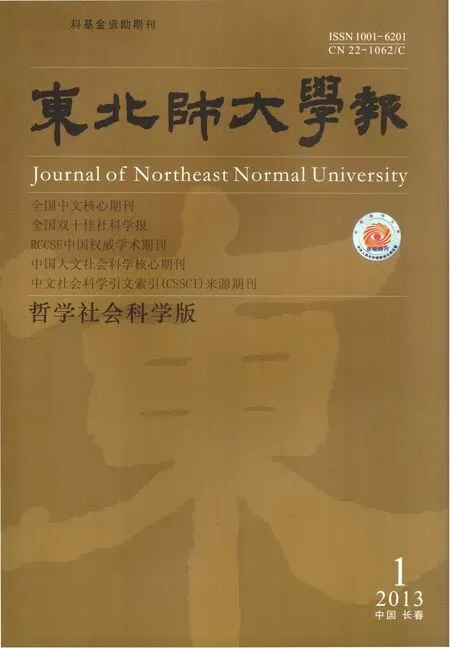試論中國傳統音樂教育的哲學基礎
鄧晴南
(1.西北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2.杭州師范大學 錢江學院 音樂舞蹈學院,浙江 杭州 310000)
中國傳統音樂教育是與中國傳統文化密切聯系、息息相關的,文化傳承的過程就是最廣義的教育過程,而教育同時又使文化得以延續而成為歷史,并成為每一代人進行新的文化創造的基點。音樂教育也是如此,它的哲學基礎和文化淵源歸根結底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正是傳統文化的滋養使得傳統音樂能延綿幾千年而不絕。
在討論傳統音樂教育哲學基礎的問題時,我們有必要對中國傳統音樂教育作一個時間段上的劃分,以近代西方音樂文化傳入,學校音樂教育出現為界,將傳統音樂教育分為古代音樂教育時期和近現代音樂教育時期,本文所作的探討主要圍繞古代音樂教育來展開[1]。
研究中國傳統音樂教育的哲學基礎,勢必要搞清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哲學基礎。如把儒、釋、道三家的“整體”觀作為中國傳統教育的哲學觀念基礎,那么潛藏于傳統樂教本體論思維中的“體用如一”則成為傳統音樂教育的哲學基礎。“體用如一”即“體用不二”,此處的“體”指本源、本體,世界之本質;所謂“用”,原指萬物,后兼指功能、現象、世界。體用的關系就是本體與現象、結構與功能、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區別[2]5。按照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本體與現象、道與器、主體與客體之間是既相區別又相互統一的,相對立卻又相互聯系,體是用之體,用又是體之用。“體用不二”的辯證思維影響并構成了中國傳統樂教的思維源泉,音樂教育從而被賦予了除音樂本體以外其他附加的功能與符號。在此基礎上,“文以載道”成為其樂教主要目的,兼以“禮樂并重”的音樂教育價值取向,“知行相即”的教育過程,“口傳心授”的教育形式,同時重“和諧”、“意象”的音樂審美心理,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音樂教育的哲學范疇。
一、“禮樂并重”的音樂教育價值取向
先秦儒家重視禮教,強調禮樂治國的作用。《孝敬·廣要道》有載:“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3]此話看似禮樂并重,其實是把“樂”作為實現“禮”的手段,而樂教本身并未獲得獨立價值。漢代文教政策兼采儒法,禮教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取得獨尊地位。東漢末年,禮教已不能滿足當時的社會需求,樂教漸漸發展起來,到了宋明新儒學時期,禮教與樂教重新統一起來,宋儒在禮教的基礎上統一了樂教,重新恢復先秦儒家禮樂并重的局面;明儒將禮教視為統一的基礎;到清代清儒提倡回到漢代,沿襲漢代舊制,禮教又重新占據主導地位[2]28-29。
通過歷史不難看出“樂”是出于“禮”的需要而生的,春秋著名樂師師曠提出“修禮以節之”,明確要求樂受禮的節制;伶州鳩強調做“樂”應“道之以中德”,以“中德”為引導和內涵,而“中德”即是要符合“禮”的規范。因此,在傳統教育中禮教的價值是“善”、“德”,即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德育,其本質功能是調和人際關系,規范行為準則,規定社會等級差別,從而維護社會穩定。而樂教則是今天所說的美育,音樂的本質功能在于感發心性、娛樂身心,強調個體個性的張揚、自我意識的覺醒,這樣禮教與樂教之間就不可避免的存在著先天的矛盾:前者壓制人性,后者則解放人性。
孔子強調“禮”,認為“禮修而形成”,禮樂能調和人性情,使人改惡為善,從而達到“移風易俗”的社會功效,正是清醒地意識到了情感在倫理、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對于“樂”的選擇,他強調“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思無邪”的“正聲”,以求培養符合封建社會倫理綱常、道德規范需要的讀書人。正如《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中趙衰所言:“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即是強調音樂與道德的關系,要求音樂受到一定的道德約束,從而符合“禮”的規范。
二、“文以載道”與音樂教育的目的
作為顯學的儒家思想,經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唐代古文家韓愈的發物道統,一直到明清歷代帝王對孔孟的優禮有加,始終是封建時代的統治思想。儒家關于文藝教育功能的理論,也就成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中的一個主體部分,并在宋儒的改造下,直接演變成“文以載道”的文藝觀和教育觀。
中國古代無論是官學還是民間私學,對于音樂功能的論述,基本上都是實用主義的,“文以載道”要求音樂服務于特定階級的政治目標和道德規范,從而達到社會的安定、和平。《禮記·樂記》有云:“致樂以制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者樂也”,儒家要求通過音樂使人愉快的屬性,把外在的道德標準轉化為內在的情緒狀態自然流露,使道德和情欲的沖突得以圓融消解,從而變成一種生命成長自身的要求[2]90。這種強調音樂“載道”作用的樂教,在教育目的上則表現為注重倫理道德的規范,追求音樂之外的“道”。《禮記·樂記》有云:“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指出音樂的思想內容是第一位的,而藝術形式則是第二位的,強調音樂對于德行情操的培養、人格塑造的重要意義,而認為只注重技藝、技巧的音樂無法達到較高水平,強調音樂之外移風易俗、教化的作用。
傳統音樂成為載道的工具,要求音樂服務于特定階層的政治目的和道德規范,固然是特定階層自身利益和規范需要在音樂教育上的具體反映,但這一教育目的作為一種傳統觀念,卻延續下來,長期扎根于人們的大腦。正是因為傳統樂教使音樂藝術過分依附于政治倫理,最終使得中國傳統音樂未能徹底獨立出來,走向專業和創新的道路。
三、“知行相即”的教育過程
“體用如一”的本體論思維反映在教育活動中則是“知行相即”的教育過程,“知”主要是知仁、悟道,即道德規范,發現自己的天德良知;“行”是人的道德踐履,是恪守道德規范并付諸于實踐的踐行。“知行相即”的目的是要受教育者在日常人倫生活中達到“道”的境域,而“道”本身卻又是形而上的,這就要求個人去“悟道”。
在音樂教育方面,則體現為教育方法中對音樂的“體悟”。中國傳統音樂傳承講究個人對音樂的“體知”和“悟知”。其中,“體知”是通過個人的實踐經驗和社會常識來做分析和推斷的學習過程。《荀子·樂論》有云:“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其中作樂者對于音樂規律與特征的把握則是來源于個人的學習實踐經驗以及前人所積累下來的對音樂旋律、結構、音色的選擇規律。《論語·雍也》提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即是孔子主張從個體體驗來理解他人,達到“推己及人”的目的。
“悟知”是一種通過個人冥想和沉思而達到的直覺“神悟”,這種冥想和沉思是建立在個人經驗、認知基礎上的,是一種含蓄、直悟與暗示的多層次含義結構。正如胡偉希先生所說:“中國思維方式不重視甚至排斥邏輯的推理,而強調直觀、直覺和頓悟,但它并不摒絕思慮,更不否認經驗本身;相反,它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長期的苦思冥想后,由于潛意識中多種心智功能的調動和激發,對要解決的問題的突然領悟。”[4]
抽象的“體悟”過程,反映在音樂教學中,則是善于采用象征的方法來隱喻深層內涵,在教學中善于通過比喻的方法,舉一反三,通過某事某物去暗示和借指其他意思。《禮記·樂記》中所說的“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即是通過音樂的旋律音調來反映、隱喻社會政治風氣,體察國情。孔子認識到音樂的移情作用,善于借助音樂這一功能達到移風易俗、感化人心的作用,《禮記·樂記》有云:“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即是看到了音樂對于人心的感化作用。
對于音樂的“體悟”過程,傳統樂教更多的強調個人的思考與自修,這需要學習者花大量時間冥想和沉思,實現自我修煉,達到“悟道”的境界。蔡邕《琴操》中記載伯牙向成連學琴三載,成連對他說:“我只能教你彈奏琴曲,如需進一步把感情貫注于音樂中,還需向我的老師方子春請教。”于是把伯牙帶到了蓬萊島。伯牙一人留守孤島,只聽到風聲和波濤之聲,之后恍然大悟,原來老師正是在讓我尋找移情之感,于是援琴彈起《水仙操》。該典故是傳統音樂教育中“點化”式教育的一個范例,它充分體現出傳統音樂傳承中,教師在傳道授業時,多是點到而不點破,擅長運用移情、隱喻等方法,幫助學習者由量的體感進而達到質的頓悟,從而達到“點化”的教育功效[5]。
四、“口傳心授”的音樂教育形式
“知行相即”的教育過程,注重體悟、自修的教育方法,使得傳統音樂教育多是“口傳心授”式的師徒口耳相傳,講究在實踐中傳授、校正、點撥學習者。如中國傳統戲曲藝術,基本是以師父帶徒弟的形式傳習,期間徒弟需拜于師父門下,從旁聽、打下手開始,逐漸由師父領入行。師父將自己幾十年的經驗、體會交給學生,一字一腔、一顰一笑、一招一式,在師父舉手投足、潛移默化中學生“茅塞頓開”。
由于隱藏于“知行相即”之中深層的“體用如一”的思維定勢,使得這種師徒相傳的方式便帶上了一層神秘感和藝術性,而不具備可量化的標準和清晰的邏輯。如距今有三千多年歷史的古琴,擁有自己固定的受眾和階層,傳承往往采用口傳心授式,千年來積累了豐富的琴論、琴史、琴曲,然而歷代琴人在傳譜時,卻多半不完全按照琴譜所寫教習,原因有三:首先,古琴譜多為簡字譜,這是一種古老的音位譜,每個譜字代表一個指位和指法,譜子沒有規定節奏和節拍,曲子旋律的強弱輕重也無標注,一些增強樂曲韻味的細微指法如“吟、揉、綽、注”也未能詳細說明指法上的細節。其次,受到簡字譜模糊性的影響,加之中國傳統樂教中重個人“體悟”、教師“點化”的思維方式,使得琴人往往拿到譜后,根據個人實踐經驗與體悟進行打譜,這也就出現了同一曲名的琴曲,旋律指法卻大相徑庭,不同琴派各有傳譜,而不同琴家所彈奏又各不相同。再次,中國傳統音樂審美重意韻、內涵,輕技藝的走向,使得琴譜、技藝、指法不再成為古琴學習、演奏中最重要的部分,而超脫于琴器琴技之外的“道”、“情”、“意”則成為琴人追求的終極目標,正如陶淵明詩句中所言:“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流傳于中國各地區的民族民間音樂,由于缺少譜本和唱本,使其傳承大部分依靠各地區音樂、儀式活動,本地區老藝人及長者的口傳心授。如今仍流傳于西北地區的山歌“花兒”,其傳唱只能在山野間、花兒會上進行,這就使得“花兒”的傳承主要依靠歌手在日常生活勞動和花兒會上通過多聽多看、耳濡目染而習得;此外,家中、同村擅長演唱花兒的長輩也是花兒傳承的主體,通過長輩的口耳相傳,晚輩從長輩那里習得“花兒”音樂與地方傳統文化。
五、倡“和諧”、重“意象”的音樂審美取向
“體用如一”的思維定勢在音樂審美方面表現為“道器合一”的審美取向,中庸、和諧之美成為傳統音樂審美之維。中國文化中的儒、釋、道都強調“和”的作用,孔子追求中正平和、“盡善盡美”的樂,老子則強調“音聲相和”、“大音希聲”,禪師們主張“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和”的理解與闡釋。
對于音樂“庸和”之美的論述,從上古時期的史伯到晏嬰、伶州鳩均認為音樂之美在于“和”,在于以眾多相異事物相輔相成,對立因素相反相濟,而達到“和樂如一”的理想。《國語·鄭語》記載周太史伯在回答鄭桓公的一段話中提到了自己對音樂持有的“和同”觀,他說:“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故王者居九垓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指的便是音樂之美不在于“同”而在于“和”,不在于“一”而在于“繁”,在于寓雜為一。孔子主張音樂“思無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中聲以為節”,要求音樂的內容與形式都是中庸而平和的,旋律需平和恬靜、溫柔醇厚,在音樂教育中音樂的情與聲、形式與內容需有所節制,符合其“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的要求,音樂學習者需抑制自己的自由情感,以禮抑情、克己復禮,從而獲得中正平和、符合禮樂規范的“中聲”。
“體用如一”的思維定勢在審美取向上還表現為對音樂“意象”的追求。“意象”是“意”與“象”的統一,即是“情”與“景”的有機融合,是寓“意”之“象”,就是用來寄托主觀情思的客觀物象。中國藝術審美注重音樂的“意境”,強調“藝”之“意”,由此升華為“道”的境界,對音樂技藝的超越在于從對“器”的掌握到對“道”的參悟。《周易·系辭》最早提出了“意象”的問題,提出“觀物取象”、“立象以盡意”之說,“象”成為求得“意”的必要手段。
傳統音樂在掌握技藝的基礎上,強調對樂曲韻味的把握,進而達到“入境”之感,希望通過“器”去尋找凝聚在“器”之外的“境”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主體的心境、情感等因素,從而達到“超以象外,得起環中”氣化圓融的審美之“境”。《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一》有云:“海讀書,能為文,士大夫多與之游,然獨以能琴知名。海之藝不在于聲,起意韻蕭然,得于聲外,此眾人所不及也。”對于“弦外之音”的追求充分體現出中國文人音樂注重“意象”,強調音韻之美的審美情趣,認為音樂需留給人無盡的遐想空間,使人品味“聲外”之余音遺響,留給人“味外之旨”,達到“深遠無窮之味”,從而達到物質與精神、生理與心理、現象與本質、形式與內含相統一的“象”外之“境”。
綜上所述,中國傳統音樂教育正是以“體用如一”的思維定勢為其哲學基礎,在此基礎上“文以載道”為其音樂教育目的,兼以“禮樂并重”的音樂教育價值取向,“知行相即”的教育過程,“口傳心授”的教育形式,同時強調音樂的“和諧”、“意象”之審美,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音樂教育的哲學。時至今日,傳統的道德文化觀念、思維定勢仍然深刻影響著中國當代的傳統音樂教育觀念和教育形式,討論傳統音樂教育的哲學基礎問題有助于幫助我們感悟和理解本民族傳統樂教文化的真諦,從而探究和尋找處理傳統音樂文化與當代音樂教育發展之間矛盾的有效途徑與方法。
[1]馬達.當代音樂教育哲學論稿[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0:83.
[2]丁鋼.文化的傳遞與嬗變:中國文化與教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3]蔡仲徳.中國音樂美學史[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54.
[4]胡偉希.意象理論與中國思維方式之變遷[A].斷裂與傳承[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71-272.
[5]王保國.邏輯學定位失范與通識教育轉向訴求[J].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