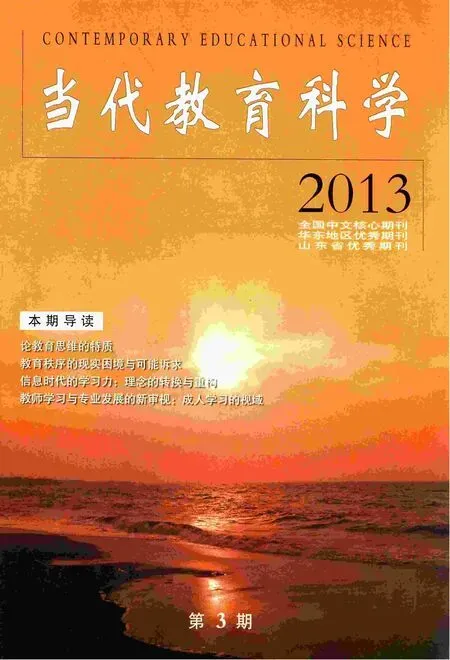教師學習與專業發展的新審視:成人學習的視域
● 蘇 紅
自20世紀20年代成人教育專業地位確立以來,成人如何學習就成為成人學習領域的核心研究問題,可惜在教師教育領域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80多年來產生了許多成人學習理論,比如成人教育學、自我指導學習、質變學習、非正式和偶發學習、情境學習以及一些后現代學習理論,隨后,成人教育學和自我指導學習理論逐漸成為該領域中最重要的兩個部分,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實踐推動作用也比較明顯。
一、成人教育學家諾爾斯的探索
1968年,美國教育學家、“成人學習之父”諾爾斯(Knowles)將成人教育學定義為一門 “幫助成人學習的藝術和科學”[1],從而將成人教育從傳統教育學中分離出來,奠定了成人教育學的理論地位,影響了并繼續影響著后續成人教育學的研究,而成人教育學也成為成人學習理論的重要支柱之一。諾爾斯認為成人學習理論長久以來一直受到針對傳統學校教育的兒童教育學的影響,忽視了成人自身的特點。他深信成人教育學中關于成人學習者的假設不同于傳統教育學中關于兒童學習者的基本假設,認為成人學習者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成人學習者有獨立的自我概念并能指導自己的學習。“兒童和成人學習者最關鍵的差別,是我們在看待他們的自我概念時所持理論的差別”[2]。兒童教育學中學生的自我概念被視為依賴性人格,并被社會和教師不斷強化,學生學習的內容、方式、時間和學習結果的評價都由教師決定。隨著個體自主心理需求和能力的不斷發展,到了成人階段,人就會產生這樣一種強烈的心理需求,即希望他人把自己看成獨立自主的人;自己能夠管理自己并為自己的決策和行為承擔后果。當社會承認成人的獨立人格時,個體才能夠擁有自主意識。正常發展成熟的成人都具有較強的自我概念,非常在意自己自我指導的人格和能力,因此,通常會不滿和抵制強加給他們的意志、觀念和行為。但是,成人學習者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常常表現出依賴性人格,被動地接受教師傳授知識。諾爾斯認為要加強成人學習者自主學習的觀念,提供自主學習的技能和學習的榜樣,讓他們體驗到成功的喜悅,更加自信、積極地投入學習,取得更好的成績。
第二,成人學習者像蓄水池一樣積累了很多生活經驗,這些經驗是豐富的學習資源。兒童由于自身經驗不多,因此更主要的是學習間接經驗。而成人學習者擁有兒童在質和量上都無法比擬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對成人的學習具有影響,表現在:一是主動地從經驗中學習比被動地從書本中學習的東西對成人更有意義,而且經驗可以成為自己和他人豐富的學習資源;二是由于成人在教育背景、生活經歷、個性、興趣愛好等方面的差異比兒童大得多,成人的經驗也是多樣化和個人化的,因此每個成人的學習也應該力求個性化;三是成人經驗和經歷是其自我身份的源泉。自我身份主要來自成人的經歷,當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經驗被貶低時,他們會認為這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進而對這種學習產生反感。因此,經驗作為成人學習的資源和身份的象征,在成人學習中具有重大意義。
第三,成人學習者的學習需求與變化著的社會角色緊密相關,具有現實需要性。兒童的學習需求是由他們所處的年齡階段決定的,他們傾向于學習那些他人告訴他們為了升入下一個年級應該且必須學習的內容。這種學習內容是根據課程標準制定的,大多數人都學習同樣的內容。但是,成人學習者不同。只有學習成為一種現實需要,他們需要更有效地完成某項任務或成功地解決某個問題時,他們才會準備學習。比如,當他們從一個發展階段進入另一個發展階段時,他們要承擔新的社會職責,面臨新的發展任務,也就產生了相應的學習需求。此外,像失業、生小孩、離婚、搬家等社會生活的變化都有可能激發成人學習的需求。
第四,成人學習者以問題為中心進行學習,并且對可以立即應用的知識感興趣。兒童以書本知識為中心進行學習,主要學習按照一定邏輯順序編織的規定教材上的書本知識,為未來的生活做準備。而成人學習以問題為中心,旨在進一步提高技能,充分發揮其生命潛能。成人不會為學習而學習,而是出于生活中的實際需要,比如為了完成一項新任務,解決一個新問題,或者是獲得一種更滿意的生活方式等。因此,圍繞提高成人解決問題的技能來組織學習,使他們所學的能夠用于解決他們工作、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才是關鍵。
第五,他們的學習興趣更主要的是來自內部而不是外部。兒童學習動機基本上來自外部,比如社會、家長、教師的要求或獎懲等。相對而言,成人學習動機體現出更多的外部性。雖然晉升、獎懲等外在因素能夠激勵或者迫使成人去學習,但是更強有力的動機來自內部,比如提高工作滿意度、維護自尊心、提高生活品質等。
二、自我指導學習理論的爭論
關于自我指導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SDL)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40年,但是直到1960年以后才逐漸成為一個主要的研究領域。然而,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期,該研究領域都是熱而不精,表現為“概念化程度不高、定義不明確、研究不充分、理解具有嘗試性”[3]。霍利(Houle)、諾爾斯等人做了先導性的奠基工作,后續的研究主要圍繞目的、過程和評價等展開。
霍利是該理論的奠基者。他采用訪談法,根據參與的原因把成人學習者分為三類:(1)目標導向者,主要是為了實現一些最終目標而學習;(2)活動導向者,他們為了交際和友誼而參加學習;(3)學習導向者,以學習本身為目的。這種分類方式對后續研究有很大影響。他的學生諾爾斯和塔福(Tough)等都是在其基礎上展開研究的。
諾爾斯在其專著《自我指導學習》中對自我指導學習作了概念界定,并談到如何通過學習契約來開展學習。諾爾斯將自我指導學習視為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依靠自己或者在他人的幫助下,主動診斷自身的學習需求,規劃學習目標,識別學習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資源,選擇和使用恰當的學習策略,并評價學習結果”[4]。他在其成人教育學的第一條假設中也提及到自我概念和自我指導的思想。
然而,塔福才是第一位對自我指導學習理論進行了系統研究的學者。他在其 《成人學習計劃》(The Adult’s Learning Projects)一書中把自我指導學習看作一種學習方式并做了全面的、詳細的闡釋,通過對66個加拿大人的自我學習計劃的研究和敘述,他認為學習普遍存在,是成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人學習具有系統性,但是不一定要依賴教師或教室[5]。該理論一經提出,就在成人學習研究領域產生了巨大影響,但是他們三人的研究還停留在基礎性、先導性的和經驗性的狀態,即使是塔福的研究也沒有真正揭示成人自我指導學習的過程。
在此基礎上,早期的研究者對自我指導學習研究多是描述性的,這些研究旨在證實自我指導學習在成人學習中的普遍存在性及其過程。關于揭示本質、建構模型、評價學習效果的研究直至今日仍都在進行之中。
梅里亞姆(Merriam)等把研究SDL的目的分為三種:第一種目的是發展學習者的自我指導能力,諾爾斯和塔福等人都是出自這一目的。布魯科特(Brokett)等也抱有同樣目的,他們建構了自我指導學習的個人責任導向模型,該模型的前提就是人類的本性基本上都是好的,成人能夠為自己的學習承擔責任。第二種目的是培養質變學習。梅茨羅(Mezirow)認為質變學習的關鍵在于學習者的批判性反思。批判性反思即是人“通過(個人所處的)歷史、文化和個人生活史去理解自己的需要、欲望和興趣等”[6],這正是獲取自我指導學習中的自我管理能力的先決條件,因此,需要通過幫助成人獲取自我指導學習的能力。第三種目的是促進解放學習和社會運動。布魯克菲爾德和科林斯(Collins)都提倡對自我指導學習進行更具批判性的、政治性的分析。
自我指導學習的過程也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問題,由此產生了很多過程模型。最早提出的是塔福和諾爾斯的模型,該線性模型包括診斷需要、確認資源和學習計劃、結果評估等環節,但是只考慮了學習者。到了20世紀末期出現的模型中,研究者不僅考慮到學習者,也考慮到學習策略、學習階段、學習內容、學習的情境和學習自身的性質等因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格羅(Grow)建構的“自我導向的階段模型”,這是一種旨在研究教師在課堂中如何培養學生的自我指導能力和學習控制能力的“指導性”過程模型。格羅把學習者區分為依賴、自我指導等階段,并提供了一個用于區分學習者所處學習階段的參考矩陣,以便一方面學習者能夠根據自己的學習準備情況確定自己所處的學習階段,進而選擇適宜的方式進行自我指導學習,另一方面教師可以針對學習者所處的階段進行針對性的指導。
評估也是SDL研究的一個重點。對學習者自我指導學習能力的測評工具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測量學習者的準備度,一種是測量學習者的人格特征。這兩種工具都在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另外,凱蒂(Candy)研究了自治力和自我指導能力的關系,他發現學習者在不同情境中的自治力可能會有所變化。一個人在某種情況下能夠進行自我指導學習,并不意味其“在新的領域中也一定能成功地進行自我指導學習;在學習計劃的新階段,定位、支持和指導對任何人都是必要的”。[7]
三、質變學習理論的影響
所謂質變,是指人身心發生的深遠的、根本性的、具有重要意義的變化。質變學習不僅能夠改變我們獲取知識的方式,還能夠改變我們的自我概念、世界觀和行為方式。
巴西教育家保羅(Paulo)提出了質變學習的解放性觀點。他在巴西成人掃盲教育的過程中深刻認識到被動的“填鴨式”的教育只能使成人“識字”,卻不能使他們“識世”,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受壓迫者的命運。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解放,是賦予人以力量,要通過對不公平社會問題的討論和反思來提升學習者的意識和覺悟,從而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看待自我和社會,進而有可能行動起來改變世界。他從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角度出發提出了解放教育學的觀點,讓被壓迫者通過學習發生質變,獲得力量并產生行動,他的書一度被當局列為禁書,但卻以更快的速度在全世界傳播。該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因此,也被稱為“被壓迫者的教育學”。[8]
梅茨羅從認知的角度提出了觀點質變理論,這種質變的特點是“更有囊括性、可辨別性、可滲透性、更具綜合性”。他強調通過理性思考和反思解決認知上的沖突,從而引發質變。觀點質變是一個循環過程,包括以下四個基本環節:(1)一種令人迷惑的困境,比如個人危機等;(2)批判性反思,由于發現個人所遭遇的事情和自己一直堅持的信念不相符時,對個人信仰、價值觀、假設或意義進行反思;(3)參與反思性對話,與他人討論自己的新觀點以獲得共鳴;(4)按照新觀點行動。后來,他還認識到情感、情緒和社會情境等因素對成人學習的影響,認為應該考慮學習發生的機構、人際、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等。梅茨羅是質變理論的奠基人,后續許多研究都是對其理論的拓展和延伸。但是,他只關注到個體的質變學習,沒有關注團體和組織層面的質變學習;他把引發質變學習的困境理解為單一的、戲劇性的偶然事件,是一種突然事件,沒有注意到這種困境實際上是長期積累而成。另外,他雖然注意到思想情感、文化和情境等因素,但是對這些因素的重視程度不夠,事實上,正如泰勒所指出的,質變學習是一個與思想和情感有關的復雜過程,個人背景以及文化等因素對質變學習的影響遠比原來想象的重要。[9]
達洛茲(Daloz)用發展觀理解質變學習,關注意義的形成。他認為,處于發展轉變期的學生把教育視為幫助自己從支離破碎的生活中找回生活意義的途徑。質變學習是一個在一定情境中發生的、有賴于直覺的整體性過程。教師在學生質變學習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而且在指導學生學習的過程中會受到學生的家庭和社會階層等社會背景的奇妙影響。達洛茲主要采用敘事方法,通過分享學生的奮斗故事來啟發學生。達洛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發現對教師專業發展都極具啟發性。敘事研究有助于對理論灰色地帶的挖掘;對成人學習者的傳統教育方式和內容的諸多弊端更是說明了關注個體背景及其意義形成的必要性。[10]
迪克斯(Dirkx)等則關注精神層面的超理性因素在質變學習中的作用。[11]他認為質變學習已經超越了以自我為基礎的、依靠語言交流的理性方法,轉向強調感覺和想象的超理性的精神學習。赫來(Healey)通過研究喜歡沉思的人的質變學習過程,發現他們都有膨脹的自我意識,因而有更深的自我意識和自我關注。長期以來精神一直是實踐中非常關鍵,但是理論研究起來又非常困難的一個命題,該研究對超理性因素的研究無疑豐富并加深了我們的理解和認知。
關于團體和組織層面的質變學習直到近些年才得到重視。約克斯(Yorks)等指出,組織質變學習旨在使組織實現其績效目標。團體學習的策略主要有行動學習和合作探究。這兩種策略都涉及反思和行動,但是,行動學習要求團隊成員集思廣益并通過反思和對話尋求某個既定問題的對策,而合作探究遵循自愿的原則,組織成員不受外界的干擾,自主決定是否加入研究小組,要解決的問題也是由參與者根據自己的興趣提出來的。
四、更加理性地看待教師學習與專業發展
長期以來,教師教育者以類似于未成年人的教學方式培訓教師,教師也習慣了被動地接受知識的灌輸和權威的指導,進而逐漸弱化甚至喪失了一個成人應有的創造力、判斷力和獨立性,教師作為成人學習者的特征沒有得到的重視。成人教育學、自我指導學習和質變學習理論的發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成人學習者,理解教師學習的特點,從而更好地指導教師的專業發展。
諾爾斯將成人學習和兒童學習區分開來,系統深刻地揭示了成人學習的特點,關注個體經驗、自我概念、內部驅動、現實需求、問題解決等在成人學習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對教師的成長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具體而言,首先,教師的經驗以及相應的實踐知識應該受到應有的重視,尤其是直接的體驗,如果能加以挖掘與積極引導,對教師專業發展意義重大;其次,通過增強教師專業學習的自主性和內部動機可以提高專業學習的效果;最后,教師專業學習的內容要圍繞現實問題,不能空談理論。我們不可能窮盡教師在教育教學中遇到的所有問題,但是,對于那些頻繁出現、影響較大的問題的關注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和實踐借鑒意義。
自我指導學習理論告訴我們:學習是人的自我實現,不能外爍,只能自發。隨著學習型社會初見雛形,人的學習意識逐漸普遍化,學習行為也在社會化。教師作為學生學習的引領者,其自身不斷學習的理念、意識、能力和行動更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如何幫助教師在繁重的日常工作之余有效地學習和成長?自我指導學習理論的研究成果向我們揭示了自我指導學習的目的、過程和評價策略,可以幫助我們更具目的性地激發教師的學習動機,指導教師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時間更快地成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自我指導學習的理論體系仍在完善當中,能給予的更多是一種理論視角上的沖擊和思考,而不是實踐的詳細指導。另外,我們不能否認系統地、集中地學習的效果,實際上,這也是一種非常受教師歡迎的學習形式,雖然,對大多數教師而言,他們更多地只能選擇在零散的日常工作空隙中尋找學習的時間,在工作情境中發掘反思和成長的資源。從這個角度說,通過提高自我指導學習能力來促進自己的成長是一種比較現實的、切實可行的途徑。此外,還需強調的是,這種自我指導學習能力的培養不僅需要自己個人的努力,更需要集體的幫助和專家的指引。尤其是在早期階段,專家的適當適時的引領是極為重要的。另外,許多研究表明,團體學習是促進個人成長的有效方式,因此,自我指導學習中也不能忽略集體的作用。
質變學習的相關觀點對于理解現實中教師的學習與專業發展,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首先,質變需要經由一個復雜的、艱辛的、反復的學習過程。在新課改背景下,教師專業發展的直接目的在于促進教師產生適應于新課程要求的變化。然而,這種變化不可能通過幾次動員會議或者培訓活動實現。事實上,教師的改變是一個復雜、艱辛的系統工程,需要全面考慮教師的“知識、信念、觀點、態度、行為和興趣”[12]等多種因素。富蘭認為教師改變至少包括使用新的教學材料、運用新的教學手段以及擁有新的教育觀念等三個高低有別的層次和類型,前兩種改變比較容易,但是教師的信念、價值觀和思想的改變則非常困難,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反復的過程。新課改在某些地方“穿新鞋,走老路”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僅僅通過合作探究、自主學習等形式上的變化只能帶來表層的變革,真正的變革需要教師走出自己的舒適地帶,勇于挑戰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學信念和價值觀,從而產生真正的深層變革。
其次,質變指人身心發生的深遠的、根本性的、具有重要意義的變化,這種變化要經由批判性反思體現在行動中。在實踐中,也常常可以看到接受了新教育理念熏陶的教師回到原有的教育教學環境中依然如故,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觀念的變革不能帶來行為的變化,而是意味著教育理念受到了新的沖擊,但是這只是一種量的積累,并沒有產生質變,因為質變是指人身心發生的深遠的、根本性的、具有重要意義的變化。只有通過質變,教師才能改變自己的原有信念和態度,進而持久地、由衷地改進自己的教育教學行為和實踐,最終提高教學質量和學生的學習成效。
最后,教師的質變有章可循,要創設理想的情境,激發和鼓勵教師解放自我,積極反思社會和個人存在的問題,改進自己的教育教學行為。弗萊爾(Freire)指出,教育的目的是解放,是“識世”。教師首先必須是一個具有獨立意識和批判精神的個體,才有可能實現教育解放的目的。然而,環境的制約和自身對舒適地帶的依戀可能會阻礙質變的發生,因此,要創設一個“安全、開放和信任的環境”,通過 “困境——批判性反思——反思性對話——行動”這一過程,促進教師產生質變。
總之,隨著社會的多元化、國際化、知識化,終身學習已經是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作為擔負著國家和民族繁榮富強重任的教師更是首當其沖。關于學習的價值爭論日漸式微,如何更高效快捷的學習逐漸成為考慮的重心。成人學習理論對學習特點和規律的探究,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作為成人學習者的教師的學習特點,更好地促進他們的發展。雖然成人教育學的理論假設未必適用于每一個成人,但是對于總體來說,還是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自我指導學習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教師更持久地、更有針對性地、更加因地制宜地學習。質變學習理論揭示了學習蘊含的真正意義。另外,這三者無一例外地強調了反思對成人學習者的意義,提高批判性反思能力成為提升學習品質的必然選擇。
[1][4]Knowles.(1975)Self Directed Learning:A Guide for Learners and Teachers.Chicago:Follett Publishing Co.19.18.
[2]Knowles.(1980)The Modern Practice of Adult Education:From Pedagogy to Andragogy.Chicago:Association Press.49.
[3][7]Philip C.Candy.(1991)Self-direction for Lifelong Learning.San Francisco&Oxford:Jossey-Bass Publishers.2.114.
[5]Tough,A.M.(1979)The Adult’s Learning Projects:A Fresh Approach to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dult Learning(2nd ed.).Toronto: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7.
[6]Mezirow J.(1981) A Critical Theory of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Adult education Quartrly32(1):4.
[8]Paulo Freire.(1972)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London:Penguin Education.
[9]Mezirow,J.(1991)Transformative Dimensions of Adult Learning.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1.5-68.
[10]Daloz Parks,L.A.(1999).Where’s the Learning in Service Iearning.San Francisco:Jossey-Bass.
[11]Dirkx,J.M(2001).The Power of Feelings:Imagination,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Adult Learning.In Sharan B.Merrian.Thw New Updateon Adultlearning Theory.San Francisco:Jossey-Bass.
[12]Polettini,A.F.F.(2000)Mathematics Teaching Life Histories in the Study of Teachers’Perceptions of Change.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17(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