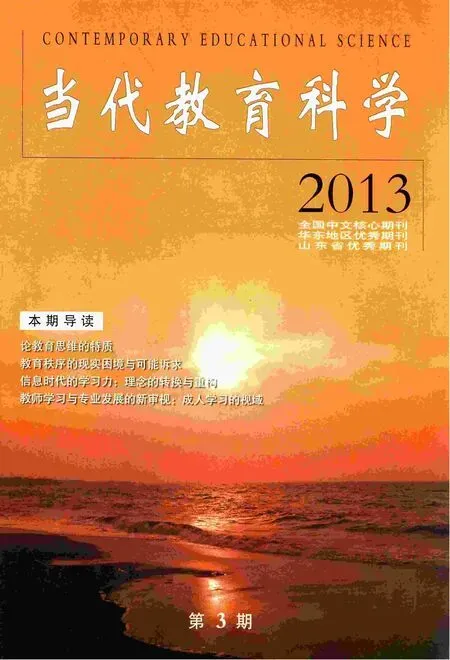教師合作文化視角下的教師專業引領
● 曾土花 胡中鋒
“專業引領”這一概念最早提出是2002年,在上海市教科院顧泠沅教授領銜的 “教師教育行動研究”的課題報告中,[1]以及福建師范大學的余文森教授在其《論以校為本的教學研究》一文中提出。[2]越來越多的學者們認為教師只有經常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學實踐和經驗,才能不拘泥于日常的教育教學,將自己的教育教學與教育理論聯系起來,不斷提升實踐智慧,進而促進自身的專業發展,[3]但是自我反思與同伴互助這種橫向支援常限于同水平反復局限性,而在自我反思、同伴互助橫向層級基礎上通過縱向層級專業引領,有可能會使教師理論與實踐的內容得到本質的提升。
一、教師專業引領的含義及表現形式
(一)教師專業引領的含義
國內學者按照專業引領中引領者主體的不同,將教師專業引領的定義歸為三種類型:一是認為專業引領就是教研部門研究、指導、服務職能的集中體現,它強調教研員要運用專業理論和專業知識,采取專業化的工作方式,去引導和帶領教師開展研究,獲得提高。它強調的是以教研部門為主體對教師群體和個體的引領。[4]二是認為專業引領通常指的是具有教育研究專長的人員通過他們的先進理念、思想方法和先進經驗引導和帶領第一線教育工作者開展教育實踐探索和研究,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促進學校內涵發展的活動形態。它強調的是某一領域的教育專家對教師的引領,在現實的學校中主要體現為教育專家和學校的骨干教師。[5]三是認為專業引領除了教育研究專家的引領,還包括教師同伴和自身的引領——專業引領包括顯性的專業引領和隱性的專業引領。顯性的專業引領人員指教育研究的專家和行家,既包括教育科研人員、教研人員和大學教師等專業研究人員,還包括資深的專家型教師,如特級教師、學科帶頭人等。隱性的專業引領指教師同伴之間通過深度對話、共享經驗和教師的自我反思。[6]
(二)教師專業引領的表現形式
根據教師領導的定義,“不論職位或任命,教師對領導的行使”,教師領導有正式與非正式之分。[7]一樣地,教師的專業引領也有正式與非正式之分。正式的教師專業引領的引領者不管是專家還是骨干教師都有官方賦予的一系列諸如優秀青年教師、學科帶頭人、特級教師等頭銜和類似于校級、區級、市級、省級乃至國家級等級。不同的頭銜和不同等級的專家和骨干教師都有相應的要求、待遇、責任和年限。正因如此,專家和骨干教師都是有特定角色與官方權威的正式的領袖教師。正式的教師專業引領在促進教師發展的過程有利于發揮教師專家和骨干教師的聰明才智、激勵被引領的教師群體具有重要的作用,促進教師引領有組織有計劃的完成。但是正式的教師專業引領也存在很多弊端,這種弊端主要體現在資源分配不均衡、導致教師之間的消極競爭和團隊合作中的功利主義。
在教師的專業發展中,為了尋求教師更好的發展,除了專家和骨干教師的專業引領之外,教師們在小組教研或者是團隊合作中,為尋求相互間的理解與支持、自發形成的教師同伴的引領和教師自身的引領,這種在教育專家引領基礎上產生的教師同伴的引領和教師自身的引領則是屬于非正式的教師引領的范疇。它強調的是教師組織的成員通過不斷參與、尋求理解和創造意義的一種互動的過程,是團隊合作引領而非角色引領。它突出的是引領、合作和關愛,而不是團隊中的正式角色和合法權力。相對于正式的教師專業引領,非正式的教師專業引領因為沒有教師專家頭銜和一系列規章制度的制約,更容易調動教師同伴和教師自身的積極性,實現教師群體發展和教師個體發展的有機統一。
二、教師專業引領和教師合作文化的匹配關系
Murphy(2004)認為教師專家就是以角色為本的教師引領;而團隊為本指得是任何教師都可以在某個時刻以某種形式成為領袖,即不僅強調教師專家的引領,還強調的教師同伴的引領和教師的自我引領。除此之外,Murphy還對比了以角色為本和以團隊為本的教師引領在不同領域的區別,這些領域有引領觀、重點基石、影響基礎、工作本質等等。具體如下表:
(一)人為協作的文化——正式的教師專業引領
“人為的協作,是指通過一系列正規的特定的官方程序來制定教師合作計劃,增加教師間相互學習的機會。”[9]這主要是一種忽視教師主體性發揮的文化,教師之間的合作關系不是由教師自發形成的,而是由行政命令催生的。在實施教師合作的過程中,很少會顧及教師的個性和教師所愛好的教研方式以及教師的實踐需要,合作的時間、地點還有主題也不是由教師自己決定的,而是由行政命令決定的,它是以實施為中心的,注重的是合作的形式,而不是合作的本質,注重的是教育理論的傳輸而不是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契合。這就容易造成教師把合作看做是應付的差事,不會主動將自己合作的理論所得遷移到教學實踐中,也不會讓教師積極主動地去反思和處理與同伴的關系,致使不能使教師學到真正有用的專業技能。
在這種帶有壓制性的文化中,教師處于正式的教師專業引領的情境。這種情境使得了被引領的教師長期處于被壓制、被管理的狀態,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這種組織形式上是結構化、等級制和制度化的的文化情境,引領者以個人為本,責任、榮譽和資源都屬于個人;加之正式的教師專業引領者產生的基礎是行政權力,教師引領者完全受行政部門的領導,其選拔和任命等都由行政部門及其下屬的教科研單位決定,這就使得教師之間為爭奪引領者的角色出現消極甚至是惡性的競爭,使得教師專業引領者與同事的關系有時是淺而分隔的,使得在完成規定任務之外與同事很少交流,容易出現合作中的功利主義的局面。
(二)自然合作的文化——非正式的教師專業引領
自然合作文化是教師之間在合作的過程中通過樹立共同的愿景,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與他人進行有效的交流、形成良好的人際關系。[10]在自然合作文化的指引下,合作是源自教師內心深處,是一種自我的愿望。它除了強調合作團體內部的教育專家的引領之外,還強調同事之間的合作和自我反思。自然合作的文化具有時間上與空間上的自由性,它是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為中心的,它需要教師同伴、教師個體以及教師專家通過深度交流、有效合作,逐漸推進合作的開展,它注重的不是合作的形式,而是合作的過程以及教師在合作中獲得發展的實質。它注重在教師的自我反思中實現教師與自我的對話,注重在同伴的互助合作中實現教師與同行的對話,注重教師在與教育專家的交流中實現理論與實踐的對話。讓教師在合作中實現教師個體與教師群體發展的有機統一,跨越理論與實踐的鴻溝。
在自然協作文化中,教師處在非正式的教師專業引領的情境中,在這種情境下,教師通過相互間的交流和溝通增進對他人的理解和支持,教師自身的失敗不僅不會受到他人的排斥和冷落,而且還會得到鼓勵,這就形成了教師之間的良好的人際關系,教師團體的責任、榮譽和資源不僅屬于教師個人還屬于教師團隊,這就使得教師對團隊具有強烈的歸屬感和榮譽感,讓教師在合作中享有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愿景,實現教師之間的深度合作;教師的引領者其選拔和任命主要是基于專業知識和教師群體的認可,這就是使得教師不再為爭奪資源進行消極的競爭,而將注意力轉移到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上。它的工作動力來自突發事件或者是合作的需要,必須服務于教師的專業發展,這就是使得教師之間的合作不再是為了純粹的理論,而是為了在合作中解決與自己相關的實踐問題,調動了教師合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三、創建自然合作文化,發揮非正式的教師專業引領的作用
處于人為合作的文化之下的教師專業引領強調的是角色本位,這種正式的教師專業引領對于樹立教師專業引領者的模范作用和使得教師專業引領得以順利進行提供了組織和制度保障,但是從長遠來看,這種文化所帶來的惡性競爭和合作中的功利主義,是不利于教師個體和教師共同體的發展的。因此我們需要創建自然合作的文化,發揮非正式教師專業引領的作用。
(一)信任互惠——建立各方對話與互動的基礎
問責制盛行的年代,為了規避懲罰和責任,教師之間出現了惡性競爭和相互提防的狀況,教師之間相互疏遠,為了個人利益孤軍奮戰。若教師之間能夠在合作中與教師同伴和教育專家實現有效的對話,相互探討解決問題的途徑,才是應對問責制的有效策略。所以我們要創建自然合作的文化,發揮非正式教師專業引領的有效作用。非正式的教師專業引領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教師的自我引領,即教師的自我反思、開展頭腦風暴。它是教師專業發展不可或缺的,所接收的理論和實踐知識,要真正內化為教師自身的專業技能,都需要教師進行自我吸收、消化和反思。二是教師的同伴引領,這主要是一種橫向支援,它促進了教師形成開放、合作、相互交流的合作氛圍。但若僅僅只有教師的同伴引領,會由于同事之間水平相當而自困于同水平得不到進一步的發展。三是教育專家的專業引領,它強調的是縱向的指導,它對教師專業技能的提升具有主要的意義。但是僅僅只有教師專家的專業引領,缺失教師同伴引領和教師的自我引領,那么教師專業引領的效果一樣不會很顯著。因此,只有實現縱向引領和橫向支援的“縱橫交錯”,加強各方的對話、建立各方信任互惠的關系,才能使得教師更好的學會開展研究,提升理論知識解決現實問題。
(二)積極行動——創建良好的合作的氛圍
孤立的、相互提防、相互推諉責任的學校氛圍抑制了教師尋求幫助的積極性,讓教師始終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致使教師在教學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得不到有效的解決。而在開放的、相互合作的、真誠交流的學校氛圍之下,不僅容易形成教師之間親密的關系,而且還能改變傳統的教師以個體發展為中心的心智模式。但是營造這種開放氛圍的有賴于校內全體成員的努力,尤其是學校合理的評價機制。建立在以結果導向和以競爭為導向基礎之上的評價模式,易使教師一方面害怕將在分享自己在實踐中探索出來的寶貴經驗,另一方面也不敢講自己在實踐中遇到的困境拿出來探討和尋求幫助。處于這樣競爭之下,合作就失去了促進教師群體和教師個體共同發展的意義。所以學校要構建以促進教師發展為核心的評價體系,在實踐中不斷完善評價體系,評價指標。在評價的過程中,不能僅僅注重對教師個人評價,還要注重對教師共同體的評價,讓教師明白個人的發展與教師共同體之間的發展是相互促進的,讓教師在合作中表現真實的自己,積極主動幫助他人、接受他人、真誠地分享信息和提出建議,實現教師真正的合作。
(三)有效對話——跨越理論與實踐的鴻溝
在教師專業引領的情境中,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會以各種方式去闡明自己的訴求,而來自不同立場的表述又共同構成了有關教師引領內容的爭議。教師的專業引領絕非是專家一方的單向信息傳輸,簡單的強求教師摸索出教育專家尚未弄明白的理論與實踐如何銜接的問題,而是基于平等的積極對話實現專家與教師雙向信息的傳遞與共振。因此,需要加強教師與教育專家之間的積極有效的對話,教師與教育專家互通有無,共同去搭建理論與實踐的橋梁。如何將多層次的實踐理論與不同的實踐主體相聯系,需要的是教育理論家與教師之間的信任互助和教育領域各個主體的積極行動,不能苛求涉及教師專業引領的某一方,而是由這幾個主體積極互動對話和積極行動形成學習共同體來實現。因此要求教師要改變傳統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心理機制,樹立教師共同體的意識。將教師個體的工作匯集為集體的資源,共同反思、學習從而達到知識和情感的交流與共享,不僅可以促進教師個體的發展還可以促進教師群體的發展。
[1]王潔,顧泠沅.行動教育教師在職學習的范式革新[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2-3,31-32.
[2]余文森.論以校為本的教學研究[J].教育研究,2003,(4).
[3]Schon D A.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M].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87,3-12.
[4]張曉明.建立校本教研制度是深化課程改革的現實良策[J].黑龍江教育,2003,(Z6).
[5]潘國清.學校教育科研中的專業引領[J].教育發展研究,2004,(10).
[6]傅建明.教師專業發展途徑與方法[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83.
[7]盧乃桂,陳崢.作為教師領導的教改策略[J].教育發展研究,2006,(17).
[8]盧乃桂,陳崢.正式與非正式的教師領導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J].教師教育研究,2010,(1).
[9]鄧濤,鮑傳友.教師文化的重新理解與建構[J].外國教育研究,2005,(8).
[10]Andy Hargreaves&Michael G.Fullan.Understanding Teacher Development[M].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2.
[11]Michael Eraut.Develop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M].The Falmer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