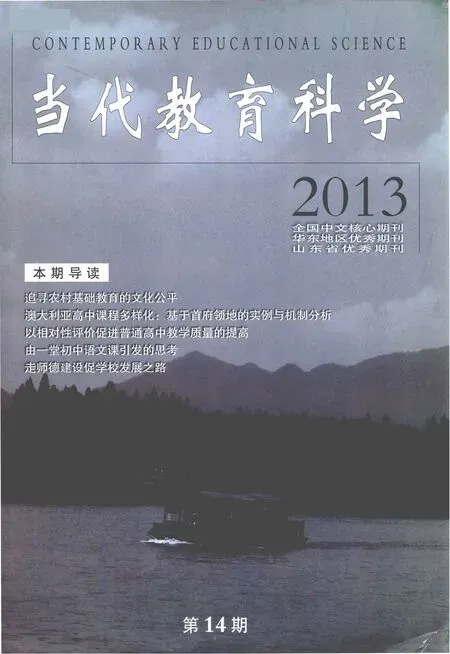全納教育視域中的留守兒童教育研究*
馬多秀
留守兒童是我國當前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伴隨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地向城市流動而產生的特殊的社會群體。據統計,留守兒童數量已經超過5800萬,而且,絕大部分留守兒童正處于義務教育學齡階段。[1]全納教育是當前全球教育發展的趨勢,消除教育中的排斥現象,推進教育民主化發展,以及實現教育公正和平等是全納教育的基本理念,它為解讀留守兒童教育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一、留守兒童教育是全納教育研究的應然領域
20世紀90年代,教育民主化成為一種國際教育潮流。1990年聯合國教科文等國際組織在泰國召開“世界全民教育大會”,發表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提出了教育是人的基本權利、教育對于個體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價值、普及基礎教育和促進教育平等的主張,把滿足所有人的基本學習需要作為全民教育要實現的目標。伴隨教育民主化思潮的發展,全納教育(Inc1usive education)也隨之興起。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西班牙薩拉曼卡召開“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會”,并發表了《薩拉曼卡宣言》,首次使用了“全納教育”一詞,強調每個人都有獨特的特性、興趣、能力和學習需要,學校要接納所有兒童并滿足他們特殊教育需要。如今,全納教育思想已經被世界許多國家接受,一些國家建立了全納教育研究機構、課程和刊物,如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建立了“全納教育研究中心”,西班牙、荷蘭、澳大利亞等設有培訓“學習輔導教師”的學士學位課程,美國、英國等聯合創辦了《國際全納教育雜志》等。全納教育的興起與特殊教育密切相關,最初關注的是特殊兒童教育問題。隨著人們對特殊教育的進一步研究卻發現,把殘疾兒童放在具有隔離性質的特殊學校接受教育不利于這些兒童社會性發展。之后,一些國家倡導一體化教育,即讓殘疾兒童進入主流學校學習。然而,一體化教育仍然面臨著困難,殘疾兒童要被迫適應主流學校,缺少從他們出發的教育設計,它雖然克服了隔離問題,但無法解決排斥問題。在現實的教育中,排斥現象卻比比皆是,不僅包括殘疾兒童受到排斥,學習困難兒童、行為不良兒童等也經常會受到排斥。因此,解決教育中的排斥成為全納教育主要的目標,全納教育關注的對象也由殘疾兒童擴展到全體兒童,從關注殘疾兒童的特殊教育轉到關注所有兒童的普通教育。
盡管全納教育研究的范疇在不斷深化和擴展,但是它的基本理念卻始終是一致的,即要推進教育的民主化發展,推進教育的公正和平等,實現沒有排斥的教育理想。正如有學者認為,“全納的宗旨就是要人與人之間共存并彼此關懷。它要創造一種沒有排斥的全新的文化,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民主的真實世界的組成部分”。[2]由此可見,消除教育中的排斥是全納教育的目標。一方面,要求教育要具有公平性和平等性。教育要關注所有兒童的教育需求,保障每個兒童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并且,每個兒童的教育權利和機會都應該是公正、平等的。不能把任何一個兒童排斥在教育之外,剝奪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另一方面,要求教育必須是多樣性的。兒童都是具有個體差異性的,他們的個性、興趣、需要等會有很大差別,教育必須要滿足他們不同的需要。這就要求教育本身應該具有多樣性,以適應不同兒童發展的需要,而不能實施整齊劃一的,統一的教育模式。此外,全納教育研究范疇從特殊教育發展到普通教育之中后,非常強調合作、參與,包括師生之間、師師之間、生生之間的協同合作,以及所有兒童積極和深入地參與課堂、課程、活動等,并且,在合作和參與的過程中創造一種沒有排斥的,民主、公平的教育氛圍。
留守兒童是當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農民工問題出現的特殊群體。由于父母外出務工,不能履行家庭教育的職能,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功能正在弱化,導致諸多留守兒童的親情需要得不到充分滿足,學業成績下降,部分留守兒童網絡成癮、輟學等問題行為增多。范先佐在調查和訪談的基礎上發現,留守生活對留守兒童心理和情感方面會產生的諸多負面影響:①柔弱無助;②自卑閉鎖,自暴自棄,喪失信心;③心理寂寞空虛;④盲目反抗或逆反心理;⑤對父母充滿怨恨,少數孩子認為家里窮,父母無能耐,才會出去掙錢。[3]從全納教育角度來審視,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產生是社會不公平和不平等現象向教育領域的延伸,留守兒童教育中存在著諸多教育排斥現象,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體制是社會根源,以應試教育為導向的學校教育氛圍和以量化考核為主的學校管理方式是致使留守兒童受到排斥的主要原因。全納教育致力于消除教育排斥,推進教育的公平和公正發展,維護每個兒童接受教育的基本權利,關注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和發展是全納教育研究的應然領域。
二、基于全納教育視角對留守兒童教育排斥現象的審視
只有對教育中的排斥有清晰的認識,才能夠實現減少排斥以至于消除排斥的可能,“對教育排斥認識的深度決定了全納在實踐中的效度”。[4]因此,認真審視留守兒童教育中的排斥現象是實現留守兒童教育全納化的前提。
對教育排斥現象的關注起因于人們對社會排斥現象的研究。社會排斥研究最初起源于人們對社會貧困與社會不平等的研究。1974年,法國經濟學家勒努瓦發表題為 《被排斥群體:法國的十分之一人口》論著,用“Les Exc1us”(被排斥者)指那些沒有被傳統的社會保障體系所覆蓋的人,比如單親父母、殘疾人、失業者等易受傷害人群,等等。[5]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會排斥”逐漸被法國以外的歐盟國家采用,并且已經傳播到世界其他國家。但是,對社會排斥卻存在著不同看法。歐盟認為,“社會排斥是一些個體因為貧困、或缺乏基本能力和終身學習機會,或者因為歧視而無法完全參與社會,處于社會邊緣的過程”。[6]聯合國開發署把社會排斥定義為基本公民和社會權利得不到認同,以及在這些認同的地方,缺乏獲得實現這些權利所必需的政治和法律體制的渠道。[7]總之,社會排斥是社會中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被相對地剝奪或削弱的現象,是社會不公平和不平等的體現。教育排斥是社會排斥向教育領域的延伸和深化。留守兒童是當前中國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他們在教育中受到排斥的現象可以劃分為兩種形態,分別是顯性排斥和隱性排斥,前者是明擺著的,顯著存在著的排斥現象,包括制度排斥、經濟排斥、文化排斥,后者是潛在的,不易被覺察到的排斥現象,包括慣習排斥、心理排斥、管理排斥。
(一)顯性排斥
首先是制度排斥。長期以來,中國實施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體制致使城市和農村成為兩個涇渭分明的相互割裂的部分。在《失衡的中國》一書中,作者認為,“二元社會結構才是中國國情的根本特征和要害”,[8]二元社會結構的內涵由14種具體制度構成,即戶籍制度、住宅制度、糧食供給制度、副食品供給制度、生產資料供給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勞動保障制度、婚姻制度,等等。這樣的一系列的制度一方面把城市和農村嚴格地區別開來,另一方面也由此形成了城市中心的社會格局。事實上,這一系列制度是與憲法所倡導的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精神相違背的,瓦解了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法律基礎。在現實層面上,它限制了社會流動,尤其是農民向城市的流動,阻礙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從留守兒童教育角度出發,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體制讓留守兒童受到雙重排斥。一方面,這種體制導致國家的教育經費的分配、師資配備、課程設置等方面的城市中心傾向讓留守兒童處于邊緣化境地。另一方面,這種體制催生了農民工這一獨特的群體,他們在城市工廠工作,但卻是農民身份,不能享有城市市民待遇。留守兒童是農民工群體的衍生物,也成為世界上罕見的特殊群體,他們被迫留在農村,不能跟隨父母到城市生活和接受教育。
其次是經濟排斥。在改革開放以前,農民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相互之間的收入相差很小。自從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農民職業多樣化,這使得農民內部也發生分化。我國農村問題研究專家陸學藝教授分析了改革開放十年后,當時八億多農民可以劃分為八個階層,即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民知識分子階層、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農村管理者階層。由于各個階層所處的經濟、社會地位不同,他們各自具有不同的政治和經濟訴求。[9]不同的農民階層也意味經濟地位的不同,作為農民工階層,由于他們自身的知識和技能有限,也決定了他們的經濟收入的微薄。事實上,農民工群體內部也在分化,經濟條件稍好的,會把孩子帶入城市,跟自己一起生活,通常只有經濟條件差的,收入不高的,才會把孩子留在農村。而且,由于家庭經濟上的貧困和拮據,諸多留守兒童不可能購買各種學習資料和課外書,也不可能聘請家庭教師給予學習上以輔導和指點,更不可能選擇教育資源相對較好的學校就讀。
第三是文化排斥。中國本身是農業大國,農耕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基石。但是,隨著中國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現代文化和城市文化逐漸成為主流文化。加之,城市中心取向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長期存在,以農業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被邊緣化。相對于留守兒童來講,文化排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活上的排斥。近年來,媒體報道了諸多留守兒童在寒暑假期間隨父母進城生活中出現的觸電身亡、溺水、自殺等事件。從根本上來看,這些事件的發生是由于留守兒童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而導致的。城市生活和農村生活是根本不同的,每一種生活方式之后是文化上差異,是文化決定了生活方式的區別。二是課程上的文化排斥。留守兒童長期生活在農村,他們身上攜帶的主要是傳統文化。但是,我們國家使用的是統編教材,而且,主要滲透和體現的是城市文化和現代文化。對于留守兒童來講,這些教材本身脫離他們的現實生活,呈現給他們是陌生的城市生活世界,勢必會增加他們學習難度,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他們學習的熱情和積極性,致使部分留守兒童成為學業上的失敗者。
(二)隱性排斥
首先是慣習排斥。中國由于長期以來在制度和政策層面對城市的偏向導致了城鄉發展極為不均衡,這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還已經深深地印入了人們的觀念和意識之中,也最終形成了城鄉兩種相互區別的、比較鮮明的生活方式、心理習性等。慣習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在考察中產階級和下層民眾生活方式差異時提出的一個概念。他認為,慣習是一套持續的、可轉換的性情傾向系統,是處于同一社會階層的人的“集體無意識”,能夠使個體以共同的特有的態度進行分類、選擇、評價和行動。在這里,我們借用慣習來分析留守兒童在教育中受排斥的現象。由于國家師范教育的大力發展和有關教育法律制度的實施,農村中小學的師資力量在發生著很大變化。以往,農村中小學教師隊伍以民辦教師占主體,隨著民辦教師逐漸退休,越來越多的接受過正規師范教育的教師補充到農村中小學教師隊伍中來,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出身于城市的教師。這些教師由于長期生活在城市,他們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出身于農村的教師的包括思想意識、文化觀念和行為方式在慣習。這樣,這些來自城市的教師在面對留守兒童時,他們一般會缺乏對農民工家庭生活貧困狀況的必要的理解和體驗,缺乏對留守兒童的同情和憐憫,相反,他們會對留守兒童表現出反感、討厭等情緒,給留守兒童帶來心理上的陰影和傷害。
其次是心理排斥。當前,高考、中考、小升初考試是風向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學校和教師的心理和行為選擇。“在強大的考試競爭環境下,教師必然遵循的是考試的邏輯”。[10]課堂是學校實施教育的重要場所,也是教育資源的集中地,學生在課堂時空中的位置決定了他們對教育資源的享有狀況,其中,座位和回答問題是學生享有課堂教育資源狀況的最直接的體現。在考試邏輯下,成績是衡量和決定一個學生能夠享有多少教育資源的重要指標。通常情況下,學習成績優異的學生不僅能夠占有較好的座位,還能夠獲得較多的課題回答問題的機會,相反,學習成績差的學生很難獲得較好的待遇。關于留守兒童學業成績狀況的研究已經表明,留守兒童在學業成績方面是分化的,有成績比較突出和優異的,也有成績比較差的。那么,對于成績比較差的留守兒童來講,在教師遵循考試邏輯的前提下,他們很難獲得來自教師給予他們在課堂中回答問題的機會,也不可能享有坐在教室里較好的座位上學習和聽課機會。
第三是管理排斥。深受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影響,當前學校管理也往往采用量化管理的手段和方式,試圖對教師工作的所有方面進行量化測評以對其工作成效做出評判。然而,事實上,教師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很難用數據來衡量的,尤其是德育、心理教育等方面,它們屬于精神、情感領域,量化方式難以測量。教師所做的這些方面的工作通常還具有遲效性,有時候很難立馬見效,要經過一段時間之后才會出現理想效果。留守兒童由于父母不在身邊,他們的親情需要得不到滿足,容易出現心理問題,他們更需要的是來自教師給予他們的心理上的疏導、安慰、鼓勵和支持,這些工作往往又比較費時費精力。在量化管理模式下,教師這方面的工作付出和努力卻容易被忽視,在一定程度上,這會導致部分教師放棄去做與此相關的工作。
三、留守兒童教育全納化的實現路徑
公平和平等是全納教育的精神內核,消除教育排斥現象是全納教育的目標。消除留守兒童教育排斥現象是保障留守兒童享有公平和平等的教育權利,以及實現留守兒童教育全納化的根本出路。這需要從教育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共同改進。
從宏觀層面來講,國家要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步伐,縮小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中國長期實施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體制導致了城鄉發展的不均衡,城鄉之間資源分配的不均衡,以及城市中心的發展格局。2008年10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要“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盡快在城鄉規劃、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一體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推動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融合”。國家提出的城鄉一體化發展規劃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城鄉之間均衡發展,縮小城鄉之間發展的差距,增進城鄉之間的流動和互動。一方面,只有實施城鄉一體化建設,才會逐漸打破城市中心的發展格局,同時,農民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制度障礙才會逐步被消除,農村和農民的經濟狀況才會得到改善,才會有更多的優質教育資源補充到農村教育中來。另一方面,只有實施城鄉一體化建設,城鄉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才會普遍化和經常化,尤其是能夠加強城鄉文化之間的互動,增進城市市民和農村農民之間的相互認識和相互理解,消除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文化上的割裂和隔膜。同時,在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中,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必然會逐步縮小,優質教育資源會逐漸補充到農村教育中去。
從中觀層面來講,學校管理要增強人文性,實施“以生為本”管理模式。如前所述,量化管理是當前中小學慣用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然而,在制度化的學校環境中,“學校推行的量化管理、規范管理是為了完成一定的任務,而不是考慮學生的感受和需要;即便是為人服務的制度,很多也是為教師服務的,而不是為學生服務的。”[11]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往往會為了完成任何去工作,而缺少教育責任意識,尤其是為學生全面發展負責任的意識,而導致學生的感受和需要得不到關注和滿足。特別是留守兒童,他們由于父母不在身邊,親情缺失,情感相對比較脆弱,在學校生活中他們需要獲得來自教師的更多的安慰、鼓勵、信任和支持。因此,學校管理要增強人文性,實施“以生為本”的管理模式,把學生的全面、健康發展放在管理的核心地位,管理內容和手段的制定要以促進學生的全面、健康發展為目標。一方面,需要學校弱化考試競爭氛圍,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尤其注重考核教師在學生道德、情感、心理等方面的付出和努力。另一方面,需要學校創造關注全體學生發展的氛圍,對特殊學生群體給予特別關愛,如建立留守兒童教育中心等,及時發現和滿足這些兒童的特殊需要。
從微觀層面來講,教師要增強全納教育意識,提升自身教育修養。教師是全納教育的實施者,在很大程度上,教師的素養決定了留守兒童教育全納化的落實程度。一方面,教師要增強全納教育意識,教師要充分認識到讓每一個學生享有同等的教育資源和機會是學生的基本權利,也是全納教育的基本精神,教師不能夠剝奪任何一個學生享有公平的教育資源和機會的權利。另一方面,教師要認真鉆研、掌握全納教育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努力提升自身的教育素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教師要具有敏感性,能夠換位思考,快速覺察和判斷學生成長和發展中出現的特殊問題和特殊需要,能夠以恰當的方式處理問題,以及滿足學生的特殊需要。
[1]蔣篤運.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與對策[N].中國教育報,2008-7-19(3).
[2]仲建維.公正和平等:支撐全納教育發展的阿基米德支點[J].全球教育展望,2002,(5).
[3]范先佐.農村“留守兒童”教育面臨的問題及對策[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5,(7):78-84.
[4]呂壽偉.排斥與全納——全納教育視野下的教育排斥研究[J].外國教育研究.2011,(9).
[5]Kevin Ryan,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Politics of Order,The new Poverty, the Underclass and Social Exclus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21-25.
[6]“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EU’s Social Inclusion Agenda”,Paper Prepared for the EU 8 Social Inclusion Study,Document of World Bank,2007:4.
[7]丁開杰.西方社會排斥理論:四個基本問題[J].國外理論動態,2009,(10).
[8]郭書田等.失衡的中國——城市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6.
[9]陸學藝.重新認識農民問題——十年來中國農民的變化[J].社會學研究,1989,(6).
[10]馬多秀.不同對待的邏輯——基于場域視角的課堂師生關系透視[J].當代教育科學,2010,(22).
[11]馮建軍.論生命視野中的學校文化[J].現代教育論叢,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