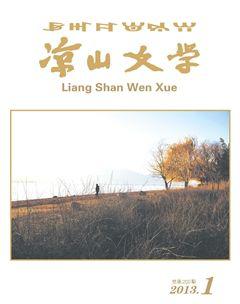魯迅五題
羅定金
小引
魯迅是誰?
這是魯迅之子周海嬰之孫周令飛,以及一些學者如陳丹青如鐘理群如張夢陽的追問。其目的是要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從過去神壇的魯迅、政治的魯迅、誤解的魯迅、還原為思想的魯迅、文學的魯迅、人間的魯迅。
魯迅究竟是誰?即魯迅在今天的意義。
陳丹青說:“‘魯迅是誰?的問題,就是‘我們是誰?的問題。”
有人說,最是魯迅應該讀。誠哉斯言。
魯迅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書。因為我的學識太淺,筆力不足,不能做宏觀的把握,我只有這微觀的點滴而已。
魯迅的筆名
我國近代以來,因為報紙、期刊和出版業(yè)的興起,于是詩人與作家就有了發(fā)表作品和出版著作的機會。那么,署什么名好呢?有些署原名,有些則署筆名,且聽尊便,這是他們的自由,是無可厚非的。
據(jù)我所知,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不少詩人與作家,是用筆名發(fā)表詩文和出版著作的。而且,同樣不少詩人與作家,是以筆名載入文學史的,這說明這個詩人這個作家已成大器,是可堪贊譽的。有的詩人與作家,終其一生,筆名不少,多至上百,比如魯迅先生。
魯迅本名周樟壽,是他祖父周福清為他起的;又名周樹人,是他一位當學堂監(jiān)督的本家爺爺給他起的,取“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意。“魯迅”,是他1918年在《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我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時,首次使用的筆名,之后先后多用“魯迅”這個筆名發(fā)表作品和出版著作,以至于后來的人竟忘記了他的原名,而只記得“魯迅”了。
“魯迅”筆名的起用,還引出了一段佳話。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在讀了《狂人日記》之后,覺得這很像周樹人的手筆,而署名都是姓魯,天下豈有第二個樹人乎?于是寫信去問,果然回信來說是“拙作”,而且那同一期《新青年》里有署名“唐俟”的新詩也是他做的。
到了九年(1920)年的年底,我們見面談到這事,他說:“因為《新青年》編輯者不愿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我從前用過迅行的別號是你所知道的,所以臨時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親姓魯,(二)周魯是周姓之國,(三)取愚魯而迅速之意。”至于“唐俟”呢?他答道:“哦,因為陳師曾(衡格)那時送我一方石章,并問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對他說,你叫做愧堂,我就叫俟堂罷。”我聽到這里,就明白了這“俟”字的含義,那時部里的長官某頗想擠掉魯迅,他就安靜地等著,所謂“君子民在晚的以俟命”也。把“俟堂”兩人字顛倒過來,堂和唐這兩個字同聲可以互易,于是成名曰“唐俟”。周、魯、唐又都是同姓之國也。可見他無論何時沒有忘記破壞偶像的意思(許壽裳:《魯迅的生活》)。
不少詩人與作家,為什么好用筆名發(fā)表作品和出版著作呢?據(jù)我揣測,緣由大致有五:一是編者在自己編輯的報刊上發(fā)表作品,用筆名以釋嫌;二、因為需要,一個作者在同一期報刊上發(fā)表兩篇以上作品時,用筆名以障人眼;三是紀念意義;四是自省情懷;五是文網(wǎng)使然。在魯迅的眾多筆名中,多數(shù)當屬后者。須知,“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毛澤東語)。
的確,魯迅的筆名,也許在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不是最多的,說是用筆名較多的作家,應該不是問題。魯迅一生,先后曾用筆名達140余個。戛劍生,是魯迅最先用的筆名,初用于他的《戛劍生雜記》一文,昭示著魯迅青年時代的激情;曉角,是魯迅最后用的筆名,首用于他的雜文《“立此存照”(一)》。許廣平說:“先生最后用的筆名,載在《中流》上的是‘曉角二字,他最后還不忘喚醒國人,希望我們大家永遠記取這一位文壇戰(zhàn)士的熱望。”意即黎明前的號角是也。
學者李允經(jīng),把魯迅的筆名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98年至1917年。其間,魯迅所用筆名12個;第二個階段,是1918年至1926年,魯迅新用筆名20個;第三個階段,是1927年至1936年,魯迅所用的筆名多達100個以上。魯迅用筆名最多的年份是1934年,多達39個,其次是1933年,達24個。魯迅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上海度過的。這10年,是敵人文化“圍剿”的10年,魯迅為了反文化“圍剿”,拿起筆,做刀槍,變幻各種筆名,發(fā)表雜文,與文化“圍剿”抗爭。
從魯迅的筆名,我們不難體會到他保存勢力的生存智慧。他曾說過:“有勇無謀,非真勇也。”他于是:一改變作法,二換些筆名,是啊,在“文網(wǎng)極密,動招罪尤”的時代,作者的筆名可以起到保護傘的作用。當然,“一名之立”,是需要“旬月躑躕”的。許廣平在《略談魯迅先生的筆名》一文中,就這樣說過:“實在他每一個筆名,都經(jīng)過細細的時間在想,每每寫完短評之后,靠在藤躺椅休息的時候,就在那里考量。想妥了,自己覺得有點滿意,就會對就近的人談一下,普通一些,寫出來也就算了。”
有人說,檢查官們是只看內(nèi)容,不管署名的,只要內(nèi)容不越軌,誰的文章都可以不刪不扣,順利放行。魯迅就不相信,說這是敵人預設的陷阱,放的煙幕,是靠不住的。他說:“檢查官們雖宣言不論作者,只看內(nèi)容,但這種心口如一的君子,恐不常有,即有,亦必不在檢查官之中,他們要開一點玩笑是極其容易的”;“我不想來中他們的詭計,我仍然要用硬功對付他們”。在白色恐怖嚴重的年代,魯迅用42個筆名在黎烈文、張樟生主編的《申報》副刊《自由談》發(fā)表大量雜文,時在1932/12至1935/10.魯迅曾說:“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申報》的《自由談》開頭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偽自由書》和《準風月談》兩本。”魯迅輯入《花邊文學》一書的文章,也是刊于《自由談》上的。編者為了醒目起見,發(fā)表時在文章的四周加了“一圈花邊”,因而在結(jié)集時,魯迅即以《花邊文學》作為書名。
“我即使講盤古開天辟地的神話,也必不能滿他們之意,而我也確不能作使他們滿意的文章”;“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這就是魯迅,我們不要誤讀魯迅的決絕;只要我們知曉魯迅所處的時代,就能理解魯迅。在“換些筆名”都還不保險的情況下,魯迅是“托人抄寫了去投稿”的。
魯迅的筆名,多數(shù)已被專家解讀,可有仍然未解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筆名被誤解。如“不堂”這個筆名,有人釋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因為有人曾攻擊魯迅的雜文,是一種“不登大雅之堂”的文體;有的人釋為“那些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并不是真正的‘堂·吉訶德”,其理由是這“正堂”之筆名,是用在那篇《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的。由此看來,這兩種解釋,都能成立,誰是誰非,就很難說了。
深思熟慮取筆名,是魯迅嚴謹作風的體現(xiàn)。他說:“一個作者自取的筆名,自然可以窺見他的思想。”凡魯迅的筆名,都是有著深刻含義的。筆名“韋士繇”,是“偽自由”的諧音,意指當時的黑暗統(tǒng)治;筆名“隋洛文”,是還擊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當局通輯“墮落文人魯迅”的;筆名“封余”,是回敬郭沫若罵魯迅是“封建余孽”的。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魯迅的筆名,也是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是很值得我們繼續(xù)學習和研究的。欲如此,就要像魯迅說的那樣: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這才較為確鑿。解讀魯迅的筆名,亦同此理。
魯迅的藏書
這個題目,已作過一篇,擬寄《會理文藝》審處。不過,那篇主要寫的是魯迅的中文藏書,欲知先生的知識結(jié)構(gòu),及其之所以成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文學家,還得較為全面地涉及先生的藏書才行。因此,再作上一篇,以饗讀者。
魯迅對書的情結(jié),似乎是與生俱來,從小開始,終其一生。“買書,對魯迅來說,不僅僅是閱讀的需要,也不是為藏書的買書;他買書,似乎已成為一種生命的需要。買書,已構(gòu)成他生命活動的重要部分,書在他的心目中是除了必要的生活資料外最重要的物品。”(何錫章語)據(jù)先生的三弟周建人回憶,還在上小學的時候,一放學就常常看見他去買畫譜。他把過年時候的壓歲錢所得,總?cè)ベI畫譜。向書場要了目錄來,看有什么可買的,如《海仙畫譜》、《海上名人畫譜》、《阜長畫譜》、《椒石來譜》等,買了很多。有次,先生在給曹白的信中說:“有喜歡的書,而無錢買,是很不舒服的,我幼小時常有此苦。雖然那時的書,每部也不過四五百文。”魯迅最早買的一部書,是兩冊裝的石印本《毛詩品物圖考》。
魯迅是書坊中的“淘金人”。先生住北京也罷,居廈門也好;先生居上海也好,住中山也罷。當然,還有在日本求學時期。人們,都能見到他訪書的身影。先生是堅持寫日記的,而且每年都有一份書賬,從中我們可以知其一斑。在此,不妨摘錄幾則,曉其大概。
1912年。共收書、各種拓片計94種。其中書籍類84種,共321冊;拓片類8種,共44張。共用去164.38元。末后又記:“審自五月至年莫(末),凡八月間而購書百六十余元,然無善本。京師視古籍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處世不必讀書,而我輩復無購書之力,尚復月擲二十八金,收拾破書冊以怡悅,亦可笑嘆人也。”
1929年。共221種,其中書208種,計402冊;畫帖畫頁15種,共161張。本年花在書畫上的錢大大超過以往,總計用去2404.5元。
1934年。全年總計304種。其中書有290種,計1188冊;拓片14種,共83張。全年共支出書費1029.20元。
這就是魯迅,這就是作為書人的魯迅。
買書,讀書,著書,是魯迅一生樂此不疲,始終不渝的事業(yè)。現(xiàn)存魯迅藏書4062種,約14000冊,其中文書籍2193種,外文書籍1869種,包括中文線裝書,中文平裝書、俄文書、西文書、日文書等。這些書,魯迅生前分別藏于北京和上海;魯迅去世后,到新中國成立不久,其夫人許廣平捐獻給了北京魯迅博物館,并專設“魯迅書庫”,滋養(yǎng)后人。
魯迅博物館前館長孫郁,曾經(jīng)這樣深情地描述“魯迅書庫”:我在魯迅博物館工作的時候,看見他大量的藏書,不免生出感慨來。那是多么博大的世界!線裝的、日文的、德文的、真是不可勝記!他的書,從來都干干凈凈,包裝得整整齊齊。我在他的藏書庫里,常可發(fā)現(xiàn)他自己包裝的書皮,上面偶爾也端端正正寫著幾行字,很是典雅。
這就是魯迅,這就是作為愛書家的魯迅。
1944年,魯迅的藏書險遭出售,由此引發(fā)了一場風波。不過,經(jīng)過魯迅友人的多方努力,魯迅的藏書終于保存了下來,這是不幸中的萬幸。關于魯迅的中文藏書,我在另一篇《魯迅的藏書》中,已有較詳細的介紹,這里從略不記,只說其他。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其資料來源自葉淑穗的《魯迅藏書概況》一文,否則會有掠人之美的嫌疑。
魯迅藏俄文書共86種96冊,以藝術和文學為主,藝術類31種,文學類29種。當時,因魯迅的朋友曹靖華在蘇聯(lián),魯迅就常去信請曹代購俄文書,因此他的多數(shù)俄文書就是這樣得來的。
魯迅藏德文、法文、英文等西文書,共有778種,1182冊,以前者為最多。以類別而言,則以藝術類和文學類最多。其中文學類358種,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德國、南斯拉夫、法國、英國、荷蘭、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美國等25個國家的名著,它們中的好些作品,成為了魯迅從事外國文學作品翻譯的母本。
在魯迅的藏書中,日文書種數(shù)最多,達955種,1889冊,且門類較全,版本最好。這些書,多是從日本的相模屋、鄉(xiāng)土研究社、實業(yè)之日本社、丸善書店、雞聲堂、辰文館、其中堂、力求堂、京華堂、三簽書房、巖波書店等處選購的。先生在上海居10年,與內(nèi)山完造交上了朋友(算是因書結(jié)緣吧),內(nèi)山書店成了先生常來常往的地方,他在這里買的日文書也就最多。從書的內(nèi)容觀之,當以馬列主義和哲學、文學、藝術為多。馬列主義和哲學有92種,如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chǎn)黨宣言》、列寧的《史的唯物論》等。《魯迅譯文全集》10卷,多以日文版本為藍本譯出。日文書中的藝術類有164種,由此可見魯迅先生的藝術情結(jié)和藝術修養(yǎng)。
魯迅是智者,這與他的知識結(jié)構(gòu)有關,這從他的藏書,我們不難讀出。關于先生的藏書,以上差不多都談到了。但是,有一方面差點被我們遺忘,這就是魯迅自然科學方面的藏書,此乃不可忽略不記的。
自然科學著作,在現(xiàn)存的魯迅藏書中,約有146部,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從涉及的內(nèi)容方面看,以魯迅作家身份而言,令我們嘆為觀止,諸如自然科學史、物理學、化學、地質(zhì)學、礦物學、生物學、動物學、解剖學,以及醫(yī)藥衛(wèi)生等。試問,在中國的近代、現(xiàn)代、當代作家中,除了魯迅,恐怕難以找到第二個像他這樣“高、大、全”的人。因此,對于魯迅,我們除了尊重、除了佩服、除了學習,已無話可說。事實就是如此明擺著,你不服氣是不行的,那些罵魯迅的人,可以閉嘴了。
魯迅的藏書,無疑是先生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同時,他又為后人研究他的思想他的文學他的藝術,提供了豐富而多彩的文本。在魯迅的藏書中,還有大量的中外藝術著作,本文并沒有怎樣說及,原因是筆者擬著專文談魯迅的藏畫。
魯迅的藏畫
在魯迅的藏書中,藝術類占有相當?shù)谋戎兀欢谒囆g類中,又以美術方面為多。
魯迅與美術的結(jié)緣,也是從小就開始了的,自始至終,晚年尤勝。先生從小有兩大愛好,一是圖畫,一是植物,因此他的購書,也就自然關注這兩方面。買《畫譜》之類,當是先生熱愛美術之初衷。隨著年歲的增長,魯迅于美術愛好也與日俱增,廣泛而深入。
先生不但在居住地買,因為不滿足,還常常托友人在外地(國)買。如此這般,使他的畫冊收藏便日益豐富起來,除自己收藏鑒賞外,還設法出版,且往往是自費的,由此可見其赤子之心。
著名女作家陳學昭,曾為魯迅先生買過有木刻插圖的書,說魯迅所要的主要是木刻,據(jù)她回憶:1929年和30年,她和魯迅通了一些信,先生給我的信,都是附在三先生(指周建人)給我的信中,偶爾也有直接寄我的。我和一位朋友跑遍了巴黎的書店,常常晚飯前后我們總要在塞納河邊的舊書攤上消磨一、二小時,搜尋有木刻插圖的版本。我和朋友也想了些辦法,例如利用特約的記者證,借理科同學所組織的一個有名無實的書店名義去購書,打折扣,省下錢來再買他多買幾本有木刻插圖的書。他收到這些有木刻插圖的書,每次都表示滿意,又奇怪書價的便宜。
曹靖華是魯迅先生的摯友,時在蘇聯(lián)的曹靖華,受魯迅之托為其買美術書。曹先生在《霧迷書畫》里談到為魯迅搜集和郵寄美術書的情形。他說:“其中有古典和現(xiàn)代的名家版畫集,漫畫集、風景畫冊等……更珍貴的有彩色精印插圖的俄文本《天方夜譚》等。”還說:“總之,從古典到現(xiàn)代,從蘇聯(lián)到西歐,凡有政治和藝術意義,足供我們借鑒和利用的,都在搜寄之列。”曹先生在講到如何把這些珍貴的圖書寄給魯迅時又說:“云山萬里,關山阻隔,怎樣才能把這些‘盒子炮送到魯迅先生手中呢?在當年反動派對蘇嚴加封鎖的局勢下,什么‘掛號、‘保險等郵遞法都歸無用。這只有用‘二仙傳道的辦法了。這就是第一步,先寄到比利時或法國,托朋友收后,除去封皮,重新包扎,寫上新的寄件人的地址。俄羅斯有句諺語:‘烏鴉是不啄烏鴉的眼睛的。這樣就過關了。”
辦事,拜托與受人之托,其間是需要相當?shù)挠亚樽鲋蔚摹D憧矗瑸榱速I畫冊,遠在異域的朋友是何等的認真負責,盡管煩瑣而累人。魯迅與陳學昭,魯迅與曹靖華,在回憶和說及此事時,如道家常,平實極了,這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從另一個側(cè)面,我們能感知到的是魯迅結(jié)交的人緣之好。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要以心換心的,一個人只希望別人對自己好,而自己則無所謂,恐怕是不行的。
在魯迅收藏的日文書籍中,美術方面的達200余種,660余冊,它占全部日文藏書的三分之一。其中,數(shù)量最多的是各國的版畫藝術,而日本浮世繪版畫又是其間的重中之重。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的“魯迅書庫”中,可見先生收藏的浮世繪書,多達16種,如《寫樂》、《北齋》、《廣重》、《浮世繪大成》12冊、《近代錦繪世相史》8冊、《浮世繪稀版畫集》等。除此而外,還有日本友人贈送先生的浮世繪畫帖多幅。魯迅之所以熱心收藏外國的繪畫藝術,正如他所說:“我們必須迅速向前發(fā)展,把當今世界上具有最大價值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拿過來”,為我所用,為促進祖國美術事業(yè)的發(fā)展服務。也就是說,是集收集、鑒賞、研究為一體的。
北京琉璃廠,是從清代乾隆年間逐漸發(fā)展起來的以書籍、古玩、碑帖、文具等店鋪為主的著名街市,位于今和平門外,因舊有琉璃窯而得名。魯迅于1912年5月5日到達北京一周后,即當年的5月12日,便光顧了琉璃廠。先生在京的十幾年,成了琉璃廠的常客,是年平均每周一次,多有所獲。這從他的日記中,我們不難讀到。
翻開《魯迅日記》,我們就見到了先生逛琉璃廠的身影,讀到了先生購買畫冊,以及碑帖的記錄。今摘數(shù)則,以見一斑。
下午至琉璃廠購……《中國名畫》第十五集一冊,一元五角。(1912.5.25);得津貼六十元,晚游琉璃廠,購……《李龍眠白描九秋圖》一帖十二枚,六角四分;《羅兩峰鬼趣圖》一部兩冊,兩元五角六分。(1912.5.30);上午赴青云閣……又赴琉璃廠購《龔半千畫冊》一本,八角。(1912.6.16);赴琉璃廠買紙,并托清秘閣買林琴南畫冊一葉,付銀四元四角,約半月后取(1912.11.9);往琉璃廠購《董香山水冊》一冊,一元二角;《大滌子山水冊》一冊,一元;《石谷晚年擬古冊》一冊,八角。(1912.11.16);午后赴琉璃廠神州國光社購《唐風圖》、《金冬心花果冊》各一冊,共銀三元九角。又往文明書局購元《閣仲彬惠山復影圖》、《沈石田靈隱山圖》、《文征明瀟湘八景圖》、《龔半千山水冊》、《梅瞿山黃山勝跡圖冊》、《馬扶曦花鳥草蟲冊》、《馬匯香花卉草蟲冊》、《戴文節(jié)仿古山水冊》、《王小梅人物》各一冊,又倪云林山水、惲南田水仙、仇十洲麻姑、華秋岳鸚鵡畫片各一枚,共銀八元三角二元。(1912.11.12)余本年12月有關購畫的3則,不再錄以釋“文抄公”之嫌。這還只是1912一年的購畫冊記錄啊,由此可見魯迅對于畫的癡了。看來,一個人最好對某些事物起碼有一癡才妙。
既重視外國木刻的收藏,也不忽略中國傳統(tǒng)美術的收藏,這就是魯迅藏畫的態(tài)度。他是我國新興木刻運動的倡導者和組織者,在他的旗下有不少的美術青年。他說:“我以為中國新的木刻,可以采用外國的構(gòu)圖的刻法,但也應該參考中國舊木刻的構(gòu)圖模樣,一面并竭力使人物顯出中國人的特點來,使觀者一看便知道這是中國人和中國事,在現(xiàn)在,藝術上是有要地方色彩的。”
魯迅是有一種割舍不掉的版面情結(jié)的,這從他不遺余力地收藏版畫集,精心編印版畫集的事跡,我們是可以知其所以然的。《近代木刻選集(一)》,是中國第一部版畫集。作為《藝苑朝華》第一期第一輯的《近代木刻選集(一)》出版之后,又出版第二輯《路谷虹兒畫選》;接著又出版了《近代木刻選集(二)》。接下來,是第一本蘇聯(lián)版畫和黑白畫集《新俄畫選》的出版;自費印行第一本復制品《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自費編印蘇聯(lián)版畫集《引玉集》;編印并作序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編印并作小引的插圖畫冊《死魂靈一百圖》;作序的木刻連環(huán)畫《一個人的苦難》;生前選編的最后一部版畫集是《蘇聯(lián)版畫集》。魯迅先生在關注外國版畫的同時,把目光投向了中國版畫;自費出版木刻青年創(chuàng)作集《木刻紀程》等便是。
先生與鄭振鐸合作編印《北平箋譜》和翻印《十竹齋箋譜》,早已成為藝壇佳話,并成為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魯迅與美術的話題,不是一篇小文可以盡述的,它需要專著的介入。
魯迅的版稅
自古以來,中國文人羞于談錢。說是,一談錢就俗,這是由于他們的社會角色所決定的;說實話,這是他們骨子里所不情愿的。但有什么辦法呢?只好閉口不談。文人談錢,是需要勇氣和膽識的。
有清一代的鄭板橋,敢于把自訂之書畫潤例張榜公布,起初也是遭到非議的。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偉大的魯迅先生就敢于在他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樣》演講中談錢。他說:
錢是要緊的。錢這個字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后,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要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后,再來聽他發(fā)議論。……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jīng)濟,是最緊要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為錢所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饑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jīng)濟權(quán)就見得最要緊了。……在經(jīng)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
這大概就是魯迅的金錢觀吧,我看是的。
是啊,人一出世,就要吃喝穿衣住宿,哪一件離得開錢。君子愛錢,取之有道,那是自然。
魯迅的一生,大致經(jīng)歷了這么四個階段:求學、公務員、教書、自由撰稿。先生的經(jīng)濟來源,主要有四:一、公務員收入。被國民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錄用,在教育部擔任公務員(1912—1926),時間長達14年之久;二、教書收入(1920—1927),在北京兼職多所大學,時間長達6年,后至廈門大學,再至中山大學。先生做專職教授,實際上就是在廈門和廣州各一學期;三、大學院特約撰稿人收入(1927.12—1931.12),四年又一個月,經(jīng)蔡元培推薦,先生受聘于“大學院”后來的“中央研究院”,為特約撰述員,月薪300圓大洋,定期支付49個月;四、寫作、翻譯和編輯收入。
《魯迅日記》,既沒有抒情,也很少議論,有的只是記事;而記事最多的,乃是經(jīng)濟收支情況,而使用較多的字是“泉”。“泉”是“錢”的古語,《金史·食貨志三》解釋為:“錢之為泉也,貫流通而不可塞。”有人說,《魯迅日記》是先生經(jīng)濟收支的明細賬,這說法是夸張了一些,但它反映的是基本事實。
也是羞于談錢的緣故吧,魯迅研究的學者們,關于魯迅精神方面的研究著作,說是汗牛充棟并不為過。而對魯迅物質(zhì)方面的研究,卻絕少涉及。其實,只有精神,缺乏物質(zhì),是不完整的魯迅。
學者陳明遠,潛心研究文化名人的經(jīng)濟生活,達20年之久,碩果累累。有《何以為生——為文化名人算經(jīng)濟賬》、《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等多部專著出版發(fā)行,魯迅是其研究的個案之一。與此同時,我還讀到學者李肆的文章《魯迅在上海的收支與日常生活——兼論職業(yè)作家市民化》。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借用了他們的一些研究成果,這是必須特別加以說明的。
1927年10月3日,魯迅攜許廣平入住上海,實現(xiàn)了他從公務員到自由撰稿人的轉(zhuǎn)變,過上了他以收取版稅和稿費的職業(yè)作家生活。
之前的1905年,魯迅與二弟周作人留學日本。1907年周氏兄弟合譯《紅星佚史》,得到稿酬200余圓,合同上注明千字2圓。這恐怕是魯迅第一次得到的稿酬。同時,魯迅還有著譯出版,還有《人之歷史》等文在《河南》雜志發(fā)表,魯迅和其他人一樣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作品是沒有稿費可拿的。
據(jù)陳明遠統(tǒng)計,魯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9年間(虛年10年),總收入為國幣78000多圓,平均每月收入723.87圓(約合今人民幣4萬多元)。“他一不靠‘官,二不靠‘商,屬于當時上海典型的自由職業(yè)文化人。”這個時期,魯迅完全依靠版稅、稿酬、編輯費為生,占他生平總收入的半數(shù)以上。魯迅所過的,是小康人家的中間階層生活,比他在北京的生活水平高多了。
因此,魯迅一到上海,先是暫時住共和旅館,幾天后入住景云里23號,于次年9月9日因鄰居嘈雜,遷至景里18號,又于1930年4月11日,魯迅一家又遷入大陸新村9號,直至1936年10月病逝。“大陸新村9號是一幢水、電、氣齊備的三層樓的闊大建筑,堪稱‘毫宅,這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不多的。”(李肆語)電風扇、留聲機等這些當時非大眾消費品,先生的家都是具備了的;同時,還長期請傭人工。至于看電影,請客吃飯,資助青年作家、自費出版畫冊之類,更是不計其數(shù)。所以,魯迅在上海時期是自食其力,自得其樂,活出了先生的獨立人格,他被視為文化人的榜樣。
魯迅時代的稿酬標準,是按作家等級給的,當時把作家分為五等。魯迅,無疑是一等作家。魯迅的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3圓,有時千字5圓,他的《二心集》是按千字6圓計酬的,是比較高的了。那么,魯迅的版稅呢?先生的版稅,一般是20%,高的可達25%。《魯迅日記》1932年12月15日記:“以選集之稿付書店印行,收版稅泉支票三百。”說的是先生的《魯迅自選集》,是天馬書店出版的,初版印1000冊,定價1.20元,魯迅得300元,版稅率為25%。據(jù)說,這在當時是特高的了。
在李肆的《魯迅在上海的收支與日常生活》一文中,有過先生版稅的記述:魯迅在上海賣文的全部收入大約是55442元,月均約510元。魯迅的賣文收入,以版稅為主,1933—1935年,魯迅的版稅收入分別為9325.93元、4962.87元和3938.47元,三年間月均收入版稅506.87元。“這一方面是因為魯迅的書銷量大且版稅高,如《吶喊》,魯迅生前即正版印行48500冊,《兩地書》 1933年4月出版,當年魯迅即收入版稅1125元,(據(jù)《魯迅日記》計算,約銷4500冊)。”
為版稅而斗爭,是魯迅二、三十年代的壯舉之一。魯迅的書,多由北新書局出版,而這個書局的老板李小峰,是先生在北大時的學生,原是新潮社成員;1925年脫離新潮社,創(chuàng)辦北新書局,主要出版新文學作品。先生的《吶喊》、《中國小說史略》等名著都是交北新書局出版的。同年11月,李小峰開始向魯迅支付版稅,魯迅南下后,直到1927年底,李小峰未向先生支付版稅;1928年1月,李小峰又向先生支付版稅,每月140元。此時,魯迅在北新書局出書已9種,而且銷路很好。魯迅感覺不對,于是托人找律師楊鏗,“委以向北新書局索取版稅之權(quán)”。最后,雙方達成庭外調(diào)解,李小峰分期補清歷年欠版稅8256.834元;雙方重新簽訂合同,李小峰向魯迅領取印花,執(zhí)行印書證制。
“(這)顯示了他(魯迅)為了自己的合法權(quán)益銖兩必較的市民觀念,并不羞于公開地為自己爭奪金錢”(李書磊語)。
魯迅的手稿
手稿,指的是著作者手寫的原稿。
如果從它的類型來看,可以大致分為為手稿本、清稿本和修改稿本三類。手稿本,是著作者的原始文本,有的涂改勾畫較多,有的稿面則非常清楚,只有個別字詞的改動;清稿本,是指著者在手稿本的基礎上重新謄清的稿本,也有“白本”之稱。這種清稿本,可以是著作者本人的手跡,也可以是家屬之代勞,還可以請善書者動筆;修改稿本,是指著者在原稿或清稿的基礎上親筆加以修改的本子。如果改動不多,就在原稿涂改,如果改動較多,則在原稿的天頭地腳標注。如果改動太多,就要對原稿進行裁剪粘貼,另加簽條。
以上說的這些,都是還在用傳統(tǒng)書寫工具著作的人,已經(jīng)感知和體驗到了的。進入電腦時代的當代,著作家們多數(shù)已經(jīng)換筆,利用電腦寫作,只有極少數(shù)的著作家還在用筆書寫。有鑒于此,目前手稿的意義就顯得越來越重大了。手稿的意義,在于它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即書法)。
話還得說回來,手稿的意義在名家那里,如名作家名詩人名教授名學者,還有就是各行各業(yè)的社會公認的名人。我輩平凡人的手稿,即使字寫得比名人的漂亮,也是沒有用的,說白了就是不值錢,所以我從來不保存手稿。
名人手稿已是極有收藏價值的珍品,現(xiàn)在你想要收藏名人手稿幾乎不可能。因為,他們的手稿,早已被圖書館博物館文學館等機構(gòu)收藏。有資料顯示,“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就藏有名人手稿1.5萬件;“上海圖書館”設有文化名人手稿館,藏有近百年來各界文化名人蔡元培、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丁玲、錢鐘書等100多位的手稿達4萬余件。
名人的手稿值錢,我們從以下的幾例,可見一斑。1996年“瀚海”春拍,梁啟超手稿一卷,底價2萬—2.5萬元,林語堂的日記手稿(1929.1—1932.2)底價3萬元,以28萬元成交。周作人一冊手稿共114頁,底價7萬—8萬元。這還是近20年前的數(shù)據(jù),而今這些名人的手稿價格,不知又漲了多少。
魯迅先生,毫無疑問是中國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名人之一;豈止于此,先生的影響力還將繼續(xù)下去。孔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魯迅先生,當之無愧矣。先生之學問博大精深,先生之修行堪為楷模,先生之才識為人稱絕。此乃先生名副其實之謂也。
文化名人都很珍惜自己的手稿,魯迅先生卻是個例外。關于這個,我至今都未想明白,先生其他方面都十分精細,為什么偏對自己的手稿不在乎?
收藏家李維基著《藏事紛紜錄·名家手稿收藏難》中,有這樣的記載:魯迅先生每出一書,手稿即棄之。有一個故事說,一次蕭紅在上海的一家炸貨店買油條,發(fā)現(xiàn)包油條的紙竟是魯迅的譯文《表》的一頁手稿。平時在家時,魯迅常用出完書的手稿擦桌子、擦手。所以魯迅先生的手稿保存下來的不多;能保存下來的,多是許廣平背著先生留下來的。在魯迅770多篇雜文手稿中,僅存170多篇;30多篇小說手稿中,只留下來8篇。因此,魯迅的手稿,就顯得更加珍貴。舉例說吧,1994年“嘉德”秋季大拍上,有5頁魯迅手稿是1933年4月寫就的雜文《言論自由的界限》和《以責制夷》,底價7500—8500元,結(jié)果以7.15萬元拍出。現(xiàn)在呢,恐怕要10倍于這個數(shù)了。
魯迅的手稿原件,已被魯迅博物館相關機構(gòu)收藏,看來我輩是無緣相見了。只好退而求其次,收藏魯迅手稿影印本,即使是這樣也很難。我知道,出版者是出版過《魯迅手稿全集》的,線裝、數(shù)函,苦干冊,價昂,我輩是買不起的,據(jù)說還有價無貨。我只收藏到《魯迅手稿選集三編》《四編》(不知道選集一共出了多少編)、《魯迅致增田涉書信選》、《魯迅批判孔孟之道手稿選編》、《魯迅詩稿》兩種,一為文物版,一為上海人民美術版。僅此而已,其他所見是關于魯迅及其作品的研究著作和先生的傳記中的斷簡零篇。極其有限是吧,但我已經(jīng)知足。
我收藏的魯迅手稿影印本前三種四冊,應該是先生的初稿,或者說是草稿是底稿是第一,是用毛筆書寫在綠格稿紙上的,當然是豎排。有的改動不大,有的改動較大,有的改動太大,甚至有粘貼有刪節(jié),從手稿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先生思想的開合,行文的嚴謹,書法的藝術。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有多封是寫在素箋上的,從而又多了幾分雅致。《魯迅詩稿》,因為沒有改動的痕跡,就應該是清稿本了。
從魯迅的手稿中,我們能欣賞到先生用傳統(tǒng)書寫工具所書書藝。只是其書名一直為文名所掩,人們很少談到先生的書法。魯迅的書法,基本功很扎實,是老師壽鏡吾嚴格訓練的結(jié)果,“正午習字,晚上對課”。每日臨書習字,足有五六年之久;先生抄錄《小學入門》、《開方提要》、《說文解字札記》等課本,亦是很好的自我訓練。同時,因為抄錄碑刻古藉,先生對漢魏六朝兩晉的書法筆意而心領神會。在《魯迅詩稿》的前邊,有一篇郭沫若手跡之序,序文中說:“魯迅先生亦無心作書家,所遺手跡,自成風格。融洽篆隸于一爐,聽任心腕之交應,樸質(zhì)而不拘攣,灑脫而又有法度。遠逾宋唐,直攀魏晉。世人寶之,非因人而貴也。”
彩箋之于魯迅,可謂情有獨鐘,編輯出版《北平箋譜》和《十竹齋箋譜》,就是證明。魯迅的手稿,不少是寫在彩箋上的,特別是書信。我見到的《魯迅書簡·致曹靖華》,前邊有6頁先生手跡是寫在彩箋上的,真是漂亮極了。
1929年5月15日,魯迅給許廣平寫信,它的特別之處在于:一、稱呼一改過去的習慣,而稱“乖姑!小刺猬”;二、毛筆手書,守法度而瀟灑;三、精心選用兩頁彩箋,一為枇杷,一為蓮蓬。許廣平收到信后,興奮不已,即回信一封,信說:“自然打開紙張第一觸到眼簾的是那三個紅當當?shù)蔫凌耍鞘俏蚁矚g吃的東西,……所以小白象(許廣平對魯迅的昵稱)首先選用了那個花樣的紙算是等于送枇杷給我吃的心意一般,其次那兩個蓮蓬,附著的那幾句(指箋紙上的題詩:并頭曾憶睡香波,老去同心往翠窠。甘苦個中儂自解,西湖風月味還多。)甚好,我也讀熟了。……”魯迅以箋紙寫信傳情許廣平,并未至此為止,先生在讀了許廣平信后,又回信一封。魯迅在回信中說:“我十五日信所選的兩張箋紙,確也有一點意思的,大略如你所推測。蓮蓬中有蓮子,尤甚我以取用的原因(當時許廣平已有身孕)。但后來各箋,也并非幅幅含有義理,小刺猬不要求之過深,以致神經(jīng)過敏為要。”魯迅先生給許廣平寫信是在他離上海去北京探母之時,所以才有魯迅用箋紙毛筆給許廣評寫信這段因緣。
我們今天能欣賞到這彩印的魯迅手稿,是感到欣慰的,那彩圖那書法那趣味,仍氤氳著我們。這,大概就是我們收藏名人手稿之至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