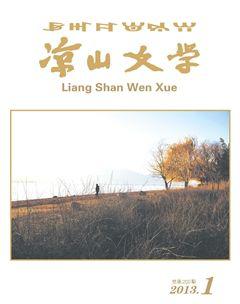散文二題
廖崇芳
外婆
外婆,昨夜我又夢見了您:還是那樣慈眉善目,和藹可親,還是那樣整整潔潔大方得體。那一身老式藍布衣褲還是漿洗得妥妥貼貼,干干凈凈。潔白的內襯衣袖口一如既往地挽在外衣袖口上。一雙三寸金蓮支撐著您那幾十年依舊腰不彎背不駝的高大魁偉身軀。難怪在您生前見到過您的人都說您富態,好福氣。就是您駕鶴西去以后,認識你的人提起您,都會情不自禁地說:“嚯,你的外婆好富態喲。”
外婆,夢中,在您洗腳時,我又一次看清了您的三寸金蓮,天啊!這是怎樣的一雙腳——那腳尖只有一個大腳趾,而其余四個腳趾則被排列有序地壓在腳掌之下。顯然,那腳趾骨在您幼時不是被折斷就是被折彎。舊時人的愚昧啊,給您的一生平添了多少痛苦和不便,然而,就是這雙三寸金蓮支撐起有著高大身軀的您,給了兒孫們多少的關愛。
外婆,您可曾記得,在我幼時,有一次母親生病了,您知道有一種草藥治母親的病是特效,您把小鋤頭放進背簍,背上背簍,拄著拐杖,帶著我急急忙忙去采草藥。
在那經常大雨過后是驕陽的夏天,我們頂著烈日,走過泥濘的水稻田埂來到山腳下。我倆在無路的山腳走走停停,尋尋覓覓,終于挖回足夠的草藥,治好了母親的病。
外婆,您可知道,您那烈日下揮動鋤頭挖草藥,一顆汗珠摔八瓣的情景,您那尖尖小腳和拐杖留在田埂上、山腳下的印痕,還有您那滿是泥巴的一雙尖尖小腳,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里。
俗話說:“憨家婆帶外孫。”而善良無私的外婆啊,我怎能忘記,在我兒時,母親因操勞過度常生病住院,我便成了外婆您家的常客。
那是國家遭受天災人禍的困難時期,當時的您無論生活多么拮據,總是和外公竭盡全力對我精心呵護、照料。那時,我吃的是您們省下的香甜的白面,而您和外公有時卻不得不吃用茅辣(一種生長在荒灘的野草)根磨面做成的難以下咽的饃。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我怎能忘懷?
外婆,您是否還記得,在“文革”那特殊年代,西昌陷入無休止的“武斗”期間,為了躲避那不長眼的子彈、炮彈,我們全家也和許許多多人家一樣,分別到鄉下親戚家躲“武斗”。在您的安排下,我們一家六口就有四口跟您生活在一起。
當時,西昌兩派混戰,炮火連天,一切都亂了套。父母單位負責發工資的人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們連最起碼的吃飯都成了問題。正當父母為生計焦頭爛額時,是您——我可親可敬的外婆毅然決定,將您顛著三寸金蓮不知背了多少豬草才喂大的一頭豬宰殺后,讓二舅走村串巷賣了豬肉,為我們一家換來了生活費,換來了希望,幫助我們安然度過了那個最困難的日子。
外婆,我又夢見了您當年為集體看莊稼的情景:無論嚴寒酷暑,早出晚歸的您依然是那樣整潔,手里依然悠閑地搖著那竹子做成的麻轱兒(一種擰麻線的工具),為自己、也幫別人擰著那永遠擰不完的麻線。偶爾,有牲口脫了韁跑到田邊,您立即一邊驅趕一邊亮開嗓門吆喝著:“牲口喔——牲口扯脫了——”這時,在田邊干活的飼養員就會立即趕來拉走牲口。在您盡職盡責的看護下,集體地里的莊稼無論種什么都始終安然無損。倒是您自留地里的莊稼有時被牲畜啃吃。當牲畜主人要給您賠償時,您卻說:“一個堡子的人,抬頭不見低頭見,哪個要你賠喲。以后把牲畜看好就是了。”
我更難忘的是在那“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的極左思潮泛濫時期,倔強的大舅認為土地在“減產”,人們在受窮,“不識時務”的他竟不合時宜地申請把屬于他的土地分給他。可想而知,當時的大舅遭到了個別“公私兼顧”的人積極組織的多次批判。而當歷史作出公正裁決時,您卻平靜地語重心長地對兒孫們說:“冤冤相報何時了?過去的就過去了吧。寬容是福。”
外婆,您一生清貧,然而,您卻是那么豁達、寬容,無論多么過分的人您都能大度相待,無論什么性格的人您都能融洽相處,無論多么大的困難您都能坦然面對。也許,這正是外婆您九十高壽的秘訣?
外婆,您不光給兒孫關愛,通過您的一言一行,使我們懂得了怎樣做人、做事,如今您傾心關愛的兒孫成為了對社會有微薄之用的人。飲水思源,我怎能不更加懷念您?
有人說: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女遠不及。外婆,今天,您的孩子們、孫輩們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過上了好日子,可是,您那比山高,比海深的情我們還未報答,“子欲養時親不在”的愧疚時時縈繞心頭揮之不去。我只能傾訴心聲,略表寸心。
苦,并快樂著
退休了,心力交瘁得快要“停擺”的我,終于有時間靜下心來梳理思緒,回首那生命長河中的朵朵浪花,回味那苦與樂相伴的歲月。
一
至今仍清晰地記得,我從師范學校畢業前夕,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校長辦公室接受上任不久的新校長召見,所談內容竟然是根據我的什么什么優點,決定讓我留校,并征求我的意見。(說實話,消息來得太突然,當時的我真感到喜出望外。)我只說了一句:“服從分配。”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后來宣布被留校的不是我,而是別人。聽了校長“要留男生,而非女生”的解釋及一些寬慰的話,我也只說了一句:“只要人能生存的地方,我都能生存!”便憤然離去。難道短短的幾天,我的性別就變了?真是世事難料,玄機弄人啊!
于是在那大中專畢業生由國家統分的年代,在當年那“做縮小城鄉差別馬前卒”的大背景下,我和班上西昌的全體同學背上行裝奔赴彝家山寨小學任教,于是有了那段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
二
我與同班的一個樸實善良的彝族女生阿洛一同被分到大箐公社(現在的大箐鄉)中心小學。
我倆按通知時間準時到校報到,沒想到學校竟無一人,迎接我倆的是那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低矮圍墻圍著的,坐落在半山腰兩級“梯田”上的泥土作墻,青瓦蓋頂的幾間小屋。它們分別是教室、教師宿舍、廚房、廁所。這,就是我們的學校。學校建在西(昌)寧(南)公路邊的一道高坎上,坎下是公路,公路下邊是供銷社、公社、林場。東、南、西三面環山,山上都是翻著綠浪的飛播林海。準確地說,學校就是建在半山腰的一個略為平坦的空地上。如果孩子們在學校門口的小小“操場”上玩球,一不小心,那么,球不是落入山溝,就是滾到山下。
開了宿舍大門,一股濃烈的令人窒息的羊羶味撲鼻而來,定睛一看,正對宿舍大門的屋子正中(即農家的堂屋)有一個火塘,火塘周圍一片狼藉,大大小小長滿白霉的羊骨頭滿地都是。也許,有人曾在這里聚餐卻未曾打掃便急于離去。
眼前的一切,著實使我猶如掉進了冰窟窿——從頭涼到腳。這時,阿洛——確切地說是即將的同事已找來清潔工具,挽起衣袖和褲腳開始灑掃,受她感染,我也屏住呼吸開始打掃衛生。我倆的勞動換來了屋內的清潔,然而仍然不見同事們的身影。
天漸漸黑了下來,一想到在這大山之間,松林之中,竟只有我們兩個黃毛丫頭,恐懼頓時襲上心頭。我們找來扁擔把那不堪一撞的破門抵了又抵,我倆傻坐在寢室內屏息靜氣,等待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屋外,呼呼的風聲掠過屋頂,遠處,不時傳來一兩聲不知名的野物的叫聲。我的心緊縮著、緊縮著,我似乎聽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聲。莫非我倆真的在坐以待斃?不行!我們又找來棍棒,甚至還找到一根短鋼釬為我們壯膽。
一整夜,我豎著耳朵聽動靜,睜著眼睛等天明,盼著黎明快快拉開夜幕,哪還有一絲困頓之意?
終于,東方漸漸露出了魚肚白,林中傳來了小鳥的啼鳴,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啊,漫長的驚恐之夜總算過去了。
三
初來乍到的彝家山寨生活開始了。全公社只有我倆是女教師,不知校長出于何種考慮,安排我倆到與公社中心校相距六里的一個生產隊創辦村小——招收一年級新生,并由我倆承擔該校的一切工作。于是,形影不離的我倆來到生產隊報到。隊長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彝家漢子。那深陷的眼眶、高高的顴骨,菜綠色的臉上寫滿窮困。對于我倆的到來他很高興,代表生產隊送給我倆老南瓜、松柴。在他的帶領下我們來到了教室——一個生產隊廢棄的牛棚,一個低矮、昏暗、無門無窗的茅草屋。天啊,這是什么教室!走進屋內,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用石頭支撐著木板搭成的“桌子”和“凳子”,竟然連砌也未砌一下。我和同伴只好在這樣的教室里執起了教鞭。課堂上有時隨著“砰”地一聲,不是這個孩子的凳子垮了,就是那個孩子的桌子又塌了。隨之而來的是孩子的哭聲和阿洛我倆既要一邊查看孩子是否被砸傷一邊安撫孩子,又要重新支撐桌凳接著進行教學的忙碌。冬天,我倆要在教室里為穿著破爛單衣的彝家孩子們燃起那驅寒的火堆。當太陽給我們送來溫暖時,當陰天茅屋內光線實在太暗時,我倆索性把孩子們帶到教室外的空地上學習。那情景是當時生活在都市的人們和今天無論生活在哪里的人們都難以想象和不敢相信的。
放學后,我倆和當地的老教師一樣種菜、背柴、做飯。所不同的是我們還有年青人昂揚向上的激情,在不愿隨波逐流的個性和害怕落入封閉、落后的心態驅使下,我倆為自己制定了作息時間,并嚴格執行。
每天早晨六點半至七點半,我們在馬燈下看書學習,鞏固所學知識并自學新的知識。接著進行風雨無阻的晨練。(跑一公里盤山公路,再做一套廣播操)。寒來暑往不懈堅持的結果受益多多,就連那常給我“預報”天氣的關節炎竟也奇跡般地消失了。
上課時,初入學的彝家兒童要完全聽懂漢語,而且還要學懂書面語言,難度可想而知。每節課,我倆都在教室里。我執教的學科,我先用漢語教學,聽不懂的地方,阿洛再用彝語翻譯,顯然,阿洛的工作量比我大多了,但為了孩子們,也為了給我排憂解難,她仍然樂此不疲。有的問題,我倆琢磨怎樣才能因人而異,由淺入深,去繁就簡。譬如當時“iu、ui、un”三個復韻母的教學,教材要求先教拼讀成音節“iou、uei、uen”然后再教省寫規則,即省寫為“iu、ui、un”,而我們干脆不走彎路直接教學生省寫后的讀寫。要知道,我們這一自創方法竟早于教材改革好幾年呢。當時我曾就這一教學的想法及這樣教孩子是否得當去信《小學語文教師》編輯部,但未得回音。
說到放學后的種菜、背柴,雖然我曾有過“知青”經歷,也非嬌生慣養之人,但與阿洛相比,無論體力還是耐力,我都只能甘拜下風。你看,她那一大背柴喲,我挪也挪不動,而善良的阿洛從不計較,每次勞動她不但竭盡全力爭取多做,還處處關照著我。
那時,我倆每月都要徒步到距學校十里之遙的崗窯糧站去買米,再把米背回學校。往返可是二十里啊。每次背米回來的路上,阿洛已累得汗流浹背,氣喘噓噓時,我要換背一程,她卻說什么也不肯。她總是放下背篼,歇歇又背上繼續前行。
我常想,在那樣艱難的環境中,如果沒有善良純樸的阿洛,苦不堪言的我豈不雪上加霜?真應了那句:命運給你關上一扇門的同時,會給你打開一扇窗啊。
四
一天,校長帶來口信,通知我倆晚飯后到中心校開會。會議結束后已是夜間九點過,但中心校沒有我們兩個女孩的住宿之處。我倆只好回村小。我倆提著一盞馬燈,手挽著手疾步走在月黑風高的林間山路上。
夜,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夜間的山風也不再溫柔,它像一個撒野的潑婦不停地暴躁地搖晃著那高高的但并不茂密的樹梢,發出令人膽寒的呼嘯。我用右手緊緊挽住阿洛的左手,因為我們誰也不會把對方落下,再說也能互相壯膽。我的左手提著那盞用煤油點燃的馬燈,我把左手盡量伸直想使馬燈離我倆遠一點,我想這樣既可恍恍惚惚看見路,又不至于讓人看清走在這恐怖之夜的林間山路中的竟是兩個女孩。
一路連走帶小跑,我們的速度已到極至。突然,我好象聽到背后有腳步聲(事后聽阿洛說,她也聽到了。)曾聽人說,在山林中走夜路,聽見背后有腳步聲千萬不能回頭看,即使有野獸的腳掌搭在你肩上也絕不能回頭,否則,野獸那尖利的牙齒就會準確無誤地咬住你的咽喉。雖然至今我也未考證過這種說法的真偽,但當時越想越怕,不寒而栗的我們也只有聽天由命了。所幸,那可怕的一幕并未出現。后來我們想也許是過于緊張出現的幻覺?也許是寂靜山谷中我們自己腳步的回聲?至今不得而知。
驚魂未定,朦朧中又見一個黑影出現在前面不遠處,我的心似乎就要停止跳動。豁出去!只有豁出去了!我想:如果來的是林中狼,我們就提著燈順公路往下跑,因為曾聽說野兔跑下坡會栽跟斗,但愿其它動物也有此共性;如果來的是人中“狼”,我就把馬燈向他砸去,然后拉著同伴鉆入灌木叢中去,這樣,漆黑的夜里誰也看不見誰,也許誰也找不到我們。總之,無論面對的是什么狼,我們只能狠命一搏了!搏的結果或許有點勝算,或許烏呼哀哉。在當時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境況下我們還能有什么更好的選擇?
近了,更近了。終于看清了,原來它是孤立于公路邊的一棵樹。我們懸著的心總算暫時放下了。接著,我倆手挽手相互依偎著走過了路邊有許多墳墓的一段路,走過了曾有人翻車被奪命的危崖之上……
終于,我們終于平安到達我們暫時借住的林場檢查站。一進屋,我倆竟都癱倒在床,許久動彈不得。
五
一次又一次的驚嚇、歷險,還有那難以想象的困難,使我真有些挺不住了。我畢竟只是一個弱女子。那時,我一遍又一遍讀著詩人郭小川的《山中》,里邊最能引起我共鳴的是:
“我要下去啦——
我思想的翼翅不能在這兒飛翔,
我要下去啦——
在這呆久了我的心將不免憂傷,
我要下去啦——
簡直來不及收拾我一小卷行裝……
冷漠、寂靜、安詳,
一切都似乎是這樣怪誕和反常,
那輕捷的蝴蝶般的落葉,
跌在地上也發出驚心的巨響。”
然而,去又怎樣?留又如何?我有些彷徨。
一天放學后,我和阿洛照例到松林中撿柴,我又看見了那點綴在山林中的山茶樹。此時已是冬季,在風霜的摧殘下,連那不畏嚴寒的不老松的些許針葉也斷了戀枝情結跌落下來.。只有山茶樹仍然新枝簇擁著老干,蓬蓬勃勃充滿生機。那油亮亮的、淺綠的、深綠的樹葉無不鮮活得就要滲出油、滴出水來,這樣的枝葉襯托著那開得正旺的或深粉、或淺粉、或白色的似童子顏面的花朵;襯托著那羞答答“半掩琵琶半遮面”的還未完全張開笑臉的粉紅色花兒;襯托著那正蓄勢待發的花蕾;簡直美得讓人心醉!每一片葉,每一朵花,真的似乎都有一個新的生命在顫動。這旺盛的生命力是被人們精心伺弄的園林茶花無法比擬的。此情此景使我陷入了沉思……
后來,我在朋友攝下的山茶花照片背面寫下了我的選擇:
植根于貧瘠土壤,
不畏冰雪與風霜,
迎風斗雪放異彩,
山茶風格應效仿。
我將照片轉贈給一個同樣處于艱難困苦中的同學,希望我們互相勉勵。同時,我采下幾枝山茶花,帶回家為父母插在花瓶中,希望他們感受女兒的愉悅(盡管當時的我并無愉悅可言),不要再為在山中工作的女兒放心不下。
六
開學一段時間了,因為我們的學生還是太少(僅附近幾個生產隊讀一年級的孩子),校長決定讓我倆帶著我們的新生合并到中心校。
轉眼間,兒童節即將到來,我倆自作主張自編、自導、自制道具為孩子們組織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別開生面的“慶六·一”文藝演出。舞臺,是那不太平整的山地操場;背景,是那郁郁蔥蔥的松林;節目,不敢用藝術的水準來評價。然而,附近的家長們來了,公社領導來了。公社書記的講話有鞭策,有希望。他們的喜悅之情溢于言表,孩子們興高采烈地唱啊!跳啊!
“六一到,六一到,
我們的節日來到了,
火紅的太陽當空照,
朵朵葵花齊歡笑。”
至今,這歌聲仿佛還縈繞在耳邊,這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你可知道,這是彝家山寨孩子們開天辟地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啊!
七
逐漸適應了山寨生活,晚飯后,晴天我倆乘著悠悠的涼風,伴著紅紅的夕陽來到天然氧吧——路旁的林中或繡花或針織,太陽透過樹梢將斑駁的余輝灑在我們身上,好不愜意;雨天,我倆在屋內或看書或聽收音機或聊天倒也自在。
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我站在高高的彝家山寨“舉頭望明月”時已沒有當初那“低頭思故鄉”的惆悵,那碩大的圓月似乎就掛在樹頂上,它將皎潔而柔和的光撒向大山,撒向林海。學校旁的一條山溪清晰可見,它來自山頂,順溝而下,在寂靜的夜晚潺潺溪水唱著歌兒彈著琴弦流向遠方。偶爾溪中的石蚌(蛙類中的一種)或獨唱或合唱與溪聲應和著。
捉石蚌去!校長一提議,我們幾乎全體出動,有的拿口袋,有的拿電筒,跟著校長來到溪邊,也許是小溪的山泉清澈透明,石蚌無處藏身,也許是在這大山里不常有人驚擾,在電筒光照射下石蚌竟傻傻的,它們有的趴在溪中石頭上,我們雙手一罩便將它俘獲;有的游在水中,我們雙手一合攏,它便被生擒。順著小溪搜索了一小段,我們便滿載而歸。第二天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這美味佳肴——被我們或清燉,或紅燒的石蚌。有時餐桌上還少不了彝族男教師夜間狩獵的戰利品——回鍋野豬肉、黃燜野雞、小炒的麂子肉。那可是真正的無污染純天然的美食啊。那香味,誰能忘?就是我們用親手種出的金燦燦的玉米熬粥喂大的豬,其肉味也不能與之媲美。(寫到這里,我感到慚愧,因為當時國家還沒頒布保護野生動物的相關政策法令,人們對維護生態平衡,保護野生動物的意識還很差。)
八
后來,因為工作調動,我和阿洛先后離開了彝家山寨。但那段苦,并快樂著的時光常使我夢縈魂繞。是那段歲月使我練就了困難面前不低頭的韌性;使我學會了在逆境中生存的技能;使我收獲了真摯的友誼;更升華了我豁達、寬容、善良的美德。
這段生活經歷還使我感悟到,身為凡夫俗子,我們的人生難免會遭遇困境,當身處困境時,如果我們沉淪、頹廢、放棄。那么,我們就會怨天憂人,一蹶不振,痛苦一生。反之,只要我們用積極向上的心態面對,那么,辦法總比困難多。那種苦并快樂著的心態會有助于我們擺脫困難,走出逆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