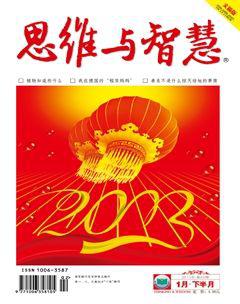拇指朝外
陳建寬
那是一堂美術課,老師教的內容是畫巧手。
老師先教同學們玩手指游戲,就是讓自己的手指變出各種不同的手勢。老師先做了幾個簡單的示范動作后,讓出了一段時間,由同學們自由想象。
班里一下子炸開了鍋,同學們一個個地伸出自己的手掌,高興地擺弄著各種可愛的姿勢。變出的手勢,有的像孔雀的尾巴,有的像山羊的角,有的像仙人掌,有的像雞冠……
一只簡單的手掌,居然能變出這么多的形象,這讓同學們愈發感到新奇,他們玩得興致盎然。
講臺上,老師看著同學們豐富的想象力,不住地頷首點頭。
接下來,老師開始布置作業——從自己變出的手勢中,挑出一個你最喜歡的,將它畫下來。班里慢慢靜了下來,同學們都拿出了圖畫紙,一只手比畫著,另一只手拿著畫筆,開始在紙張上描畫起來。
同學們都沉浸在藝術的海洋中,就在這時,角落的一個女生,突然“哇”地一聲哭起來。老師循聲望去,坐在女生旁邊的男生,正用拇指和食指,比畫著一個“手槍”的動作,指著小女生的頭,嘴里興奮地喊著:砰——砰——旁邊的幾個同學忍不住哈哈大笑,旋即學起那位男生的動作,指著小女生的后背、后腦勺。
坐在后面的同學見狀,也不由地學起了那個動作,不亦樂乎地像諜戰片里的鏡頭一樣,對著那個女生的方向,玩起了“手槍”游戲,有幾個男生,甚至右手架在左臂上,玩得起勁。角落的那個女生,嚇得躲到了桌子底下。
學校百年校慶,校方邀請了一批曾從這里畢業的老校友,為師生們做講座。其間,葉教授飽含深情地回憶起她學生時代的這一幕。
這位蜚聲海內外的大師級教授,那是需要仰視才能見到的。
禮堂里一片沉寂,臺下所有的師生,仿佛置身于神圣的教堂里,接受著圣潔的洗禮。
葉教授的聲音有點顫抖,她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鏡,繼續說:“那是我最為難忘的一堂課,至今仍針尖般地扎在我的心窩。我是個早產兒,那時候的身子骨比其他同學都要弱,經常在課堂上打瞌睡,成績老上不去。那時的我既黑又瘦,同學們常戲弄我、取笑我,叫我笨小孩兒。”
“我很感激當時的那位老師,是他的一番話,讓我得以轉身,從而瞥見了窗外的陽光。”葉教授雙眼朦朧地說。
老師看見同學們在欺負我,語重心長地說:“同學們,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兩個口袋,前一個口袋,裝著的是他人的不足;后一個口袋,裝著的是自己的缺點。我們總是習慣把前一個口袋掛在顯眼的地方,把后面的口袋深藏起來。殊不知,當你轉身時,你后面的口袋,便一覽無遺地暴露在眾目之下了……”
“那位老師的一句話,至今還溫潤著我的心田,它成了我這一生的座右銘。”葉教授滿眼淚花地說,“那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學會將這個手勢反朝自己,讓問責的食指反視自我,讓長著天使般眼睛的拇指,朝向他人。”
臺下,良久的沉默后,響起了浪潮般的掌聲。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舉起手來,模仿著那個平常而不平凡的動作,然后調轉方向,拇指朝外,食指朝內,向著自己的胸膛比試……
(余娟選自《山東青年》2012年第7期)
- 思維與智慧·下半月的其它文章
- 漫畫之頁
- 或許你就在成功的路上
- 善良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事情
- 逼良為優
- 說“錢”
- 書籍本來沒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