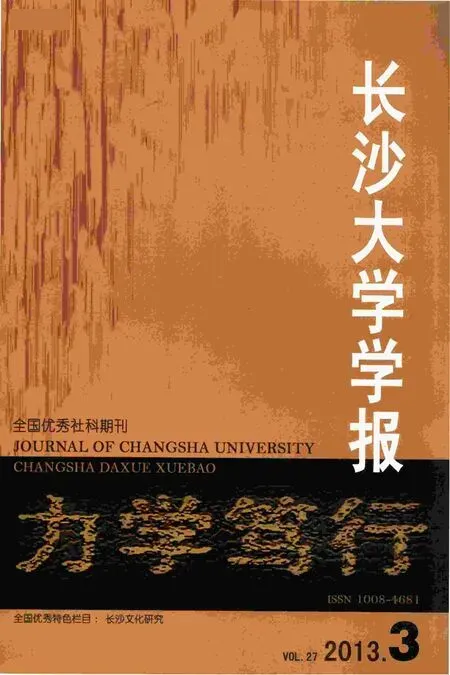對《戰爭垃圾》中戰爭創傷的解讀
李明嬌
(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廣東廣州510520)
迄今為止,哈金出版的很多作品獲得了美國文學界重要獎項,《戰爭垃圾》獲得2005年度美國筆會/福克納文學獎。本文將通過對哈金長篇小說《戰爭垃圾》的文本分析,結合創傷理論,指出小說主人公“我”所經歷和見證的戰爭創傷和政治創傷以及“我”的創傷治愈過程。
一 創傷概述
《韋氏第3版新國際英語詞典》指出,創傷是指“外部暴力對人體造成的傷害,可能導致受害者行為或情緒混亂,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精神和心理上的震驚。”[1]早期創傷研究者皮埃爾·熱奈認為,自我意識是一個人心理健康的關鍵。一個人過去的經歷與他對現狀的準確的感知直接決定這個人是否能夠對精神上的壓力做出適當的反應。對過去經歷記憶的合適分類和完善使得人們能夠形成不同的認知框架,這些框架能夠幫助他們面對相應的挑戰。然而,在創傷經歷和強烈情感的折磨下,人們無法把他們那些恐怖的經歷與現有的認知結構一一對應。當創傷經歷無法被融入到創傷幸存者個人意識的整體框架中時,他對過去的創傷經歷會產生一種依戀,這種依戀將會逐漸腐蝕人的心理健康。Dori Laub以類似的方式對創傷做出了闡釋。他指出,“創傷幸存者不是跟過去的記憶一起生活,而是跟一個沒有結尾、沒有結局的事件一起生活,幸存者雖然得以幸存,但是在日后的生活中仍然為這種創傷所困。”[2]創傷最常見的表現形式有三種:歇斯底里癥,“炮彈休克癥”——即戰爭中由于炮彈爆炸而導致的士兵的精神錯亂或精神崩潰,以及由于強奸、亂倫或家庭暴力而導致的心理創傷綜合癥。對于創傷的治療,熱奈建議治愈創傷的關鍵在于把創傷的記憶轉化成個人敘事。19世紀90年代中期,研究者們也發現當創傷記憶以及伴隨創傷記憶的一些強烈的感情能夠以語言的方式呈現出來時,歇斯底里癥的一些癥狀也會有所減輕。Dori Laub在闡釋創傷的同時,也對創傷的治療提出了一個方案——“建構一種敘事,重建一種歷史,使創傷事件得以外在化”。他認為,當一個人能先置身事外地清晰地用文字來表達這個故事而后接受這個故事時,這種創傷事件的外在化才能得以實現并產生效果。
二 創傷的見證
《戰爭垃圾》的敘述者“我”是一位退休英語教師。“我”經歷了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多次巨變,其中抗美援朝戰爭中為期三年的戰俘營經歷成為了“我”內心深處最痛苦的記憶,它就像一場揮之不去的噩夢,給“我”的身體和心理造成了永久性的創傷。小說通過主人公回憶錄式的敘述,向讀者講述了作為戰俘的“我”在朝鮮戰爭戰場上所經歷的戰爭創傷和政治創傷。
戰爭一開始,“我”就見證了戰友唐晶所經歷的“炮彈休克癥”。“炮彈休克癥”給“我”帶來了強烈的心理震撼和沖擊,作者敘述到:“唐晶張開了嘴巴卻沒有發出聲音,他全身顫抖著,說不出話。兩個醫生一致診斷他是患了‘炮彈休克癥’。‘炮彈休克癥,他精神錯亂了。’李醫生說。‘我不信,他的身體如此健壯,怎么會這么容易就神經錯亂了?’”整個師的軍官都因為死亡的士兵和損失的軍需品而惋惜,而最讓“我”震驚的卻是唐晶的事。一個星期以來,他那張麻木的毫無表情的臉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我”從沒想到一個身體如此健壯的軍官在戰爭中是如此不堪一擊,精神是這么地容易被打垮。如果說唐晶是親身經歷了“炮彈休克癥”的話,那么敘事者“我”就是親眼見證了這次創傷的起因和后果。對于這種創傷的見證也對敘事者內心造成了巨大的震撼。
在“我”看來,這場戰爭不僅讓戰俘飽經創傷的折磨,還把他們變成了戰爭垃圾。作者把小說的題目定為“戰爭垃圾”不僅表明了作者對這場戰爭的反對和厭惡態度,還揭露出了它的荒謬性和對人性的摧殘。作者花了很多筆墨來描述戰爭給士兵造成的身體和心理上的創傷,“……新收容所的傷員比其他收容所的要多得多,缺胳膊的,瞎眼的;由于凝固汽油彈的轟炸而沒了頭發,缺了耳朵,少了鼻子的;借助手勢語來進行交流的聾子;借著拐杖和木制的假腿而到處走動的瘸子……看到他們,我不禁黯然傷神:沒有國家會收留像他們這樣殘缺不全的人,他們只是一堆戰爭垃圾……”這些士兵曾經懷著“保家衛國”的熱情和信念參加了這場戰爭,然而結果卻是,戰爭過后他們成了身心都不健全的戰爭垃圾。他們這樣的人,對于他們自己的家庭、國家甚至整個社會,都將成為一種負擔。沒有國家愿意收留他們,即使他們回到中國,他們的生活也會因為自己身體的不健全而擁有諸多的不便,他們不僅要想辦法去面對身體上的創傷,更要設法走出心靈的創傷。
另外,在國民黨操控的戰俘集中營,存在兩個政治黨派——國民黨和共產黨。戰俘營中對待兩個黨派戰俘的態度和待遇有天壤之別。這種差別在“篩選”一章體現得尤為明顯。堅守共產主義信仰的劉武深因為拒絕去臺灣,被親美派的劉泰安當眾割去了胳膊上那塊紋有國民黨徽章的肉。這種因為國共兩黨之爭而引發的變相的暴力不僅給“我”和“我”的戰友帶來了身體上巨大的傷害,也給“我們”的心理造成噩夢般的創傷,它讓“我們”對自己的政治信仰充滿了危機感的同時,還讓“我們”對于未來充滿了迷茫——到底“我們”該何去何從?跟劉武深一樣,一直堅守共產主義信仰的“我”也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轉夜之間,“我”身上被人紋上了“(FUCK COMMUNISM)”的字樣。這個紋身讓同“我”一樣有共產主義信仰的士兵遭受了永生難忘的政治創傷。“紋身讓我不寒而栗。帶著這樣的紋身,我又怎么能回到中國?”這個創傷成為了“我”永生難言的秘密,成為一種無法言說的傷痛,伴隨我的余生。這一點在小說結尾部分得到了充分的印證。“在我的肚臍下方有一排英文字母‘FUCK…U…S…’,這些點點所覆蓋的皮膚看上去像燒傷的傷疤……它成了我心里揮之不去的陰影。兩周前我在亞特蘭大過海關時,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生怕海關官員會發現什么可疑的地方,然后把我帶到一個屋子里讓我脫下衣服來檢查。這個紋身是很有可能讓我進不了美國大門的。我走在街上時,會時不時地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似乎有一只無形的手會掀開我的T恤,把我的秘密——紋身暴露給旁邊的行人。無論天氣多么酷熱,我都不會解開所有的衣扣。當我洗澡時,我會很小心地鎖上浴室的門,以防我出生在柬埔寨的媳婦會無意中瞥到我肚臍上的字眼。”雖然戰俘營中的身體上的創傷早已忘卻,但身上的紋身對“我”戰后的生活而言就如同一個揮之不去的噩夢。“我”時刻擔心“我”的秘密會被人發現,更加擔心會因為這個紋身而無法跟家人過上正常的生活。很顯然,這個紋身不僅僅是戰爭給“我”帶來的最直接的身心創傷,更把戰爭中的政治創傷表現得淋漓盡致。
三 創傷的治療
心理創傷的核心經歷是創傷者覺得自己被剝奪權利以及與外界的正常聯系。因而,治療創傷首先應該授予創傷者以權利,并幫助創傷者重新建立他與外界的聯系。創傷的治愈應該以豐富的人際關系為背景,孤立的狀態無法實現創傷的治愈[3]。縱觀整部小說,雖然身為戰俘的“我”身心備受戰爭的摧殘,但家中老母以及未婚妻對“我”的牽掛和期盼,是“我”受到打擊和經受創傷時的一種莫大的安慰。出征前夕未婚妻贈送的半根玉簪伴隨著“我”度過了戰俘營中的日日夜夜,對過去溫馨的記憶和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撫慰著我寂寞和痛苦的身心,一直鼓勵著我堅持到最后。
另外,戰俘生活中的友情也是幫助我走出創傷的一個非常重要因素。除了我與戰友白大建、善明等的友情之外,小說還單獨用了整整一章(第四章)的篇幅講述了“我”與格林醫生的相遇和相識。作者用小說最長的一章強調了友情在“我”的創傷治愈過程中起的非同一般的作用。在戰俘集中營的醫院,戰友古樹的受傷的腿在托馬斯醫生給動完手術之后因為潰爛而長滿蛆的情景讓“我”觸目驚心,因此“我”堅持拒絕讓托馬斯醫生給我的腿動手術。這才有了格林醫生的出場:“新來的醫生走過來拍了拍我的額頭。我睜開眼睛,居然看到一個女醫生。她看上去不到30歲……她淡褐色的眼睛盯著我,眼中充滿了和善,嘴角露出了一絲微笑。讓我吃驚的是,她居然用一口漂亮的漢語說道:‘我是格林醫生,可以讓我看看你的傷嗎?’……她的手指在輕輕的觸摸、按壓著我的傷口。我感到她似乎把某種涼涼的、緩解疼痛的東西放在了我的傷口上,我不再感到那么痛了。”對正在忍受病痛折磨和內心充滿了恐懼的“我”而言,格林醫生的出現就像是圣母瑪利亞的再現,頓時給了我一種安全感,這種安全感不僅幫助我緩解了身體上的疼痛,而且還讓我在絕望中重新看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她的出現讓我感到很平靜,似乎她就是被派來救我的……‘別擔心,我一定會治好你的腿,你一定可以重新站起來的!’”能擁有格林醫生如此細微的關心和幫助,戰俘營中的“我”慢慢走出創傷的陰霾!“看到我醒了,她對我笑了笑,說:‘一切進展得都很順利。’她的話讓我很放心。”動完手術之后,格林醫生又幫助“我”練習走路,在她耐心的幫助和鼓勵下“我”終于重新站了起來,終于能夠走路了!“我”與格林醫生的相遇、相識到深厚友情的建立,是“我”可以治愈自己身體創傷的關鍵。除此之外,與格林醫生的友情也讓戰俘集中營中的“我”擁有了安全感,在殘酷而令人絕望的戰爭生活中找到了生存下來的希望,這在很大程度上對“我”走出前后經歷和見證的心理創傷奠定了基礎。
此外,小說中多次提及學習英語這一事件,從“我”的敘述中,讀者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學習英語知識對于治療創傷的作用。戰爭剛開始不久,裴委員長就讓“我”教我的戰友們一些簡單的英語,在漫天炮火的戰場上,他們居然學得非常帶勁,而且進步很快。“我很好奇為什么他們會這么用心地學這些他們可能永遠也用不上的英語單詞。我猜想學習對于他們而言肯定代表著某種希望。至少這對他們來說意味著還有將來,他們可以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將來。他們對這個大千世界有限的認識和他們對死亡的遲鈍反應給了他們求生的力量。他們強烈的學習欲望中折射出了他們對于生命的堅韌不拔的精神,我深深地為這種精神所打動了。”學習代表著還有未來,代表著一種希望。有了希望,有了對未來的那份信念,眼前一切的創傷和痛苦都會因為對未來的這種信念而漸漸消逝。戰爭留下的創傷會被暫時性地遮蔽起來,甚至逐漸被淡忘。對“我”而言,英語既是“我”學習的動力,也幫“我”度過了戰俘營中很多難熬的時光,對“我”在集中營生活中暫時性地走出創傷甚至最后治愈創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與伍德沃斯神父的相遇讓“我”很幸運地得到了一本《圣經》。《圣經》的出現很及時,它里面的英語不難,“我”沒有碰到不認識的單詞。這意味著從現在開始“我”每天都可以讀幾頁《圣經》了!”“我”對英語知識的渴求和《圣經》的出現對于治療“我”所經歷和見證的創傷起了催化作用,它不僅撫慰了備受戰俘生活折磨的“我”的孤獨和寂寞,而且還讓“我”在戰火連天的令人絕望的戰爭生活中找到屬于自己內心的一片凈土,在這片凈土中,找到了心靈的慰藉和寄托。最后,“我”甚至還用英語寫出了自己三年戰俘生活的經歷,講出了自己經歷的創傷和見證的歷史,從而為敘事治療提供了可能。
創傷研究者指出,與所有的敘事一樣,創傷敘事首先具有認識論的價值,我們在敘事中把握了生命中令人驚悸或疼痛的時刻,為它賦予了意義。對于創傷性事件的敘述往往包括對事件來龍去脈的呈現、對原因的探索和對內心的描繪,這其中包含著外部世界的豐富信息,和對人與世界關系的認知,并有可能指向人性的深處。創傷敘事也同時具有倫理學的價值,它可以是一種撫慰,還可以是一種治療,說出是康復的前提[4]。整部小說以“我”對朝鮮戰爭經歷的回憶來講述了“我”親身經歷的創傷以及“我”所見證的戰爭給中國戰俘帶來的心理創傷。通過主人公“我”的敘述,建構了一種敘事,重建了一種歷史,使得創傷事件外在化。小說的主人公“我”以回憶錄的形式講述了他深藏心底的最痛苦的記憶——“抗美援朝”戰爭中三年的戰俘生活。這部回憶錄他計劃了大半輩子,在開篇的序言中,他便點出了寫這篇回憶錄的初衷,“我要用我從十四歲起就開始學習的英語來寫,要用紀錄片那樣的方式說出我的故事,保留歷史的真實。我希望有一天,坎迪和鮑比(他的兩個在美國的孫子)和他們的父母讀了這些事情,能感覺到我肚子上紋身的分量。”[5]對于“我”而言,通過回憶錄方式講出自己人生中這段創傷性的經歷,是我治療創傷、最終真正走出這段創傷經歷的必然選擇。很顯然,最終“我”做到了,因為“我”通過自己的敘述,成功地講出了“我”所經歷和見證的創傷,重新見證了歷史,“讓自己的苦難有了出聲的機會”[6],讓自己的創傷得到了治愈。
哈金的長篇小說《戰爭垃圾》通過“我”講述自己在戰俘營中經歷和見證的戰爭創傷和政治創傷以及“我”走出創傷的過程,不僅讓讀者看到一個戰俘獨特的生活命運,見證了歷史和真相;而且還通過對“我”的戰俘生活經歷的描寫,揭露了戰爭的殘酷與荒謬,鞭撻了戰爭對人性的扭曲和摧殘,再現了戰爭給人類帶來的難以磨滅的精神創傷。
[1]韋伯斯特.韋氏第3版新國際英語詞典[M].馬薩諸塞州:梅里厄姆·韋伯斯特公司,1909.
[2]弗洛伊德.歇斯底里癥研究[M].倫敦:霍加斯出版社,1962.
[3]Shoshana Felman.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M].臺北:麥田人文出版社,1997.
[4]羅爾夫·泰德曼.阿多諾全集[M].法蘭克福:休坎普·維格威公司,1970-1980.
[5]Ha Jin.War trash[M].New York:Pantheon Books,2004.
[6]Judith Lewis Herman.Trauma and recovery[M].New York:Basic-Books,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