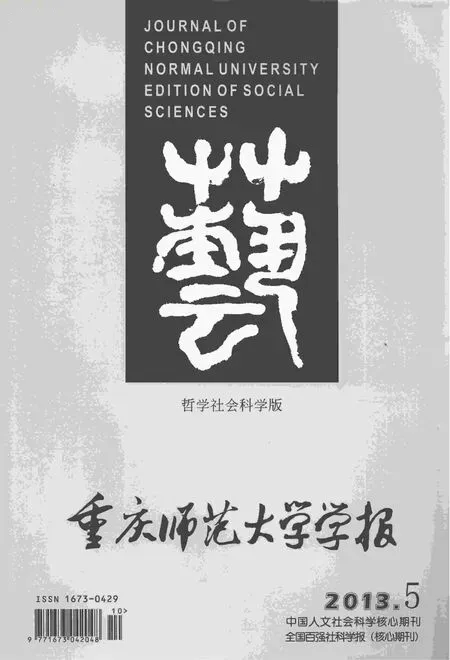論抗戰電影知識分子“被大眾所化”的“原罪”意蘊
張育仁
(重慶師范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0047)
一、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雙重身份
由于左翼政治文化思潮以及“五四”民粹主義的持續影響,在抗戰文化運動的演進中,宣教者,亦即啟蒙者常常又是以“被改造者”,亦即被啟蒙者的雙重身份出現的。文藝服務于抗戰,首先必須服務于大眾,因此,文藝必須大眾化。而文藝大眾化的前提必須是放下知識分子的“臭架子”,迫使其重新站在大眾的立場、向大眾學習,并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在“文藝大眾化”的討論中,這種理念占壓倒性優勢。幾乎同一時期,重慶及大后方文藝界廣泛展開的關于“民族形式”的大討論中,這一“改造自我”使之轉變到大眾立場,進而通過服務大眾,更好地服務戰爭的“邏輯思路”,得到了更加廣泛的回應,其中詩人的回應更富有激情。田間寫道:“人民,每一分鐘在前進著,我必須每一分鐘跟著人民前進。為著取得我與人民的共鳴——謹防為一朵花而耽誤,謹防為一杯酒而耽誤,謹防落伍,要不斷改造自我。”【1】(36)
也就是說,若不虔誠地“改造自我”,是根本沒有資格作民眾的宣傳員和啟蒙者的。1942年,“邊區詩人”嚴辰的表態傳到重慶,竟獲得重慶和整個大后方文藝界廣泛而熱烈的喝彩。他在《關于詩歌大眾化》的文章中闡述說:“我們必須先被大眾所化,融合在大眾中間,成為大眾的一員,不再稱大眾為‘他們’,而驕傲地和我們一起稱‘我們’,不只懂得大眾的生活習慣,熟知大眾的語言,更周身浸透大眾的情緒、情感、思想。以他們的悲痛為悲痛,以他們的歡樂為歡樂,以他們的呼吸為呼吸,以他們的希望為希望……只有這樣,我們的思想才不會矛盾,我們的創作才不會有兩面性,我們的大眾化才不是勉強而是自然的了。”【2】我們因此又不能不注意到,抗戰文藝大眾化除了戰時宣教目的外,更是以文藝家“自我改造”為深層原罪背景而提出來的。從抗戰時期詩文藝家的主觀愿望來看,固然有其積極的意義,但無疑也為日后他們能“自覺”投入“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埋下了具有悲喜劇意義的伏筆。抗戰文藝運動在持續推進的過程中,與這個強勢運動所提出的“大眾化”、“通俗化”口號緊密聯系著的,是同時又提出了文藝工作者以及所有服務于抗戰的知識分子,必須迅速達到自身的“大眾化”的要求,就實質而言,這是一場知識分子“被大眾所化”的轟轟烈烈的身心改造運動。電影界知識分子勢所必然地被這股強勁的運動浪潮所裹扶。
在這場“被大眾所化”的運動中,反明星、反技巧、反蒙太奇等等,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精神強制性的政治文化勢頭。這種政治文化“慣性”及壓力,反映到電影編創者、表演者乃至所有的電影知識分子那里,就形成了電影和電影人“被大眾所化”的一種政治文化奇觀。與戲劇、詩歌、小說等藝術樣式的創作者所遭遇的情景不完全相同——在電影和電影知識分子“被大眾所化”的語境中,蘊含著很深的原罪意識。
二、從資本的“原罪”到電影的“原罪”
戲劇(除了話劇)、小說和詩歌在民族身份認同方面,幾乎沒有太多的原罪意識。它們大多與民族傳統文化,包括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有著天然的血緣聯系,因而,電影以外的文藝知識分子在“被大眾所化”,特別是在向民族傳統文化“認祖歸宗”的過程之中,很少產生認同和被接納的文化心理障礙,尤其是文化自卑心理。但是,由于電影和電影知識分子思想深處有著濃重的原罪意識,因此這種“認祖歸宗”的過程就相當的艱難,其文化自卑意識也就在所難免。由于與民族傳統藝術缺乏血緣關系,電影在中國民族文化和民族藝術的譜系中,其地位就顯得十分尷尬——它不是民族文化藝術的“親子”,最多只能算作一個外來的“養子”,而且是“來路不正”!只是因為,電影不僅是西方現代文明的產物,而且從一開始就是商品經濟“唯利是圖”的產物,其原罪之深重可想而知。
在抗戰之前,電影界知識分子就已經發表了大量文章,對這種產生于“資本”的電影的“原罪”進行過凌厲的批判和深刻的控訴。最早,我們可以在郁達夫的《如何救度中國的電影》中,見到他對電影“原罪”的批判和調侃。之后,陸續在鄭正秋的《如何走上前進之路》、嘉謨的《電影之色素與毒素》、唐納的《清算軟性電影論》,舒湮的《中國電影的本質問題》、塵無的《中國電影之路》,特別是席耐芳的《電影罪言》等等批判文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目睹這種“原罪”批判者的風采。
抗戰全面爆發以后,雖然電影知識分子對中國電影的“大眾化”乃至“民族化”轉型充滿了熱情與焦灼,然而,慚愧于電影藝術本身不是民族藝術的“親子”這樣的文化心理障礙,就使得他們在檢討和反思電影“大眾化”和電影人的“被大眾所化”時,顯得負罪感十足,因而對這種來自“資本”和“商業屬性”的原罪耿耿于懷,痛苦萬分,在批判中充滿著深深的自責。這種源于非“文化血親”的心理自責,在電音的《電影是什么東西》一文中有十分具體生動的控訴描述:“當歐美影片初到中國來的時候,把歐美的習慣也傳到中國來了。在銀幕上映現出一男一女,扭抱著親嘴,甚至做出種種難堪的行為,于是場中的觀眾,‘吱……’地做怪聲大鬧。最近我看了一部歌舞片,表演的人,穿了薄到像蟬翼一樣的衣服,簡直就和沒有穿一樣,一面唱些下流的歌曲,還把接吻的聲音,插在歌詞里,跳舞的樣子,淫蕩極了。當時使我想到瘋人院里的情形,看到一些神經病人,脫光了衣服,手舞足蹈的樣子,毫無差異。這時,我又看到了環繞的觀眾,大都興高采烈,甚至模仿這些下流動作。我真懷疑我是在瘋人院里面而不是在電影院里。還有一些歐美片子,描寫強盜如何打劫銀行,如何綁票,如何殺人……”他因此還特別強調說:
根據美國社會學家布魯馬和浩灑的調查,在110個男犯中,有40℅說電影引起他們帶槍的欲望;28℅說電影教他們怎么去愚弄警察;12℅說看了電影,他們便計劃去綁票。又年齡在14至18之間,在252個女犯中,百分之25℅說看過描寫熱情的戀愛影片后,她們引起了性欲而有性交行為;38℅說電影使他們逃學去過放蕩的生活;72℅說電影教他們如何打扮使男人注意;30℅說因為電影的緣故和他們的親生父母有了沖突。【3】
電影知識分子的困惑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電影,為什么熱衷于拍攝這樣的反文化、反道德,甚至是反審美的影片呢?這種帶著“原罪”輸入中國的現代藝術形式,為什么又總是樂于被中國的編創者和制片商接受并仿效呢?電音在這篇文章中解釋說,這是因為——“有人說,電影的生意,是一宗冒險的買賣。各位試想想,事先花上那么大的一筆款,萬一賺不回來,豈不糟糕了嗎?可是,我們不必替他擔心,平均來說,這一批買賣,很少虧本的,有些竟大賺其錢,一本萬利。這又是什么緣故呢?上面說過,電影是大眾的情侶,每一個人,只要他耳目不殘,無論男女老少都喜歡他,只要是好影片,沒有不賺錢的。所以,一般聰明的商人,便樂于投資在這樁事業上面來。”
批判者們一致認為,“資本”的原罪,體現在電影從一開始就把它看做是“一樁冒險的買賣”。所以,電影和資本一樣,一出生就帶著深重的“罪孽”——“每一個毛孔里都流著骯臟的血!”電影最先引入中國,是在上海這個“冒險家的樂園”。資本家視電影為賺錢的工具,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到了抗戰期間,絕大多數電影知識分子都忌諱說“電影是商品”,而只能說,電影是“教育民眾的工具”或者“電影是戰斗的武器”。這種對電影商品屬性的有意識的規避,其實就不自覺地流露出一種深深的“原罪感”。中國電影界此時甚至還以一種痛不欲生的口吻苦訴道:
我們知道產生于資本主義國家搖籃中的電影藝術,如果我們不能意識著其內容的政治警覺性,而批判地去接受,勢必流為城市小市民層所欣賞的單純的娛樂品的。電影移植到我們這古老的民族里來,這一危機不僅隨帶著,甚且無形中構成中國電影界一種傳統的癥像。抗戰雖然使我們的制作方針在大體上進了一步,但嚴格地講,我們在抗戰初期的電影,無論內容與形式都還是停留在小市民群中。換言之,那時我們的作品,還夠不上走向街頭、走向農村與戰地的條件,因而起初我們實在沒有使電影對于抗戰中國的大眾與士兵,負起了教育和宣傳的作用。【4】
這段中國電影知識分子致蘇聯電影界的說辭,就是深負“原罪感”而痛不欲生的又一富有悲喜劇意味的生動證明。
三、聲討電影“原罪”是一條政治文化主線
中國電影在抗戰中為何沒有像戲劇、小說和詩歌等藝術品類那樣,很好地負擔起“教育和宣傳的作用”?沒有很好地轉型為“大眾化”和“民族化”的戰斗利器?在“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戰協會”的精英們看來,說白了,就因為它是由“資本主義國家”“移植”而來。它既是資本家賺錢的商品,同時又是“小市民層所欣賞的單純的娛樂品”。所謂的“危機”是與生俱來的,這“危機”其實就是“原罪”。許多電影知識分子之所以堅持認為“中國電影的路線”只能走“國營化”的道路,其實也是為了試圖使其擺脫“原罪”;電影“國營化”論者之所以要對“電影商人”作“最深苛的譴責”,也是尖銳地針對這種“原罪”而生發的:“自反侵略戰爭發動以后,戰線的延長使國家對于每個民營事業,不能予以切實的管轄,電影事業也不能例外,尤其中國電影的生長地都是處在半殖民地的租界上。我們可以看到,上海電影商人在大量制作雖與抗戰無關,可卻是充滿極麻木毒素的電影,香港電影商人照樣還在粗制濫造著所謂言情武打電影。一方面由于國家管理上有鞭長莫及之勢,再由于敵人惡勢力下被威逼利誘;更由于每個電影商人的利益關鍵所在,我們當然要對他們作最深苛的譴責。”【5】在“中國電影的路線問題”的討論中,對電影“原罪”的聲討,自始至終作為一條政治文化主線,貫穿在幾乎所有的討論者的意識之中。劉念渠說:“中國電影的路線問題,在基本上是中國電影的內容問題。如果我們不像電影商人那樣專從營業上著眼,而認識到電影是一種藝術;把握住藝術的社會任務,來制定攝片計劃,使每一部電影都是現實主義的作品,能夠反映現實,預示將來,無疑的,中國電影可以走向一條光明的道路。目前,像上海各公司競相攝制民間故事,只是一種投機取利,有意無意的幫助了敵人做粉飾太平的工作。”然而更嚴重的是——“抗戰電影也還是一頁空白。它沒有為抗戰中的中國留下劃時代的記錄,這都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6】“電影商人”“專從營業上著眼”,這就是一宗“罪惡”。電影要想擺脫“罪惡”,只有走反映抗戰現實、預示和指示未來建國的道路。而上海的電影商人之所以“有意無意的幫助了敵人”,也是源于利用電影“投機取利”的本性。不僅如此。王平陵的聲討,更將“資本家”的謀利本性與封建迷信的舊路劃了等號。他說:“關于今后中國電影的路線問題,個人覺得在消極方面必須打倒噱頭主義。必須肅清上海電影界開倒車的傾向。例如,仍回到過去神怪、迷信、封建的舊路、為娛樂而提倡電影、死抱著賺錢主義,把電影盡量迎合一般有閑者的嗜好。”【6】其實,這樣的聲討,無不是著眼于電影的商業性“原罪”。在這樣的語境中,所謂“封建的舊路”,所謂“為娛樂而提倡電影”,所謂“死抱著賺錢主義”,所謂“迎合一般有閑者的嗜好”等等,說的幾乎都是同一個意思,那就是電影是有“原罪”的。針對電影的這種“原罪”,田漢更憤慨地提出要堅決肅清電影戲劇界的準“農奴制”。在他看來,這種準“農奴制”的形成,就是電影被“資本家”視作商品而必然產生的另一重“罪孽”。為此,他義憤填膺地高喊出“這種可惡的準農奴制必須打倒!中國無數的‘肅蔗普欽’(俄國農奴制時代的名伶)必得解放!”【7】蘇怡甚至提出應該掀起一場激進的“電影清潔運動”的倡議,說到底,其實都是針對電影的原罪發出的。他說:“我們試一回憶,中國自有電影史以來,有沒有過清潔的時期?沒有的。盡管有不少制片公司、制片家、工作者曾經做過不少的有益于社會的清潔巨片,但是不清潔的神怪打殺、誨淫誨盜的片子,卻依然未曾絕跡。粵語片興起以后,盡管也有不少優良的巨片,但到了去年,整個影業所表現的事實,已是每況愈下,越來越糟。過去,現在,為什么不能清潔呢?”【8】
四、“電影清潔運動”與電影知識分子的身份焦慮
蘇怡本人也是一個堅定的“電影國營”論者。在將資本的罪惡與封建的罪惡做等量齊觀的評價和批評方面,他與田漢、王平陵他們一樣充滿著對電影原罪的文化道德批判激憤。在這篇名為《電影清潔運動之我見》的批評文章中,他義憤填膺地控訴道:“實在說,在今日這種封建殘余迄未肅清,一切以經濟為中心的社會里,真正的藝術,已經得不到本身忠實的評價,何況作為一種商品的中國電影事業,其不能盡如人意,自是當然。所以我們不提清潔運動而已,一提起清潔運動,便需積極的從根本問題著手,然后乃能改良整個電影事業的機構,然后才能談得到清潔”。
他們認為,為電影贖罪的第一步,就是必須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清潔運動”,否則,中國的“電影事業”無法贖回清潔之身,中國“電影事業的機構”,亦無法擔當起抗日救國乃至復興民族文化的歷史重任。然而,為電影贖罪若不深刻地延伸到對電影知識分子自身“原罪”的反省這一層面,這“清潔運動”恐怕是開展不起來的,中國電影事業的前途亦是令人擔憂的。
電影的原罪與電影界知識分子的“原罪”,從一開始就是緊緊捆綁在一起的。如前所述,電影知識分子認為,電影不光是“西洋文化”,特別是“資本文明”的產物,而且也是西方“殖民化”的產物。在半殖民地的租界上,既生長了中國電影,也生長了中國的電影知識分子。由于中國電影從一開始就與中國傳統文化沒有“親緣”關系,因此,很長一個時期中,都無法在中國傳統文化譜系上找到它的合適位置。電影“民族化”或者“民族本位”的身份焦慮,其實深刻反映出的,不僅是“中國電影”試圖在民族文化譜系上急切尋找合適位置的精神焦慮,而且更反映出電影知識分子同樣急切地尋找自身合適位置的精神焦慮。在整個抗戰文化運動向“民族化”和“大眾化”推進的過程中,電影界知識分子與戲劇界、小說界、詩歌界知識分子的“原罪”意識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其奧秘就在于他們的“出身”,或者說“出處”,自來是有問題的。因為,站在“出身論”或者“發生學”的視角來嚴厲地審查他們,他們“屁股上”與生俱來的“殖民化”或者“半殖民化”的紋章,是如此的醒目。還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上,他們投身于“自我改造”和“被大眾所化”的內心苦衷,以及所面臨的現實處境,也就明顯的要比戲劇界、小說界和詩歌界知識分子要深重和困難得多。
電影知識分子當然渴望自己“被大眾所化”,并且能“融合在大眾中間,成為大眾的一員”,也當然渴望能驕傲地和大眾融合在一起,共稱為“我們”。但是,就如同王小波調侃的那樣,驢子在草原上見到了馬群,自以為找到了“同宗”,而急切地飛奔過去,而馬群卻發現身邊來了個“怪物”,反而急切地逃離,故而形成了“炸群”的文化奇觀。電影在農村大眾——我們必須承認,抗戰文化運動發展到“電影下鄉、電影入伍”階段所說的“大眾”和“大眾化”,其實主要說的是“農村大眾”和“農村大眾化”——那里所產生的戲劇性效果,即“炸群”的奇觀。就實際情況而言,所反映出的卻是電影知識分子渴望融入“我們”,而普遍遭遇到的困難和尷尬。葛一虹所親歷的一個細節就非常有意思的反映了這一點。他說:“我看過一場抗戰電影,其中的一節是描寫的英勇作戰的游擊隊。它是以這樣的畫面開始的:在森林中跳出一個神采奕奕的游擊英雄,穿的是馬褲和翻領襯衫。一槍打去,一個美麗的臉蛋從一頂大草帽下翻露出來了……這樣便展開了全部游擊隊的故事。那時候,我雖然還未去過戰場,也未見過真正打游擊的英雄。但是我感到老大的不舒服。我想,看過這個電影的人們,一定會有著我同樣的感受。影片所描寫的并不是我們在深山密林中艱苦游擊著的匹夫匹婦,而是好萊塢制出來的武俠片中的英雄和美人。”【9】的確是具有戲劇性。中國電影的知識分子本意是好的,但滑稽的是,這種以好萊塢西部片的殖民化敘事模式塑造出來的“游擊英雄”,在農村大眾那里,怎么能產生“同宗同族”的接受心理?美國西部片中的武俠人物,怎么可能與農村大眾所認識和理解的本土抗日英雄劃上等號?由于“自我改造”不得要領,因而“被大眾所化”的渴望就必然成為這樣的笑料。這種悲喜劇情景,不光使廣大的農民大眾不得要領,甚至連電影知識分子,即我們習稱的“電影藝術宣傳家”自己也感到無地自容。劉念渠的另一段描述,毋寧說是在自我解嘲,或者說是自我挖苦。他如是寫道:“最容易的事情是找一個現成的故事,分幕、分鏡頭、開拍。但老是《三笑》或者《玉蜻蜓》之類,那就比較麻煩。不妨編一個新故事,有男有女,有戀愛有抗爭,有歌唱有戰爭,然后分幕、分鏡頭、開拍。連這個還不行,要創作典型,那真就使人感到困難了。這一件工作,從劇作者起,導演以及演員(明星們哪)都要知道得更多一點:攝影場上的藝術知識和電影藝術修養以外,還必須加上對現實的正確認識、理解與把握。”【10】
五、中國電影的“原罪”與美國電影的“罪孽”
對蘇聯影片的極致贊賞,特別是對能生產這種“人類杰作”的蘇維埃國家體制的極致贊賞,在整個抗戰期間,一直是左翼力量“設置議題”、“生產意見”的重要“功課”。與此形成鮮明反照的,是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商業電影”的批判。這也一直是左翼力量“議程設置”中樂此不疲的論題。在整個抗戰期間,中國電影知識分子從蘇聯電影和蘇維埃國家體制中,獲得了創造“抗戰電影”和未來自由民主“新中國”的巨大啟示和靈感。這多少意味著,曾經出盡風頭的美國電影和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在中國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精神境域中的敗落。
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電影在討論電影的“民族形式”,討論“大眾化”和“通俗化”問題,在反明星、反技巧,以及怎樣才能體現電影的“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甚至在探索怎樣才能使抗戰電影真正沿著正確的工具理性道路前行等等問題時,無不將蘇聯電影作為正面典型,進行極致的稱頌和膜拜,而同時將美國電影作為反面典型,進行尖銳的鞭撻和批判。這種愛憎分明的立場和涇渭立判的價值取向,雖然在戰前已經形成了某種政治文化態勢,特別是在左翼電影運動中,這種價值判斷早已成了一種思維定勢,但就其發展勢頭而言,在抗戰期間卻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中國電影知識分子在檢討中國電影和他們自身“原罪”時,對美國電影長期以來“麻醉”和“奴化”中國電影和電影知識分子“罪孽”,在進行控訴和批判時,更是不遺余力。關于這一點,我們在潘孑農的《釋“美國作風”》和《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致蘇聯電影界書》等大量的文獻資料中,已經有了充分的領略。盡管美國和蘇聯一樣,被我們視為“幫助中國抗戰的民主國家”,特別是因其與中國的“戰略同盟”關系,而受到中國朝野的認可與尊重,但具體到美國電影和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問題上,中國知識分子的立場和態度就發生了“不可思議”的轉變——這與他們對蘇聯電影和蘇聯國家意識形態的極至稱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難道在這場反法西斯戰爭中,美國不也同樣代表“人類正義”和“文明科學”的方向嗎?可是,具體到美國電影及美國國家意識形態方面,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卻并不這樣認為。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電影知識分子在尋求“中國電影的出路”時,就是以毫不猶豫地批判“美國作風”和堅定不移的選擇“蘇聯道路”為立論的前提的。實事上,這種態勢正深刻地反映了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在尋求民族國家現代轉型道路時,在思想文化意識上所發生的戲劇性變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變化并不是出于政治家或軍事家那樣的策略性考慮,而根本原因卻是來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義利之辨”,特別是對“仁愛”和“大同”理想的執著追尋,終于在體制化的蘇聯和蘇聯電影中找到了“文化同構”的重要啟示和“準確答案”。
“在社會主義國家,電影藝術是件莊嚴的工作”,而在美國則“把電影作為純粹的娛樂品”;【5】“電影在蘇聯是更迭人類的世界觀的武器和文化革命的兵種。”【11】可是在美國,電影則“被利用為宣傳工具,是利用來麻痹大眾的意識的”【12】。這種深刻浸入中國電影知識分子靈魂的文化意識和價值定論,并非出于簡單的民族主義好惡,以及政治審美偏至,而是來自中國文化人在為整個國家民族尋求現代化出路時,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價值判識和文化確認。
愛森斯坦說,蘇聯電影的藝術功用在于鼓舞蘇聯人民和整個人類“去建設新社會”,蘇聯電影所“提供的電影的真實”,正是“蘇維埃國家”“現實的真實”反映。相反,美國電影的政治目的卻是在“麻痹人民”,逃避對“現實”的“干預”,特別是在抗拒革命、瓦解人民“建設新社會”的意志上面。蘇聯電影所體現的“電影辯證法”和“新的美學原則”,極大地有助于人民去積極參與電影的政治審美過程,而美國電影卻頑固地排拒革命,宣揚“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愛森斯坦所說的那種“電影辯證法”和“新的美學原則”在這種腐朽和墮落的境地中是無法生長起來的。【13】(542)這樣的價值判斷,對中國電影知識分子來說,可謂影響深遠。
[1]田間.抗戰詩抄[Z].新文藝出版社,1955.
[2]嚴辰.關于詩歌大眾化[N].解放日報,1942-02-11.
[3]電音.電影是什么東西[N].新蜀報,1944-02-03.
[4]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戰協會致蘇聯電影界書[J].中國電影,第1卷第1期,1941.
[5]唐煌.電影國營論[N].國民公報,1939-02-12.
[6]中國電影的路線問題——座談會記錄[J].中國電影,第1卷第1期,1941.
[7]田漢.怎樣從蘇聯戲劇電影取得改造我們藝術文化的借鑒[J].中蘇文化,第7卷第4期,1940.
[8]蘇怡.電影清潔運動之我見[N].國民公報,1940-05-19.
[9]葛一虹.關于民族形式[N].文學月報,第2期第1卷,1940.
[10]劉念渠.在銀幕上創造典型[J].中國電影,第1卷第1期,1941.
[11]羅亭.蘇聯電影觀覽席[N].國民公報,1938-03-20.
[12]宋之的.略論電影通俗化問題[N].掃蕩報,1939-04-10.
[13]西頓.愛森斯坦評傳[Z].中國電影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