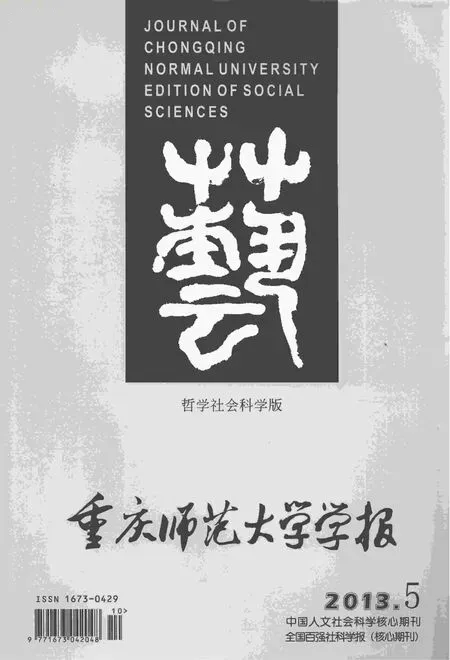蜀地民眾國家認同研究
——從古蜀國到秦代
王 瑰
(四川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成都 610064)
一、問題的提出:國家認同與古代時期蜀地民眾國家認同的特殊性
當代民族國家的概念是基于西方歷史演進的結果產生的,西方理論界一般也不認可近現代民族國家之前的古代時期存在國家的說法,但這并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1]中國古代也不只是一個“文明共同體”,而是一個觀念天下與實體國家同一的“天下國”[2],這也已漸成共識。因此,國家認同雖然是一個當代政治學術語卻并不意味著它不可以適用于古代史的研究。在古代中國,盡管這個國家在疆域上并非界限清晰,但其文化覆蓋核心區卻是穩定擴展的,那么在這個穩定擴展的文化核心區內的民眾與政權之間必然存在著認同的問題,因為中國古代國家共同體的持久運轉是無法否定的歷史事實。套用楊士彬先生“沒有‘國家’這個術語,并不等于沒有‘國家’觀念”[3]的說法,中國古代“沒有國家認同這個術語,并不等于沒有國家認同現象的存在”。對此,彭豐文女士的《兩晉時期國家認同研究》作了很好的嘗試,也證明“中國古人所特有的國家認同心理被完全忽略掉了”[4](358)是多么不應該。
當然我們在探尋古代中國國家認同同一性的同時,也不該忽視各地區民眾國家認同的非同步性和差異性,這對揭示整體同一性的形成機制和形成原因也是有著莫大作用的。
在地區國家認同研究中,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蜀地又有著獨特的研究價值。本文蜀地大體指秦朝蜀郡,或漢代蜀郡、廣漢郡、犍為郡及以后由其中分置出去的郡。蜀地既曾有過自己獨立的文明生成和演化歷史,以及本身由此產生的歷史文化積淀。當她融入華夏文明后,又是以華夏文明的邊疆重鎮地位存在于世的。再加上獨特的地理結構,每逢亂世總有獨立割據政權存在,明清之際即有所謂“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歐陽直公《蜀警錄》)的諺語流傳,可見該地區的國家認同應當是很有其特殊性的。
至于國家認同的定義,國內外從不同學術領域和觀察立場出發有很多種,但卻幾乎都是針對當代國家狀況所下。對中國古代時期的國家認同,彭豐文定義為“人們對國家政權的態度與情感,指對國家政權的認可、選擇和自愿將自己同化于國家這個集體中的心理活動”[4](44)。這個定義既緊扣了中國古代的特殊性,如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互動,也體現了認同問題的心理本質屬性,是頗可采用的。
本文擬探討古蜀時期,即秦并蜀之前,以及入秦后以至秦朝滅亡時期蜀地民眾對國家的認同狀況,因此此處的認同對象有兩個,一個是古蜀政權,一個是秦政權,包括戰國秦和統一秦朝。對于前者,尚未有所明確的論述,后者則主要是從文化融合的角度探討了蜀地對秦文化的認同過程,也未明確地以國家認同為研究客體。
二、古蜀國家與古蜀民眾
(一)古蜀國家的界定與古蜀國家的序列
古蜀國家,一般以秦并蜀為界,入秦之前的蜀地政權是為古蜀國。從《華陽國志》的記載來看,古蜀國家的序列是由五個朝代構成的,依次是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常璩謂蠶叢“始稱王”[5](卷3,118頁)。任乃強先生考證指出,蠶叢時期尚未脫離原始社會,蠶叢氏也還活動于今茂縣疊溪,尚未進入成都平原,“所謂‘王’,乃后人加于其氏族首領之稱,正如稱伏羲氏、神農氏曰‘帝’,非即已有國家制度之王號。”[5](卷3,219頁)成都平原最早出現的能稱得上國家的文明體,現代考古學表明是在三星堆文化的鼎盛時期,即距今3600~3200年左右的三星堆文化第三期出現的。[6](190-191)學術界一般認為此時古蜀的早期國家算是誕生了,盡管這個國家還有著相當的神權色彩和血緣組織形式。[7]通過該時期三星堆所展示的文物和古蜀歷史文獻的擬合,這個時期一般被認定為魚鳧氏的鼎盛時期。
同樣借助著成都平原地區不斷涌現的考古發現,魚鳧氏之后,成都十二橋文化、羊子山遺址見證了杜宇王朝的興盛,船棺葬、新都大墓等晚期巴蜀文化則留下了開明王朝的遺跡。[6](223)因此,在此基礎上,我們再以文獻所載魚鳧、杜宇、開明事跡來探尋古蜀民眾的國家認同就有比較穩固的歷史根基了。當然在此之前,我們還有必要了解一下古蜀民眾的心態,畢竟認同是一種心理活動。
(二)考古發現所反映的古蜀民眾的開放心態
段渝先生指出四川盆地在地理上具有山川與河流雙重向心結構的特性,而這個心就是成都平原,這種結構具有吸納周邊文化于盆地之心融合的先天優勢,成都平原因之具有形成古文化中心的優越自然基礎。[8]川北廣元中子鋪遺址、川東三峽大溪遺址,其早期文化都在6000年以上,考古發現它們對四川盆地內新石器文化的最初產生可能是有影響的。[6](90)至于盆地西部青藏高原東緣的若干考古發現,也表明“西藏和四川自遠古時代開始,便可能有著不同程度的文化聯系”[9],也是四川盆地向心結構優勢的反映。
對此,即便僅從三星堆考古發現來看,也是有著很好證明的。通過對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銅人像人體裝飾、面部特征,并結合人種學的研究已經揭示出,至少該時期的蜀人從族系上看是由西北氐羌人與東南濮越人構成的。[10]人種尚且如此,文化可想而知了。實際上,三星堆文化不僅存在著本地文化的整合,甚至中原商文化、長江中游荊楚文化也為所吸收,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對此已有明證。甚至在精神世界里,三星堆文物也反映出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巫祭崇拜共存的信仰結構。[6](241)
因此,雖然文物是靜態的,但也讓我們看到當時的蜀人確實已經具有一種開放的心態。他們不僅不介意吸收其他地區的物質文明,甚至也不排斥與異族人共同生活。而這種心態在對統治自己的國家的認同上也是必定有著影響的。
(三)開放坦然的最優選擇:古蜀民眾的國家認同
魚鳧、杜宇、開明不僅是三個朝代的創業之主,也是他們建立的朝代的稱號。
對于魚鳧氏國家,文獻失載,更可能是蜀人對它的集體失憶。常璩撰述《華陽國志》時,僅知道他在柏灌之后,生前的事跡也已失傳了,只是留下了去世時的神話圖景“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于湔”〔5〕(卷3,118頁)。成仙升天是假,但在這個神化圖景的背后,卻透露了他治下的民眾對其統治的認同,所以才會把他的死亡美化為仙化升天。而三星堆遺址的規模和出土文物的龐大精美,也足以說明這個國家得到了相當人眾的認同與服務。有學者估計,三星堆古城作為魚鳧王國的中心城市,其人口在24000人以上[10],在當時生產力水平和成都平原尚未有都江堰調節水流之前,即能聚集如此之多的人口于統治中心,可見魚鳧氏國家的民眾聚合力是很高的。
至于魚鳧氏所以能擁有如此認同基礎的原因,通過對考古文物發現的解讀也能告訴我們一二,至少神權作為一種凝合因素必然是發揮了巨大作用的。趙殿增先生研究揭示出三星堆祭祀坑文物“表現了以宗教祭祀為最高形式的‘三星堆古國’意識形態的古樸面貌”〔11〕。
不過,當杜宇氏取代魚鳧氏的時候,似乎世俗的因素在古蜀民眾對國家認同的影響中便漸漸增大了。
關于杜宇,《華陽國志》載:“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悅之,納以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為后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5〕(卷3,118頁)杜宇氏如何取代魚鳧氏,所有記載了杜宇的文獻上都沒有言及。但是,通過對代表杜宇氏文化的成都十二橋考古文化與代表魚鳧氏鼎盛期的三星堆三期文化的比對研究,發現“兩者不是簡單的并列,更不是兩個共存的中心,它們有一個相互交錯的時期(商代晚期),又有前后銜接關系。”[6](220)因此,杜宇氏應是在魚鳧氏勢力籠罩下逐漸發展壯大后才取代魚鳧氏而讓三星堆文化終結的。
不過也需要說明的是,杜宇氏取代魚鳧氏并不是異族之間的政權交替,而是蜀族內不同部落在相互競爭中對統治權的獲得。
杜宇氏為什么能取得成功呢?雖然有與其他部落結盟的原因,但根本的還在于他的“教民務農”。杜宇氏以成都平原地區農業的開創者身份獲得了本土蜀民的認同,實現民眾聚合,從而最終取代魚鳧氏。其作為四川農神影響之大,非但在常璩之時“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就是在解放前四川各縣城還都有祭祀他的祠廟。〔5〕(卷3,119頁注5)
農業生產在成都平原的出現,對整個古巴蜀地區歷史發展有著莫大影響,從此成都平原的巨大生產力才真正得到開發和發揮。因為有了農業,成都平原才會聚集人口并使之長期定居,也因為有了農業,才有了日后“決玉壘山”、“建都江堰”的客觀需要,也才最終有了日后獨占“天府”名號的富庶成都。《蜀王本紀》載蠶叢氏退出成都平原時有“蜀民稀少”的現象。〔12〕緊承其后,就講杜宇事跡了,可見杜宇時代的蜀民是大大超過魚鳧時期的(上文已提及魚鳧時期三星堆古城即有不下24000人口),可見杜宇時期成都平原人口之盛。
杜宇也看到了農業在成都平原上發展起來后,國家空前的興旺,所以他才會滿懷成就感,“自以功德高諸王”〔5〕(卷3,118頁)。也正因此,杜宇氏獲得了成都平原古蜀民眾的廣泛認同,隨魚鳧氏退出成都平原的“化民”也受定居農耕生活的感召而“往往復出”〔12〕。農業傳播的成功使杜宇氏還獲得了開疆至“以褒斜為前門,熊耳為后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5〕(卷3,118頁)的龐大而持久的人力支持。
我們再看取杜宇氏而代之的開明氏。
關于開明氏取代杜宇氏,《華陽國志》云開明末期時“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5〕(卷3,118頁)。至于開明氏之族源及如何成為杜宇之相,都未有言及。為什么呢?因為常璩著書有“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于篇”的材料取舍原則〔5〕(卷3,723頁),他自覺太為荒誕的東西,是不予采入的。不過,《太平御覽》所引《蜀王本紀》中卻保留下了比較完整的開明事跡,其云:“望帝積百有余歲,荊有一人名鱉靈(鱉或作鄨),其尸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尸隨江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靈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決玉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出后,望帝與其妻通,慚愧。自以德薄不如鱉靈鱉邑之長官,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帝,帝生盧保,亦號開明。”〔12〕在不少其他文獻中也多有相似的記載,只是鱉靈所決多有記載為“巫山”“巫峽”者。鱉靈即鱉令,地在今貴州遵義。被常璩舍棄的最大的荒誕處,就是鱉靈尸體浮江而上至郫而活的故事。不過這個故事雖然不足取信,但若是剝去古蜀人循著英雄圣王的固定模式去回憶建構自己歷史時的“歷史心性”來看[13],這個荒誕故事背后的歷史真實或許正如任乃強先生所說,“鱉令犯罪當死,乃偽稱投水而潛走投蜀。故楚人求其尸不得,而謂在蜀復生。”[5](卷3,122頁注14)
因此從開明的族源來看,他或許是楚人,但這也無定論,楚人、巴人、濮僚人都各有持議者,但肯定不是氐羌系蜀人,而是來自四川盆地東南外的異族。盡管從三星堆文物反映出蜀人族系的復雜,但異族作為蜀地的統治者,到開明氏時至少是蜀民數百年沒有經歷過,且更是蜀地自魚鳧時期王權國家建立以來第一次面對的異族作主的問題。那么開明氏又是怎樣獲取蜀地民眾的認同的呢?
文獻的指向是“治水”。“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決玉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出后,望帝與其妻通,慚愧。自以德薄不如鱉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舜。”〔12〕由于杜宇氏晚期,成都平原突生嚴重水患,以至于民眾無法“陸處”。杜宇氏面對如此局面,一時無法解決。如果我們承認農業生產對杜宇氏國家的重要意義,那么我們就能了然水患問題的無法解決,會給杜宇氏國家帶來多大的認同危機。
正是在這個時候,異族人開明卻承擔起了治水的任務,且是以“相”的職權主持治水。雖然當時杜宇氏王朝未必會有“相”這個官職,但常璩用這個詞至少表明在他掌握的資料中,開明在杜宇氏國家中的級別是有如中原之“相”的。這也間接表明了治水事業成敗真是關乎杜宇氏國家存亡的大事。
開明受命后,采取了決山泄水的方法。他所決之山,具體為何山,處地何處,迄今仍是爭而無定的問題。不過,相較而言,李紹明先生主張的鱉靈決玉壘山之后,再疏通金堂峽的看法,既有史料依據又符合實際地理形勢,還有民間傳說佐證,是頗有道理的。當然,無論是否,鱉靈之治水工程在當時條件下都是相當艱巨的。鱉靈治水的足跡似乎還不止在成都平原及其周邊,甚至還達到了嘉陵江流域,《太平寰宇記》卷86和《輿地廣記》卷185的“閬中”條目下都記載了閬中城東十里靈山有鱉靈廟。
開明治水的成功,顯然大大提高了成都平原的生產能力。《華陽國志》記載,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秦遣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舶舡萬艘,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周赧王三十年至三十二年,蜀守張若又“因取筰及楚江南地”。[5](卷3,128頁)這兩次戰役都大舉征發了蜀地是必然的,而這時使得成都平原成為“陸海”的都江堰工程尚未動工,可見經過開明治水后,成都平原的生產能力(包括人口的生產)必定是極大提高了的。
開明氏的統治持續了十二代,其間,向北一度“攻秦,至雍”(卷3,128頁)[5],其勢力不僅占有漢中平原,還越過秦嶺進入渭水流域;向南一度“攻青衣,雄張僚、僰”(卷3,128頁)[5],勢力進入南中地區,向東甚至還“伐楚,取楚茲方。於是楚為捍關以距之”(《史記·楚世家》)。開明氏的強大又遠在杜宇氏之上了。
開明氏國家的超邁前代,顯然在于他獲得了蜀地民眾比杜宇氏更為廣泛深刻的國家認同,得到了蜀民的擁護和支持。而這種認同的取得則首在于鱉靈治水成功對蜀民生產、生活的極大改善,使他們持久感念,以至于在他的后人身上寄予期望。
通過考察杜宇氏、開明氏國家建立的事跡,我們發現古蜀民眾在國家認同上都保持了一個特點,即以世俗生活的良性改變為基礎,他們對這種滿意世俗生活的預期則決定了他們對一個政權認同的持久程度。不過,這是基礎,不是全部。
當杜宇氏取代魚鳧氏后,雖然古蜀民眾也感念魚鳧氏,但當面對杜宇氏開創的農業定居生活的美好圖景時,他們又往往選擇從山林中復出。當開明氏成功解除水患后,盡管杜宇氏統治已百余年,古蜀民眾還是選擇在開明氏治下生活,盡管另一方面他們又對杜宇氏十分感念,既立廟祭祀,又神化之以杜鵑鳥,還“聞子鵑之鳴,即曰望帝”(卷3,118頁)[5]。透過這些現象,我們看到古蜀民眾在國家認同上是開放坦然的,誰能提供更好的生存預期,就選擇誰,但并不否定未被選擇者,而且還長久感念于心。
古蜀民眾這種國家認同的特點,在開明氏國家遭遇異族秦人滅亡進入秦國家的統治之后,是否會改變呢?
三、開明氏蜀國的衰亡與秦滅蜀后蜀地民眾國家認同的復雜化
盛極而衰是事物發展的規律,開明氏雖然把獨立的古蜀國帶入了發展巔峰,自身的衰弱也隨之而來。
(一)開明氏國家的衰亡與認同危機
在開明九世在位期間,蜀仿中原立制,建立帶有自身特色的禮樂宗廟制度,并自郫邑遷都成都,甚至還可能建立了以“五丁”為單位的基層行政組織[14]。作為異族統治者,能進行如此深入的改制,透露出的顯然是強烈的統治自信,而這份自信顯然基于蜀地民眾國家認同的深厚程度。這個時期可能就是開明氏蜀國的鼎盛時期。但在此之后,開明氏蜀國的國家認同就開始降低了。其降低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是戰爭的持續。以一小小成都平原為經濟支柱的開明王朝,四面環山,千里不盡,在重山之間擴張勢力乃至越山水千百重與秦楚爭鋒,本身就是對民力和國力的極大消耗,理智的統治者必定會適可而止,但《華陽國志·巴志》記載蜀國后期的形勢是“巴蜀世戰爭”[5](卷1,11頁),代代蜀王都與巴國進行戰爭。結果,當秦軍開始滅蜀行動后,盡管蜀王頗有氣勢地親自北上葭萌拒敵,還是一戰敗績。而秦軍就憑此戰之勝,追亡逐北,蜀王“遯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鄉,死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5](卷3,126頁)蜀軍戰斗力之低下,蜀地民眾作壁上觀的冷漠,可想而知了。
其二是以蜀王為首的統治者的荒淫。蜀人對統治者荒淫的揭露是以編排蜀王的荒誕故事為方式的,《華陽國志·蜀志》記錄下了這些故事。如蜀王貪秦惠王便金石牛,而開通石牛道,卻為秦軍入蜀開辟了進軍道路的故事,足見對蜀王貪財的辛辣諷刺。武都男子化為美女,蜀王納以為妃,美女不習水土要離開,蜀王又作歌取悅,結果還是死了,最后蜀王又為之大興土木作墓冢而成今成都北郊武擔山的傳說;以及秦恵王知蜀王好色嫁五女于蜀王,結果半路山崩覆沒而死,成五婦冢山,蜀王因而作思妻臺的傳說等,都可見蜀王好色荒淫。
其三是王族內部的分裂。蜀王還不能協調王族內部的關系。蜀王封其弟葭萌為苴侯,葭萌卻投靠世仇巴國,惹得蜀王興師討伐。可見,開明氏王族內部并不團結。
總之,開明氏蜀國末期,由于民力疲耗、統治荒淫、王族不和等因素,蜀國民眾的國家認同程度大為降低,可謂戰士無斗志、民眾如散沙、王族懷異心,衰亡的征兆已經顯現。
(二)秦滅蜀及蜀地民眾國家認同的復雜化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出于滅楚與并天下之戰略考慮,秦遣張儀、司馬錯等趁蜀亂之際伐蜀,開明氏蜀國在其第十二世時滅亡。蜀地民眾的國家認同驟然復雜。這種復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對開明氏亡國與秦入主蜀地的態度。雖然,在開明氏蜀國晚期,蜀地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度已經大大降低,在開明氏與秦的戰爭中,士兵沒有足夠斗志,民眾也沒有參與救亡。但是,這并不表明蜀地民眾對開明氏已毫無認同。開明氏之驟滅,應該說是在蜀地民眾意料之外,畢竟長期以來蜀都至少是稱雄一方的“戎狄之長”,且在以往與秦楚的交戰紀錄中,并不落于下風,因此當蜀地民眾認識到亡國是真實事件之后,必定會對開明氏的滅亡重新考量。正因如此,秦滅蜀后,不僅沒有立即消滅蜀王族,而且還在蜀民多次擁護開明氏舊貴族反秦的情況下,仍然三次立蜀王之子為蜀侯[15],這樣做無非是盡可能地穩定蜀地民心和局勢。此外,就心理上看,在上文所引關于蜀王貪財好色諸故事中,我們一方面看到蜀民眾對蜀王的不滿和嘲諷,但另一方面也可見對秦為滅蜀處心積慮預先謀劃之卑劣手段的不滿,其實質就是蜀民心中秦滅蜀成功頗屬僥幸的看法。
對于秦成為蜀地新的統治者,雖然蜀地民眾向來有著對異族人的開放心態,但由于秦對蜀地統治權的取得既非光明正大,又非救人水火,要獲得他們的認同是很難的。秦直到公元前280年,滅蜀30余年后才在蜀地“但置蜀守”,蜀才完全納入秦的政治系統,便是這份艱難的見證。不過,當又面臨秦的強大武力,使得反秦活動風險極大時,蜀民對秦的國家認同就不得不強行生長出來,對秦的國家義務也不得不在糾結中有所表示。
第二,秦移民大批涌入的影響。秦對蜀移民,基本伴隨秦國和秦朝的始終,既有政治目的鮮明像“以戎伯尚強,移秦民萬家實之”[5](卷3,128頁)的大規模移民,也有制度性的“秦之遷民皆居蜀”,(《史記·項羽本紀》)或“秦恵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俠于蜀”[5](卷3,148頁)的小規模移民。雖然本土蜀民的構成從來不單一,但他們在古蜀國的融合卻主要是以長期共同生活的方式和平漸進地實現的,而秦移民的進入卻是突發性的強勢行為。這種突發性的強勢行為,一方面確實為本土蜀民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組織方式等一系列中原先進物質文明,足以改善本土蜀民的生產生活,另一方面卻也急速擠占了他們的生存空間,這就使本已陷入新舊國家認同兩難的本土蜀民又不得不面臨異族認同的問題。
第三,秦移民入蜀后蜀人組成結構的改變。秦移民有三種,一種是被迫背井離鄉的一般秦民,如初入蜀地的萬家秦人,一種是國破之后被秦強制移入蜀地的關東六國人士,如趙國卓氏,一種是秦之罪人,如受呂不韋案牽連的人等。不管哪種,都是被逼背井離鄉的,多懷故土之思,因此這些移民對秦的國家認同必定不會高,而且他們來到蜀地后還必須先解決對蜀的地域認同問題,才談得上去“資我豐土”發展生產。因此,當本土蜀民加入秦移民后,兩者的相互認同問題、地域認同問題一時都摻雜進來,秦國家認同的形勢更為嚴峻。
四、“新蜀民”對秦的國家認同
秦是出于整體戰略考慮滅蜀的,所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5](卷3,126頁)。這就決定了在對蜀的態度上是盡可能利用。在這種形勢下,新蜀地民眾對秦的國家認同又是什么模樣呢?
(一)以被迫為特征的蜀入秦前期蜀地民眾的國家認同
但是當秦軍攻下蜀國后,卻發現蜀民并不那么容易利用。其一,是“戎伯尚強”的緣故,既有開明氏殘余勢力的強大,也有蜀周邊原臣服于蜀的部族,如秦武王元年所伐之丹、犂(《史記·秦本紀》),仍保有較大勢力。其二,本土蜀民新亡舊國,人心尚未附集。
面對這樣的局面,為了盡快穩定蜀地局面,秦采取了比較務實同時也很強硬的方式。在巴蜀全部平定后,首先立蜀王子通國(秦本紀為通)為蜀侯,并先后分巴蜀地為巴、蜀、漢中三郡,各以郡守治事,既維持開明氏對蜀民的名義統治,收平撫本土蜀民心理創傷的效果,又架空蜀侯權力,實現秦的統治實效。然后又移萬家秦民于蜀,這既能充實蜀地的生產力量,彌補部分隨開明氏逃亡而減少的戶口,又能起到分割蜀民降低蜀民聚集造反的效果,更能增強蜀地防衛力量,從而盡可能地穩固蜀地統治秩序。還很有可能,為了保持蜀地生產不致于因政權更替而荒廢,秦還在本土蜀民逃亡的交通要道或監視成都平原的戰略要地駐兵建城,以造成對成都平原的關門之勢。今雅安滎經(秦漢時嚴道)和成都龍泉驛發現的秦人墓葬或許正是秦當年強硬對待蜀民的見證。而在本無城墻的自由市場成都[16],仿咸陽制一口氣建成成都、郫邑、臨邛三城,則更使秦的強硬姿態畢露無遺。
雖然,秦的強硬在滅蜀之初,確實較好地起到了維持蜀地統治秩序的作用,但也在暗中積蓄了蜀地各勢力集團反抗的力量。秦惠文滅蜀后,關東合縱抗秦,秦國東方形勢較為緊張,一時無暇西顧。秦惠文王后元14年(公元前311年),蜀侯趁機與丹、犂聯合反秦,蜀侯之相陳壯殺蜀侯,平息叛亂。而后秦惠文王死,陳壯卻與丹、犂聯合反秦,欲自主蜀地。[5](卷3,120頁注4)秦武王元年(公元前 310 年),秦以甘茂等再入蜀平亂,并伐丹、犂。亂平又以蜀王子惲(《秦本紀》作煇)為蜀侯,重新恢復蜀地秩序。之后,秦可能憑借平亂之勢,向蜀地大力推行秦國制度,進行強制性政治整合。據1980年青川郝家坪戰國秦墓出土的“更修為田律”木牘所記載,可能在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秦已經在蜀地強勢推行丞相甘茂更改制定的一系列田地整理和田地生產系統設施,如除草、道路、水利等的管理律法,開始從統治終端把新蜀民納入到秦的治理系統之中了。而之后,虛設的蜀侯雖還繼續保留了數十年,但政治經濟上大約已與秦的其他地區一體對待了,如昭襄王四年為田開阡陌令,秦始皇使黔首自實田令等。[17]
通過為田律的推行,蜀地的生產可能又提高了一步。《華陽國志》記載在此次平蜀后二年,“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舶舡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卷3,128頁)[5]。夸大至此,至少表明當時蜀地生產確有提高。
不過,秦的強制整合似乎并沒有換來蜀地民眾的積極認同。《秦本紀》載昭襄王6年(公元前301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史記。秦本紀》),蜀民對秦的強制整合似乎仍然是不滿的。又載昭襄王27年(公元前280年)“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同上),從蜀攻與巴蜀相鄰的黔中,不發巴蜀士卒,而發千里之外的隴西士卒;昭襄王30年,蜀守張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同上),也未見調動巴蜀士卒的記載。可見,秦滅蜀36年后,蜀民對秦的國家認同還沒有建立起來,他們最多被迫屈服于秦的強大武力,為秦國家交糧納賦,若要武裝起來為秦服兵役,秦自己都沒那份信心。看來秦國家還要繼續對復雜化了的蜀民進行整合。
(二)以消極為特征的入秦中后期蜀地民眾的國家認同
從考古上看,在入秦之后,蜀文化與秦文化的融合是有鮮明階段性的。在秦統一前,蜀文化保持繼續發展態勢,統一后中原文化特征加強,蜀文化特征削弱。[6](430)促使這種變化出現的,應當是蜀守李冰治水的結果。
李冰約在公元前250年被秦孝文王任為蜀郡守,他任內最大的功績就是治水。其治水具體情況,《史記·河渠書》有60余字簡單介紹,常璩《華陽國志》則頗為詳細。結合兩書來看,李冰治水功績主要有三:一是鑿離堆建都江堰,在岷江入平原處建立科學的自流分水調節系統,確保成都平原水旱無災;二是引岷江水入成都,所謂“穿二江成都之中”,遂使成都成為成都平原上的航運中心,坐致竹木銅鐵資源;三是建成覆蓋成都平原的密如蛛網的自流灌溉系統,成都平原遂成“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的一方寶地。在治水之外,李冰還“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解決了蜀民本地食鹽的問題,“蜀于是盛有養生之饒焉”。[5](卷3,133-134頁)
李冰治水最直接解決的問題就是本土蜀民與秦移民爭奪生存空間的問題,成都平原盡成沃土,從此本土蜀民與秦民和平共處,相互之間的融合和認同加深,逐漸達成地域認同的一致。此外,當本土蜀民想到開明氏蜀國的建立也是仰賴于治水時,對李冰的認同愛戴之情自然會讓他們降低對秦的不認同。可以說,李冰治水正是蜀民對秦國家認同轉變的關鍵。
但是實際上李冰治水的功績在轉化為蜀民對秦國家認同上,達到了足夠效果嗎?答案是否定的。這,只須看看劉邦王巴蜀漢中后,蜀地毫無反應不說,還照樣向劉邦上交租賦并為之服勞役,甚至當劉邦征戰關中與關東時,他們仍然默默盡著國民的義務,以至于劉邦都大為感動,于漢二年(公元前205年)下書“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漢書·高帝紀上》)。為什么會這樣呢?
首先,我們清楚當秦孝文王任命李冰為蜀郡守時,東方六國在秦的持續打擊下,已經全部喪失了抵抗能力,秦國一統天下的最后之戰已經提上議事日程,李冰為蜀郡守正是秦國為最后統一積蓄經濟基礎的戰略棋子。因此,雖然綜合整治和完善成都平原的水利工程,既能解決蜀地社會矛盾的根源,也能夠得到蜀地民眾的認同,但在時效性的追求上,必然也帶來了民力的疲耗。
其次,水利工程完善后,秦國必定要加大經濟剝削和勞役征發,以為統一天下的后勤保障,這必然加重蜀地民眾的負擔。而到了秦統一,蜀民仍然沒有休息,因為秦始皇南平百越、北筑長城、建殿造陵、巡行四方諸事,無不需要征發大量勞役和糧食布帛,天下騷擾并不減于戰國。蜀地民眾即使沒有被大量征調服役,其租賦負擔卻必定是不會稍減的。對此,《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上一則常被忽視的史料很能說明,其云平棘侯林摯“以客從起亢父,斬章邯所置蜀守”。章邯是秦末名將,陳勝起義軍失敗主要是被他鎮壓的結果,巨鹿之戰大敗于項羽,投降,項羽入關中,封雍王。章邯任命蜀郡守,只能是他還在與陳勝或是項羽大軍戰爭的時候,因為被秦二世任命為將時,他居官少府,為皇帝掌管山池陂澤之稅,是沒有任命蜀郡守職權的,而被項羽封王后,他的封地在關中西部,蜀郡是劉邦的封地,他還是沒有任命的可能。也就是說,章邯所任的這個蜀郡守只能是他被秦二世任命為將,以一身肩負起秦之存亡時才可能具有的特權。由章邯任命蜀郡守,可見越是危亡秦對蜀地經濟的依賴越強,蜀地被過度汲取實在是貫穿到秦的滅亡了。
其三,從蜀民構成來看,不管新舊其早先一輩,大多都是被秦傷害過的群體,或者亡國遷徙,或者被迫遷徙,或者就是亡國之余。這種民眾構成,如果沒有在秦的特有文化系統里融合為一體,當面對秦的危亡,而自己生命卻不受危害的情況下,他們或許應該是喜大于憂的。而至秦滅亡時,蜀地民眾的文化融合還沒有完成,他們還沒有在秦王朝治下達成地域認同的一致。
“天下苦秦久矣”的呼聲,是包括僻處西南的蜀地的。因此,如果要總結蜀入秦中后期,包括李冰治水時期至秦朝滅亡,蜀民對秦的國家認同,大約可以用消極來表示。具體說來,他們只是默默無聞地承擔秦國家所加的租稅勞役負擔,對秦國家的興衰存亡漠不關心,甚至支持成功推翻秦統治的勢力。但是他們不會親自起而反對秦國家,因為對秦他們還有著一定感念心理,畢竟是由于秦的關系,他們才得以步入更高的文明階段,尤其秦蜀郡守李冰的功績在客觀上對他們的造福是永遠的。
五、結語
當古蜀還是一個具有獨立文化系統國家的時候,蜀地民眾的國家認同是開放坦然的,其國家認同的基礎更多地是基于世俗生活良性變化的自發生成,而不是種族、文化的一致,這是由蜀地民眾形成和生活的共同地域影響下形成的。入秦之后,在其前期,他們對秦國家的認同是被迫的,因為秦國家的突發強勢介入和強制整合,完全打破了他們既有的認知系統,再加上生存空間的被擠占造成世俗生活的緊張,他們對秦只能是否定于心而勉強配合于身。當秦蜀郡守帶領蜀地民眾治水成功,解決長期積壓的矛盾,本來蜀民眾國家認同轉化的契機已經出現,但由于秦統一戰爭和統一后的無節制征發,卻使得轉化契機一直被浪費。
民眾的早期國家認同,其實不管是蜀地還是中原,其認同根本點都應是世俗生活的良性改觀。這從堯舜禹禪讓以造福于萬民的大德,以及夏啟因其父禹治水功績而成功以家天下取代“公天下”也能看出。
就蜀地說蜀地,當本土蜀民與移民在相互融合中漸漸達成文化認同的一致時,其國家認同的的面貌必定也會出現新的特征。而歷史在不久之后,確實在文化上,讓蜀地民眾進入了華夏民眾的大家庭。
當然,由于史料的匱乏,對漢以前蜀地民眾的國家認同,我們是缺乏民眾個案研究的,這對認同本質的心理屬性來說甚為不該,不過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1]葛兆光.重建“中國”的歷史論述[J].(香港)二十一世紀,2005,(8).
[2]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3]楊士彬.我國古代社會的國家觀念[J].河北學刊,1996,(6).
[4]彭豐文.兩晉時期國家認同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9.
[5]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趙殿增,李明斌.長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7]段渝.從血緣到地緣:古蜀酋邦向國家的演化[J].中華文化論壇,2006,(2).
[8]段渝.論巴蜀地理對文明起源的影響[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
[9]霍巍.西藏考古新收獲與遠古川藏間的文化聯系[A].李紹明,林向,趙殿增.三星堆與巴蜀文化[C].巴蜀書社,1993.
[10]林向.論古蜀文化區——長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A].李紹明,林向,趙殿增.三星堆與巴蜀文化[C].巴蜀書社,1993.
[11]趙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A].李紹明,林向,趙殿增.三星堆與巴蜀文化〔C〕.巴蜀書社,1993.
[12](宋)李昉.太平御覽[M].中華書局,1960.
[13]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J].歷史研究.2001,(5).
[14]羅開玉.蜀王開明九世改革初論[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6).
[15]任乃強.國亡后的蜀民[A].川大史學·任乃強卷[C].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
[16]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說[J].成都文物,1984,(1).
[17]段渝.論秦漢王朝對巴蜀的改造[J].中國史研究,1999,(1).